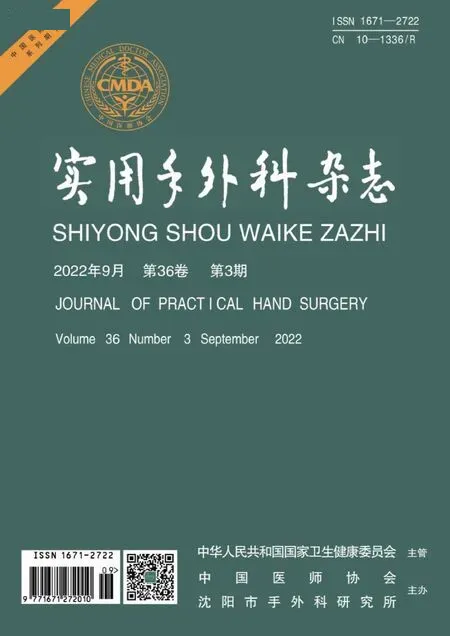感染性休克治療中并發手足缺血性壞死的臨床分析
魏鵬飛,謝振軍,趙國紅,孫華偉,張建華,白輝凱
(1.鄭州聚誠醫院 骨科,河南 鄭州 450003;2.鄭州大學人民醫院 河南省人民醫院手足顯微與創面修復外科,河南 鄭州 450003)
感染性休克的發病率持續升高,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及治療手段不斷完善,其病死率有所下降,由原來的30%~50%降至近幾年統計的20%~30%[1-2]。但感染性休克治療過程中并發手足缺血性壞死的情況時有發生,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未見相關報道,為此我們收集并分析了2016年11月-2020年9月我科收治的4例感染性休克治療過程中并發手足缺血性壞死的病例,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4例,男1例,女3例;年齡32~58歲,平均46歲。感染性休克的原因:外科手術術后感染3例,胰腺炎1例;4例發生手足缺血性壞死前均大量應用血管活性藥物。入院化驗:4例WBC、CRP均明顯增高,1例 WBC高達 28.96×109/L、CRP 200.0 mg/L;4例血小板、ATPP均明顯降低,2例血小板低至7×109/L,APTT縮短至13.6 s。發病后4例均使用了肝素治療。為了維持血壓穩定,1例泵入去甲腎上腺素由32.0 mg/50 mL降至8.0 mg/50 mL,1例泵入去甲腎上腺素由4.0 mg/50 mL升至16.0 mg/50 mL然后降至8.0 mg/50 mL維持。2例因入院后血壓穩定均泵入去甲腎上腺素4.0 mg/50 mL、8.0 mg/50 mL維持。4例均快速地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四肢末端壞死,快則發病后6 d,慢則19 d。4例下肢壞死程度均重于上肢,其中3例出現雙手9指、雙足10趾不同程度壞死,1例出現了雙足10趾不同程度壞死。1例甚至出現了右足中足以遠壞死(表1)。

表1 本組入院檢驗與治療數據一覽表
1.2 手術方式
本組患者均采用平臥位,患肢外展,全身麻醉。1例入院約1個月后患者病情平穩,手足發黑壞死界線清晰,無繼續向近端蔓延癥狀,給予雙手9指、雙足10趾壞死組織清除+殘端修整+腹股溝帶蒂皮瓣修復左示、中指皮膚缺損術。2例入院1~4個月后患者病情平穩,給予壞死組織清除+殘端修整術。1例發病3個月后患者病情平穩,行左示中環小指、右拇示中環小指截指+左足2-5趾截趾+右足中足截肢+殘端修整術。
1.3 術后處理
術后第1天繼續ICU治療,順利拔管、生命體征平穩后轉入普通病房。密切觀察患者生命體征變化及殘端切口愈合情況,加強換藥,預防切口感染不愈合。
2 結果
4例生命體征平穩,手足殘端傷口均一期愈合,例1左拇指完好,余雙手9指、雙足10趾壞死界線均在中節以遠;病例2雙足10趾末節部分壞死;病例3左拇指完好,余雙手9指、雙足10趾壞死界線均在近節以遠;病例4左拇指及左趾完好,余雙手9指、左足4趾壞死界線在中節以遠,右足壞死界線在中足以遠。術后隨訪6~18個月,平均12個月,根據中華醫學會手外科學會制定的《手功能評定標準》及臨床上廣泛應用的Kuyvenhoven足功能-5分評分量表綜合評定殘肢功能:優1例,良2例,可1例,殘肢外形良好,殘留手足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復。
典型病例:患者 女,48歲,因右髖關節高位脫位合并髖關節骨性關節炎,行右側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術后第2天一般情況可;術后第3天出現右髖關節輕度疼痛不適,切口無紅腫及滲出;第6天出現全身多處疼痛,體溫高達40°,脈搏130次/min,呼吸20次/min,血壓117/80 mmHg;術后第7天出現四肢抽搐、牙關緊閉、腹脹、黑便等癥狀。患者神志清,精神差,訴口渴,心率 101 次/min,血壓 61/45 mmHg,血氧飽和度測不出,呼吸31次/min,雙側橈動脈及足背動脈搏動未觸及,全身皮膚可見花癍,四肢紫紺,皮溫低,轉入ICU。化驗示:白細胞17.25×109/L、紅細胞2.25×1012/L、血紅蛋白64.0 g/L、血小板41×109/L、C-反應蛋白 116.08 mg/L、APTT 16.15 S、D-二聚體30.53 mg/L;血培養示:大腸埃希菌(+)。考慮:感染性休克。予美羅培南1.0 g、Q12 h靜脈點滴抗感染治療,特比薄150 00 U皮下注射升血小板治療,前列地爾10 υg泵入改善微循環,依諾肝素2 000 AxalUQ12h抗凝,泵入去甲腎上腺素4.0 mg/50 mL~8.0 mg/50 mL~16.0 mg/50 mL~8.0 mg/50 mL 維持血壓,以及抗休克補液、抑酸護胃、保肝、補充白蛋白及營養等對癥支持治療。轉入ICU第1天全身散在花癍、瘀紫,四肢冰涼;第3天出現雙足趾末梢皮膚紫紺,末梢循環較差;第6天以右下肢術區周圍皮膚花癍、瘀紫為重,雙手及雙足末梢發黑,出現干性壞疽,指脈氧測不出。發病3個月后患者病情平穩,行左示中環小指、右拇示中環小指截指+左足2-5趾截趾+右足中足截肢+殘端修整術;術后1年隨訪,手部功能恢復滿意,右足行走不穩,需假肢輔助(圖1-6)。

圖1 雙手指末梢干性壞疽創面

圖2 雙手指末梢干性壞疽創面

圖3 雙足趾末梢干性壞疽創面

圖4 雙足趾末梢干性壞疽創面

圖5 截指術后1年隨訪

圖6 截趾(肢)術后1年隨訪
3 討論
3.1 手足缺血性壞死與感染的相關性
感染性休克又稱為內毒素休克,臨床上以革蘭氏陰性細菌感染最為常見。表現為高排低阻型,感染病灶的微生物和毒素進入身體的血液循環后激活宿主的各種細胞和體液免疫系統,產生細胞因子及內源性介質,在不同的器官和系統中發揮作用[3]。由于各種原因產生的炎性介質及氧自由基直接破壞微循環的屏障功能,同時導致組織水腫、凝血功能異常及氧攝取異常,從而引起組織缺血缺氧、代謝紊亂、功能障礙,甚至壞死[4]。休克早期液體復蘇治療提高了休克的生存率,微循環低灌注是導致患者預后不良的主要原因[5],因此控制感染、避免微循環低灌注也是避免手足缺血壞死的關鍵。
3.2 肝素的應用
肝素是目前最主要的抗凝治療藥物之一,微循環障礙發生DIC時肝素的應用一般是認可的。在感染性休克狀態下,APTT縮短至10 s以上、血小板降至120×109/L以下,提示可能存在高凝狀態,警惕DIC的發生。積極的抗感染、調控血壓、改善微循環的同時,應該積極預防機體的“高凝狀態”,早期防治肢端壞死的發生,臨床上尚未確定出現廣泛性出血,為預防新的凝血繼續發生,可盡早考慮應用肝素。
3.3 血管活性藥物的應用
膿毒性休克早期即可出現微循環變化,內毒素降低了微小動脈收縮的反應性。僅依賴液體復蘇很難糾正患者的低血壓狀態,過度輸入液體,還會增加循環負擔,進一步加重了組織灌注障礙。及時有效地使用血管活性藥物,可有效提高循環血量,改善臟器的微循環。湯熠[6]的研究顯示,多巴胺及去甲腎上腺素在對感染性休克的應用價值比較中,去甲腎上腺素組患者HR、MAP、CVP恢復更好,血乳酸水平及6小時乳酸清除率也明顯好于多巴胺組,具有更好的6小時復蘇成功率,在治療開始后7 d內的臨床病死率更低。綜上,本組4例感染性休克患者均不同劑量地應用了去甲腎上腺素,不同時間內并發了指(趾)體壞死,我們通過查閱相關文獻及結合以上4例患者病情認為,感染性休克患者手足缺血壞死可能與去甲腎上腺素濃度的高低有關。
去甲腎上腺素是臨床常見的兒茶酚胺類血管活性藥物,去甲腎上腺素可對α受體產生興奮作用而促使外周血管阻力增強,升壓藥物中的甲氧胺、新福林和增血壓素等的主要作用在于使血管強烈收縮,外周阻力增加明顯,雖可達到升高血壓的目的,但常對微循環造成不利后果,如使用得當,可以適當增加血管張力、增加靜脈回流量、減少血流瘀滯,但如盲目加大劑量,則主要興奮交感神經的α受體,使血管強烈收縮,外周阻力明顯增加,從而增加心臟負擔,使心輸出量減少,使生命器官組織的血液灌注進一步惡化,同時增加循環的負擔,減少手足末梢血液循環供應,增加手足缺血壞死風險。
在搶救中如僅著眼于應用升壓藥升高血壓,而忽視其他矛盾的解決,其最終結果往往是不滿意的。去甲腎上腺素是推薦用于將MAP(平均動脈壓)恢復至65 mmHg的首選血管升壓藥物。Robins在綜述時提出,反復觀察證明,如果患者對小劑量升壓藥反應不好,即使增加劑量還是無效。Georger等[7]認為,對于嚴重的感染性休克患者,應用去甲腎上腺素維持灌注壓可改善而不是惡化組織微循環。方華等[8-9]將75只大白兔隨機分組為低劑量組0.5 υg/kg/h、中劑量組 1.5 υg/kg/h、高劑量組 3.0 υg/kg/h,通過用藥后不同時間點對大白兔心率、平均動脈壓、乳酸、TNF-a、IL-8水平監測分析,認為中劑量治療組各監測指標下降更明顯,膿毒癥休克模型的微循環障礙改善更明顯。
3.4 其他有效措施
微循環障礙是感染性休克患者組織缺血缺氧和細胞代謝障礙的根本原因,是直接導致手足缺血壞死的因素。其治療目的是盡早穩定血流動力學,達到早期復蘇目標,恢復組織器官氧代謝,降低病死率及組織缺血壞死的發生[10]。適當鎮靜治療對感染性休克患者具有免疫調節、組織保護等作用。趙淵博等[11]通過對94例進行治療的早期感染性休克患者的研究認為,右美托咪定可改善早期感染性休克的微循環灌注、氧代謝及血流動力學指標,降低免疫抑制。
有研究證明,感染性休克患者血漿彈性蛋白酶活性增高,從而導致彈性蛋白降解加速釋放出血漿彈性蛋白肽(EP),EP促進一氧化氮釋放,而NO是感染性休克循環功能障礙最終共同的關鍵介質之一,生理狀況下,合成適量的NO,對調節心血管舒縮功能、維持內臟灌注和氧合、保護重要器官,具有重要意義[12]。感染性休克時通過多種途徑異常合成和釋放大量NO,引起循環功能嚴重紊亂,內臟血流分布異常,重要器官缺血缺氧。班煒軍、陳麗[13]通過對30只健康雄性SD大鼠研究認為,應用彈性蛋白酶特異性抑制劑-西維來司鈉后,血漿EP含量降低,MAP進行性下降明顯,血管最大收縮張力增高,從而有效地改變了感染性休克的血流異常分布,改善了組織缺血缺氧狀態。
3.5 手術治療
手術盡量一次成功,避免多次手術。本組4例患者生命體征平穩后,手足缺血壞死界線清晰,無繼續向近端蔓延癥狀,進行了外科手術。手術應盡量保留手指、足趾長度,盡量保留功能指及足部負重區,減少手足部功能的缺失,降低由感染性休克并發的指(趾)體壞死而造成的不良預后的發生率。由于1例左拇指完好,考慮到壞死區周圍血管可能被破壞或受到影響,所以我們放棄局部轉移皮瓣和游離皮瓣修復缺損,采用了更安全有效的腹股溝帶蒂皮瓣修復左示、中指皮膚缺損,恢復了左手部分功能[14]。
通過對以上4例感染性休克治療過程中并發手足缺血性壞死病例的研究分析并查閱相關文獻資料,我們提出幾點建議僅供參考:⑴使用低濃度、中小劑量升壓藥物,如去甲腎上腺素達8 mg/100 mL時升壓效果仍不好,不要再急于增加劑量,應注意是否合并代謝性酸中毒、心功能不全、血容量不足等情況,如升壓效果滿意后應及時減停;⑵糖皮質激素可以改善微循環,減少升壓藥的副作用。因此,如單用升壓藥后數小時,病情不見好轉或反而惡化時,則應并用糖皮質激素;⑶適當地應用右美托咪定有助于改善微循環灌注、氧代謝,西維來司鈉可改善組織缺血缺氧狀態;⑷發病后手足末梢即刻出現花癍、瘀紫、冰涼,積極控制感染、改善微循環的同時在臨床上尚未確定出現廣泛性出血時應早期應用肝素改善高凝狀態,一旦發生壞死,很難逆轉;⑸即使搶救成功的患者,如手足趾壞死,生活質量也會明顯降低,作為臨床醫生我們需要研究的不僅是保全患者生命,也要保護肢體功能,在壞死組織清除的同時,通過顯微外科技術盡可能地保留手足功能[15]。
由于臨床病例數量有限,引起患者手足缺血性壞死的原因尚不十分明確,預防措施及治療方案仍需要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