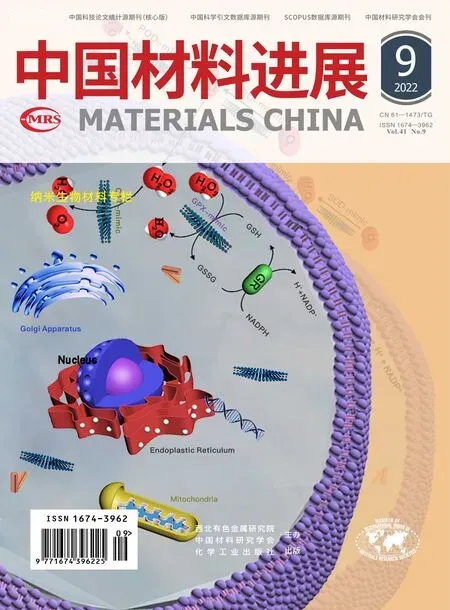鐵基磁性納米材料在神經調控應用中的研究進展
柳東芳,顧 寧
(1.東南大學醫學院 江蘇省分子影像與功能影像實驗室,江蘇 南京 210009) (2.東南大學生物科學與醫學工程學院 生物電子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江蘇省生物材料與器件重點實驗室,江蘇 南京 210009)
1 前 言
神經調控技術是通過物理或化學手段調節神經元活性,影響特定神經網絡功能,從而改善患者臨床癥狀的生物醫學工程技術。作為一種可逆的物理調控過程,神經調控技術能夠引起局部神經功能改變、神經可塑性變化和神經環路重塑,是神經科學基礎研究和神經系統疾病治療的重要手段。
神經調控技術發展迅速,包括腦深部電極植入術(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迷走神經刺激術(vagus nerve stimulation, VNS)、重復經顱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光遺傳學、超聲腦刺激術等,被廣泛應用于臨床治療或基礎研究中。不同的神經調控技術各有其特點和局限。例如,DBS是目前臨床上最常用的神經調控技術,能夠有效治療帕金森病、特發性震顫和癲癇等疾病[1-3],但這種方法具有侵入性,且缺乏細胞類型特異性,不適合對特定神經元進行刺激。光遺傳學可以高時空精度地控制神經元,但需要引入外源性的光敏蛋白。此外,電場和光會被組織強烈衰減,使用電場或光學方法分析大腦深部核團的復雜網絡,需要向大腦中植入電極或光纖,這為研究在自由活動狀態下的深部腦區神經回路功能和疾病治療帶來了不便[4]。rTMS是已經應用于臨床的一種無創的磁刺激神經調控技術,但隨著刺激深度的增加,磁場在腦中的刺激范圍也會增大,無法實現對深部腦區的精確調控[5]。納米技術的發展為解決神經調控研究中的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途徑。由于小尺寸效應,納米材料具有獨特的物理性質,定植于目標腦區后,能夠將外部電場、光、磁場或超聲波等能量轉化為目標區域的局部信號,如電、光、熱、機械力等,實現對大腦的遠程無線精確調控[6-8]。例如,在光遺傳學中,由于可見光穿透深度有限,需向大腦中植入光纖來激活神經元光敏蛋白。植入腦中的上轉換納米材料,能夠將具有較高穿透深度的近紅外入射光轉化為可見光,實現無需植入光纖的光遺傳學刺激[9]。
磁性納米材料具有獨特的磁學性質,將其植入目標腦區,結合低頻磁場高組織穿透性的特點,有望實現對任意深度神經元的無線精準調控。例如:植入腦中的磁性納米顆粒(magnetic nanoparticles, MNPs)在低頻磁場作用下,通過磁熱遺傳學調控神經元,可控制小鼠的神經活動、基因表達和激素釋放等[10,11]。本文將對MNPs介導的神經調節研究的最新進展、納米顆粒的設計和工作原理等進行總結;討論磁性納米材料在腦中的植入穩定性、生物安全性以及納米材料與神經元之間的相互作用。
2 磁性納米材料介導的神經調控技術
磁性納米材料能夠介導外部磁場產生高度局限于納米顆粒表面局部區域的熱、電、機械力等刺激信號[12-14],激活神經元上內源性表達的或轉基因表達的敏感離子通道或特異性受體。其工作機制主要有5種,包括磁遺傳學、磁熱、磁機械、磁電和磁化學遺傳學。
2.1 基于磁遺傳學的神經調控技術
為了實現磁場對神經元的遠程調控,科學家設計出磁性合成蛋白,如將鐵硫簇組裝蛋白1、鐵蛋白等作為磁受體,通過基因技術融合到神經元膜或離子通道上,實現磁場對神經元的非侵入性激活,這種技術被稱為“磁遺傳學”[15,16]。Wheeler等將大鼠的瞬時受體電位陽離子通道亞家族V成員4(TRPV4)蛋白與鐵蛋白融合,稱為“Magneto 2.0”,通過磁遺傳學將Magneto 2.0表達在紋狀體多巴胺受體神經元上,在5 mT的弱磁場刺激下,即可實現對斑馬魚和小鼠的行為控制[16]。Stainly 等利用融合了鐵蛋白納米顆粒的熱敏性辣椒素受體陽離子通道蛋白(TRPV1),在磁場作用下對胰島素基因表達進行調控。利用射頻或靜磁場刺激鐵蛋白TRPV1和鈣離子依賴性胰島素共表達轉基因間充質干細胞,能夠激活TRPV1引發鈣離子內流,刺激胰島素基因表達和胰島素原釋放。該研究表明,磁遺傳學能夠實現對轉基因表達的遠程無創調控[17]。
磁遺傳學具有遠程無創精確調控神經元的潛力,為研究不同類別神經元在大腦發育和疾病中的生理功能提供了有力工具。因此,磁遺傳學的研究一經報道就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也引起了爭議和質疑。Meister認為這些實驗結果違反已知的生物物理機制。他通過理論計算證明,在上述報道中所使用的鐵蛋白由于含有的鐵原子數量少,僅具有弱順磁性,在磁場作用下產生的力、扭矩或熱量遠小于激活機械敏感性或熱敏感性離子通道的閾值,無法對膜通道產生預期的作用[18]。一系列獨立的實驗研究也表明,表達融合了鐵蛋白的敏感離子通道(TRPV1、TRPV4等)的神經元,在已報道的磁場條件下不能被有效調控[19-22]。最近有研究者嘗試從生化或物理等不同的角度解釋磁遺傳學刺激機制,提出鐵蛋白標記的離子通道激活可能與射頻波通過鐵誘導的脂質氧化[23],或鐵蛋白納米顆粒在磁場磁化過程中磁熵變化產生的熱量相關[24]。
2.2 基于磁熱遺傳學的神經調控技術
磁性材料在交變磁場(alternating magnetic field, AMF)下能夠產生熱量,這種物理現象被稱為磁熱效應。磁性納米材料在AMF作用下產生的熱量,可激活表達在神經元上的熱敏離子通道(如TRPV1),引起神經元活性改變。TRPV1是瞬時受體電位陽離子通道的一個亞家族,在外界條件如熱、辣椒素、細胞外低pH值等刺激下,允許鈣離子選擇性地進入細胞,導致神經元膜去極化[25]。內源性TRPV1在嚙齒類動物大腦中低表達。在人腦內側額葉回和扣帶回中,TRPV1主要表達在星形膠質細胞上,而在神經元中低表達[26]。因此,磁熱調控神經元的研究,往往需要引入外源性的熱敏離子通道,又被稱為“磁熱遺傳學”。
TRPV1離子通道的激活溫度為42 ℃[27],接近人體正常體溫,在磁熱升溫激活TRPV1離子通道的同時,還要防止過量熱量對腦組織的損傷。鑒于此,在磁熱遺傳學神經調控的研究中,多采用具有高產熱效率的MNPs對神經元進行短時間的磁熱刺激[28, 29]。例如,Chen等合成了粒徑為22 nm的氧化鐵納米顆粒,這種納米顆粒具有高比損耗功率,在AMF下作用10 s,即可使水溶液溫度快速上升到43 ℃,在隨后50 s的靜止期,又冷卻到37 ℃。這種短時間、間歇性的AMF能夠有效激活TRPV1離子通道,引起神經元膜去極化,并避免對腦組織的熱損傷。植入小鼠腹側被蓋區(ventral tegmental area,VTA)的氧化鐵納米顆粒,在外加AMF作用下可選擇性地遠程激活VTA腦區神經元[29]。Huang等將直徑為6 nm的錳摻雜氧化鐵納米顆粒靶向到表達了外源性TRPV1的細胞膜上,在射頻磁場下作用5 s,即可引起細胞膜局部溫度升高到43 ℃,激活TRPV1離子通道,引發神經元動作電位。該研究首次實現了對活細胞TRPV1離子通道的遠程磁激活,并觸發秀麗隱桿線蟲的熱回避行為。結合在細胞膜上的MNPs產生的熱量高度局限于膜區域,與游離MNPs相比,其升溫速度和停止加熱后恢復到環境溫度的速度也更快,有助于更好地避免對腦組織的傷害[30]。隨后,該研究組將CoFe2O4-MnFe2O4核殼結構納米顆粒靶向到小鼠不同腦區的神經元膜表面(圖1),通過AMF 進行間隔1 min的循環刺激,可調控相應腦區神經元,喚起自由活動小鼠的運動行為改變,選擇性地激活大腦深部神經回路[10]。

圖1 膜結合的磁性納米顆粒(MNPs)磁熱激活TPRV1離子通道[10]:(a)中和親和素修飾的MNPs通過生物素化靶向神經元膜蛋白的抗體連接到神經元膜上;(b)施加交變磁場(AMF)加熱膜結合MNPs,激活TRPV1通道,引發鈣離子內流;(c)用于體外研究的結合了AMF的熒光顯微鏡裝置;(d)MNPs的TEM照片,圖中標尺為100 nm;(e)GCaMP6f+神經元(綠色)、MNPs標記神經元(紅色)、GCaMP6f和MNPs信號疊加的熒光顯微鏡照片及光學顯微鏡照片(從左至右),圖中標尺為10 mm;(f)AMF作用下DyLight 550熒光強度、MNPs附近的溫度(灰線)和GCaMP6f熒光信號的變化(綠線)Fig.1 The TPRV1 ion channel is activated by heating membrane-boun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MNPs) using an alternating magnetic field[10]: (a) MNPs are functionalized with NeutrAvidin, and attached to the neuronal membrane via biotinylated antibodies targeting membrane proteins; (b) alternating magnetic field (AMF) heats the membrane-boun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and activates the TRPV1 channels, resulting calcium influx; (c) the experimental setup combines AMF and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for in vitro studies; (d) TEM images of the magnetic nanoparticles, scale bar is 100 nm; (e) from left to right: fluorescence micrographs of GCaMP6f+ neurons (green), MNPs labeled neurons (red), overlay of the GCaMP6f+ and MNPs signals, transmitted light image of the same neurons, scale bar is 10 mm; (f) the change of DyLight 550 fluorescence intensity (red line), temperature near the MNPs, and the GCaMP6f fluorescence signal recorded in the neuron decorated with nanoparticles during AMF application
最近,氧化鐵納米顆粒還被用于磁熱遺傳學治療帕金森病的研究中[31]。注射到小鼠丘腦底核區的氧化鐵納米顆粒,在AMF作用下能夠刺激表達了TRPV1的神經元引起神經興奮,遠程誘導小鼠運動行為的改變,從而顯著改善輕度和重度帕金森病小鼠模型的運動缺陷。
外周神經和胃腸道、胰腺、心臟等器官高表達內源性TRPV1[32],利用磁性納米材料對這些神經或器官進行磁熱刺激,可實現不依賴于轉基因技術的神經和器官功能調控。如在最近的研究中,Rosenfeld等使用MNPs,在AMF作用下激活小鼠腎上腺皮質和髓質細胞的內源性TPPV1離子通道,可控制腎上腺素和皮質酮的快速釋放[11]。
2.3 基于磁電效應的神經調控技術
神經網絡是由眾多神經元組成的復雜生物電回路,神經元之間通過電場能量直接或間接地傳遞信息。因此,神經網絡對外界電場非常敏感。基于微電極的DBS是目前臨床應用最廣泛的神經調控技術[33]。然而,由于電極具有侵入性,且需要定期更換電池,為患者帶來隱患和不便,因此發展非侵入性的無創DBS技術具有重要的意義[34, 35]。磁電(magnetoelectric, ME)納米顆粒能夠將遠程的磁場原位轉化為目標腦區局部電場,實現對神經回路的無線精確調控[36-39]。Yue等對利用ME納米顆粒刺激大腦深處的神經活動進行了計算研究,并優化了將帕金森患者大腦電場脈沖序列調節到正常人水平的刺激條件,從理論上證明了ME納米顆粒調控神經系統的可行性[38]。隨后,他們利用ME納米顆粒,對小鼠大腦神經網絡進行調控。ME納米顆粒由2種材料復合而成:磁致伸縮的CoFe2O4納米顆粒和壓電納米粒子BaTiO3。在外部AMF作用下,CoFe2O4發生應變,施加在BaTiO3上產生電荷分離(圖2)。將該納米顆粒通過尾靜脈注射到小鼠體內,在腦部外加磁場作用下,ME納米顆粒通過血腦屏障進入腦實質內,影響神經網絡局部電信號,引起鈣離子內流,激活神經元動作電位[36]。通過對小鼠尾靜脈注射ME納米顆粒能夠實現無創的神經調控,然而,僅有約10%的納米顆粒能夠進入目標腦實質中,且納米顆粒分布范圍不能精確定位,在磁場作用下,可引起整個神經網絡的激活。此外,通過尾靜脈注射的ME納米顆粒進入腦內后有效工作時間僅為24 h,無法滿足神經調控需要反復操作的需求。Kozielski等利用立體定位儀將ME納米顆粒定向注射到小鼠丘腦底區域,在外加直流和交流磁場共同作用下,能夠激活小鼠丘腦底神經元,并調節皮質-基底神經節-丘腦皮質神經回路,提高丘腦運動皮層和室旁核區域的神經元活性,同時引起實驗小鼠丘腦皮層回路刺激相關的運動行為改變[39]。

圖2 磁電(ME)納米顆粒用于遠程調控小鼠神經元[39]:(a)磁致伸縮和壓電復合材料在磁場下產生電荷分離示意圖,(b)ME納米顆粒在直流磁場疊加交流磁場下最佳磁電輸出原理示意圖,(c)體內ME納米顆粒給藥方法及磁場刺激示意圖Fig.2 Magnetoelectric (ME) nanoparticles mediate remote regulation of mouse neurons[39]: (a) schematic demonstrating two-phase magnetoelectricity in ME nanoparticles made from magnetostrictive and piezoelectric materials that are strain-coupled, (b) schematic demonstrating the rationale for using a large direct current (DC) magnetic field overlaid with an alternating current (AC) field to generate optimal magnetoelectric output, (c) diagram for method of in vivo ME nanoparticles administration and wireless stimulation using an AC and DC magnetic field
超順磁性氧化鐵納米顆粒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是研究最為廣泛的一類磁性納米材料。目前,已有多種超順磁性氧化鐵納米顆粒獲FDA批準應用于臨床。作者團隊利用已獲批臨床試驗許可的超順磁性氧化鐵納米顆粒(瑞存?),結合輕度磁脈沖序列,建立了聯合磁性刺激系統[13]。將氧化鐵納米顆粒定位注射到抑郁癥模型小鼠的左前額葉皮層,在低頻脈沖磁場的刺激下,可快速改善抑郁癥小鼠的抑郁樣癥狀。氧化鐵納米顆粒在磁場下的電磁感應引起磁感應電壓的增強(圖3)[11],并且這些效應高度局限于納米顆粒周圍區域,對神經回路調節具有高選擇性,具有潛在的臨床應用價值。

圖3 水凝膠模型中氧化鐵納米顆粒的電磁感應效應[11]:(a)γ-Fe2O3納米顆粒TEM照片和γ-Fe2O3水溶液照片(插入小圖),(b)磁電感應測量示意圖,(c)不同磁場頻率下的感應電壓,(d)加入γ-Fe2O3引起感應電壓增強Fig.3 Magneto-electric induction effects of a hydrogel phantom injected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11]: (a) TEM image of the γ-Fe2O3 nanoparticles and external view of the γ-Fe2O3 aqueous solution (inset), (b) schematic of measurement of magneto-electric induction, (c) magneto-electric induction under different field frequencies, (d) the presence of the γ-Fe2O3 nanoparticles enhances the induced voltages
2.4 基于磁致機械力的神經調控技術
在運動磁場的作用下,磁性納米顆粒能夠產生機械力,激活表達在神經元上的機械敏感離子通道,如TRPV4、壓電型機械敏感離子通道元件(PIEZO)和N型機械敏感性鈣離子通道等,實現對神經元活性的調控[40, 41]。
Tay等將神經元網絡生長在具有高磁場梯度的微加工基底上,將淀粉包覆的氧化鐵納米顆粒附著在神經元膜上,在外加永磁鐵的作用下,膜結合的氧化鐵納米顆粒可以拉伸脂質雙層,誘導內源性機械敏感性N型鈣離子通道的開放,活化神經元。通過長期磁刺激,可調節興奮性和抑制性離子通道/受體的比率,促使脆性X綜合征(FXS)神經元網絡模型過表達的N型鈣離子通道數量恢復到正常神經元水平,并增加抑制性GABAA離子受體的表達[41,42]。他們還利用透明質酸磁性水凝膠對高表達TRPV4和PIEZO2離子通道的背根神經節(DRG)神經元進行磁刺激,發現短暫磁機械刺激通過激活TRPV4和PIEZO2離子通道誘導DRG神經元活化;長期磁刺激會降低DRG神經元PIEZO2離子通道的表達,有望用于調節慢性疼痛中過表達的PIEZO2離子通道[40]。在上述研究中,神經元需要生長在高磁場梯度的基底或水凝膠中,這限制了其在活體中的應用。
在激活機械敏感離子通道的研究中,磁性顆粒需具有較高的磁感應強度,因此往往采用鐵磁性的磁性顆粒。在提高磁性納米材料磁感應強度的同時,還需要解決其膠體穩定性的問題。Gregurec等制備了具有磁渦旋基態的Fe3O4納米盤[43],在沒有磁場的情況下,納米盤的渦旋結構表現為接近零的凈磁矩,因此磁性納米盤具有良好的膠體穩定性;在磁場作用下,納米盤磁矩從渦漩轉變為平面內磁化狀態,產生較大的磁扭矩,在緩慢變化的弱磁場作用下就可以在細胞水平上誘導DRG神經元TRPV4離子通道開放。
Lee等制備了一套模擬自然界中磁感應的磁扭矩裝置,在外加磁場下對小鼠神經元進行遠程刺激,調控自由活動小鼠的行為[44]。他們將粒徑為25 nm的鋅摻雜氧化鐵八面體納米顆粒連接到粒徑為500 nm的聚苯乙烯基底上,組裝合成了粒徑約500 nm的磁性納米球。組裝后的納米球飽和磁化強度比單個的氧化鐵納米顆粒大~470倍,能夠為機械敏感離子通道激活提供足夠的扭力;磁矯頑力保持在30 Oe的弱鐵磁性,使其在溶液中保持良好的膠體穩定性。通過表面修飾的Myc抗體,磁性納米球能夠特異性靶向神經元Myc標記的外源性PIEZO1通道蛋白。在圓形旋轉磁場作用下,產生皮牛頓數量級的扭力,激活運動皮層神經元,增強小鼠的運動能力。
2.5 基于磁化學遺傳學的神經調控技術
磁性納米材料在AMF下的磁熱效應除了能夠激活神經元熱敏離子通道外,還可通過與熱敏化合物結合,遠程觸發神經調節劑的局部釋放,實現對神經元高時空精度的化學遺傳調控。
Rao等將神經調節劑和Fe3O4納米顆粒共同負載到熱敏脂質體中,通過低頻AMF觸發神經調節劑的釋放,遠程對神經元進行化學調控。利用特定藥物激活特定受體(DREADDs)技術,將負載氯氮平N-氧化物(CNO)的磁性熱敏脂質體注射入小鼠VTA腦區,通過低頻AMF遠程刺激熱敏脂質體釋放CNO,激活表達hM3D(Gq)受體的轉基因神經元,增強小鼠活動性。隨后,他們又將多巴胺受體1(DRD1)激動劑SKF-38393負載到熱敏脂質體中,用于低頻AMF刺激小鼠伏隔核中表達DRD1的神經元,控制小鼠的社交行為[45]。Park等將Fe3O4納米顆粒包覆到聚酸酐或聚酯支架中,利用磁性納米顆粒在AMF下的磁熱效應,加速聚酸酐或聚酯化合物水解生成羧酸基團,釋放的質子能夠顯著降低細胞外pH值,并激活海馬神經元的酸敏感離子通道(ASICs),引起鈣離子內流[46]。
綜上所述,目前已有多種磁性納米材料應用于神經調控的研究(表1),并顯示了良好的調控效果。在下文中,將對納米材料在腦中的植入穩定性、生物安全性及與神經元膜的相互作用這些與磁性納米材料的神經調控應用密切相關的內容進行討論。

表1 應用于神經調控的磁性納米材料Table 1 Magnetic nanomaterials for neuromodulation
3 腦中植入納米顆粒的穩定性
慢性神經疾病的神經調控治療是一個長期重復的過程,而納米材料需要通過立體定位注射等微創手段植入大腦,不宜經常反復操作。因此,納米植入物在注射部位的穩定滯留時間對其臨床轉化進程具有重要的影響。然而,僅有少量研究工作關注到納米植入材料在腦中植入區的穩定滯留時間。日本REKIN腦科學研究所Chen等通過將上轉換納米顆粒植入小鼠大腦,對不同特定腦區進行經顱近紅外光遺傳學深部腦刺激,結果表明了該技術在抑郁癥、癲癇以及阿茲海默癥等疾病調控治療中的應用前景。在該工作中,植入的上轉換納米顆粒在植入區穩定存在1個月時間,神經調控功能可維持2周[47]。聚乙二醇(PEG)修飾的氧化鐵納米顆粒在植入小鼠的VTA腦區后,可在1個月內對大腦進行磁熱刺激。Muldoon等利用磁共振成像研究了3種FDA批準的氧化鐵納米顆粒ferumoxide、ferumoxytol和ferumoxtran-10在腦中的分布和磁共振信號隨時間的變化。結果顯示,注射到小鼠腦內的氧化鐵納米顆粒,磁共振信號強度和范圍隨著時間的延長顯著下降,半衰期為14~30 d左右[48]。Kozielski等報道的CoFe2O4@BATiO3NPs,在小鼠腦中能夠保持7周[39]。綜上所述,在已知報道中,植入腦中的納米材料穩定滯留時間不超過2個月,無法滿足慢性神經疾病長期重復神經調控的需求。
納米材料的植入穩定性與其在腦中的擴散和免疫清除密切相關。研究表明,大腦細胞外基質孔隙大約在38~64 nm[49]。納米顆粒在大腦細胞外基質中的擴散速度和粒徑相關,顆粒粒徑越小,在細胞外基質中的擴散速度越快。納米顆粒在腦中的清除與小膠質細胞的免疫作用有關。據報道,高密度脂蛋白納米球和聚乳酸-聚乙二醇納米球在腦中被小膠質細胞攝取,然后經血管旁膠狀通道到達頸窩淋巴結和外周血中,最終通過腎臟和肝臟進行代謝[50]。葡聚糖包覆的氧化鐵納米顆粒腦內注射20~24 h后,通過頸深淋巴結排出大腦[51]。納米顆粒表面化學修飾會影響其在腦內的擴散和清除。通過具有抗調理素吸附性質的PEG修飾納米顆粒,可減少磁性氧化鐵納米顆粒被小膠質細胞攝取和清除[52],然而,PEG修飾會促進聚合物納米球在人大腦皮層中的擴散[53]。因此,納米材料如何有效逃避大腦免疫系統清除,并且減少在腦中的擴散,是延長其在腦中穩定工作時間需要考慮的問題。
4 鐵基納米植入材料的生物安全性
納米顆粒臨床應用的一個主要障礙在于其生物安全性。目前大部分磁性納米顆粒介導的神經調控研究主要聚焦于調控效果和調控機制方面,僅有部分工作涉及對氧化鐵納米顆粒的生物相容性研究。Chen等的研究結果表明,與相似尺寸的不銹鋼植入物相比,植入Fe3O4納米顆粒的腦組織接觸面顯示出更低的膠質細胞激活和巨噬細胞聚集[29]。注射到大腦皮層的磁性脂質體和CoFe2O4@BATiO3納米顆粒溶液,在短期內也不會引起植入組織小膠質細胞激活和星型膠質細胞增生[10, 45]。以上結果表明,磁性納米植入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體外細胞水平的研究顯示,磁性納米材料對大腦不同類型細胞的毒性反應不同。例如,氧化鐵納米顆粒通過內吞作用進入星型膠質細胞,并定位于細胞內囊泡中,在鐵含量高達毫摩爾數量級的濃度下,也不會對細胞產生明顯的毒性[54]。而對于小膠質細胞,在與微摩爾數量級的氧化鐵納米顆粒共孵育后,細胞活性會受到嚴重影響。這可能是由于氧化鐵納米顆粒進入細胞后,迅速進入溶酶體中,在酸性環境下,引起氧化應激造成的[55]。氧化鐵納米顆粒對細胞的不同作用可能與其類酶活性相關。氧化鐵納米顆粒的酶活性具有pH依賴性,在酸性條件下,主要表現為過氧化物酶活性,通過芬頓反應產生羥基自由基,引發氧化應激產生細胞毒性。而在中性條件下,氧化鐵納米顆粒主要表現為過氧化氫酶的活性,可將H2O2分解為對機體無害的氧氣和水[56]。由此可見,磁性納米材料的細胞毒性可能和材料與細胞的相互作用及在細胞中的定位密切相關,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5 納米顆粒與神經元膜的相互作用
通過納米材料轉化的局部光、電、熱等信號僅局限于納米顆粒周圍的區域,隨著距離的增大,信號強度急劇下降[13, 47],將納米顆粒附著在神經元表面或直接作用在離子通道蛋白上,可以有效提高神經調控效率[15]。納米顆粒與神經元膜的相互作用與材料表面電荷密切相關。ζ電位小于-22 mV的負電荷納米顆粒能夠附著在神經元膜上[57],但負電荷磁性納米材料也會內化進入神經元[58]。一方面,如上節所述,可能會產生不必要的毒副作用,另一方面,納米材料還會在細胞內和細胞間進行輸運,造成在腦內的擴散。而帶正電或電中性的納米顆粒不與神經元發生作用,也不會附著在神經元細胞膜上[57]。因此,制備能夠特異性識別并附著于神經元細胞膜,但不內化進入神經元細胞的納米植入材料,將有利于提高神經調控的效率。
6 結 語
磁性納米材料介導的神經元磁調控是一種有前景的技術,通過介導磁場轉化為局部的熱、電、機械等信號,磁性納米材料為大腦深部腦區神經元的遠程精準調控提供了有力工具。磁性氧化鐵納米顆粒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結合磁場能夠有效緩解小鼠帕金森模型和抑郁模型的癥狀,對神經性疾病的臨床治療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然而,該領域仍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主要為:① 磁性納米材料介導的神經磁調控技術對神經疾病的療效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需要進一步研究其對不同疾病神經修復的效果和機制;② 進一步研發能夠特異性識別神經元的高性能磁性納米材料,提高神經調控的時空分辨率,降低毒副作用;③ 納米材料植入腦內穩定工作的時間較短,需要研發植入大腦后能夠長時間穩定滯留的磁性納米材料,以滿足神經調控治療長期反復操作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