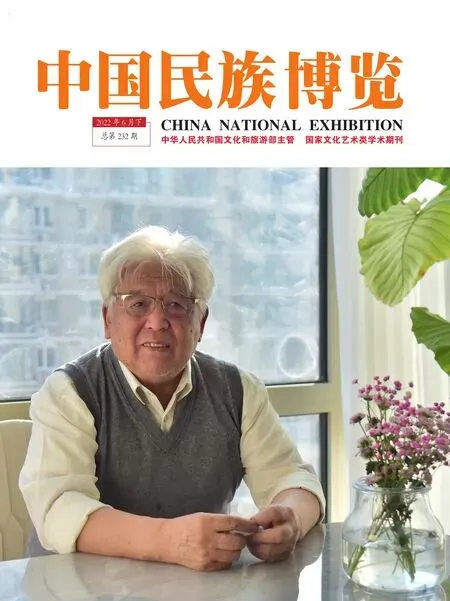黃河文化的核心特征與時代價值
文/張冬寧

滾滾黃河萬年長,綿綿華夏文明始。作為養育中華億萬兒女的母親河,黃河自巴顏喀拉山北麓的一縷清泉緩緩流下,繞過九曲十八彎的河套平原,以萬馬奔騰之勢從壺口瀑布傾瀉而出,最終在長河落日的美景下匯入浩瀚的渤海。在這130多萬平方公里的黃河流域內,黃河孕育出了璀璨的中華文明,歷史悠久的黃河文化更凝聚而成中國人民高尚的民族品格與奪目的時代精神。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著重強調要“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其中第十二章提出要:“著力保護沿黃文化遺產資源,延續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深入挖掘黃河文化的時代價值,加強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要推進黃河文化遺產的系統保護,守好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要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含的時代價值,講好“黃河故事”,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
黃河文化作為一種深邃博大、涵蓋廣泛的文化復合體,其概念非常豐富,既包括政治制度、文化藝術、經濟成就、哲學思想等方面的內容,也囊括了文化概念中所包含的思想模式、情感模式和行為模式即民間信仰、道德規范和社會生活習俗等方面的內容。從廣義上來說,黃河文化是指黃河全流域的廣大勞動人民在從事相關生產實踐活動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就其主要特征來看,黃河文化具有起源性與延續性、開放性與包容性、正統性與典型性、創新性與象征性等核心特征,而這些核心特征又賦予了黃河文化重要的時代價值。
一、黃河文化的起源性與延續性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根源之本
黃河文化具有起源性與延續性的特征。中華文明發祥于此,中華民族發源于此。正是在黃河文化的豐富滋養下,諸多區域文明中唯有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中原文明綿延不斷持續發展,最終成為華夏文明前身伊始。從舊石器時代的許家窯遺址、丁村遺址、下川遺址等,到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裴李崗遺址、中期的仰韶遺址、晚期的廟底溝遺址、龍山時代的陶寺遺址等,再到三代的二里頭、鄭州商城、殷墟、湖北盤龍城、鄭韓故城、曲阜魯國故城等,以及自秦漢以降的漢長安城、漢魏洛陽城、隋唐長安城、隋唐洛陽城、北宋東京城等等,以上遺址不僅見證了整個中國歷史綿延不斷的持續發展,還反映了盛世文明的偉大記憶與歷史成就。在這個漫長發展過程中,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龍山文化一脈相承;城市、文字、青銅器、農業灌溉、畜牧養殖、宮室宗廟等文明要素熠熠生輝;夏商周三代文明禮儀承襲不曾斷絕;儒、道、法、農、兵、商、墨百家爭鳴;漢代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代際有承;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盡顯風華。可以說中華文明的眾多元素,其根源均深植于黃河文化之中。
二、黃河文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帶來了民族團結的精神之脊

黃河文化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的特征。沿黃地區自古就是多民族和多文化的水乳交合之地。無論是最早中國的二里頭遺址,還是恢弘雄偉的漢長安城,抑或是氣象萬千的漢魏洛陽城等,這些黃河文化主地標不僅見證了炎黃時期多部族的融合、秦漢時期漢民族的形成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族與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多民族的交融,更蘊含著“尚和合”“求大同”民族文化認同和主流意識。最終形成了兼容并蓄、博采眾長的黃河文化,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精神紐帶。“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從先秦時代起,中華大地的錦繡河山就是在各族先民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的開拓中奠定了藍圖。黃河文化恰恰能凸顯各民族共同開拓中華疆域的悠久歷史。通過對重大考古遺址的展示與挖掘,能夠充分證明黃河流域的中原先民與邊疆民族是在不斷的交流碰撞中,逐漸形成了以炎黃華夏為核心、凝聚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通過梳理黃河文化可以將眾多見證民族融合、開疆擴土的重要沿黃歷史遺跡加以系統保護、重點展示與有效傳承,讓中華兒女都深刻感受中國“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光輝歷史。
三、黃河文化的正統性與典型性展現了傳統文化的精魄之魂
黃河文化具有極其顯著的正統性和典型性的特征。中國作為以農耕文明為底色的文明復合體,發達的農業經濟是黃河流域始終處于中心地位的重要支撐。依托先進的生產力,黃河文化發展出了兼容并包、海納百川的豐富文化內涵和深厚思想傳統,創造了代表當時中國最先進物質文化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的文明成就。以能代表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最高發展水平的都城遺址來說,無論是考古發現可能是黃帝之都的雙槐樹遺址、堯都的臨汾陶寺遺址、大禹之都的登封王城崗遺址,還是二里頭夏都遺址、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安陽殷墟、豐鎬、洛邑,都是說明自傳說時代自夏商周都居于黃河中下游的相關流域,證實了黃河文化長時間占據中華文明的發展主流地位。此后直至北宋滅亡的千百年間,漢唐時期西安洛陽雙京閃耀,五代北宋開封異軍突起,歷史時期中華文明最具正統性的文化象征大都孕育于黃河流域。從典型性來看,黃河文化可謂是集傳統文化精華之大成者。無論是傳統哲學的儒家、道家、法家、佛教思想不斷碰撞而迸發出的思想火花和經典著作;還是文學方面的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百花齊放;亦是秦始皇陵、萬里長城、大運河、鄭國渠等宏大工程;抑或是“漢字”“河圖洛書”“四大發明”“二十四節氣”等偉大創造,都是黃河文化汲取各地優秀傳統文化書寫在中華大地上的璀璨篇章。可以說黃河文化用自身的正統性和典型性時時刻刻影響著中華民族的呼吸命運。

四、黃河文化的創新性與象征性塑造了堅定自信的文化之光
黃河文化具有明顯的創新性與象征性的特征,其在數千年綿延發展的過程中注重不斷吸收各地的先進文化和生產經驗并加以轉化。古代文獻就記載了嫘祖發明桑蠶養殖技術,倉頡創制文字,黃帝造舟車作《黃帝內經》并教人民順應四時播種百谷、馴化鳥獸等諸多發明創造。而反映在古代遺址方面,無論是鞏義雙槐樹遺址的桑蠶牙雕,還是襄汾陶寺古城的古觀象臺,抑或是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的城壕布局和版筑技術,以及之后偃師二里頭的“井”字型道路布局、都城規劃、綠松石龍形器和青銅冶煉技術,這些重要考古發現都力證黃河文化是在不斷創新中賡續著中華文明的旺盛生命力。從象征性特征來看,黃河文化還代表著中華文明的第一印象。以文字的發明發展為例,早在裴李崗文化時期的舞陽賈湖遺址就出土發現了最早的契刻符號,之后安陽殷墟又出土了中國最早的系統性文字體系——甲骨文,隨著商周金文到大篆再到秦始皇時期“書同文車同軌”的小篆出現,以及世界首部字典許慎的《說文解字》的橫空出世和宋代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可以說漢字文明每一次最具象征意義的歷史節點產生于黃河流域,孕育自偉大的黃河文化。可以說,黃河文化不僅是中華文化不斷吸收外部優秀文化融合創新的產物,其亦是中華文明不斷更新自我、奮力創新的具象表征,更是我們堅定自信的文化之光。
綜上所述,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事關中華文脈的綿延賡續,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堅實基礎。加強對黃河文化的保護、弘揚與傳承,不但是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舉措,其所蘊含的巨大價值更是中華民族增強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彰顯中華文明、增進民族團結的時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