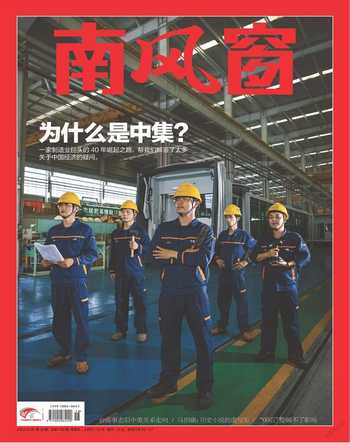拜登“經濟外交”圖窮匕見
顧登晨

9月初,“芯片四方聯盟”(Chip 4,成員包括美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將召開初步磋商會議。這個由美國牽頭草創的產業聯盟,究竟能不能促進半導體產業回流美國還很難說,但它代表著拜登政府在這個民主黨“行動之夏”實質性推進“經濟外交”的企圖。
作為Chip 4的經濟誘餌,美國總統拜登8月9日簽署的《芯片與科學法案》,提出撥款527億美元用于補貼建設和翻新晶圓廠(芯片是晶圓切割而成的),并對相關晶圓廠給予高額稅收減免;獲得上述優惠的企業,未來10年內將不得擴大在中國大陸部署28納米以下(不含28納米)制程的芯片技術,違反相關規定的企業需要全額退還相關補貼款項。
芯片法案的意圖、目標清晰明了。站在“芯片四方聯盟”草創的關口,回望立法歷程,可以大致看清美國最近兩任政府經濟外交的“打法”。這對于跳出芯片法案,以更全面、縱深的視角看待美國經濟外交的影響并評估預判其效果,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為芯片法案鋪路的管制名錄
芯片法案的主要立法目標,是鼓勵半導體制造產業鏈回流美國。法案的發起人、來自深紅州俄亥俄州的民主黨籍國會眾議員蒂姆·瑞安,認為芯片法案“將重振俄亥俄州制造業、帶來高端就業機會”。這不禁讓人想起特朗普2016年競選期間即鼓吹的“制造回流”“工作機會回流”。
事實上,蒂姆·瑞安一直被稱作“特朗普式的民主黨人”。特朗普執政后也一度邀臺積電等半導體代工企業赴美辦廠,疫情期間還曾幾番會晤日韓首腦,鼓勵東亞半導體制造商赴美投資。可見,芯片法案這一被視作拜登政府產業政策的代表性法案,其實早在特朗普時期就已埋下了種子。
然而,在缺乏外力強行扭曲供應鏈的情形下,產業資本全球布局的既有格局并不易逆轉,加之特朗普對外單邊主義疏遠了盟友、對內與國會高烈度對峙亦引發國會立法不支持,半導體制造回美問題一直是“只打雷不下雨”。
但這不意味著特朗普與芯片法案落地無關。除了前述“精神淵源”之外,特朗普開啟的對華科技競爭,尤其是貿然啟用以“打”為主的政策工具,是當下芯片法案落地不可或缺的環境因素。
不同于一般性貿易與關稅糾紛,在半導體領域,外商投資審查與出口管制,構成了特朗普在芯片領域的主打工具。
外商投資審查方面,2018年美國通過《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給外商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擴權,納入審查涉及關鍵技術、關鍵基礎設施、敏感個人數據的非控制性對美投資。其中,“關鍵技術”欄中新增“新興和基礎技術”。此后,海外資本對美國芯片公司的戰略投資,遭到了越來越嚴苛的審查。
出口管制方面,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將“新興與基礎技術”納入出口管制。此后,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多次更新出口管制名錄,如2020年10月名錄修改中,納入“用于生產5納米精加工晶圓的某些技術”;最新的動作則是今年8月12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將三項與半導體相關的“新興和基礎技術”納入出口管制名錄,包括兩項超帶寬半導體材料技術和一項EDA軟件技術。
芯片法案中要求“10年內不在特定國家投產先進半導體制程”這一條款,單靠少量補助并無法實現,但在出口管制與事實上雙向投資審查工具的作用下,這一條款才具備了落地的可能性。
半導體產業生態復雜,利益主體間相互依存度高,無論是針對個別企業的芯片禁運,或是針對個別國家生產制造環節的強行轉移,單一政策工具難以奏效。特朗普任內,以“新興和基礎技術”為抓手,首次實現了國內投資審查與出口管制之間的“水位拉齊”,甚至在2018年即已醞釀“反向CFIUS”機制,即試圖在管住技術出口、管住外國資本來美投資(以獲取技術)的同時,對美國資本的海外投資也嘗試審查,防止投資引致技術轉移。
截至目前,“反向CFIUS”機制雖未建成,但基于“新興和基礎技術”串聯起來的赴美投資審查、技術出口管制,已對芯片行業海外投資產生引導效應。此番,芯片法案中要求“10年內不在特定國家投產先進半導體制程”這一條款,單靠少量補助并無法實現,但在出口管制與事實上雙向投資審查工具的作用下,這一條款才具備了落地的可能性。
拜登“加碼”供應鏈審查
特朗普任內即已關注供應鏈審查,先后發布涉“電力系統設備”“信息通信技術與服務(ICTS)”“無人機”三大領域的行政令,通過拒絕特定來源國的軟硬件設備采購,來確保所謂的供應鏈自主和國家安全。
特朗普時期供應鏈議題呈三大特征:一是議題零散,偏離核心目標。電力系統、ICTS、無人機三個供應鏈領域缺乏邏輯關聯,且特朗普基于個人風格,在供應鏈審查過程中常常對外發聲,甚至表現出為追求經濟利益而扭曲供應鏈的傾向,讓外商投資審查、出口管制偏離了“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利益”這一基本框架。外界甚至認為,白宮打壓特定企業是為了賺取利潤。
二是法律效果不確定。相關供應鏈議題操弄,多依賴基于《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而出臺的行政令,法理上屢屢受到挑戰。以ICTS領域為例,特朗普2020年對TikTok的禁令,即因援引法律依據不充分而遭法院禁制,并在拜登任內被終止。
三是無盟友協同,效果僅限于美國國內。相關動作局限于對美本土供應鏈中特定外國元素的排除,除了5G等個別領域,排除動作很難與盟友協同,且在與盟友商定替代供應鏈方案方面毫無進展。
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在執政之初的2021年2月即頒布行政令,要求100天內完成對包括藥品、稀土、半導體及大容量電池在內的四類美國關鍵產品供應鏈的風險審查,1年內對包括國防、公共衛生、信息和通信技術、能源、交通運輸、農產品和糧食生產在內的六大重點行業進行供應鏈審查。行政令還要求將關鍵產業鏈移回美國國內,并與盟友商定可替代的供應鏈方案。
在執行方面,拜登政府一方面借助美歐技術與貿易委員會、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多邊機制,部分實現了與盟友的供應鏈轉移合作(芯片法案瓜熟蒂落,很大程度上與盟友協同方面取得突破有關);另一方面,以建制派的打法,去化解法理上可能遭遇的挑戰,即行政部門不急于針對特定行業、企業“下手”,而是通過評估報告的方式去推動國會立法,獲得進一步授權再執行,執行的過程也務求低調。
仍以ICTS領域為例,雖然《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即禁止美國政府部門使用華為與中興產品,但民間使用不受限;此后,美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禁止美運營商使用聯邦補助款購買兩家中企的設備或服務,但直到去年10月,美國才通過《安全設備法》立法,明確FCC將不再對5家中企頒發新的設備許可證,從而徹底關閉了相關設備在美的銷售渠道。
對比特朗普與拜登對供應鏈議題的操弄,容易得出前者“以打為主”而后者“打拉結合”的結論。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披露,截至去年7月,累計有600家中企被納入“實體名單”,其中拜登執政以來新上榜中企的數量,遠低于特朗普時期。
然而,數量上的克制并不代表拜登政府在制裁議題上的保守,“善于拉攏盟友”也絲毫沒有減損拜登政府對“單邊打擊”手段的依賴。事實上,拜登任內,對外美歐在立法、執法方面展現出協同制裁模式,對內美國也呈現出多部門、多手段協同制裁的局面。
當下,拜登政府正力推國會立法將“供應鏈審查”常態化,同時不斷細化、固化“投資審查”與“出口管制”等各類政策工具項下的措施。例如,作為特朗普時期制裁手段之一的“涉軍清單”最初由于意涵不清屢遭挑戰,拜登政府去年對此予以明確,從而為涉軍清單“續命”,同時還敦促國會明晰“新興和基礎技術”條目。
此類包裹于“供應鏈審查”項下的投資審查和出口管制工具體系的完善和制度化,反映出拜登政府經濟外交的“變本加厲”。在有盟友助力的情形下,破壞全球產業分工、為安全目的重塑供應鏈,反而可能成為一種所謂的“政治正確”。
整體上,拜登經濟外交政策重回“比較優勢論”,即主要借助美國的所謂“規則與科技優勢”,在特殊關鍵敏感供應鏈領域跑通“競爭閉環”。
圖窮匕見:重回比較優勢?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等智庫基于測算,認為在特朗普執政后期的無差別貿易戰效果有限,原因在于其偏離了美國在科技與規則方面的比較優勢。這些智庫建言:將科技領域“小院高墻”等政策復用到經貿領域,放寬一般性貿易,將資源集中投入高科技類產品的貿易和制造環節,重塑相關供應鏈。
拜登執政以來,商務部長雷蒙多、財長耶倫等核心內閣成員,一直對特朗普無差別貿易戰持批判態度,拜登政府也第一時間擱置與盟友的鋼鋁關稅糾紛。即便受貿易代表戴琪和美本土制造業協會的掣肘,對華關稅調整目前仍然遲緩,白宮也已不追求全面脫鉤,甚至希望實現一定程度的“再掛鉤”。
整體上,拜登經濟外交政策重回“比較優勢論”,即主要借助美國的所謂“規則與科技優勢”,在特殊關鍵敏感供應鏈領域跑通“競爭閉環”。
致力于促成半導體產業回流的芯片法案,既折射出美國對高端敏感供應鏈控制力不足的焦慮,也承載了兩黨試圖通過復興本土高端制造、緩解產業空心化以解決就業問題、重振中產階級從而提振選情的愿望。在特朗普、拜登兩任政府以各類制裁工具反復捶打之下,借助國會對產業政策的支持,芯片法案終獲通過,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受到擾動在所難免。
但拉攏盟友扭曲全球供應鏈,需要國會立法提供真金白銀的支持,成本高昂。另外,當下韓國對正式加入Chip 4的遲疑(韓方稱,前提是“各方尊重‘一個中國立場,不以‘貿易排華為目的”),也折射了這一機制的缺陷。未來,受兩黨競爭和民主黨進步派的掣肘,類似芯片法案這樣的立法很難成為新常態,其大概率只是半導體這一特殊重要的供應鏈領域的單一立法成果,而難以在各類供應鏈領域展開復制。
至于在被美國納入審查的更為廣泛的其他供應鏈領域,中國產業需要在美方既有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等政策工具日益精細化、體系化的背景下,發揮好自身既有大市場的規模優勢,與日、韓等在先進制造領域有話語權的國家對話,尋找到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平衡點,有效融入世界高端制造的產業鏈體系,從而化解美國對華產業壓迫的攻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