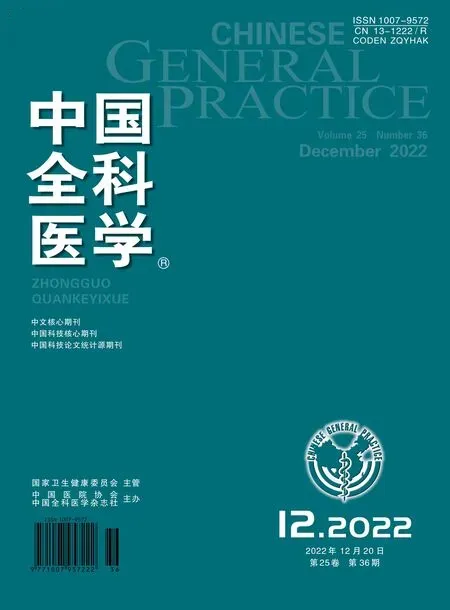取環致宮腔化膿性感染引發腰椎間盤炎一例報道并文獻復習
楊艷艷,王新玲,李娜,王蓓,段曉妍,張蘊霞
盆腔炎性疾病(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PID)是婦科常見感染性疾病,包括子宮內膜炎、輸卵管炎、輸卵管卵巢膿腫和盆腔腹膜炎[1]。我國育齡期婦女中PID的發病率高達40%[2-3]。對PID進行及時診斷并規范化治療是全科醫生面對的重要問題之一。宮腔化膿性感染是由子宮內膜炎發展而來,是PID的一種特殊、嚴重的表現形式,治療以抗菌藥物為主,治療原則要求經驗性、廣譜、及時并個體化。對于抗菌藥物控制效果不佳的化膿性感染病灶,需要及時進行手術治療。椎間盤炎是發生于椎間盤間隙和鄰近椎體或軟骨板的感染性病變[4],通常認為椎間盤炎是由細菌感染的血源性傳播引起的[5],其癥狀及體征缺乏特異性,臨床上容易延誤診斷甚至出現椎體骨質破壞及下肢肌力減弱。門診流產手術和取環手術可誘發盆腔感染,引起患者腰腹痛、月經失調等,甚至引發全身感染。研究發現流產手術后盆腔感染的發生率為5.88%~8.79%[6-7]。門診取環手術可引起宮腔化膿性感染,臨床表現為發熱、腹痛、陰道分泌物增多等。而宮腔化膿性感染引發腰椎間盤炎目前國內外尚未見相關報道。本文報道了1例取環手術致宮腔化膿性感染引發腰椎間盤炎患者的診療過程,并結合詳細的病例資料及復習相關文獻,分析、探討了該例患者的發病原因、感染途徑、治療經過、抗菌藥物應用及手術時機,總結經驗,以提升臨床醫生對PID及腰椎間盤炎的認識,為規范診治方案和開展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1 病例簡介
患者,女,44歲,因“取環術后腰痛1月余,左下肢疼痛伴行走障礙5 d”于2021-09-08至河北省人民醫院疼痛科就診。患者因陰道出血伴重度貧血超過1個月,就診于當地縣醫院,超聲提示:子宮肌瘤,子宮內膜病變,宮內節育器。給予輸血糾正貧血后行診斷性刮宮術+取環術,手術困難,操作時間約2 h,取環失敗。術后2 d患者出現高熱、寒戰伴腰骶部疼痛,體溫最高達41 ℃,考慮感染性休克轉至當地醫院重癥監護監護病房(ICU)治療,于ICU抗炎治療9 d體溫恢復正常,腰骶部疼痛較前稍減輕,下肢活動自如。診斷性刮宮病理回報:增殖期宮內膜。出院后腰痛仍持續存在,呈過電樣銳痛,間斷發作,夜間顯著,與活動、體位改變及排便等無關,無法長時間保持平臥位,無雙下肢乏力及感覺異常。于當地醫院查腰椎CT示“腰3~4、腰4~5椎間盤膨出、腰4~5椎間盤鈣化、腰椎骨質增生”,未予特殊治療。隨后由于患者出現左下肢抽搐樣疼痛,自覺無力及行走困難,疼痛每次發作持續約數分鐘,持續5 d后到河北省人民醫院疼痛科就診并住院治療。
既往病史:確診“子宮肌瘤”3個月,擬擇期行手術治療。無高血壓病、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史,否認肝炎、結核病史。4年前因“甲狀腺結節”行“甲狀腺部分切除術”,20年前因“產后出血”輸血治療,1個月前因“重度貧血”輸血治療。
體格檢查:體溫36.3 ℃,脈搏98 次/min,呼吸20 次/min,血壓122/69 mm Hg(1 mm Hg=0.133 kPa)。患者神清語利,查體合作,心肺腹查體未見明顯異常,脊柱無畸形,無側彎,各椎體無壓痛及叩擊痛,活動無障礙。雙側骶骨外側及坐骨結節之間壓痛,雙側骶髂關節處無壓痛,雙側直腿抬高試驗陰性,雙側4字征陰性,骨盆分離試驗陰性,骨盆擠壓試驗陰性。雙下肢無畸形,無水腫,活動自如,各關節無紅腫,活動無障礙。肌肉無萎縮,肌力正常。
實驗室檢查:紅細胞沉降率、C反應蛋白升高,白細胞計數及降鈣素原正常。影像學檢查:腰椎MRI平掃,腰5、骶1椎體及部分附件、椎體后方硬膜外異常信號(圖1),考慮感染性病變可能。PET-CT檢查:腰5骶1椎體上下緣代謝增高伴骨質破壞,腹盆腔多個輕度高代謝淋巴結,考慮椎間盤炎伴淋巴結炎癥。子宮體積增大、壁增厚、內膜不均勻、代謝增高,考慮為刮宮術后改變伴感染可能,子宮壁內節育器影。

圖1 患者腰椎MRI檢查結果,可見腰5骶1椎體骨質破壞Figure 1 Lumbar spine MRI findings of the patient
診斷與治療:入院后給予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聯合奧硝唑靜脈滴注抗感染,持續靜脈泵入鹽酸右美托咪啶及地佐辛鎮痛、鎮靜。患者仍訴腰部及左小腿發作性疼痛,同時出現雙側臀部劇烈疼痛,坐位明顯,側臥位可稍緩解。因患者子宮肌瘤繼發重度貧血,且宮內節育器嵌頓,遂轉入婦科行腹腔鏡下子宮切除術及椎間盤探查術。術中見子宮均勻增大如妊娠3個月,表面光滑,與周圍組織無粘連。雙側輸卵管充血并見炎性滲出小泡,雙側卵巢外觀未見異常。子宮離體后剖視:宮腔內為化膿性感染,可見直徑約7 cm黏膜下肌瘤,表面有膿苔附著,其中部分肌瘤組織壞死、感染化膿,局部見膿腔及灰白色膿液,有臭味,留取黏膜下肌瘤化膿感染組織送細菌培養。宮腔內見吉妮致美節育器1枚,嵌頓扎入子宮后壁肌層內。經陰道探查,陰道后壁與直腸之間有一膿腔,黏膜腫脹充血、糟脆,留取膿腔壁送細菌培養。骨科醫生行腹腔鏡下椎間盤探查術,粗針穿刺腰5骶1椎間盤,未見膿液流出,分離椎間盤間隙,見暗紅色血水樣滲液約20 ml自椎間隙流出,留取部分椎間盤組織送細菌培養。以大量稀釋碘伏、0.9%氯化鈉溶液沖洗盆腹腔后關腹。術后病理結果:(1)子宮黏膜下平滑肌瘤,局部梗死,表面潰瘍壞死,伴化膿性炎癥、子宮腺肌癥;(2)增生期子宮內膜;(3)子宮頸輕度慢性炎癥,腺體鱗化;(4)(雙側)輸卵管充血,伴泡狀附件。宮腔內及直腸前組織細菌鑒定:大腸埃希菌感染,椎間盤組織細菌培養為陰性。細菌培養結果顯示大腸埃希菌對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敏感,故未再調整抗生素,術后繼續給予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聯合奧硝唑靜脈滴注抗感染,總療程14 d,配合局部理療。術后第5天,患者所有癥狀均得到緩解,腰部疼痛消失,下肢活動自如,可以正常行走,出院前復查紅細胞沉降率、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及降鈣素原均在參考范圍,準予出院。術后2個月患者返院復查,陰道殘端愈合好,盆腔空虛,未觸及腫物,無壓痛。腰椎椎體無壓痛及叩擊痛,雙側骶髂關節處無壓痛,雙側直腿抬高試驗陰性,雙側4字征陰性,骨盆分離試驗陰性,骨盆擠壓試驗陰性。復查腰椎MRI顯示正常。
2 討論
PID是女性上生殖道感染引起的一組疾病,包括子宮內膜炎、輸卵管炎、輸卵管卵巢膿腫和盆腔腹膜炎[3]。PID主要的病原體是淋病奈瑟菌和沙眼衣原體[3],生殖道支原體感染也是不可忽視的病因之一[8]。陰道菌群中的微生物包括鏈球菌、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和流感嗜血桿菌與PID的發生也有關[2,9],多為混合感染。有文獻報道因盆腔炎引起脊髓硬膜外膿腫的病例[10],其病原體為陰道加德納菌和羊膜普雷沃氏菌,顯示了與PID相關的厭氧菌群的致病潛力。宮腔化膿性感染是由子宮內膜炎發展而來,是PID的一種特殊而嚴重的表現形式。此患者因宮內節育器嵌頓合并黏膜下肌瘤,使得取環困難,宮腔手術操作時間長,造成子宮內膜損傷后發生子宮內膜炎,又因同時合并子宮黏膜下肌瘤,炎性滲液引流不暢,造成宮腔內化膿性感染。正常女性生殖道有一定的自然防御能力,此患者陰道流血時間長使得生殖道的防御功能和自凈能力降低,容易出現陰道菌群異常并發陰道炎,加之患者重度貧血、身體虛弱,均促進了宮腔化膿性感染的發生。取環術后患者出現高熱、寒戰,體溫最高達41 ℃,已經出現感染性休克,此時細菌入血引發菌血癥。由于縣醫院條件有限,未行血培養檢查,患者病程遷延近2個月,期間多次接受抗菌藥物治療。前來本院就診時體溫已恢復正常,考慮留取血培養意義不大,未再留取血培養化驗。PID治療以抗菌藥物治療為主,正確、規范使用抗菌藥物可使90%以上的PID患者治愈,抗菌藥物治療至少持續14 d,必要時需行手術治療[1]。此患者因院外使用多種抗生素治療且效果欠佳,入院后即給予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聯合奧硝唑靜脈滴注抗感染治療并進行腹腔鏡下子宮切除術及椎間盤探查術。術中見雙側輸卵管充血及炎性滲出小泡,剖視宮腔內為化膿性感染,均符合PID特異性診斷標準[2,11]。術后細菌培養結果顯示大腸埃希菌對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敏感,故未再調整抗生素,給予足療程應用14 d,出院前患者復查各項炎癥指標及血紅細胞沉降率均已恢復正常。
椎間盤炎亦稱化膿性椎間盤炎、椎間隙感染等,指椎間盤間隙和鄰近椎體或軟骨板的感染性病變[4]。其病因主要有以下3種學說[12],血源性細菌感染、無菌性炎癥和人體自身免疫反應。多數學者認為椎間盤炎是由細菌感染的血源性傳播引起的[13-15],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約占50%,革蘭氏陰性桿菌如大腸桿菌感染(大多源自盆腔及泌尿系統)占7%~33%。細菌通常經動脈或靜脈途徑血行感染侵入椎間盤[16]。脊柱椎體-間盤在解剖結構上類似于關節,尤其是椎體前部動脈血管終末支分布豐富,因此血源性感染最先、最常累及椎體前部終板下骨質,炎癥隨后可突破皮質,向韌帶下、椎間盤、鄰近椎體、后柱及椎管侵犯。靜脈途徑為細菌通過無瓣膜的Batson靜脈叢,是泌尿系統及盆腔器官感染脊柱的主要血源擴散途徑。原發性椎間盤炎可發生于頸椎、胸椎、腰椎,因腰椎間盤承受的應力較大,又靠近盆腔,更易受細菌侵擾,故以腰椎更常見[17]。女性盆腔靜脈密集,膀胱、生殖器官、直腸及其周圍具有大量靜脈叢且相互吻合,使得盆腔靜脈感染易于蔓延[18]。女性盆腔淋巴結解剖結構復雜,淋巴結轉移途徑相互交織,當發生局部感染時細菌可沿淋巴管侵入,引起局部淋巴結腫大,進而病變可沿淋巴管的流注方向擴散和轉移[19]。椎間盤炎癥狀及體征缺乏特異性,臨床上容易診斷延遲,文獻報道確診時間從30~90 d不等[20]。椎間盤炎的診斷要點:大部分緩慢起病,腰骶部疼痛,休息平臥無法緩解。實驗室檢查中,紅細胞沉降率和C反應蛋白被廣泛應用于椎間盤炎的初步診斷[21],而白細胞計數的敏感性較低,僅在42.6%的患者中升高[22]。影像學檢查中早期X線檢查常無明顯異常,CT掃描靈敏度為67%,特異度為50%,但其對軟組織的評估有限[23]。MRI是診斷椎體骨髓炎的金標準成像方式,因其靈敏度、特異度和準確性高(96%、92%和94%)而被推薦[24],MRI可在X線、CT檢查陰性或難以確定時早期診斷[25]。PET-CT依據不同細胞的葡萄糖代謝情況差異,炎性細胞葡萄糖代謝旺盛呈“熱點”顯像,診斷脊柱感染的靈敏度可達100%,特異度為87%[26],特別推薦在不能進行MRI時,PET-CT可作為替代診斷成像方式,在鑒別腰椎感染和退行性改變方面具有顯著優勢[27]。椎間盤穿刺取樣微生物培養是抗生素選擇的金標準[28],但其陽性檢出率并不高。對于標本取樣前接受過抗菌治療的患者,微生物培養結果陰性并不能排除感染。本例患者取環術后出現高熱、寒戰及腰骶部疼痛,曾診斷為感染性休克,存在細菌血源性傳播,住院后查紅細胞沉降率沉及C反應蛋白均升高,但白細胞總數正常,僅中性粒細胞計數稍高,考慮與院外應用抗生素有關。PETCT提示腰5骶1椎體上下緣代謝增高伴骨質呈片狀破壞,椎體形態仍然存在,周圍伴發軟組織密度影,考慮感染性病變。手術探查發現陰道后壁與直腸之間有一膿腔,宮腔內組織及直腸前組織細菌鑒定均為大腸埃希菌,但椎間盤組織細菌培養為陰性,考慮與術前應用抗生素有關,仍考慮為宮腔化膿性感染引發椎間盤炎。分析其感染途徑有可能為細菌通過直腸周圍淋巴管向后蔓延,沿子宮骶韌帶到達骶前間隙;也可能為細菌通過損傷的子宮內膜及肌層入血,通過椎旁靜脈叢感染椎體,透過終板發展到椎間隙出現椎體骨質破壞。
查閱國內外相關文獻,目前尚無取環引發宮腔化膿性感染進而引發腰椎間盤炎的報道。國內有學者報道1名女性患者因異位妊娠行陰道后穹隆穿刺術后出現下腹及腰部疼痛,誤診為腰椎結核,病程遷延約3個月,最終確診為腰椎椎間隙大腸埃希菌感染[29]。GENTILE等[5]報道1名女性患者因“子宮Ⅲ度脫垂”行腹腔鏡下Y型網片子宮骶骨固定術,術后1個月患者出現持續性腰骶部僵硬伴腰痛及右下肢疼痛等癥狀,進而癥狀惡化不能站立及行走,最終診斷為腰椎化膿性椎間盤炎。結合本例患者,提示臨床醫生,患者接受盆腔有創操作后出現持續性腰背疼痛,同時伴有紅細胞沉降率、C反應蛋白明顯升高及腰椎MRI的異常改變,應考慮椎間隙感染的可能。
綜上所述,取環手術為臨床常見手術,但因取環致宮腔化膿性感染引發腰椎間盤炎及行走障礙的病例較罕見。此病例提示宮腔操作存在感染風險,除應嚴格無菌操作之外,還需動作輕柔,遇取環困難時,應由有經驗的醫生完成或改行宮腔鏡下取環,不能粗暴實施手術造成損傷、感染、穿孔等不良后果。對于臨床上遇到腰椎間盤炎的女性患者應詳細詢問病史,警惕盆腔炎癥所致的可能,如做到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根除原發病灶,能夠縮短病程,減輕患者痛苦,減少由其導致的嚴重后果。
作者貢獻:楊艷艷進行資料收集整理、撰寫論文并對文章負責;王新玲、李娜、王蓓進行文章的修改;段曉妍負責英文修訂;張蘊霞指導論文撰寫與修改,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并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