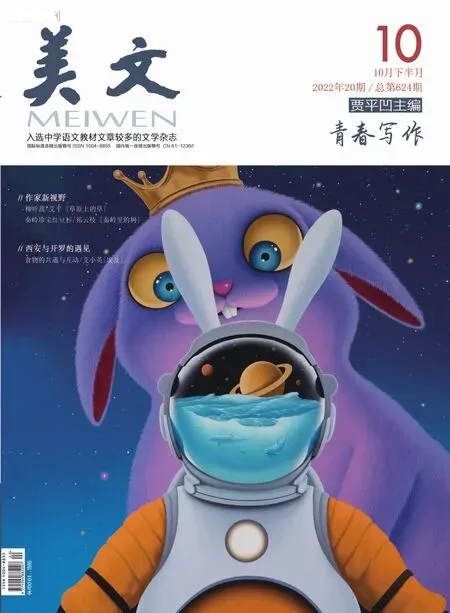爺爺的斗笠碗
崔安寧
在爺爺家碗櫥的最頂層,放著一個斗笠碗,那是爺爺的專用碗,也是他的寶貝。
碗的口徑大,底小,外壁盤著兩條粗細均勻的藍色條紋,看著不過是一個樸實無華的瓷碗。可是聽家里人說,這碗是祖上留下來的老物件兒,也是我們家的傳家寶。逢年過節,我都會看到爺爺把斗笠碗請出來,用毛巾小心翼翼地擦拭。
最初,爺爺的斗笠碗一直鎖在衣柜里。有一天,我剛踏進家門,就聽到父母在房間里激烈地爭吵著,言語中提到了“賣糧還債”這幾個字。“哐啷”一聲響,爺爺的屋內傳來了一陣碎瓷聲,我和父親急忙跑過去一瞧,只見一個粗瓷碗,摔碎在爺爺的腳邊。父親提出給爺爺取一個新碗,可爺爺輕輕地搖了搖手,小心翼翼地從衣柜里請出了斗笠碗,感慨道:“打今兒起,我用這個吧。”
爺爺的斗笠碗雖然瓷質好,但容量太小,盡管所有人都多次勸阻,可爺爺堅持用這個斗笠碗吃飯。
就這樣,爺爺從那天開始,就和斗笠碗綁在了一起。斗笠碗雖然好看,但個頭小,爺爺又借消化不好為由,每頓僅添半碗飯。這個剛上任的斗笠碗,從那天開始就過上了“盛不滿”的生活。有次半夜,我被窗外“咕咚咕咚”的聲音吵醒,借著月光仔細一瞧,爺爺正站在院子里的水缸邊,端著碗喝水。白亮的斗笠碗在月光的照射下,散發著潔白的光芒,那道神圣的白光照亮了外院,也照亮了我的心,我仿佛明白了爺爺換碗的原因。
父親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家里不僅還清了外債,餐桌上也豐富了起來。可突然有一天,我剛放學回家,就聽說爺爺住進了醫院。
原來那天家里來了許多客人,有幾個調皮的孩子見碗好看,便隨意拿來把玩,爺爺見狀,便急急忙忙去討碗。調皮的孩子朝爺爺扮了個鬼臉,緊接著向后一轉,撒腿兒就往外跑。爺爺二話沒說,直接就跟著跑了出去。眾人瞧見后,便連忙去追,可終究是遲了一步,路上早就沒了他們的身影。
不一會兒,這個孩子就哭著跑回來說,爺爺摔倒在村前的老樹林里。眾人聽罷,便著急忙慌地跟著孩子的腳步,向樹林里跑去。當我們在老樹下找到爺爺時,他正舉著斗笠碗趴在那里,盡管他的兩只胳膊試圖撐起整個身軀,卻無法起身。爺爺卻咧著嘴笑道:“好在這個碗沒碎!”他揚起手中的斗笠碗一瞧,碗確實沒碎,但是碗口的位置碰掉了一塊瓷,這下這個碗是真的盛不滿了。父親將碰掉的瓷片收進口袋里,背著爺爺便往回走。
家里人急急忙忙把他送到了醫院。因為骨折,爺爺在醫院里住了幾天。
爺爺出院后,村里的近親紛紛前來探望,他們看到爺爺用殘缺的斗笠碗吃飯后,開始輪番向父親討伐,而父親只是沉默。就這樣,沒幾天的時間,父親苛待爺爺這件事,在村里傳得沸沸揚揚。
使父親惱火的不僅僅是名聲,還有莫名其妙丟失的生意。那段時間,父親在工廠沒日沒夜地趕訂單,眼看就要完工了,客戶卻連夜打電話要求撤單。父親始終想不通原因,他托人打聽后才得知,正是因為父親“不孝”的傳聞。一大早,父親就怒氣沖沖地從廠子里回到家,抓起爺爺的斗笠碗就出了門,等到父親再回來時,兩手空空的,什么也沒有。
午飯時,爺爺看著擺在面前的新碗,一臉疑惑地問:“我原來的碗呢?”我們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誰都不敢說出實情。父親清了清嗓子輕聲說道:“爸,用新碗吧,原來的碗被我扔了!”父親的話音剛落,爺爺雙眼一瞪,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喊:“我跟你說,抓緊給我把碗找回來,否則我就不吃飯了!”說完,爺爺就氣呼呼地回屋了。
我們都認為爺爺僅僅是賭氣而已,直到他連著兩頓沒吃飯,全家人才慌了神。無論派誰去商量爺爺,都得到同樣的回復:見碗吃飯。一向沉穩的父親首先敗下陣來,一大早他就帶上鐵锨出了門。出于好奇,我偷偷地跟在了父親的身后。
只見父親在老屋的東北角下,用鐵锨慢慢地挖著,不一會兒,土里就露出了一個紅匣子。父親拍了拍紅匣子上邊的泥土,輕輕地打開了側邊的鎖扣,里邊放著的正是爺爺的斗笠碗。父親將紅匣子放回屋里,揣著斗笠碗又出了門。
午飯時,父親把斗笠碗交給了爺爺,與之前不同的是,殘缺的斗笠碗已經被父親拿出去鋦好了。爺爺捧著完整的碗哽咽著說:“這個碗其實并不值錢,卻是我娘唯一留下來的東西。這個碗救活了我們家,也救活了我的命。”
爺爺說,當年太祖父早逝,家里上上下下六七口人,全指望太祖母一個人掙錢。可爺爺剛出生那年,正趕上鬧饑荒,太祖母四處挖野菜,撅樹根,掏魚苗。實在沒有收獲,她就端著這個斗笠碗,挨家挨戶借米、借面,這才養活了一大家的人。
我從沒見過太祖母,家里也不曾留有她的照片,但她的故事被爺爺深深地印刻在心里,一如這個斗笠碗,被爺爺小心翼翼地珍藏著。
白駒過隙,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爺爺依舊用著這個斗笠碗。我們也漸漸明白,爺爺懷念的不僅是太祖母,還有往昔的歲月。而這個碗里,也承載著爺爺對我們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