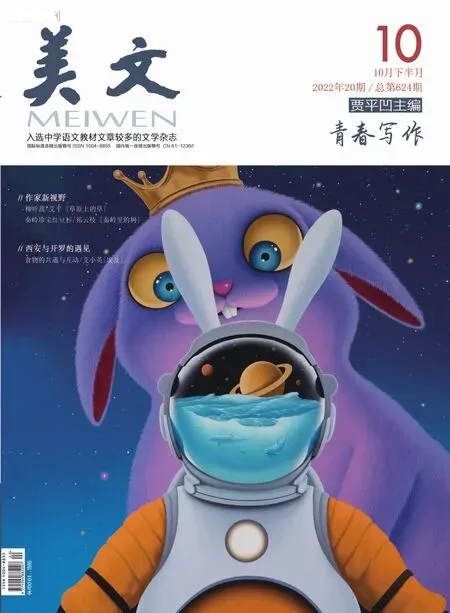另類的手抄本
書民
我讀過一種異樣的書,叫影卷,實際是皮影戲劇本。多為毛筆字手抄,普普通通,沒有作者,沒有書號,更沒有出版社。這種不起眼的書,兒時看過,退休前后又讀過。
初讀影卷,那時農村文化生活極其單調枯燥。罕有文藝節目,小說畫冊也少得可憐。家里就兩本評書《薛禮征東》和《小五義》,簡直能全書背下。沒書可看,就到處借。村里有書人家很少,沒書可借,急得抓耳撓腮。忽然靈光一閃,何不找影卷看?
村里“請”回了影箱子。如同相聲大師侯寶林老先生《請灶王》說的那樣,明明花錢買來,非說是“請”。從此,唱影成了村里文化生活的頭等大事。一遇大事小情,就連著唱上幾宿影。影棚里,打開的影卷放在貼近影窗的案頭上,影匠們不時眼瞄著本子去耍去唱。盡管住當村,有些人卻無師自通,分扮著角色,照樣表演得活靈活現,把下面的觀眾們唱得棚里哭也跟著哭,棚里笑也跟著笑。
那天去二表哥家串門真的發現了影卷。二哥千叮嚀別弄丟,萬囑咐別撕了,我拍得胸脯生疼,才借到手三本。
進了家就迫不及待地打開,清清楚楚記得三本是兩出戲的。一出《青龍劍》,又稱《馬潛龍走國》;一出《四平山》,又稱《薛海征西》。前者兩本順序不挨著,后者偏巧是第一冊。不管怎樣,總算有書可看了。
真正讀起影卷,卻令人大失所望。
手抄本,比16開稍窄,比32開稍長。用毛筆字在毛頭紙上抄寫,牛皮紙做封皮,粗線裝訂而成。里面既沒有插圖,也沒有目錄,封面只標明影卷名稱及第幾冊,再沒有其他文字與圖案。不像京劇評劇劇本,鉛字印刷,彩色封面,有人物介紹和劇情介紹,注明唱段唱腔。影卷沒有,人工抄寫,土里土氣。有否正宗印刷的,曾請教過許多人,都回答沒見過。

我又發現問題了。影卷字雖大,可并不好認。好多的錯白字或象形字,有些字圖省事去寫,有的干脆以圖代替。眼睛,直接畫上去。圈套,前面字畫一〇,后面字跟上一◎。“嘴”字不好寫,干脆以“口”頂上。賊,寫為“則”;鞭,寫為“卞”;小番,寫成“小反”。我想,大概是原作者或抄寫人圖省事、搶速度所致,或是考慮到皮影戲本是鄉土劇目,皮影藝人們大都文化程度不高,這樣寫更趨于大眾化吧?出于這種情況,讀影卷就得琢磨著讀,不能開快車。記得有四句臺詞:大夕南征膽氣豪,腰一秋水丫令刀,風吹庀古山河動,電閃京旗日月高。“夕”應是“將”,長長的“一”應理解為“橫”;“丫”應是“雁”,“令”代替的是“翎”,旌旗的旌被寫成了“京”字。聽看過許多場皮影,臺詞也就記得一些。惟有“庀古”字樣的兩個字,幾個人討論了好長時間。有說“鼙鼓”,戰斗中催征的小鼓;有說“鼉鼓”,更顯氣勢恢弘。
我三個表哥都會唱影,有兩人在外上班,卻常惦著回村唱影。反正有影卷,照本唱就是。有時“影匠”們并沒有照本宣科,而是添枝加葉,聯系實際現編些。有一次,我發現他們唱了好幾分鐘的影,詞竟是影卷里沒有的,一個不孝之子被老員外罵了一通幡然悔改。我問二表哥這是哪部影卷里的,他哈哈一笑,傻兄弟,現攢的,謅書咧戲扯淡影,七老爺子讓加上,我們也是氣不公,教訓教訓那不養老的犢子。
那時鄉間唱影,如同唱戲,也有票友。隨著鑼鼓琴弦家伙式一響,有些人按捺不住,嗓子發癢,擠入影棚吼上幾嗓。村外唱影更不能輕易得罪票友,出于客氣,要多唱幾宿,必須禮讓當地票友特別是當權的。不過,票友對劇情或影卷不熟,容易出錯落下笑柄。
再讀影卷,已是退居二線時。我真心佩服村里的影匠們,能逃過“史無前例”一劫,把影箱子影卷保護下來。可隨著農村落實大包干生產責任制,電影進入農村,電視又緊步后塵進入家庭,圍觀皮影的人群日漸減少。不服勁的影匠們試圖用行動與電影電視較斗一番,村里村外極力攛掇唱皮影。盡管外村唱影一晚上每人只分得一元五角錢,可演員們仍樂此不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還要出去唱。
終于難以應對現代影像的壓倒式沖擊,支撐不住,皮影落敗,村里的影箱子解體。看影卷后面的抄寫時間,多為1982年至1984年,少為1990年,推斷村里影箱子解散時間不會超過九十年代初。影箱子被表哥們買下,喜發大哥拿了他鐘愛一生的皮影主弦“四股子”。影卷是皮影的腳本,自然跟了影箱子。
影箱子在三表哥家,也隨著遷進縣城。
有了影箱子,三表哥就多了寶貝。影箱子里裝著影人影具,每逢炎熱夏季都要晾曬,偶爾趁沒人就自我把玩耍弄一番。可惜我身居外地,很想現場目睹那令人眼饞的影人影具,由于種種原因錯過了機會。即使幾次去他家,年近八十不便行動的三哥只是爽快地捧出一套影卷,有時將復印了的幾枚影人頭茬子送我。問起影箱子,他只說沒在樓上。越是不能大飽眼福的東西,心里越惦著揮之不去。于是,即將“奔六”的我又再度癡癡地捧起了影卷。
與兒時曾經看過的大不相同,大概是原有影卷已經銷毀或缺失的緣故,再見到的影卷尺寸明顯縮水,外皮更加簡單。影卷多用白紙抄寫,也用印過材料的背面紙,16開豎寫對折裝訂。毛筆字抄寫的居多,偶有用鋼筆字抄寫的。從影卷后面附注的抄寫時間看,一個人抄寫一冊,耗時一周左右。有些影卷是多人抄寫。表侄子林告訴,抄寫人除了幾位在外上班的,大多為村上人,有會計,有電工,還有沒上幾年學的皮影愛好者。有些影卷從外借來限時間返還,就得發動大伙兒動手。他們的字難以說好,但對皮影戲的癡愛卻令我汗顏。
我連續讀過《四平山》《長壽山》《小西涼》《五峰會》《青云劍》《破沐陽》《香錦帕》《赫陽山》等影卷,做了一些筆記。《香錦帕》缺了第3冊,《四平山》第6冊中竟有11人的筆跡,字跡有的娟秀,有的粗獷,有的工工整整,有的白字連篇。影卷《長壽山》抄寫比較規范,都是毛筆字,長達十一卷,分別注著頁數,最少50頁,最多61頁。沒注抄寫者名字,大概認為是集體勞動的結晶吧?
影卷的共同特點仍是一律豎寫,“白”和“唱”加黑四框,字與字之間空格,整段唱詞不加其他標點符號,唱段間僅用“∟”號隔分,注明人物出場,如出老旦坐,出××詩,出元帥馬上,等等。前面曾寫到的“鼉鼓”那一段臺詞,在多部影卷中常能看到。只不過首句稍有差別:《四平山》里為大將“南征”膽氣豪,《小西涼》為西征,《長壽山》里則是生來……后三句基本沒有變化。用符號代替文字的少了,錯字白字也少了許多。有的劇本臺詞中竟分明準確地寫著“鼉鼓”兩字。當然,也有寫為“駝古”或“托古”的。再度抄成的影卷,充分證明新一代影匠們文化水平普遍有了提高。

關于影卷的來龍去脈,我也曾查找過一些資料,仍是沒看到原版印刷品,或是高手在民間,口口相傳而來。
影卷臺詞多見7字或10字唱段。也有33、44、55、66、77或33、44、55句 式 遞加遞減。而探子報軍情常用五字句式:報報報軍情,細聽小人報,小人探的真,不敢不來報……
談起影卷,三表哥津津樂道。他說最難唱的唱段當屬《四平山》里的蘭鳳英滾箭。幾頁的長段,夾雜著對唱,有“五字緊”、硬唱、代板唱、贊一三五,等等,不停歇地唱下來,很難很難。他輕晃著頭一口氣說出來,我卻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雖然也喜歡皮影,但各種唱腔已全然生分,再去看那唱段,仍感覺唱段好長,缺乏文采,更出不來像三表哥那樣的盎然興致。
我曾在基層遇到過一個唱過皮影戲的老藝人,席間談起皮影,我特意問過影卷《香錦帕》,他說好像有。我大喜過望,我很想為三表哥補齊缺失的那一冊,可惜時間倉促后來沒有聯系上,算是一種藝術的遺憾吧。
有人來訪,見我在讀影卷,詫異地翻了翻就棄置一旁,一臉的不屑:什么年頭了。我不去解釋,因為一捧起影卷,心中眼前耳畔分明就有那別具一格的影調,那行云流水的琴音,那戰場廝殺的畫面,那花前月下的情景,在動,在響,在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