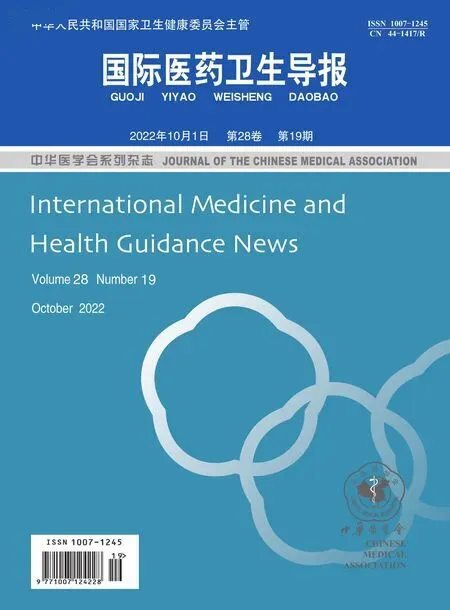某專科醫院723例學生肺結核住院患者診療延誤情況分析
陳文翰 周強 劉玉美 鄭閩莉 卓文基 余美玲 劉志輝廣州市胸科醫院,廣州 50095;廣東省結核病控制中心,廣州 50630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2019年全球5~<15歲、15~24歲人群中新發結核病患者數分別約占全人口新發結核病患者數的6%和16%,其中分別約有42%和26%的病例尚未被發現[1]。5~<15歲人群多數為中小學生,其免疫系統發育尚不成熟,15~24歲人群大部分亦為在校學生,且處在社交活動最為活躍的年齡階段,為結核病流行的高危人群[2-3];學校作為其主要生活場所,具有聚集生活、接觸密切的特點,各類學校結核病暴發流行的情況屢見不鮮[4-6]。我國結核病專報網的數據報道:2008—2018年11年間共報告肺結核病例10 295 212例,其中學生為487 633例,占比4.74%;2016年6~<20歲和20~24歲結核患者約12.5萬例,但職業欄中為“學生”者僅為3.4萬例[7]。2020年WHO全球結核病報告則顯示2019年我國5~<15歲、15~24歲人群中結核病例發現率分別約為28.57%和91.18%[1]。我國這些數據充分表明我國學校結核病流行疫情可能遠遠被低估,加強學校結核病控制刻不容緩,已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目前已有明確的工作技術規范出臺[8]。然而,在學校結核流行控制中,人們需要面對的遠遠不僅是流行率高、發現率低的難題,正如其他人群結核病患者存在就診延誤和診斷延誤一樣[9-12],學生人群結核病患者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作為結核病的主要傳染源其延誤時間長短重要影響學校結核病流行與控制,但目前相關研究報道不多。筆者對2019—2021年在廣州市胸科醫院住院的723例學生肺結核患者的就診延誤和診斷延誤情況進行了分析,現報道如下。
對象與方法
1、研究對象
2019—2021年廣州市胸科醫院收治入院的大、中、小學肺結核患者723例,其中男386例、女337例,平均年齡17歲(6~30歲);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本科生、研究生患者分別為118、106、231、256、12例。肺結核診斷依照《中華人民共各國衛生行業標準肺結核診斷WS288-2017》進行。
2、病例收集與信息查尋
在“醫院統計病案系統”內以“出院時間”“職業”“主要診斷國際疾病分類編碼”(A15.000-A15.309、A16.000-A 16.210)獲取2019—2021年3年間入住廣州市胸科醫院的學生肺結核病例;從“電子病歷系統V6.0”調取患者住院病歷、病程記錄、影像資料,獲取患者的癥狀出現時間、初診時間、廣州市胸科醫院入院時間、確診時間、確診病名、病原學依據、影像特征等相關信息資料。
3、相關定義
主要概念包括:⑴因癥就診,指患者因肺結核可疑癥狀直接到結核病定點醫療機構就診;⑵因癥推薦,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將肺結核可疑癥狀者推薦到結核病定點醫療機構就診;⑶轉診,指患者出現肺結核可疑癥狀后到醫療衛生機構(包括結核病定點醫療機構非結核科和非結核定點醫療機構),經胸部X線或痰菌檢查等診斷為肺結核或疑似肺結核后,醫囑患者到結核病定點醫療機構結核科就診;⑷就診延誤,目前尚無統一標準,根據WHO建議結核病可疑癥狀出現2周則應進行結核病診斷檢查的建議,本文指從結核可疑癥狀始發日至首次到醫療機構就診日(就診時間)≥15 d者;⑸診斷延誤,與就診延誤類同,目前尚無確切定義,本文指患者首次到醫療機構就診日至結核病確診日(診斷時間)≥15 d者[7,12]。
4、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 20.0軟件包進行統計學分析,應用百分構成描述就診延誤和診斷延誤率,應用χ2檢驗比較各類別人群間率的統計學差異。各類別人群延誤平均時間(d),正態分布資料計算其算術均數,各類人群間的均數比較采用t檢驗;非正態分布資料計算其中位數,各類人群間的中位數比較采用Mann-WhitneyU檢驗(兩組間比較)和Kruskal-Wallis秩和檢驗(多組間比較)。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就診延誤和診斷延誤總體情況
723例住院肺結核學生患者就診時間、診斷時間分別為0~92 d、1~95 d,時間資料均為非正態性分布,其時間中位數分別為15 d和19 d。就診無延誤與有延誤者分別為317例、406例,就診延誤率為56.16%;診斷無延誤與有延誤者分別為220例、503例,診斷延誤率為69.57%。
2、男女學生間兩種延誤情況比較
男女性別間就診延誤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748,P=0.387),診斷延誤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0.029,P=0.002)。經Mann-WhitneyU檢驗,兩類人群間就診延誤與診斷延誤中位數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U=18 694、27 096,P=0.946、0.295。見表1。
3、不同學生類別間兩種延誤情況比較
將住院學生患者分為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本科生、研究生4類,各類學生間就診延誤率和診斷延誤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7.396,P=0.116;χ2=2.814,P=0.589)。經Kruskal-Wallis秩和檢驗,就診延誤中位數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3.000,P<0.001),診斷延誤中位數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4.278,P=0.370)。見表1。
4、不同病例發現方式兩種延誤情況比較
如表1所示,4種病例發現方式間就診延誤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3.288,P<0.001),診斷延誤率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3.879,P=0.275)。經Kruskal-Wallis秩和檢驗,兩類人群間就診延誤與診斷延誤中位數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0.950,P=0.810;χ2=2.585,P=0.460)。
5、癥狀始發月份間兩種延誤情況比較
如表1所示,依據學生學習、生活特點按學期與假期分為1—2月、3—6月、7—8月和9—12月4種時間類別,其診斷延誤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8.187,P<0.001),就診延誤 率 差 異 無 統 計 學 意 義(χ2=2.725,P=0.436)。經Kruskal-Wallis秩和檢驗,就診延誤和診斷延誤中位數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12.750,P=0.005;χ2=15.987,P=0.001)。

表1 723例學生肺結核患者依性別、學生類別、發現方式和癥狀始發月份不同的分類人群診療延誤情況
討 論
Campbell等[13]的研究顯示:在結核病接觸者中,皮膚結核菌素試驗(TST)≥5 mm者中,全年齡組和小于18歲年齡組人群中結核病的發生率分別為2.8%和2.6%,TST≥10 mm者中則分別為6.6%和7.2%,后者感染結核分枝桿菌后結核病發生率為前者的近3倍。小于18歲年齡組人群多為中小學生,他們處于人生成長的階段,機體免疫系統發育多數尚未成熟,免疫功能尚不穩定,加之學習壓力較大,一旦感染結核分枝桿菌較易進展為結核病,是結核病發生的高危人群。大學生雖然已經成年,但處于社交活躍期,所處環境變化較大,疾病防范和自我保護意識還很薄弱,而且對結核病知信行狀況不良,容易引起結核病流行,高校結核病健康促進和預防控制措施亟待加強[14]。從另一層面看,學校人口密集,教室與宿舍空間相對狹小,校園內一旦出現結核病例,極易引起學校結核病暴發流行,而嚴重影響師生身心健康、擾亂學校正常教學秩序并造成重大社會影響。近年來常有相關研究報道,未被發現病例或病例發現延遲則為學校結核病流行的最大傳染源,同時也嚴重影響患者自身的身體健康[15-17]。如何提高病例發現總體水平和及時水平是擺在人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就提高病例及時發現水平而言,我們認為首先必須理清就診延誤、診斷延誤的重要影響因素。本研究結果提示:病例發現方式是影響就診延誤發生率的重要因素。我國多年來著力推行的因癥就診的結核病例被動發現方式卻有最高的就診延誤發生率,健康體檢則為就診延誤發生率最低的病例發現方式;學生類別與癥狀始發時間嚴重影響就診延誤時間,延誤時間與學生年齡段呈反向水平,放假期間延誤時間長于上學期間;診斷延誤發生率女生明顯高于男生、上學高于假期,診斷延誤時間在兩個學期和兩個假期間也存在顯著性差異。在實踐中,人們發現被動方式發現率低且會造成大量診療延誤[9-12],和本研究結果一致。因此,加強結核病例主動發現為必由之路。目前人們對此進行了諸多探索,也取得了不少令人欣慰的成果[18-22]。我國則在《中國結核病預防控制工作技術規范(2020版)》(國衛辦疾控函[2020]279號)[8]中將結核病例發現方式歸結為因癥就診、主動篩查和健康體檢,將病例主動發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就診延誤時間方面看,由低年級到高年級學生表現出不斷延長,可能與長期遠離家庭照護有關,放假期間長于上學期間,則可能與學生生活活動安排有關,目前同類分析報道不多,有待深入探討。至于診斷延誤發生率和診斷延誤時間所表現出的性別、癥狀始發時間差異,個中原因我們目前不得而知,有待進一步進行大樣本量分析。
總之,為消除上述因素的重要影響,學校、家庭、社區必須聯合行動:一是在學校方面將日常晨檢、因病缺勤追蹤、學生入學體檢、畢業生體檢等學校結核病疫情監測措施必須落實到位;二是在社會層面促進在學生中進行肺結核病例密切接觸者篩查的工作力度,力爭早期發現潛伏感染者和活動性肺結核患者;三是在學校、家庭、社區全方位加強結核病健康促進工作,努力提高學生、教師、家長的結核病知信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