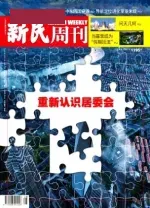日本華人社會的“定海神針”
進入9月,日本相繼舉辦一些中日邦交正常化慶祝活動。這些活動,有的是日方主辦,但多數是在日華僑團體主辦。當下,中日關系微妙,盡管主辦方多是民間,理應不受官方關系影響,但從實際情況看,氣氛還是不如想象中的熱烈。
盡管如此,在日華人社會對紀念活動十分投入,最近見諸報章的有文藝演出、書畫展覽、學術講座等。華僑華人高度關注兩國關系,這是因為這個群體得益于中日關系的發展,而中日關系走向,也系關在日華人社會存續安危。
這半個世紀,中日關系從細小到宏大,在日華人社會受益良多。這50年來,在日華人社會出現若干變化,值得欣慰。
首先是華人社會擴大。邦交正常化時,在日華人不足10萬。而今天在日華僑有70余萬,如加上華人則“華人社會”人口超過100萬。這個龐大的群體,為日本社會以及中日兩國交流做出了他們的貢獻。此外,在這50年間,在日華人職業構成從傳統的餐飲業向社會各領域擴大,廣泛分布在商貿、科研、教育等各領域,成為日本社會的組成部分。
另外華人社團的發展值得注目。有人統計,在日華人社會中有近千個華人社團。這些社團內容林林總總,其中既有職業團體,也有興趣團體或聯誼團體。這種現象折射出在日華人社會的活躍。

劉迪
在日本社會,“中日友好”遇到犬儒主義態度。
此外,進入本世紀后,在日華文教育出現井噴式發展。在日本,隨著華人社會擴大,既有的正式僑校無法滿足華人子弟的教育需求,于是日本各地出現了眾多周末中文校。這類學校雖然微小,但數量眾多,彌補了正規僑校不足的缺憾。這類小微僑校今后的發展,也是日本華人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
今天的中日關系非常宏大,但卻仍不夠穩定。如何維系、促進這個社會的健全與發展,既需要中日兩國關系的穩定,也需要全體在日華人社會的努力。
日前,筆者參加某僑團活動,偶遇一華人評論家。他對我說,今天的在日華人社會變得“更加封閉”,這讓我感到意外。
今天在日本,華人社會存在兩種“封閉”。一種是“生活圈封閉”。以東京為例,許多甫抵東京的中國學生,甚至不用日語仍可用微信支付,在這里租房、購買手機、找補習學校考大學乃至讀研究生都非常方便。從這個角度看,在日華人社會的確存在一個封閉的“舒適圈”。
但前述評論家想指出的是另外一種封閉,即“社交封閉”。即從社團或社會角度看,華人社會與日本社會漸行漸遠,溝通與交流不足。這位評論家說,以往僑團的大型活動,許多日本高層政要積極出席,日本主流媒體均有密切跟蹤,但今天我們慶祝兩國邦交正常化,常常出現的都是若干老面孔,日本主流社會對參與這類活動喪失了興趣。
回想上世紀,盡管兩國關系也有低落時刻,但民間交流卻很頻繁,隔閡較少。那個時代,中國留學生常邀日本居民在自己宿舍辦“餃子大會”,一起包餃子,喝紹興酒,唱兩國歌曲。那時,許多日本人拿出自己零花錢,來幫助中國失學兒童。但今天,時代不一樣了,兩個社會如何找到共同點?
最近日本華僑社會的“50周年慶典”熱背后,不乏隱憂。盡管華人團體不遺余力為兩國友好奔走,但在日本社會,“中日友好”遇到犬儒主義態度。我相信這種態度不代表日本民眾最根本的意愿,但眼下日本社會對兩國關系的某些懷疑,也讓在日華人社會感到某種艱難。
不論如何,筆者以為,5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構筑了一個讓兩國維系和平的制度。這個制度才是維系在日華僑社會發展、兩國關系穩定的定海神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