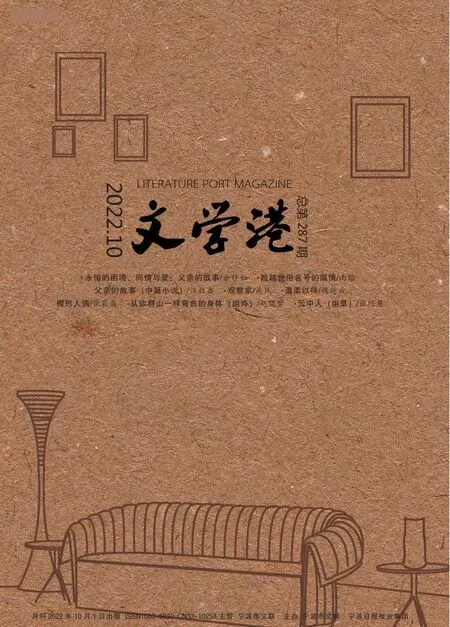創作談:父親是什么
□汪毅鑫
終于寫完關于父親的故事,感慨頗多。
寫作的起緣在于,某一天,我的堂妹突然告訴我,說:“你爸又離婚了。”我轉而告訴了母親,母親一時很難相信,就給四姑打了電話,電話那頭傳來嘆氣聲,母親便知道父親的的確確做了件傻事。“這么大的人了,好好過不好嗎?孩子是最可憐的……”母親在電話里說道。我感到十分疑惑,即使現在,她早已建立了新的家庭,但還是會對父親的事表現出親人一般的關心。母親說到我的弟弟——父親后來的孩子時——眼眶猛然變紅了。我確信,母親不是為了某種“義務”去關心的,她確確實實在同情這個人,哪怕這個人曾經給她帶來了很深的傷害。
這讓我對父親產生了無比的好奇。自我初中起,父親便離開了這個家,而童年的記憶我成功保存下來的又少之又少,之前在許多場合中,我被問道:“你父親是怎樣一個人?”我想了想,難以捕捉出一個確切的形象。我問過母親這個問題,經她之口,我得出了父親是一個好賭、不負責、愛面子但長得確實帥氣的人這一結論。但光依靠這些單薄的標簽,我還是無法理解他,至少在人生的岔路口他所做出的那些選擇,是出于什么目的?之后是否后悔?如果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父親對我而言,仍幾乎是等于不存在的。
可是為什么父親的存在就如此重要呢?或者說,為什么父親一定“必須”存在呢?
在我的觀念里,繁育后代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一個孩子,被父親和母親帶到這個世上,從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未來的路已經被篩選了(當然不止一條),父母對孩子能給予的影響多停留在表面,他們能左右的事情其實很少,從這個角度來說,生孩子這件事,跟孩子這個個體本身,并沒有那么強烈的聯結。總的來說,我質疑生育關系中孩子與父母之間那種在習俗中不證自明的、但實際上又脆弱無比的綁定感。

因此,這么久以來,我并不覺得了解父親是一件必須的事情,直到母親給四姑打的那個電話,我回想起,曾有人這樣說父親:“一手好牌打得稀爛。”也許自己也到了要談婚論嫁的年紀,不免想到,當年父親也是處在我這個階段,然后跟母親展開了新的故事線。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我站在此處向后看,父親一生的經歷投來星星點點的影子。大家口中所謂的“一手好牌”,無非是指父親慈愛,兄弟姐妹關系和睦,妻子賢惠持家,孩子聰明聽話。但父親一樣一樣地把這些珍貴的東西親手葬送了。
需要說明一點的是,我并不想單純地了解父親做了哪些“稀爛”的事,僅僅是故事本身的話,我想虛構更能滿足寫作者以及讀者的閱讀期待。我想展現的,是父親做出這一切的原因。在動筆之前,我其實對父親的想法知之甚少,在搜集資料,訪問各種人(包括他本人)后,我獲得了一大把各種事件的概述。一開始我準備先還原出父親主要的人生軌跡,然后在書寫的過程中,我愈發地意識到這么一點:父親生活中的悲劇,都跟他的性格有至關重要的聯系,所謂“性格悲劇”大概就是如此吧。
因此,整個寫作過程就很奇妙地演化成了我對父親性格特點的追溯之旅。為此,我特意從父親的童年開始,因為無論在誰的記述中,奶奶與父親的關系都十分重要。她從小最疼父親,而父親本也是懂事聽話的小男孩,在他正值青春叛逆期的時候,奶奶因病去世,這對父親來說無異于晴天霹靂,加之爺爺那時候忙于工作,沒時間照看家里,父親便走上了自我放縱的道路。一個人在青年時期養成的脾氣和習性,就這么在生命中落下了根。父親不管是剛與母親談戀愛時,還是撫養我時,抑或是現在失去一切時,我還是能看見父親性格中沾染“江湖氣”的那一部分。“江湖氣”讓他年輕的時候能呼朋喚友,名震一方,但因敢打敢混而獲得好處這一回報模式,在成熟的社會機制中是會失去效力的。父親似乎一直無法明白這一點,對于曾經的輝煌,他雖然表面上不再說起,但內心深處,一直還是希望回到那時候,希望找回自己的話語權。
除了“江湖氣”,父親性格中當然還有更為復雜的成分。跟父親交好的人,往往在對他的一生境遇表示感慨之后,會加上這么一句:“但你父親,本性是好的。”我對此愿意相信,因為即便是現在,當父親想起奶奶和爺爺時,還是會動情地哭出來,其中有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也有自己一生唏噓、愧對父母的懺悔。當一個人,把他內心中最柔軟的那一部分展示出來時,我想我并沒有什么資格去審判他,此時,我終于能體會母親的心情,正如我在作品中寫的那樣:“人與人之間超越世俗名號的溫情,以及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最本質的慈悲。”是的,當再次面對父親時,我意識到,眼前的這個人,不再僅僅是我在血緣上、法律上的父親,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擁有完整獨立的生命體驗的人。
關于作品本身,雖名為 《父親的故事》,但全篇并沒有只從父親的角度出發。我對母親的著墨也比較多,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來母親是許多關鍵劇情的提供者,我并沒有懷疑母親對其添油加醋,而是每個人的敘述難免會代表著人物背后的立場,為了避免讓“母親的敘述”變成一種“正確”的敘述,我認為有必要把作為敘述者的母親形象描述出來,這樣讀者便能建立對此人的理解,以此為基礎,去產生自己的判斷;二來我認為,和父親一生關系最復雜也最微妙的人是母親,如前面第一章所述,母親從未對父親“真正地”放下過,因此如要講述父親的故事,母親是必然繞不開的環節。
作品中還有許多以“我”的視角“抽離出來”的描述,諸如第一章中:“我當時并不明白,后來慢慢地發現,人是很依賴解釋的動物,不管歸因恰不恰當,這總會帶來安心,而只要良心被說服過去,人便能與自己的千種猙獰和諧相處。”還有第五章中“多年之后我才發現,其實我對父親追求胡阿姨這件事本身缺乏道德層面的批判,我并不覺得這是什么萬惡不赦的罪孽。”以及同一章中“后來的我常常感慨,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這片土地上,無數奔波忙碌、追逐名利的風景,都跟塵土散去一般虛無,這總讓我感到無比的悲涼,可是辛苦扎根在土地之上的人,他們之間超越世俗名號的溫情,以及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最本質的慈悲,又使我忍不住地落下淚來。”這些描述我個人認為是必要的。因為如前所述,我的意圖并非僅僅是呈現一個故事,我想走近一個人的內心,需要讀者通過事情的來龍去脈、臺前幕后來“理解”一個人,我希望這里的“理解”也不僅僅是針對“一個”人,而是通過作為“人”的個體在家庭以及社會中的關系來理解人的“生命狀態”,我當然明白,要使作品達到這樣的高度是非常困難的。但我想,作為寫作者,至少我自己應該從中汲取一些“抽離出來”的感悟,我難以奢望這些感悟與讀者產生共鳴,但必須面對自己真實的想法,因為在寫作過程中,我最看重的便是“真誠”的品質。
最后不得不說,完成這部作品最大的收獲,便是其記載的故事本身。真實的故事往往具有更非凡的力量,與自己有關的更是如此。長久以來,我一直容易陷入一種對人類發展歷程的虛無感——個體生命如果完全是獨立的,那么從群體的熵值來說,把某一個個體割裂出去的影響幾乎為零。簡單來說,就是無法回答“我從哪來?”更無法回答“我為何存在?”對于后者,我至今沒有答案,但是對于前者,我在追尋家庭的歷史過程中,漸漸地得到自己的解答:從父輩來。這個回答看似簡單,但其實對我寓意深重。之前我身上怪異的脾氣、一些自然產生的想法、對某些品質的追求等,本不知這些組成我的東西從何而來,但在更多地了解了父親和母親后,我明白了,許多東西就流淌在血液里,它們以我不可抗拒的方式傳遞給了我,而將來的某一天,又會把我血液里保存的一部分,獻給我的后代,從代際,到家族,再到人類群體,我看到了一種堅定的、實質的聯系。
當然,由于作品完成的時間和筆者的自身水平有限,難免有許多還未能盡善盡美的地方,敬請讀者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