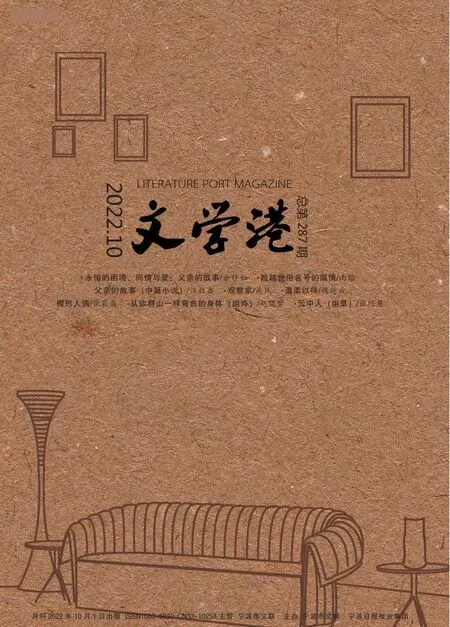溫柔以待
□侯德云
在我出生以前的很多年,它已經坐在那里等我了。等我爹從山東地界踉蹌而來,等我爹經人撮合與我媽結成一段姻緣,等我的兄長們先我而生,再等我生于斯、長于斯。等我磕磕絆絆長到十八歲,旋即用盡渾身力氣,掙脫它的懷抱,義無反顧,遠走他鄉。
它叫卡屯,一個芝麻大的村莊。偏踞遼東半島東南端,守望黃海之波涌。往東北,去丹東市,二百二十公里;往西南,去大連市,一百公里;往西北,去沈陽市,三百三十公里。
卡屯隸屬皮鎮管轄。某日把玩 《皮鎮志》,翻開首頁便愣住了。首頁是皮鎮地圖。這地圖讓我心里咯噔一下,原來讀高中之前,自己的生活空間,竟是那般狹小。屈指算來,只涉足過皮鎮和周邊的五個居民組。居民組,早年叫生產小隊,也就是屯。從地圖上看到:由卡屯往北,我到過前哨、修屯、唐屯;往南,到過涼水灣;往西,到過北姜子;往東是海域。周邊海域,二島二砣四礁,我去過螞蟻島、牛眼砣,以及平礁和老母豬礁。有一回光腳上了平礁,剛走幾步,腳底全是血口子。平島、韭菜砣、大礁、二礁,都不曾光顧。我喜我怒,我哀我樂,我憂我悲,都只在這區區彈丸之地,說來叫人好生慚愧。
記憶里,卡屯只有數十戶人家,二百左右人丁。
卡屯現已不存。城市化的嘴巴幾乎將它全部吃光,只余一點殘渣黏在嘴角,不定什么時候,會被一張紙巾輕輕抹掉。
二百左右人丁也漸漸散去。一些安眠在山坡,與草木相伴,聽風聲雨聲鳥聲蟲聲。一些住進樓房,懷揣一腔發財夢,整日爭斤論兩,忙忙叨叨,儼然活出城里人模樣。后者有個頗為莊嚴的稱呼,叫失地農民。
這么多年,在我的鄉村記憶里,有父母,有兄弟,有童年,有少年,有山有海,有春的繁花,有秋的冷月,有夏夜蛙鳴,有冬日寒霜,卻偏偏漏掉了一些別樣的靈魂。他們是一些已經冷卻或即將冷卻的名字。他們都有過悲摧的、或不那么悲催的人生經歷和情感經歷。他們不流芳,也不遺臭。
且讓我掬起這一捧淺薄文字,重返舊日時光,對這些名字,溫柔以待。
尖把梨
尖把梨,不是梨,是綽號。此君姓馬,叫馬武藝。
卡屯流行過一段順口溜:“馬武藝他爸,得了高血壓,脖子粗,卵子大,一出門就爆炸。”
其實誰都說不清楚,馬武藝他爸,到底得沒得高血壓。脖子粗不假,因為老馬是廚師,在皮鎮一個什么單位的食堂里掌勺,吃得好不好不知道,至少是吃得飽。換成兩氏旁人,想粗也粗不成。
順口溜的最后一句,那什么大不大,同樣誰都說不清楚。老馬是個瘸子。好端端的平地,讓他走成山高路陡,兩瓣屁股之間,關系很不協調。順口溜沒拿這事開涮,挺仗義。
當年老馬找對象,媒婆許二仙設計讓女方到食堂去見他。老馬當年是小馬。小馬倚著鍋臺炒菜,天熱,只穿一件紅背心,姿態頗為瀟灑。姿態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背心又緊,半隱半現的兩扇胸大肌,鼓楞楞地博人眼球。上臂的三角肌、肱二頭肌,有節奏地鼓縮,讓人眼亂。從整體上說,瞅著不亞于為國爭光的運動健將。姑娘被上半身深深吸引,心都要化掉,眼仁不舍得往下瞅,沒看出小馬腿腳有毛病。姑娘對人滿意,對彩禮更滿意。既然滿意,那就啥也不說了,趕緊辦喜事。婚禮那天接新娘,小馬騎一頭騾子,無論如何不下地。迎親隊伍到了卡屯,小馬不能不下地,剛一下地,就露了腿腳上的別扭。新娘一瞅,我的天,頓時一陣嚎啕。可是后悔已經來不及。小馬是廚師,特別擅長將生米做成熟飯,且臂力過人,他連鍋臺都能扳倒,還扳不倒一個丫頭片子么?
從那天起,直到死,尖把梨他媽都沒搭理過許二仙,別說見面打招呼,連正眼瞧她一回都沒有。許二仙卻因這件偉績豐功,名聲鵲起,一躍成為卡屯公認的首席媒婆。跟尖把梨他媽正好相反,馬武藝他爸一見許二仙就眉開眼笑,就差摟住親一口。
有那么一段時間,屯中的小玩鬧,整天把那段順口溜掛在嘴上。聽者抿嘴,笑意漣漣。尖把梨從來不笑。他一聽就火,撒腿就追,追上就打。有時會把人打得鼻青臉腫。
屯中跟尖把梨年齡相仿的小玩鬧,沒被他打過的,極少。我是那極少數中的一個。
奇怪的是,不少小玩鬧一見尖把梨,就陡然唱得沖動。遠遠地唱,害得尖把梨氣喘吁吁去追,有時追得上,有時追不上。他再豪橫,也不至于追到誰誰家里去打人。
但離得太近時,沒人敢唱。尖把梨冷不丁一絆子,就能把人撂倒。
尖把梨是不是真的練過武,我不知道。不過有一點我敢肯定,他剛走出小學校門,就甩了卡屯的小玩鬧。他瞧不起他們,甚至可以說,他鄙視他們。他到皮鎮闖天下。
當時的形勢是這樣的,用古詞來說,倘若卡屯是“江湖之遠”,那么皮鎮就是(或接近于)“廟堂之高”。我們在地上,在山水間;他們在天上,在祥云里。不說別的,一個城鎮戶口,就讓卡屯的兄弟姐妹喘不上氣,一輩子深深低下自卑的頭顱。那時不像現在。那時城鎮戶口的好處,你得把手指頭和腳趾頭加在一起才能掰扯出來,或者說,加在一起你也未必能掰扯出來。而當時的我們,包括我們的父母,誰都看得見,今天的小玩鬧,就是明天的農民。今日回想,就是這么個情況,我是其中唯一的另類。
一個小學畢業生,敢把自己的未來,直接拴系到皮鎮身上,這愿望本身,就讓我好生欽佩。當年欽佩,現在依然。這叫胸有大志。遺憾的是,尖把梨的手段,似乎不太正當。他整日在皮鎮打架,有時會被那些天上的孩子打得鼻青臉腫。
有那么幾年,尖把梨打人或被打的消息,在卡屯連一點點新聞性都沒有。要是他長時間沒打人或沒被打,才會引起村民的警覺,咦,這癟犢子走人道了?
此外還有關于尖把梨“進去”的消息,在卡屯也沒多少新聞性。
讀小學時,尖把梨就進去過一回。他用鉛筆,在一個大人物的宣傳畫上,打了一個×。不料剛剛×完,就被人舉報給校長。全校為之震驚,師生無比激憤,一齊動手,將他五花大綁,直接送進了監獄。進去不到半年,那個大人物突然不是大人物了,于是有關方面立馬把他給放了。放是悄默聲地放,一點動靜都沒有。
后來一次一次又一次進去,都是因為打架。
有一年搞“嚴打”,尖把梨又進去了。這回時間長。進去時,我剛讀高中,等他出來,我已大學畢業。
此后尖把梨的種種行狀,對我而言,都是耳聞。我從未見過成年的尖把梨。
尖把梨出來之后的第二年夏天,我回老家,在村口遇見表哥。表哥再三邀請我去他家里坐坐。按說我應該先回家看望父母才對,但表哥執拗,只好隨他。好在去他家,不過多走幾步路。
在表哥家客廳,我坐掉兩個多小時。
坐下沒幾分鐘,我就覺察到,表哥不是跟我敘舊,相反,是滅我的威風。說他蓄謀已久,伺機報復,可能性不大。他很可能是在遇見我的第一瞬間,陡生奇想,摟草打兔子,隨手給我一家伙。
幾年前,我曾毫不客氣,給了表哥一家伙。不是主觀故意,是客觀事實。我和表哥同年參加高考。我很努力,他也很努力。結果我努上去了,他卻努下去了。表兄弟倆人的一上一下,在屯中,引來許多異樣的目光,以及異樣的嘰嘰喳喳。我能想象得出,相當長時間內,表哥見誰都抬不起頭。
跨進表哥家客廳的那一刻,我并不知道,他在卡屯的地位已經發生逆轉。他羽化成蝶,變為卡屯為數不多的驕子。我說的是,那種人人注目的經濟驕子。
表哥給我倒一杯茶,隨后笑瞇瞇地、詳細地詢問了我的經濟收入,以及我在瓦城的住房情況,而工作情況、人際關系情況、婚姻情況、婚外戀情況、暗戀情況、一夜情情況,等等,他一概不問。那時候我和表哥,都新婚不久。表嫂我見過,該表嫂的面容、膚色、體魄、臀圍、腰圍、胸圍等各項指標,均高于賤內,是以在婚姻的擂臺上,我已先敗表哥一招。住房,我老老實實承認,是表哥的大。這就敗了兩招。收入一項,表哥聽完我的匯報,很大度地將手一揮說,差不多,咱倆差不多。
表哥在皮鎮開一家熟食店,豬頭豬尾豬雜碎,能賣的都賣,生意興隆,其利潤,完全可以碾壓我的微薄工資。他說差不多,是故意放我一馬,不想讓我輸得太慘。
表哥的手揮得很有特色,不是一揮而就,而是就勢在房間里滑翔一周。房間四壁,都靠墻立著,或坐著,新錚錚的,高矮不一的木質家具。我的眼神不由自主被他的手勢牽引,在那些木質家具上,也高高矮矮地滑翔一周。
表哥說:“都是紅松的。”
我說:“噢。”
說完馬上知道,自己又輸一招。
隨后不知為什么,表哥話題轉移,不用過渡,一下跳到尖把梨身上。曾經,在村民眼中,我跟尖把梨,是卡屯兩個極端。我算人才,他是人渣。表哥在我面前談他,細品,還是滅我威風。
表哥話里的意思是,人渣出息成人杰,堪稱皮鎮翹楚。
表哥說:“尖把梨把皮鎮漁港給霸了,小販賣魚賣蝦,都得給他提成。還有港中的漁船,他說把魚蝦賣誰,就得賣誰。誰敢不聽,刀棍伺候。”
表哥頓了一頓,說:“尖把梨,錢多得包里裝不下。”
說這話同時,表哥抬右手,拇指、中指、食指,三個手指肚聚在一起,蹭了幾蹭。
我瞥一眼表哥的手指頭,心想,尖把梨那廝是不是香港電視劇看多了?
他的兩個女秘書,叫大花和二花,一個胸大,一個腚大,街上一走,香味飄出五米。表哥繼續說,尖把梨走哪把她倆帶哪,晚上一張床上睡。
表哥咽了口唾沫,再次抬右手,豎起兩根手指頭,盯著我說:“兩個呀,嘖嘖。”
我暗中撇嘴,尖把梨這么整,早晚還得進去,這廝指定是腦子壞了。
轉過年再回老家,跟大哥一起捏酒盅,耳熱酒酣,大哥突然說一句:“尖把梨死了。”
我一愣:“怎么死的?”
大哥說:“到望海樓舞廳跳舞,讓舞廳經理一槍打死了。”
怎么聽著真就是香港電視劇?我瞪大眼睛,瞅大哥。
是這樣,大哥補充說,尖把梨經常酒后到舞廳鬧事,把那經理氣得肝疼。經理發狠,費了老大力氣,還有好多錢,七拐八拐,從黑道弄到一把手槍,找人傳話給尖把梨,再來鬧事,有他好看。偏偏尖把梨不信邪,扛著一把大刀就去了。
于是,大哥說,砰!
說這話時,大哥右臂向前屈伸,拇指食指張開,其余三指收攏,做手槍狀。
后來呢?我問。
尖把梨的尸體被三個親兄弟給凍在冰柜里了。大哥說,三兄弟到鎮里縣里市里,到處鬧賠償。
我說,噢。
尖把梨的故事到此結束。翹楚不是翹楚,還是人渣。故事的尾聲是,三年后,大哥告訴我,三兄弟平分十萬賠償金,樂得屁顛屁顛。
從三兄弟屁顛屁顛到現在,不知不覺,又逝去二十多年。不知當年卡屯的那些小玩鬧,是不是還有人會偶爾想起一個名字:馬武藝。
牛 眼
鐘家老三,綽號牛眼。眼珠子大,還圓,不是瞪眼勝似瞪眼,不是牛眼近乎牛眼,于是得名。
牛眼家有故事。先說牛眼他爹。
卡屯三大窮,牛眼家排第一,其余兩家,一個是我家,一個是尖把梨家。我家窮,緣于瞎折騰。爹的老家,在山東掖縣。爹有一年不知受了誰的蠱惑,拉家帶口奔山東。動身前,賣房子,賣家具,都賤賣。在掖縣生活沒幾年,媽又開始折騰。媽跟奶奶處不好,動輒一人氣哄哄上路,往來時的方向暴走。爹怕出事,咬牙跺腳,舉家遷回卡屯。再次賣房子賣家具,都賤賣。如此這般,不窮才怪。尖把梨家窮,是他爹不著調,好賭。只有牛眼家,窮得沒有來由。父母和姐弟六人胳膊腿齊全,無不良嗜好,怎么就窮得掉底?尤其他爹,早年還當過大隊干部,一個當過大隊干部的人竟然窮得出名,讓人殊不可解。
某年,牛眼他爹借了我家三張豆餅,一直沒還。小時候,我聽爹念叨過。那時,豆餅一張五十斤。平常日子,豆餅是豬食,餓狠了,人也吃。牛眼他爹借豆餅,是對付人嘴。
牛眼他爹犯錯誤被免了職。消息傳出,沒幾天,家里闖進一人。那人掄著一把鎬頭,進門就把火炕給刨了,取走一塊炕石板。臨走,嘴里還說炕石板當初是借給牛眼他爹的,媽了個巴子,竟好意思拖著不還,現在自家急用,只好來取。牛眼一家八口人,瞅著火炕中間那個黑洞洞的坑,感覺特別他媽的。據說那人是南邊涼水灣的,姓菊,武藝高強,能飛檐走壁。當初尖把梨要拜他為師,他不干。
牛眼到了婚娶年齡,卻無媒婆登門。牛眼他媽厚著臉皮,挨個去求人。礙于老親古鄰的情面,有人挺身,為牛眼牽線。可女方一見牛眼,就倏然把腦袋縮回,說媽呀,那一對大眼珠子,能嚇死人。
一連嚇走三個女的,卡屯的媒婆個個死心,連許二仙都沒轍,任牛眼他媽怎樣嚼舌頭,始終不為所動。牛眼他媽一想起這事,就忍不住用衣襟擦眼。
屯東老趙家有個女兒,一條胳膊殘疾,老大不小了還沒嫁人。有人跟她開玩笑,說你嫁給牛眼好不好?話音剛落,殘疾女的眼淚如小溪水般汩汩而出,還差點為這事去跳海。
聽到殘疾女要跳海的消息,牛眼立馬就繃不住了,當即扔了手中的鋤頭,撇開眾人,一個人來到海防林里,扯著嗓子干嚎,遠遠聽來有如牛哞。
不久,皮鎮電影院放映 《天仙配》,牛眼每晚都去。電影放了十天,他去了十回,故事情節自己都能背出來。十天里,牛眼不愛跟人搭話,常常望著東子家門口的那棵老槐樹發呆。有人看出端倪,念了一段 《天仙配》 里的臺詞:“老槐樹,老槐樹,我要與這位大姐結為夫婦,請你為媒,開口講話。”牛眼扭頭瞪了那人一眼,氣嘟嘟走開。
村花王淑蕓嫁到皮鎮,讓整個卡屯深受刺激。為什么受刺激?只因淑蕓嫁了個獨眼龍。淑蕓要模樣有模樣,要個頭有個頭,要身段有身段,要彈性有彈性,卡屯的年輕男人哪個不對她垂涎三尺?但淑蕓對他們瞅都不瞅一眼。人家淑蕓發誓要嫁到皮鎮,徹底擺脫在牛腚后邊討生活的日子。
卡屯一時議論紛紛,說那獨眼龍不得了,特別特別有錢,第一次見淑蕓,就拍出一千塊見面禮。淑蕓一見,渾身立馬沒力氣,兩條腿軟綿綿,好不容易才邁出那人的門檻。工廠里的八級大工匠,一個月才掙八十八。卡屯就有一位,在縣城上班,每月回家一次。屯中人見了他,目光里什么顏色都有。見他老婆也一樣,也是目光里什么顏色都有。而那獨眼龍,似乎比八級大工匠還要牛氣,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四大件,縫紉機、收音機、自行車、手表,八級大工匠家里三缺一,而他樣樣齊全,還都是響當當的名牌。
比打閃還快,淑蕓結婚了。
牛眼從淑蕓的婚姻里,嗅到一縷錢的香味。為此,他豁出去了,手腳越發不干不凈。
牛眼從小手腳就不干不凈,到農機廠偷幾塊廢鐵,到捕撈場偷幾條咸魚,是常事。至于偷瓜偷棗之類的勾當,更是不在話下。
牛眼把廢鐵或咸魚賣了錢,買一兜子水果糖,嘴里嘎巴嘎巴,一路走,一路嚼。有時一群小玩鬧,包括他弟弟小五瘩,都跟在他身后起哄。牛眼抓一把水果糖,往空中一揚,讓小玩鬧們去搶,然后再抓一把,塞給小五瘩。小五瘩跟我要好,每次都送我三兩顆。
小五瘩行五,是他爹他媽的寶貝疙瘩。我倆是小學同學,一個班,坐前后座。我吃糖少,發育不好,坐他前排。他吃糖多,發育好,坐我身后。他身后是墻,墻上是花花綠綠的“學習園地”。
受獨眼龍的刺激,牛眼的賊膽越來越大。以前偷魚,是幾條幾條偷,后來改成一筐一筐偷,從幾斤發展到幾十斤。不光偷魚,連漁網也敢偷。偷漁網那回,運氣不好,被逮個正著。正逢“嚴打”高潮,“從重從快”,沒幾天就判了七年,到盤錦種水稻。
牛眼行三,等他從盤錦的水稻田里拔出腿,回家一看,四瘩已經有妻有女,而小五瘩正在籌備婚禮。
小五瘩在皮鎮一家運輸公司當裝卸工,抽不開身,牛眼他媽連句客氣話都沒有,把籌備婚禮的種種瑣事,統統交給牛眼去辦。
牛眼他媽決策英明。此時生產隊已經解體,家里只有兩畝旱田半畝菜地,既無工分可掙,也無稻田可供牛眼展示技術,一個壯漢整天待在家里干嘛?練習一下籌備婚禮也好,興許這本領將來還能用上。
牛眼很賣力,就像自己要大喜一樣,一件件,一樁樁,都給小五瘩打點整齊。眼瞅著吉日降臨,卻晴天一聲霹靂,小五瘩不能參加婚禮了。
頭天夜里下過一場雨,早晨路滑,一個急剎車,小五瘩猝不及防,從卡車的貨堆上掉下來。后邊一輛卡車,司機沒踩住閘,發生追尾事故。比追尾更鬧心的是,小五瘩躺著車輪底下,誰叫都不吱聲。
喜劇變悲劇。還沒等給小五瘩燒完“七七”,沒結成親家的前親家,糾集一伙青壯,吵吵巴火地打上門來。悲劇于是轉成鬧劇。情況是,小五瘩身手敏捷,在別人毫無察覺的情況下,給準新娘下了種,此時已經顯懷,再也藏掖不住,于是坦白。準新娘父母一聽就坐不住了,瘋癲癲來卡屯,找牛眼爹媽要說法。小五瘩死了不假,但人死不能賴賬,總得有個說法才好。
為這事,兩家反復糾纏幾個月。準新娘早就生出打胎念頭,可事情沒談好,必須保留證據。可肚子不懂事理,一天比一天膨脹,于是問題開始變異。誰都看得出來,再拖兩三個月,那證據一定會離開母體。離開母體后會更麻煩。于是吵鬧聲愈發響亮。危難之際,許二仙挺身而出,這邊咕咕咕,那邊咕咕咕,居然讓她咕咕成一件好事。像廣告里說的,你好我也好,當事人雙方,都有臺階可下。臺階是:準新娘不用打胎,而是再次扮演新娘,擇日出嫁。那么誰當新郎?連傻子都想得出,除了牛眼還能有誰?至于肚子里的孩子,反正是老鐘家骨血,誰當爹,還不都一樣?牛眼的父母不在乎,牛眼本人,白撿一件大便宜,也就不好意思在乎,但人家新娘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老鐘家不能一點表示都沒有。許二仙下令,在原彩禮的基數上,老鐘家再添兩萬塊,以示拳拳誠意。
于是鬧劇又變喜劇。因為這,許二仙在卡屯的首席媒婆地位更加牢固,幾乎堅不可摧。
等牛眼的兒子,確切說,是小五瘩的兒子,能滿院子攆雞,牛眼喜歡坐在自家門檻上,一邊吸煙,一邊凝視那孩子,此時牛眼的一雙眼睛,真的像牛眼一樣,注滿水樣的慈祥。
小白菜
張邊外家前院,住著兩戶人家,一戶是牛眼家,一戶是小白菜家。
小白菜原先不叫小白菜。一天中午回家吃飯,嫌下飯菜不合胃口,他把閨女訓斥一通,嗓門太高,讓牛眼聽見,這才變成小白菜。
小白菜老婆死得早,給他遺下兩個雛,一個閨女,一個兒子。
那天中午,飯菜上桌,還是老一套,玉米餅子,玉米粥,都冒著熱氣,還有一盤鹽漬蘿卜條,和一盤剛出鍋的小咸魚。小白菜一見,頓生莫名之火,對閨女大吼,小白菜正在營養的時候,凈吃些媽的小咸魚。
閨女受不了這委屈,哇一聲哭起來,從屋里哭到屋外。隔壁,牛眼站在自家院子中央,隔著一道矮墻,向這邊張望,目光里全是柔情。
小白菜是卡屯的語言大師,“正在營養的時候”是他的口頭禪。無論想吃個啥,章魚、爬蝦、海螺、豬雜碎,或者地瓜土豆,那東西在他嘴里,指定都是“正在營養的時候”。他說,牛眼蛤正在營養的時候,做個湯。于是閨女趕緊做湯,牛眼蛤菠菜湯。那湯,真的好喝。
小白菜還有一句名言,也在卡屯廣為流傳,“大哥,我是不是比你大一歲啊?”
訓斥閨女的當日,一家三口,有了兩個綽號,爹叫小白菜,閨女叫小咸魚。
我聽見小咸魚恨恨地對別人說,都怪俺爹那張歪嘴。
小咸魚長到二十幾,還沒有婆家。這事,跟她爹的歪嘴無關,而是跟她的個頭有關。小白菜個頭矮,兒女都跟著矮,無論誰誰,都習慣于俯視他們。俯視的直接后果是,小咸魚在找對象的問題上,陷入困境。借用許二仙的話說,挑擔水都打晃,怎么過日子?
小咸魚心里有人,只是不敢說。那人就住在她家后院。那人便是張邊外家的二小子,小珍的弟弟張立貴。那時候,三哥和小珍結婚已經四五年,卡屯的家庭成分觀念,已普遍淡薄。小咸魚生出這份心思,也算正常。
立貴的個頭,不高不矮,膀子上有力氣,是個干莊稼活的好手,也是打魚撈蝦的好手。這是招人稀罕的一面。另一面,恰好他的嘴唇上下,都生出毛茸茸的小胡子。小咸魚一見那兩撮毛茸茸,身子就軟得不行,還水汪汪的,捂都捂不住。簡直的,讓人沒法活了都。
小咸魚人前人后跟立貴套近乎,立貴假裝不知,看起來很傻很天真。
小咸魚暗中生氣。久而久之,讓立貴給氣得,嗚嗚嗚,哭一場又一場。
一場接一場的嗚嗚嗚,讓小白菜對小咸魚的情緒動向有了警覺。他用掃帚把,把炕沿拍得啪啪響,叫小咸魚老實交代。經過多年斗爭洗禮,小白菜的政治覺悟,比以往高出好多個百分點,動不動就拿黨的政策說事。他肅著面孔,加重語氣,對小咸魚說,黨的政策,你知道的吧?你知道,要交代,不知道,也要交代,聽見沒?小咸魚受不了他的翻來覆去,只好交代。她對她爹說,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說了,你得從寬才行。
小咸魚流著眼淚向她爹傾述她對立貴的百般喜歡。小白菜聽完,長出一口氣,默了一陣,扔下掃帚,去了海邊。他站在懸崖邊上眺望大海,整整一個下午。他覺得小咸魚的選擇,還是實事求是的,里邊有相當的唯物主義含量。可是呢,這個事情,說一千道一萬,還得去求許二仙。要是連許二仙都撮合不成,別人就不用找了,找也白找。
許二仙坐在小白菜家炕頭上,擰眉頭,咬嘴唇,長時間不吭聲。小白菜一聲聲大妹子,把自己的眼圈都叫紅了,許二仙這才端起碗,一大口一大口,吃了小白菜孝敬她的一碗荷包蛋。
許二仙說:“我試試吧。”
許二仙一個回合就敗下陣來。她坐在張邊外家炕沿上,剛說出來意,就發現張邊外,張邊外老婆,還有立貴本人,臉色都不對了,都鐵青。許二仙多聰明的人哪,她轉瞬間想起來了,家里的豬還沒喂呢,雞鴨鵝,也都沒喂,她得趕緊回去瞅瞅,親事以后再說,以后再說吧。
許二仙在回家喂豬之前,先去小白菜家,把張邊外家的臉色,夸張了一通。
三哥說,當晚,小白菜家一點點聲音都沒有。都啞著,吃飯,熄燈,睡覺,誰都睡不著。小白菜眼里放光,往天棚上照。天棚上糊著舊報紙,上面有很多“最高指示”,可惜黑色太濃,眼光穿不透,那么好的指示,他一條也看不見。小咸魚不想看指示,她只覺得臉上發癢,摸一把,一手眼淚,再摸一把,又一手眼淚,一把一把,摸到天亮。
蹊蹺的是,一個月后,張邊外家出事了。大女兒從北大荒寫信來,一連三封,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說立貴的親事。
我常去三哥家,這事是三哥跟我說的。邊說邊笑,小珍坐在一邊,也笑。看樣子,小珍才是真正的知情人。
大女兒在第一封信里說,咱家小立貴有對象沒有啊?得趕緊找。俺在北大荒找大仙算命,大仙說俺沒事,說家里人都沒事,但有一樣,小立貴今年必須結婚,不然有血光之災。
第二封信里說,咱家前院是不是有個沒出嫁的閨女?大仙說有,那就應該有。大仙說小立貴的對象就是她。要是真有,那就趕緊找人提親,趕緊的。
第三封信里說,頭兩天,卡屯是不是下過一場大雨?大仙說下大雨,也不知是真是假,要是真下,趕緊讓小立貴結婚!不然有血光之災啊,你們不怕我怕!
張邊外一家,讓這個多年沒見的大女兒給嚇傻了。大仙說得對啊,前幾天,卡屯真就下過一場大雨,院子成了水塘,差點把圈里的那頭小豬給淹死。罷了罷了,小立貴和小咸魚,是天作之合,是命!
張邊外去求許二仙,客氣得不成樣子,連炕沿都不敢坐,一直貓著腰,站著說話。許二仙不知發生了什么事,但既然張邊外求上門來,那就得好好拿捏一下,至少,得把自己丟掉的面子找回來。
拿捏了半個時辰,許二仙終于答應,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就舍了這張老臉,替你們兩家再串通一下,丑話說在前面,成不成是天意,不成的話,可不能怨我。
張邊外嘴里含著蜜,再一次顛頭搗蒜。
等張邊外走遠,許二仙猛拍一下大腿,扎撒著兩條胳膊,一溜小跑,去小白菜家報喜,少不了,再享用一碗荷包蛋。
小咸魚和立貴的婚事,不出兩個月就辦了。辦得很好,新郎、新娘、新鋪、新蓋,還有糊了花紙的新房。張邊外發話,該新的,都得新。婚禮當天,張邊外穿一身新洗的衣裳,在自家院子里,也就是在那坑里,張羅了四桌酒席。屋里的炕上地下,也張羅了四桌。討個四平八穩的口彩。連吳大疤都給面子,坐了婚宴的首席,還講了話,話里頭,一句階級斗爭都沒有。小珍和三哥,在婚禮現場唱了一曲二人轉,不是小拜年,不是豬八戒背媳婦,是農業學大寨,學小靳莊,都學得很起勁。在張邊外看來,婚禮很圓滿。在小白菜看來,當然也圓滿。
圓滿之后,張邊外像他在生產隊飼養的那些老少黃牛一樣,一天天反芻這事,腦子里猝然一硌,覺得有點蹊蹺,立貴他大姐,以前從不往家里寫信,這回一連寫三封,著實反常。何況那三封信,都是寄到自家院里的臺階上,連郵遞員的影子都沒見。
找出那三封信,細細端量,終于發現漏洞,我的天,郵票上沒蓋郵戳。

趕緊給立貴他大姐寫信,把話往委婉里說,說立貴的事讓你費心了哈,現已遵照大仙的指示辦完婚事,考慮路遠費用大,沒叫你來參加婚禮。
一個月后,張邊外收到立貴他大姐的回信,信中說:立貴的婚事,俺沒操過心。什么大仙算命,全扯淡。俺也沒往家里寫過信。寫信不花錢啊,沒事寫什么信……
說到這里,三哥笑得合不攏嘴。
我說,臺階上的三封信,都是小白菜寫的,對不對?
你怎么知道?小珍問。
猜的,我說。
立貴得知被騙,心里有氣,有氣就得撒氣,于是夜夜搗鼓小咸魚。三哥說,搗鼓一次不解氣,再搗鼓,還不解氣,就再再搗鼓。小咸魚讓他搗鼓得一夜一夜睡不成個囫圇覺。路上碰見小珍,忍不住訴苦。小珍卻繃著臉說,得便宜賣乖,你掉進福坑里了,知不知道?
三哥說的搗鼓,讓我迷惑了挺長時間。當時還納悶,一夜夜搗鼓,立貴那廝,累不累啊。
前年清明節,我回老家給父母上墳,途中遇見小咸魚。她來給她爹小白菜上墳。兩家墳地相距不遠。等上完香,燒完紙,磕完頭,她主動過來,跟我說話。她明顯見老,臉上皺紋密布,真的像小咸魚一樣,有脫水后的抽巴感。她說她家的房子已經動遷,年內可能會住上樓房。她還說,張立富、張立貴、張立剛三兄弟,合伙出錢,買了一塊墳地,她不用擔心死后沒住處。
臨別一瞬,小咸魚說的那句話,我至今不忘。她說,活著能住樓,死了有墳頭,這輩子,值啦。
趾 六
趾六就是六趾。鄉下人喜歡正話反說,含一縷戲謔意味。
趾六姓柳,是個木匠。屯中老少,當面都叫他柳木匠,背后都叫趾六。
五歲那年,趾六他爹,瞅著兒子的六趾,直愣愣,特別鬧心,一狠心,拿起菜刀,將多余的一趾,切了。
切了也叫趾六。
活到二十出頭,趾六結婚生子。婚前鄭重其事,讓新娘脫了鞋,反復打量她的腳。一二三四五,很好,一共十個腳趾。趾六對新娘表示滿意。婚后數年,接連兩個女孩來家中報到。沒想到都是六趾。趾六對女孩并不反感,對六趾卻難以忍受。他像他爹一樣,瞅著也鬧心,也拿菜刀,將多余的一趾,都給切了。
趾六當木匠,頗有名氣,周邊十里八村,都知道有他這一號。他有絕活。一是蓋房子,會唱“上梁歌”。“鞭炮連天滿地香,打開八卦定陰陽。今日上梁,大吉大昌……賢東賜我一匹棉,我把棟梁纏幾纏。左纏三纏生貴子,右纏三纏中狀元……”諸如此類,變著花樣唱,嗓門亮,詞也好,午宴必坐首席。二是棺材打得好。鄉下人活得粗糙,死后卻要精細。所謂精細,是孝子在活人眼前掙的面子。棺材是重要一項,不可馬虎大意。此外還有紙車紙馬,吹打嗩吶,等等哩哩啰啰。趾六知道輕重,手下留了分寸,沁出一身汗水卻從不計較雞零狗碎,故而名聲鵲起。
趾六有一把大鋸,是他師父臨死前傳給他的。那把大鋸,他師父用了整整五十年,鋸過無數棺材板子。趾六常對人講,大鋸通靈,誰家夜里有喪事,打發人請他做棺材,來者尚在途中,掛在墻上的那把大鋸,便會錚錚作響。大鋸一響,趾六即刻起身,穿戴整齊,走出家門,喊他的助手。等來者到達,這邊已經蓄勢待發。這話是趾六自己說出來的,有人信,有人不信。某一天,趾六醉酒,說了實話,不是大鋸錚錚作響,是他做夢,夢中大鋸錚錚作響。這回都信,嘖嘖稱奇。
趾六不光會唱上梁歌,還滿嘴都是俏皮嗑,光“四大”我就聽過好幾種,至今我還記得兩段,一個叫 《四大黑》:“黑鍋底,黑炕洞,鐵匠的脖子,包文正。”還有一個 《四大紅》:“廟上的門,殺豬盆,大姑娘嘴唇火燒云。”諸如此類,張口就來。
我二哥結婚那年,趾六創作了一段新詞,讓小玩鬧們唱,我也跟著唱:“竹板一打一根棍兒,侯二奎娶了個小媳婦兒……”
有人說“馬武藝他爸”那段,也是趾六整的。趾六聞言,把頭搖得像撥浪鼓,連說扯淡扯淡。
趾六的故事,我耳聞得多,目睹得少。主要是大哥和三哥對我講。
我上初中那年,深秋的一天,放學回家,見大哥坐在院子里,一邊脫鞋一邊喚雞。嘍嘍,嘍嘍嘍,幾聲過后,雞都圍攏過來。一個個不疾不緩,猶如閑庭信步。大哥揚起手臂,將一只解放鞋在空中翻轉,掉出二三十粒玉米。那些黃澄澄的、沾有腳汗和腳臭的玉米,有如按鈕,讓雞群秩序大亂。它們咯咯咯,撲棱棱,張開翅膀,你沖我撞,還邊吃邊點頭,像是對大哥的善舉表示嘉許。待眼前的緊張局勢稍微平緩,大哥拿起另一只解放鞋,又從中掉出二三十粒玉米,雞群再次秩序大亂,再次沖撞,再次點頭,再次嘉許。大哥漾了一臉漣漪般的笑意。
我拿來一把杌凳,坐在大哥對面,看雞。那時候我并不知道,在既得利益面前,人群也如雞群,秩序大亂,你沖我撞。
吃完玉米,雞們站在原地,歪著腦袋,瞅大哥,見他久久沒有動作,才一個個將翅膀收緊,模仿小隊長吳大疤,背起手,邁方步,緩緩走開。大哥的目光從雞身上收攏回來,不緊不慢,卷一支喇叭筒旱煙,點火,深吸,吐一團濃濃的煙霧。
大哥在煙霧里說話。大哥說,趾六,穿一雙大號農田鞋,一回能裝一斤玉米,或者大豆,或者高粱,回家洗了,曬了,當口糧。
一天裝兩回,一個秋收季,大哥說,趾六能倒騰幾十斤糧,全家人吃一個月不止。
話里話外,大哥似乎對自己腳上的解放鞋很有意見。
解放鞋,類似當年解放軍標配的黃膠鞋。農田鞋,跟解放鞋材質一樣,差異在鞋幫,前者鞋幫高于腳踝,后者鞋幫矮于腳踝。誰都看得出,同樣鞋碼,前者容量大,后者容量小。可是鞋幫偏高,價格也就偏高,眼眉淺的人,很少有人穿,幾乎都穿解放鞋。我也是。
趾六的肚子,看著不大,卻特別能裝東西。除了上梁做棺材,很少有他吃飽的時候。說是木匠,但要經過吳大疤允許,才敢出去混飯。而吳大疤只允許他干兩件事,一是上梁,二是做棺材。可這兩件事,哪能天天都有?
于是生產隊的廣闊田野成為趾六的半個食堂,凡是能摸索到的,可以入口的,他都吃。茄子辣椒,黃瓜西紅柿,白菜蘿卜,等等,對它們,他從來都不客氣,就連生豆子,生玉米,他照樣大嚼特嚼。
秋收季,趾六在自家吃飯的次數明顯減少。
很多年后,關于趾六,三哥也跟我講過一段。
皮鎮一個什么單位的頭頭,跟吳大疤有交情。頭頭讓吳大疤找人給他干點木匠活,管飯,但不給工錢。吳大疤派趾六去。不能只讓他一個人去,得帶個助手。助手是吳大疤的小舅子。這事不算曠工,生產隊這邊記工分。
趾六和小舅子,兩人整整干了一天,干得利利索索。頭頭高興,晚上弄了一桌好飯菜。主菜是豬頭肉,滿滿兩大盤,飯是大米干飯,管夠。
吃得那叫一個好!
踩著夜色回家。兩人并肩走,都不說話。正值深冬,一股疾風襲來,掀掉趾六的火車頭棉帽。趾六止步,想彎腰,卻礙于身上背著工具袋,彎不下。稍頓,他扭頭,瞅小舅子。小舅子也止步,扭頭,瞅他。兩人還是都不說話。僵持兩分鐘,或者三分鐘,趾六像是跟誰賭氣,飛起一腳,將帽子踢到前邊,走幾步,再踢。
當晚,趾六把棉帽一直踢到自家院子里。跟小舅子分手時,他嘴里嗚嚕嗚嚕,說,你這人,太不夠意思。小舅子愣愣地,眼睛瞪得溜圓。
第二天一大早,小舅子抱一只大南瓜,上門向趾六道歉,說對不起啊柳木匠,我不是不想幫你,是幫不了。抿抿嘴唇又說,你比我厲害,你能說話,我昨晚不光彎不下腰,連話也說不出來。
趾六晚年有個心愿,給自己做一副好棺材,為卡屯制造佳話。早年,日子過得艱難,村民普遍用柳木殯葬,久之成為慣例。他不,他打破慣例,用松木。松木耐腐,不像柳木易爛。烘干,脫脂,開工。給別人做,他都是一兩天做完,給自己做,他做了半年。抄古書,在棺頭刻了篆體“福”字。請畫匠,在棺身畫了八仙過海。他渴望死后日子能過得逍遙,像那些神仙。末了,他請最好的漆匠,漆了三遍。三遍都是紅色。紅色象征長壽,是喜喪的標志。做完這些,再前后左右打量,找不出一點瑕疵。這時,一個爆炸性消息傳到耳邊,說殯葬改革利國利民,上級劃出紅線,本年農歷八月初一之前,死者可以土葬,過了這條紅線,無論是誰,哪怕天王老子,也必須火化。聽到消息時,離八月初一還不到十天。
趾六悶悶不樂,到屯東海防林轉悠一整天,腦袋里全是火光。晚上回家,一句話不說,操刀殺雞。此后三天兩頭殺雞,吃完一只,再殺一只。吃到七月三十日中午,酒肉之后,他往房梁上掛根繩,把自己吊了上去。沒成想,繩子不結實,呼嗵一聲,跌到地上,崴了腳。
趾六躺在炕上養腳。躺到第三天,一夜無話,無疾而終。
趾六是卡屯第一個火化的死者。出殯那天,全村男性,凡是會走路的,都上山送他。當地民俗,女人不準送殯上山。
不少老人感嘆,可惜那具上好的松木棺材,就裝了幾把骨灰。
連續多年,一提這事,大哥嘴里都嘖嘖有聲。三哥也一樣,嘴里嘖嘖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