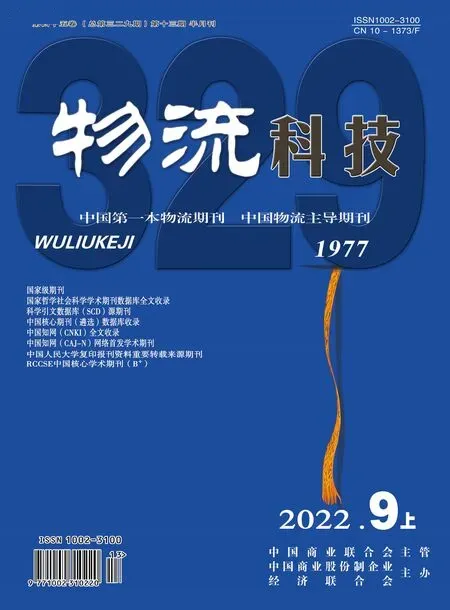物流業上市公司大股東減持對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研究
白曉月,吳 清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1600)
0 引 言
股權分置改革后,市場解除了對原非流通股的限制,原持股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東(以下簡稱大股東) 可以按照規定出售其所持股份,推動了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然而隨著我國A 股市場的股權全流通,市場上也出現了大股東利用其信息優勢操縱信息披露進行內部交易的問題。目前我國資本市場對中小股東的保護力度較弱,大股東能夠通過掌握的企業內部信息判斷股票交易價格是否與真實價值相符,進而進行做出股權增減持決策。具體來說,大股東在股價被高估時減少持股數量,股價被低估時增加持股數量,以此來獲得超額收益。此外大股東會聯合管理層操縱企業的強制性披露信息和自愿性披露信息,對于自愿性披露信息大股東根據增減持調整披露時機,而對于強制披露信息則通過盈余管理來掩飾大股東內部交易的負面影響。2017年,中國證監會發布了約束大股東減持行為的新規,明確提出大股東減持股份應按照相關規定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本文選取了我國滬深A 股物流業上市公司2010~2019 年的財務數據,以此作為樣本研究了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再引入股權集中度和董事會獨立性調節變量,研究它們對上述關系的影響。本文的貢獻有:(1) 實證分析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的關系,豐富了有關大股東減持經濟后果方面的研究。(2) 引入調節變量,探討了其對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關系的調節作用,進而探究降低大股東減持對盈余信息質量影響的方法。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代理問題是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的情況下產生的管理者和股東間的利益不一致問題,主要出現在股權結構比較分散的公司中。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較高,大股東能代表股東的利益監督管理層,能有效緩解管理層和股東間的代理問題。在股權結構非分散的情況下,大股東和小股東間的代理問題就更為突出。如果大股東追求短期利益,則會以犧牲公司利益、侵占小股東利益為代價獲得私人收益。已有研究表明大股東會在售出股份前對企業進行盈余管理,調整對外報告企業盈利情況,造成股票價格高估并以此來獲得額外收益。此外,追求個人利益的大股東利用其控制權“掏空”公司,對企業的盈利狀況造成影響,為掩飾其自利行為對企業的負面影響,大股東與管理層合謀調整可操縱應計利潤進行盈余管理。我國大股東和管理層面臨的監管壓力較小,企業管理者可能來自控股股東單位方,或者薪酬和任職由控股股東決定,雙方利益一致關聯性高,管理者則很可能“迎合”大股東對公司盈余信息進行調整。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設1。
H1:大股東減持與企業盈余管理正相關,即大股東減持比例越高,企業盈余管理程度越大。
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度相對較高,當股權較為集中時大股東可以利用控制權操縱報告的盈余信息,或者促使管理層迎合大股東的自利動機,在大股東減持前進行正向盈余管理。董事會的獨立性影響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作為監管管理層的制度安排董事會行使其決策權和監督權,董事會的獨立性越強其對盈余管理的監管力度就越大,企業披露盈余信息的質量也就越高。如果董事長同時兼任總經理,或者董事會中外部董事占比高,那么說明董事會的獨立性較弱,此時公司治理環境的透明度較低,進行內幕交易操縱盈余信息的可能性更大。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設2 和假設3。H2: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公司股權集中度越高,大股東減持對盈余管理的正向作用越明顯。H3: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董事會獨立性能夠抑制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間的反向關系。
2 樣本設計
2.1 數據來源及樣本選擇
本文選擇2010~2019 年滬深A 股113 家物流業上市公司為樣本,相關數據來自于國泰安CSMAR 數據庫和同花順iFinD 數據庫,其中與大股東減持相關的數據來自iFinD 數據庫。本文實證部分采用OLS 回歸方法,計量統計軟件為Stata16。并對樣本數據進行了以下處理:(1) 剔除面臨退市風險的上市公司(ST 公司);(2) 剔除缺失數據;(3) 剔除金融業數據。
2.2 定義變量
(1) 被解釋變量。借鑒陸建橋(1999)的做法,本文采用應計利潤法計算出非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衡量盈余管理程度。該模型考慮了收入、應收賬款、固定資產、無形資產以及其他長期資產對操縱性應計利潤的影響,是目前國內對盈余管理進行實證研究廣泛采用的模型。
(2) 解釋變量。本文采用iFinD 數據庫中關于大股東減持比例的統計數據作為解釋變量,篩選出大股東變動股數合計數為負的數據,計算出大股東變動股數占流通股數的比重即為大股東減持比例。
(3) 調節變量。本文的調節變量為公司股權集中度和董事會獨立性。公司股權集中度用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來衡量,當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高于平均數時賦予1,表示股權集中度高,否則賦予0。董事會獨立性則用董事長是否同時兼任總經理衡量,當存在兼任情況時賦予1,表明董事會的獨立性較弱,0 則表示董事會的獨立性強。
(4) 控制變量。借鑒相關研究成果,本文控制了如下影響因素:公司是否虧損、公司規模、每股收益、股權性質、資產負債率。并設置了行業和年度虛擬變量。具體定義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定義
2.3 模型構建
本文用如下回歸模型來驗證H1~H3。利用模型(1) 檢驗假設H1,即檢驗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間關系。在模型(1) 引入調節變量Owner 和變量交互項Owner*Sell 建立模型(2) 來檢驗H2,驗證股權集中度對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的調節作用。在模型(1) 引入調節變量Indep 和變量交互項Indep*Sell 建立模型(3) 來檢驗H3,驗證董事會獨立性對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的調節作用。

3 實證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的結果如表2 所示。其中DA 的最小值、最大值和均值分別為0、2.224 和0.057,樣本公司中的盈余管理水平普遍不高,但極差較大,數據變異程度大。

表2 描述性統計結果
Sell 的均值為1.184,說明在觀測樣本中平均大股東減持股票比例為1.184%。Sell 的中位數為0,說明大部分公司并沒有發生大股東減持事件。Owner 的均值0.532,說明高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平均數的公司更多。
Indep 的平均數為0.298,有29.8%公司存在董事長和總經理兼任的情況。另外,公司規模、每股收益、資產負債率的波動較大,選取樣本具有代表性。
3.2 相關性分析
表3 列示出了樣本觀測值的相關性分析結果,表3 中數據顯示,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程度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038,顯著性水平為5%。表明大股東減持規模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則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水平顯著負相關,相關性分析結果初步驗證了H1。此外,公司虧損情況、公司規模以及資產負債率與盈余管理的相關系數為正,表明三個控制變量與盈余管理正向相關。每股收益與盈余管理的相關系數為-0.024,每股收益與盈余管理負相關,但不顯著。

表3 主要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3.3 回歸分析
(1) 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的回歸分析。大股東減持與盈余信息質量的回歸結果如表4 所示,結果表明,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有顯著正相關關系,回歸系數為0.058,顯著性水平為1%。該模型通過了F 檢驗,且調整R為0.324,說明擬合優度良好。該回歸結果可以驗證假設H1 的正確性,盈余管理程度隨著大股東減持比例的增大而增大。

表4 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的回歸結果
(2) 股權集中度和董事會獨立性的調節作用。表5 所示的是模型(2) 和模型(3) 的回歸結果,由表5 可知Owner 和交叉項Owner*Sell 的回歸系數均為正數,顯著性水平分別為5%和1%。說明股權集中度與盈余管理顯著正相關,股權集中度能夠加強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假設H2 得到了檢驗。說明股權越集中,大股東就越能利用其控制權和信息優勢,與公司管理層合謀操縱公司盈余信息,高價減持攫取公司利益。同樣由表5 可知Indep 和Indep*Sell 的回歸系數均為負數,顯著性水平為5%和1%。說明大股東減持與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顯著負相關,公司董事會的獨立性能夠抑制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假設H3 得到了檢驗。則表明當公司董事會具有獨立性時,董事會能夠發揮其對公司大股東和管理層的監督作用,能夠減少減持過程中的盈余管理現象,抑制大股東“掏空”行為。

表5 股權集中度和董事會獨立性的調節作用
4 結 論
本文以2010~2019 年我國滬深A 股物流業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實證分析研究大股東減持對物流業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1) 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顯著正相關,大股東減持前公司傾向于進行盈余管理。(2) 在此基礎上研究發現:股權集中度能夠正向調節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的正向關系,股權集中度越高,大股東減持前的盈余管理行為越明顯。董事會的獨立性能負向調節大股東減持與盈余管理的正向關系,董事會能夠發揮其監管作用,抑制大股東減持前的盈余管理行為。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