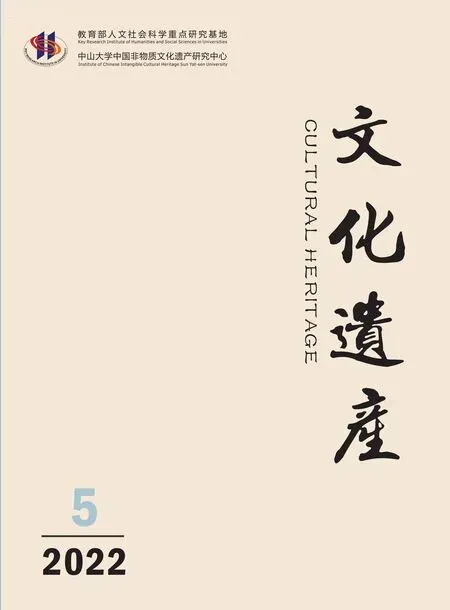散存清宮大戲《征西異傳》考述*
李飛杭
《征西異傳》是清代內廷的一部連臺大戲,演薛丁山征西事,以往著作論及清代宮廷戲曲時都會提到該劇。相較于《鼎峙春秋》《勸善金科》《昭代簫韶》等較為完整的劇本留存和系統研究,學界對《征西異傳》的了解甚少,只聞其名不見其劇,未有任何的專項研究。目前《征西異傳》劇本散佚嚴重,是已知清宮大戲當中面貌最為模糊的一個,如吳新雷在《二十世紀前期昆曲研究》中著錄《征西異傳》已收入《古本戲曲叢刊》第九集,部分學者也延續其說法,但事實上該劇一冊也未收入其中。關于《征西異傳》的相關情況,只有王芷章在《清昇平署志略》中的簡要論述值得一敘:
《征西異傳》,演薛丁山征西事,共演二次。第一次,道光四年二月初六日演頭段,十二月二十三日演十六段(系外學所承應)。光緒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演頭本,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演至二十四本(此次系內學承應,原檔案仍舊稱,加府字以為說明,且又改段為本與前亦異)。
王氏所觀資料均是來自朱希祖先生所購得的一批昇平署檔案和劇本,現已出版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其中僅收錄《征西異傳》之殘本6段,未見《西異傳》之名。在王芷章之后,學界對于《征西異傳》的研究停滯不前。目前已知《征西異傳》藏于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首都圖書館三處,劇本數量多,形制較為復雜,其中國家圖書館的小部分劇本、故宮博物院的全部劇本已經出版。本文先對已出版的劇本進行梳理,奠定基本認識,而后再著重根據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所藏其余劇本進行深入考察比對,對各處劇本之間的先后承襲及相互關系進行細致探究,力圖對該劇有一明晰的認識。
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之《征西異傳》
該部分劇本共6冊,現藏于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閱覽室,已于2011年影印出版于《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以下簡稱《檔案集成》)第60冊。該套劇本長24.5厘米,寬16厘米,無框欄行格,每頁8行,每行20字,劇名均為《征西異傳》,分別是第二段、三段、十三段、十四段、十六段、十七段。二段封面題“二段征西異傳 六出總本”,右側題“廿一日折全角”;三段封面題“三段征西異傳 六出總本”;十三段封面題“十三段征西異傳 八出總本”(缺后四出),右側題“廿四本 舊十三段 一二出”;十四段封面題“十四段征西異傳 八出總本”(缺后四出);十六段封面題“十六段征西異傳 八出”;十七段封面題“十七段征西異傳 八出”,封面右側題“卅二本”。
現存檔案記錄中,《征西異傳》第一次演出為道光四年(1824),均由外學上演,一年之內共演出了十六段,未全部演出,每月演出兩到三段,其中七月份為朔望承應,前十二段的演出地點為同樂園,后四段為重華宮。這套劇本顯然是不完整的,能提供給我們的信息就是《征西異傳》以段為演出單位,至少編創了十七段。在十三段劇本的封面右側題寫了“廿四本 舊十三段 一二出”,第十七段封面右側題寫了“卅二本”,這些信息是否對應為光緒朝的《西異傳》,待下文詳述。
二、《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南府昇平署戲本》之《西異傳》和《征西異傳》
2001年《故宮珍本叢刊》出版了《征西異傳》的曲譜本和題綱本,之后2016年《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南府昇平署戲本》(以下簡稱《戲本》)又將包括同一批曲譜本、題綱本在內的故宮博物院所藏全部《征西異傳》和《西異傳》出版。根據對《戲本》的檢索,梳理出相關劇本的收錄情況:
第39冊有《西異傳》第二本、三本、四本、七本總本。
第40冊有《西異傳》第十本、十二本、十四本、十五本、十六本、十七本、十八本、二十本、二十一本、二十二本、二十三本總本,另有一本無本數標識《西異傳》。
第41冊有《西異傳》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本總本,又分別有首頁標“征西異傳”(無段數標識)、“西異傳”(無本數標識)、“十六段征西異傳 八出總本”3個本子。
第42冊有《西異傳》總本第十四本。
第152冊有《征西異傳》(曲譜 頭本)一本,其余均名為《西異傳》曲譜,根據出版所列順序分別是二本、四本、五本、八本、八本、十二本、十四本、十六本、廿本、廿一本、二十二本、二十五本、二十七本、二十八本、二十九本、廿九本、三十本、三十一本。其中第八本和第二十九本均有兩本。
第190冊有1冊名為《征西異傳》的題綱本,為第七段,其余均是名為《西異傳》的題綱本,根據出版所列順序為二十四本、二十五本、五本、二本、三本、六本、七本、八本、九本、十本、十一本、十二本、十三本、十四本、十五本、十六本、十七本、十八本、十九本、二十本、二十一本、二十二本、二十三本、二十四本、二十五本,另外有4本沒有本數標識的《西異傳》題綱本。
第436冊有《西異傳》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本總本,另有1本無本數標識《西異傳》。
第437冊有《西異傳》二十四本總本、二十五本鼓板本。
(一)《西異傳》
1.總本
根據光緒一朝《西異傳》的演出記錄來看,其演出單位由“段”改“本”,所以《西異傳》與《征西異傳》劇本形制的最大不同也在于此,并且不分出目,如彩圖1、2:
該部分劇本每頁4行,每行18字,共25本(以下簡稱《戲本》25冊本),為第39冊《西異傳》第二本、三本、四本、七本總本;第40冊《西異傳》第十本、十二本、十七本、十八本、二十本、二十一本、二十二本、二十三本總本;第41冊《西異傳》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本總本以及無本數標識《西異傳》;第42冊《西異傳》第十四本總本;第436冊《西異傳》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本總本,另有1本無本數標識《西異傳》(經考證與第41冊第二十五本《西異傳》相同);第437冊《西異傳》第二十四本總本。
將《檔案集成》中的《征西異傳》和《戲本》當中《西異傳》總本進行對比,發現這兩種文本之間可以相互對應,其中二段《征西異傳》的頭三出與三本《西異傳》相對應,后三出與四本《西異傳》相對應;第十三段《征西異傳》與二十四本《西異傳》相對應;第十四段《征西異傳》與二十六本《西異傳》相對應;第十六段《征西異傳》與十二本《西異傳》相對應。還要說明的兩點是,第一,從整個劇本的故事情節來看,《戲本》第40冊“十二本《西異傳》”的順序應該在《戲本》所收錄所有《西異傳》總本的最后,至少在第二十九本《西異傳》之后,標注為“十二本”應該是錯誤的。第二,第41冊無本數標識《西異傳》暫不知為多少本,留待下文。
除以上25本《西異傳》總本外,第40冊中的《西異傳》十四本、十五本、十六本的劇本較有不同,不僅在抄寫行數、字體大小上與其他劇本有差異,而且它們雖已經改段為本,但內容仍然是《征西異傳》的形制,分出且有出目,如彩圖3:
這應當是《征西異傳》在改編為《西異傳》過程中的一種劇本形制,這類劇本很有可能是在原《征西異傳》的劇本上重新粘貼《西異傳》封皮,特別是第十四本是直接從第五出開始的,明顯是從《征西異傳》的總本當中截取而來,筆者將此類劇本稱之為“準《西異傳》劇本”。第十四本《西異傳》有兩本,對比這兩種劇本發現,《西異傳》總本在準《西異傳》總本的基礎上有所刪減,如彩圖4、5:
此處為第五出至第六出之間的銜接處,在第40冊十四本《西異傳》中為樊龍、樊虎念白后唱,唱罷后,樊洪念白后唱,唱罷后眾人下場。接第六出開始,姜興霸與李慶先上白。在第42冊十四本《西異傳》中刪除了樊龍、樊虎、樊洪三人的唱詞,眾人念白完畢后緊接著姜興霸與李慶先上白。這樣的改動是《征西異傳》到《西異傳》的一種改編手段。
2.鼓板本
為第二十五本《西異傳》鼓板本,每頁8行,每行20字,鼓板本的抄寫形制上與總本不同,分出且有出目,曲文不注工尺,另有勾畫的痕跡,如在第四出“斬妖破敵”中,有圈住更改的墨跡,如彩圖6:
此處刪去了【金盞兒】【醉中天】兩支曲,并且增加樊梨花“退后者定按軍刑”一句道白。將更改過后的二十五本《西異傳》鼓板本和二十五本《西異傳》總本比較后發現,兩者內容一致。
3.曲譜本
共18冊,每頁4行,每行15字。分別為頭本、二本、四本、五本、八本、八本、二十本、十四本、廿本、廿一本、二十二本、二十五本、二十七本、二十八本、廿九本、二十九本、三十本、三十一本,其中第八本、第二十九本均重復出現一次。第一本首頁標“頭本 征西異傳 曲譜”,除頭本外,其余均標“西異傳 曲譜”。每頁11行,每行14字,有勾畫痕跡。此曲譜本是否是刪減過后的劇本,留待下文。
4.題綱
題綱本共30冊,可以分為五種。
第一種,共1冊,分出,有出目。封面題“七段征西異傳 六出 題綱”。共記錄演員73名。通過對演員的生卒年考證可知王喜的出生年最晚,為乾隆五十三年(1788),那么他入南府的時間最早也應是嘉慶年間了,得保去世時間最早,為道光二年(1821)。道光元年在服期內沒有演劇的相關記錄,所以此題綱本的使用時間是在嘉慶年間,也就是說至遲在嘉慶一朝,《征西異傳》就已經開始編排。
第二種,共2冊,為第二十四本和第二十五本,不分出,記錄了該本所需角色和演員。第二十四本《西異傳》題綱記錄的演員共計31名,通過演員生卒年考證可知此題綱本的使用時間為光緒十五年至十六年。第二十五本《西異傳》題綱記錄的演員共計有23名。通過考證可知此題綱本的使用時間為光緒九年(1883)至光緒十六年(1890)。
第三種,共2冊,分出,有出目,未標注“段”或“本”,封面標“西異傳”,但標題字體與劇本內容很不一致,角色名記錄較多,演員記錄不完整。通過演員生卒年考證第1冊使用時間為嘉慶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三年,第2冊的使用時間為道光三年(1823)至同治六年(1867)。
第四種,共2冊,分出,無出目,未標注“段”或“本”。其一封面題“西異傳 三出 題綱”,僅記錄角色名稱,無演員記錄。其二有添改記錄,封面題“諸路合師 四出 改西異傳 題綱”,僅記錄角色名稱,無演員記錄,該冊應是在原來《征西異傳》題綱上修改得來。
第五種,共23冊,分出,無出目。該版本劇本記錄了每本所需角色名字,并且部分本中標注了所用的道具和砌末,如第五本注“背壺三身,內有女一,黑棒一對,公案一分,紅纛一,長短把子”;二本注“匾 界牌關、金霞關,五色背壺十身、黃金馬鞭子、長短把子、金大刀”等。
(二)《征西異傳》
《戲本》中共收錄2冊名為《征西異傳》的劇本,分別為第41冊中“征西異傳”和“十六段 征西異傳”。“征西異傳”未標注具體段數,封面貼一紙條寫“第一出 掃除火鵲”,共4出,有出目,其余各出為“第二出 采樵巧遇”“第三出 饋禮允親”“第四出 送女就婚”,每頁8行,每行20字,曲文未注工尺。
《戲本》和《檔案集成》當中均收錄有十六段《征西異傳》,但是二者的內容卻不一樣。通過對前文各本故事情節的梳理對比發現,《檔案集成》中第十六段與《檔案集成》第十七段的故事情節并不連貫,但《戲本》第十六段卻與《檔案集成》第十七段故事內容連貫,《檔案集成》的第十六段經考證應該銜接在第十七段的故事內容之后,所以《檔案集成》的十六段實際應為《征西異傳》第十八段。
三、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閱覽室與古籍館之《征西異傳》和《西異傳》
(一)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閱覽室藏《征西異傳》和《西異傳》
共30冊。除第1冊封面將劇名寫為“征西異傳”外,其余均寫作“西異傳”。該處所藏劇本可以分為三種形制,第一種共26冊,總本;第二種共1冊,鼓板本;第三種共3冊,總本。
1. 第一種
為第一本至第二十六本(下文統稱為“國圖善本26冊本”)。除第一本腐朽比較嚴重外,其余各本狀況良好。該套劇本均分出,但出目時有時無,第一本封面寫“頭本 征西異傳 總本 曲譜 四出”,如彩圖7:
第二本封面寫“二本 征西異傳 總本四出”,從第三本開始,劇本均是以“西異傳”來命名。此種劇本從形制、字體來看均是同一時期的手抄本,長30厘米,寬24厘米,每頁6行,每行20字,無框欄行格,抄寫十分工整。曲文注工尺譜,每冊劇本的曲牌曲文大都有被括號或圓圈標記勾畫的痕跡,如第一本第三出中【鏵鍬兒】一曲上寫“不用”,并前后勾除;第二本第三出中【玉胞肚】的曲文被前后勾除;第四出中【越恁好】【紅繡鞋】的部分曲文被勾除,諸如此類在每本當中大都有出現,與《戲本》第437冊二十五本鼓板本的情況十分相同。
將該套總本與《檔案集成》和《戲本》所藏《征西異傳》總本相比較發現,三者不同之處在于該套總本以本為單位,另外兩者以段為單位,其余內容均一致。這套劇本是《征西異傳》改段為本后的第一種形態,其中第三本對應二段《征西異傳》前三出;第四本對應二段《征西異傳》后三出;第十三本對應《戲本》第41冊無段數標識本《征西異傳》;第二十四本對應十三段《征西異傳》前四出;第二十六本對應十四段《征西異傳》前四出。這套劇本與《戲本》25冊本同一本數之間的劇情內容是相同的,將該套劇本相關勾畫更改等處刪除后,就與《戲本》25冊本相一致了,再加之它承襲了《征西異傳》分出或有出目的形制,所以可以認為國圖善本26冊本早于《戲本》25冊本但晚于《檔案集成》本。
這是現今可見《征西異傳》(或《西異傳》)最完整的總本版本。一般每本劇本由劇本、題綱本、串頭本三部分組成,題綱本和串頭本均是小冊子夾帶在劇本中,或者是題綱和串頭本合訂一冊,也有的劇本會多夾帶一張長62厘米、寬50厘米的題綱紙,內容與題綱本基本相同,但是也有劇本當中無任何夾帶,如第二本、第十四本、第二十一本。下面以第一本中夾帶的冊子為例進行說明。
首先是題綱。第一本當中夾有一個題綱本冊子,封面左側寫“頭本 征西異傳 四出題綱”,右側寫“光緒十五年九月 準 四刻五分”,中間寫“鼓 沈大”,如彩圖8:可以肯定該本為光緒時期《征西異傳》或《西異傳》的抄本,與光緒一朝《西異傳》從光緒十五年(1889)十月初一日開始的演出記錄也可以相對應。沈大是光緒一朝的鼓師,其人技藝極受內廷賞識,之后幾乎每個題綱本的封面都會寫“鼓 沈大”。題綱本內容為每一出劇目所需角色及所用演員,有些演員的名字被貼上黃色小紙條,紙條上寫另一位演員的名字或者“撤”字。
其次是題綱紙。與劇本、題綱本所用材質相同,記錄了上場角色和演員,分出記錄。題綱紙未寫朝年,通過對比發現演員名字的記錄與題綱本基本一致,少數演員有更換,應為同一時期的題綱。兩個題綱抄寫時間應該是題綱紙在前,題綱本在后,題綱紙的部分演員到了題綱本上經過了貼紙更換,除去更換的演員外其余則保持了一致。
最后是串頭。如第一本中夾帶的串頭本,封面即首頁寫“頭本 征西異傳 一出 串頭”,長25厘米,寬14.5厘米,如彩圖9:
串頭本并非每本每出都有,當舞臺上有多人熱鬧的武打場面時才需要串頭本的存在。串頭本是研究清宮戲曲舞臺的重要參照,特別是光緒時期清宮武戲盛行,串頭本以文字記錄的方式提供了較為形象的直接材料,如第十七本當中第一出和第二出念白較多無武打場面,故未有串頭,而第三出青龍關外敵軍趁夜劫營打的十分精彩,故附以串頭本描述舞臺調度。
除劇本、串頭、題綱本、題綱紙外,在第九本總本當中還夾了一張“閑人紙”,長29厘米,寬23.5厘米,上寫“閑人”二字,后附16個演員的名字,這些人員是排演過程中的機動人員,可以隨時增補或替換上臺。根據以上總本以及總本當中所夾帶的題綱本、串頭本、題綱紙等信息來看,該套劇本為光緒一朝的實際演出用本,是經過《征西異傳》改段為本而來,并且在排演的過程中進一步的磨合,通過刪減曲詞等完成最終的改編。
2. 第二種
為第二十六本的鼓板本,封面寫“二十六本 西異傳 鼓板”,長29厘米,寬24厘米,無框欄行格,每頁8行,每行20字,抄寫工整,字體比總本要小。首先經過對比發現,相較于總本,鼓板本曲文未注工尺及第四出沒有標出目,其余內容和總本均一致。其次,該鼓板本與《戲本》第434冊所藏二十五本鼓板本的形制完全相同,字體、字跡、間行等也無差異,但沒有進行任何勾畫刪減,與《戲本》第41冊第二十六本《西異傳》內容相同。
3. 第三種
為第27、28、29本(下文統稱為“國圖善本3冊本”),這種劇本沒有墨題封面和本數,只有在第一頁直接寫“西異傳”和劇本內容,現存的順序是國圖的工作人員根據劇本的留存順序用鉛筆在第一頁的右上角標注的,并非劇本的編演順序,如彩圖10:
該3冊本與國圖善本26冊本從形制、紙張、抄寫形式上完全不一樣,通過考證發現其與《戲本》25冊本為同一種劇本,第28本對應《檔案集成》十七段《征西異傳》的前四出,第29本對應《檔案集成》十七段《征西異傳》的后四出,第27本對應《檔案集成》十六段《征西異傳》(前文更正其為第十八段)第五至八出,所以這三本劇本的編演順序都在國圖善本26冊本之后,以國圖現存的鉛筆標注順序為名,它們的正確排序應為28本、29本、27本。
4. 通過國圖善本特藏閱覽室劇本考證所得結論
(1)《戲本》第40冊“十二本《西異傳》”的本數標識有誤,其順序應當在國圖善本3冊本第29本和27本之間;將《戲本》第41冊無段數《征西異傳》分別與國圖善本26冊本相比較,其與第十三本《西異傳》相對應;《戲本》第41冊無本數標識《西異傳》經過對比發現應為第十二本《西異傳》。
(2)將故宮所藏曲譜本與《戲本》總本、國圖善本26冊本進行對比發現,故宮所藏曲譜本與國圖善本所藏26冊本相同,屬于準《西異傳》所用曲譜,即曲牌曲文為原《征西異傳》中未經刪減的內容,并且頭本名為“征西異傳 曲譜”的本中也有與國圖善本26冊本有著相同內容的勾畫。另外,第八本曲譜存有兩本,其中第一本的曲牌曲文經過刪減,第二本則是準《西異傳》所用曲譜,曲牌曲文完整。
(二)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藏之《征西異傳》
共2冊,形制相同,長24.2厘米,寬15.9厘米,無框欄行格,每頁8行,每行20字。分出,有出目,朱筆點有標點,曲文不注工尺。索書號149801本封面即第一頁,右上角寫“唐 十四段 廿七本”“第五出 法擒一虎”,共四出,其余為“第六出 遵諭歸唐”“第七出 盜鈴獲偶”“第八出 獻關納婿”。索書號149802本封面即第一頁,右上角寫“唐 廿五本 舊十三段”“拆得了”“未寫末折”,其中“未寫末折”四個字被圈住。兩冊劇本的封面如彩圖11:
經過對比,這兩冊劇本的形制、筆跡等與《檔案集成》本完全一致,為同一時期同一人所抄寫。索書號149801為《檔案集成》第十四段缺失的后四出,索書號149802為《檔案集成》第十三段缺失的后四出。將兩處劇本相加即為原先的十三段和十四段完整的《征西異傳》,并且從“拆得了”一句可以印證前文的判斷,內廷將原來《征西異傳》的劇本拆開組成新的《西異傳》劇本。
四、首都圖書館歷史文獻閱覽室之《征西異傳》
該部分劇本共9冊,為《征西異傳》劇本,清書堂藏版,每冊長23.3厘米,寬15.6厘米,無框欄行格,每頁8行,每行20字。分出,有出目,朱筆點有標點,曲文不注工尺。每一本的第一頁同時鈐“首都圖書館藏”和“馬氏彥翔藏書”或只鈐后者。經過比對,首都圖書館藏本、《檔案集成》本、國圖文津街古籍館藏本為同一版本的《征西異傳》抄本,抄寫形式、筆跡等完全相同,首都圖書館的留存狀態最好。
第1冊首頁標“四段征西異傳,六出總本”,第2冊直接進入第四段第四出。每冊三出,第1冊為“徂征被截”“施法遭擒”“仙緣奇遇”,第2冊為“虎寨成親”“盤腸大戰”“代任取關”。其中第2冊第一頁右上角貼一張紅紙片寫“六本”,如彩圖12:
第3冊首頁標“□段征西異傳,六出總本”,共六出,分別為“要求鳳侶”“盜取飛鈸”“大敗妖僧”“錦蓮督旅”“一虎成親”“復困鎖陽”。通過查找比對,該本與故宮所藏七段《征西異傳》題綱的出目相對應,封面缺失的字應“七”,此為七段《征西異傳》。
第4冊首頁標“十段征西異傳 □□總□”,共六出,缺失的字應為“六出總本”,分別為“祖餞進兵”“偵報設謀”“抵關劫寨”“交鋒大潰”“破扇斬鵬”“妖仙布陣”。本冊最后夾了兩張黃色紙片,一片寫“二本 二出”,一片寫“十二本 西異傳”。
第5冊沒有封面,共六出,為殘本,開篇即為三頁劇本,之后就是“第三出”。從第三出至第八出,分別為“敗陣設謀”“劫營誘因”“被圍議救”“突谷產兒”“唐軍得信”“星宿歸垣”。通過與其他所有劇本進行對比銜接發現,該冊和《戲本》25冊本中的第二十八本、二十九本《西異傳》內容相同,應為第十五段《征西異傳》,但是缺少第一二出。筆者發現這幾頁殘本其實是二十八本《西異傳》第二出的結尾,這說明這一段《征西異傳》完整的分成了第二十八本和第二十九本,第十五段的第一出和第二出并沒有被刪除,只是該冊劇本保存不完整無從得見。
第6冊封面為“六段征西異傳 六出”,第7冊直接進入第六段第四出。每冊三出,分別為第6冊“解圍面圣”“施藥救親”“責妻斬子”,第7冊“敕命回鑾”“行兵合旅”“施展邪威”。
第8冊封面為“五段征西異傳 八出”,第9冊直接進入第五段第五出。每冊四出,分別為第8冊“合隊取關”“詐降授首”“回營聞報”“驟警攻城”,第9冊“點兵分擊”“命將夾攻”“解圍卻敵”“破法化虹”。
將該套劇本與國圖善本26冊本、《戲本》25冊本對比后發現,四段《征西異傳》前三出對應第五本;四段《征西異傳》后三出對應第六本(與四段《征西異傳》劇本第一頁紅紙片所寫“六本”相對應);五段《征西異傳》前四出對應第七本;五段《征西異傳》后四出對應第八本;六段《征西異傳》前三出對應第九本;六段《征西異傳》后三出對應第十本;七段《征西異傳》前三出對應第十一本;七段《征西異傳》后三出對應第十二本;十段《征西異傳》前三出對應第十七本;十段《征西異傳》第四、五出對應第十八本;十段《征西異傳》第六出對應第十九本;第十五段前四出對應第二十八本;第十五段后四出對應第二十九本。
五、從《征西異傳》《西異傳》看清宮大戲編創過程
通過對以上諸多劇本的考證和梳理,可以將《征西異傳》和《西異傳》相關劇本的特征及其對應情況進行說明,該劇在有清一代內廷的編創過程中一共產生三類劇本:
(1)《征西異傳》劇本:以《征西異傳》為名,以“段”為演出單位,每段分出且有出目,曲牌曲文完整。分別為《檔案集成》所收錄全部劇本;《戲本》第41冊無段數標識“征西異傳”和“十六段征西異傳 八出總本”;國家圖書館文津街古籍館所藏兩冊劇本;首都圖書館所藏全部劇本。
(2)準《西異傳》劇本:以《征西異傳》或《西異傳》為名,以“本”為演出單位,每本分出且有或無出目,或者不分出。曲牌曲文與《征西異傳》劇本一致,但或有勾畫圈除痕跡。分別為國圖善本26冊本;國圖善本第二十六本鼓板本;《戲本》第40冊第十四、十五、十六本;《戲本》第437冊第二十五本鼓板本;故宮所藏曲譜本(除第一冊“八本 西異傳 曲譜”)。
(3)《西異傳》劇本:以《西異傳》為名,以本為演出單位,每本不分出,曲牌曲文經過刪減更改。分別為國圖善本3冊本;《戲本》25冊本;故宮所藏第一冊“八本 西異傳 曲譜”。
這三種劇本的排列順序事實上也是劇本內容之間的承襲順序。從《征西異傳》到《西異傳》應該有這樣一個大致的過程,首先將以段為編創演出單位的《征西異傳》按出劈開(在原《征西異傳》劇本上進行或另起爐灶,以《征西異傳》劇本封面所題“廿四本 舊十三段、唐 廿五本 舊十三段、唐 十四段 廿七本”即可證明),組合成以本為編創演出單位、分出但沒有出目的《征西異傳》(或《西異傳》)。其次在此一批劇本上進行曲詞、念白等勾畫刪減,最后再進行《西異傳》的謄抄,將原先勾畫的內容徹底從劇本上消除并取消分出,形成最終版本的《西異傳》。
為更直觀的展現各處劇本之間的先后順序及《征西異傳》與《西異傳》改編前后的對應關系,現將劇本根據編演順序排列梳理如下:

劇本不存但可能對應的劇本《檔案集成》收錄《征西異傳》首圖歷史文獻閱覽室藏《征西異傳》《戲本》收錄《征西異傳》國圖古籍館藏《征西異傳》國圖善本室藏26冊本和3冊本《西異傳》《戲本》收錄《西異傳》可能為頭段《征西異傳》第一本第二本第二本第二段前三出第三本第三本第二段后三出第四本第四本第三段第四段前三出第五本第四段后三出第六本第五段前四出第七本第七本第五段后四出第八本第六段前三出第九本第六段后三出第十本第十本第七段前三出第十一本第七段后三出第十二本第41冊無本數標識第41冊無段數標識(應為第八段前四出)第十三本第十四本第40冊十四本(應是第八段后四出)第十五本第40冊第十五本(應是第九段前三出)第十六本第40冊第十六本(應是第九段后三出)第十段前三出第十七本第十七本第十段第四、五出第十八本第十八本第十段第六出第十九本可能為第十一段前四出第二十本第二十本可能為第十一段后四出第二十一本第二十一本可能為第十二段前三出第二十二本第二十二本
雖然現存劇本分散且形態各異,但是已經能夠將這部劇較為完整的串聯下來,并且,筆者據此推算出未注明段數或本數的劇本原有順序,以及其余不存劇本的可能對應情況,還原清楚該劇的前后整體樣貌。除第三段《征西異傳》在改編過程中被棄之不用外,《西異傳》的改編將《征西異傳》的一段分為了兩本或三本,刪減部分曲牌曲文,再取消出目等,大多數念白的更改也是為了使曲牌減少后更加連貫,不影響劇情走向。不過也存在完整的劇本承襲情況,如二十六本《西異傳》的曲詞、念白、科介等和十四段《征西異傳》的前四出完全一致,總的來說兩部戲為異名同本,故事情節相同。
《征西異傳》現存劇本已經達到一百二十出,體量雖不及《鼎峙春秋》《昭代簫韶》等十本二百四十出的連臺大作,但是將其稱為“內廷大戲”是符合編創事實的。通過對劇本的梳理可知,該劇敷衍唐薛家將征西事,從群仙商議教授薛丁山、竇一虎等人助李唐征西開始,唐王御駕親征,攻破界牌關、金霞關、接天關后被困鎖陽城,薛丁山率二路大軍搭救,路上收服竇一虎、竇金童,一路過關斬將后與唐王里應外合攻破鎖陽城。唐王回朝,薛家將繼續西征,先后戰勝了飛鈸禪師、蘇錦蓮等,又收服了陳金定。在唐軍攻打樊江關時,樊梨花將薛丁山三擒三放,最終樊梨花歸唐。在樊梨花的幫助下,唐軍連戰連勝,但薛丁山始終辜負樊梨花令其負氣出走。在攻打白虎關楊凡時,薛仁貴中計誤被薛丁山射殺,唐王派太子為監軍揮師西進,并說服樊梨花再次同行。唐軍征戰楊凡,樊梨花再次排兵布陣大敗楊凡,并分路將其截殺。至此,如果不考慮出目體制或曲詞的因素,那么現有劇本已經可以拼湊出一套從唐王決定征西到大敗楊凡的完整劇本,也就是筆者表格中所推算的《征西異傳》頭段至第十八段或《西異傳》第一本至第三十五本,但該劇是否編創至此,仍需更多新的發現以探究竟。
對于《征西異傳》的相關整理與研究價值,筆者以為目前主要有兩點:
第一,從劇本本身而言,一套內廷大戲劇本包含了大量的總本、串頭本和題綱本,填補了宮廷戲曲劇本整理的相關空白。并且,串頭本、砌末題綱本等為我們了解和探究清代宮廷戲曲舞臺的排演提供了最為直接的信息,是研究清宮戲曲表演藝術的重要參照。而且,以往多認為光緒一朝在大戲上以昆弋翻改皮黃為主,但是從《征西異傳》來看仍有部分昆弋大戲在清末被搬上宮廷舞臺,受到統治者賞識,不過將其改段為本及刪減曲詞等反映了宮廷戲曲的何種藝術走向,仍需從劇本入手進行詳細探究。
第二,根據《征西異傳》的編演內容來看,其與清代章回體小說《說唐三傳》高度一致。雖不能確定戲曲是否直接來源于小說,或是中間由鼓詞等講唱藝術形式發揮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小說應是戲曲的改編藍本,從民間小說到宮廷戲曲經歷了何種改編手段,是劇本整理后需要進行的重要研究方向。劇中薛家將的忠君愛國和樊梨花等巾幗英豪的形象貫穿始終,程咬金、竇一虎等角色充滿喜劇色彩,雖略顯輕浮但卻不令人厭惡,在刻畫人物方面是比較成功的,這其中所透露出的宮廷劇作家的取材和編創風格以及清代統治階級的審美傾向等均值得探討。
清代宮廷演劇一向以劇目眾多、內容豐富而稱道,特別是四大宮廷戲曲均上承前代戲曲或小說之余響。在花部戲曲興起之后,宮廷大戲又和民間戲曲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承上啟下之功顯而易見,例如《鎖陽關》《樊江關》《馬上緣》等各種梆子劇目與《征西異傳》之間枝附葉著,甚至有可能從大戲當中抽出來“改調而歌之”,當然,這一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進一步整理研究《征西異傳》可以從中揭示出清宮大戲的編創理論、演出特色,有助于對眾多薛家將劇目的形成和演變有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