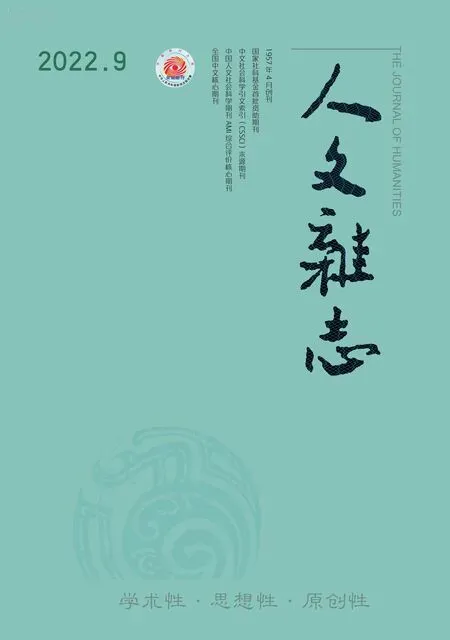被誤讀的朱光潛:對陶淵明公案的澄清*
朱光潛與陳寅恪圍繞陶淵明闡明各自的學術立場和論辯關切,展開過學理爭鳴,這是不爭的事實。學界后期多有探討,主要集中在爭議與釋義、闡釋與轉換以及整合與重塑等諸多方面,引起諸多學者的誤讀乃至誤解。面對學界紛繁復雜、眾說紛紜的討論,時至當下,重回這段詩學爭鳴的歷史,重新審視《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陶淵明》的文本本身,厘清有關問題,還事實以真相,是值得再探究和再省思的問題。
一、誘因暗含:是“心悅誠服”還是執著追求?
20世紀30—40年代末,以陶淵明為研究對象,學界發生過兩次重要的學術爭辯。一次是在“京派”與“海派”兩大文化陣營對壘的背景下,魯迅在雜文《“題未定”草(七)》中批評《說“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答夏丏尊》所論,認為朱光潛對錢起詩的評價是尋章摘句、以割裂為美,“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批評語言極為犀利,矛頭直指朱光潛提出的“靜穆”論斷,“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為并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為‘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凌遲了”。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朱光潛選擇“沉默”的方式予以應答,“為避免陷入一場真正的筆戰,因此我決定沉默”。學者就誤認為朱光潛已“心悅誠服”地接受批評,“在《西方美學史》里,他完全接受了魯迅的觀點,并以此批評了溫克爾曼”。第二次是朱光潛對陳寅恪的《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一文中的部分論斷提出質疑,隨后發表《陶淵明》。朱光潛在回憶這段歷史時道:“二十年前就已蓄意寫一部《魏晉人品》,想在魏晉時代選十來個代表人物,替他們寫想象的傳記(如同Ludwing和Maurois所做的),綜合起來可以見出那個時代的精神,這些年來,我頗留意中國詩,也想挑選一些詩人出來作一種批評的研究(如同我去年寫的《陶淵明》那一類文章)。”這是1946年10月《陶淵明》發表在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后,時隔兩年即1948年,朱光潛接受《大公報》記者采訪時的一段真實獨白。大致可以推算出,所謂“二十年前”,也就是最晚不遲于1928年,朱光潛還在愛丁堡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就已有撰《陶淵明》等寫作構思和寫作規劃,表明他更早就可能已經關注甚至研讀了陶淵明相關詩作和研究史料。另外,朱光潛在1948年增訂版的《詩論》中增加了三章,《陶淵明》一文收錄其中,并作為全書的第十三章。增訂版序言:“從前我還寫過幾篇關于詩的文章,在抗戰版中沒有印行,原想將來能再寫幾篇湊成第二輯……《陶淵明》一篇是對于個別作家作批評研究的一個嘗試,如果時間允許,我很想再寫一些像這一類的文章。”結合《大公報》記者采訪史料和1948年《詩論》增訂版序言,不難發現一個問題,朱光潛何以將原本屬于“個別作家作批評研究”范疇的《陶淵明》納入增訂版,而不等日后編入《詩論》第二輯?答案其實就隱藏在寫作《陶淵明》的直接誘因和間接誘因之中。“朱光潛撰《陶》,其直接誘因,是對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一文的‘接著說’。”夏中義的這一判斷,不論是就兩文發表時間的先后順序,還是就文章內容而定,都是確信無疑、無可置辯的。探明直接誘因的存在之后,還需仔細甄別隱秘的間接誘因。
間接誘因的存在是基于對客觀事實的判斷。宛小平提供的史料極具參考價值,他在《功利與超功利——從朱光潛和魯迅的一場爭辯談起》中說道:“金紹先回憶了他在1941年到樂山(抗戰時武大校址所在地)拜訪朱光潛時就這場紛爭所進行的訪談。商金林在1979年至1986年這七年間曾多次與朱光潛接觸,并談及朱光潛與魯迅的這場爭論,他所記錄的朱光潛的回答和金紹先的回憶文章‘相吻合’。”關于材料中提及的訪談事宜,金紹先整理并撰寫《“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憶朱光潛與魯迅的一次分歧》一文,于1993年發表于《文史雜志》。這段材料和金氏的訪談回憶可以說明上述問題。首先,訪談涉及問題分歧的實質。1941年距朱、魯爭辯事件過去不足6年,這期間朱光潛雖未發表任何文字予以“還擊”或再論辯,“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內心接受了魯迅的批評,在私下場合,一有機會,朱光潛仍要說明他與魯迅在此問題上的分歧實質是什么”。朱光潛認為他與魯迅“分歧實質”是對文學批評范圍認知的不同,他指出魯迅“沒有把他的意見僅僅局限于文學批評的范圍”。在此基礎上,朱光潛進一步論及文學藝術審美共同性與差異性的問題,強調這場爭辯不是文學藝術審美差異性的分歧,而是魯迅的批評是否屬于審美批評的問題。他在訪談中說道:“所以嚴格說來,這不是一個審美差異性的問題,而是是否屬于審美的問題。”言下之意,魯迅的批評范圍超出了文學藝術審美的范疇。其次,訪談的內容來看針對性強。朱、魯之爭,表面上以朱光潛“沉默”而告終,但爭鳴的余波并未平息。在訪談中,朱光潛不僅毫不避諱此類問題,而且針鋒相對地亮明自己的主張和觀點。“‘美學’一詞是德文‘感性’之意,它不涉及理性分析研究,因而也不涉及功利的判斷。”朱光潛從美學超功利的視角出發,堅持自己的主要立場,“認為文學藝術是一種審美創造活動,它的創造者應當以一種超越一切憂喜的純粹審美的態度來觀照社會人生,而不應當直接卷入社會人生中的紛繁矛盾沖突之中”。最后,從訪談的結論來看,朱光潛的觀點鮮明。朱光潛說:“我認為魯迅先生不幸把他的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復雜的社會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誠如他自己所說的,他看見日本人砍中國人的頭就決定從事文學,以改造國民的精神。但文學其實并不具有這種偉大的功能。政治的目的應當用政治的手段去實現,而我們中國人從傳統上總是過分夸大文學的力量,統治者也由此總是習慣于干預、摧殘文學,結果是既于政治改革無效,也妨礙了文學自身的發展。”僅從闡述的視角來看,朱光潛認為魯迅對他的批評,完全依據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性,并過分夸大了社會政治功能性在文學藝術的美感觀照和美感體驗中的作用,完全忽略了文學藝術本身所具有美感的一面,從而認為魯迅批評帶有偏見性。明乎以上,在金氏的訪談回憶文中,就涉及此次爭辯的具體問題。朱光潛的應答,不論是分歧實質、針對內容還是結論觀點,均表明他與魯迅學術取向和審美旨歸存在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性突出地表現在文學藝術審美的功利與超功利上。對于魯迅的批評,朱光潛既非全盤接受,也非全面否定,他回應道:“審美應當是超功利的,但不一定與功利絕對不相容。”此觀點從朱光潛對《陶淵明》“靜穆”論的修正中便可得出,他有意識地隱去“渾身”的字樣,以此糾正在《說“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答夏丏尊先生》一文中用語不當的問題。此外,王攸欣的判斷也表明朱光潛撰寫《陶淵明》與魯迅的批評極為相關。他指出:“受到魯迅的批評,使朱光潛早就立意,就他涵泳已久的陶淵明,全面闡述自己的觀點。后來又在對《詩論》的不斷修改中,反復細讀古人詩集……陶淵明自然成為他的首選。”由此,朱光潛的“沉默”絕不是其面對學術責難應有的方式和態度,在合適的時機,他一定會再次闡明或重申自己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觀點。宛小平的判斷亦是如此,他說:“對于學術爭論,朱光潛素來是有來必往的。”
自從2003年10月中央出臺 《關于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實施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又出臺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動東北全面振興。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關心東北,多次對東北振興發表重要講話,提出明確要求。大連市委市政府積極響應國家戰略號召,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以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為指引,深入實施 “四個著力” “三個推進”,結合大連實際,圍繞 “兩先區”建設目標,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勇于創新,銳意進取,在全面振興發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東北全面振興發展中領頭羊和排頭兵地位凸顯。
明晰了“間接誘因”的存在,再回答何以難尋的問題。仔細品味《說“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答夏丏尊先生》和《陶淵明》這兩篇作品,這個問題便迎刃而解,現茲引錄,以便疏解:
“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以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里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淵明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水利普查數據處理和西部湖泊測量。完成水利普查成果建庫和查詢及服務系統開發,為第一次全國地理國情普查等重大任務和項目提供信息服務,完成2 866套縣級水利普查空間數據電子成果圖制作和分發;完成水利普查成果建庫和查詢及服務系統開發。開展河湖普查成果整編和分析工作;組織完成西部地區重要湖泊工作,完成羊卓雍錯、扎日南木錯和博斯騰湖測量。
揭示了朱刻意要說陶“儒多于道”,其根子,是在朱要為自己“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之角色自期提供隱喻型鏡子。“隱喻”系修辭格,其特點是在“本體”與“喻體”間不置系詞“像”或“是”,然執筆者明瞭他為“喻體”寫的每一字,皆是為了暗示“本體”的性狀。這就是說,假如朱自信他把陶“道大于儒”寫成“儒多于道”,不僅是動機使然,且在學理上也說得通;那么,他作為一個在紅樓清園著書教書的學者(跡近“道”之“出世”和“看戲”),若想到公共空間去議政,參政(跡近“儒”之“入世”和“演戲”),其內心也就無甚精神障礙了。倒過來說或許更恰當,即朱在1945—1947年已不滿足于“大隱隱于學”或“坐而論道”,他頗想上社會—政治舞臺“起而行道”,故才別具匠心地把陶寫成了“儒多于道”或“內儒外道”。
非生長季自然覆蓋物主要為凋落物與積雪。凋落物積雪是否存在及其厚度對土壤溫度高低及變化程度有很大影響,尤其是在低溫的冬季。凋落物或積雪能夠改變(增加)所覆蓋土壤的溫度,從而對溫室氣體的產生和排放產生影響。例如較厚的覆蓋層能夠隔離表層土壤與低溫空氣,降低土壤凍結的強度及凍結的深度,這種環境會有利于反硝化作用[41,34]。據報道冬季放牧會減少土壤調落物覆蓋,從而導致凍融期草地N2O排放顯著降低[15]。
淵明在中國詩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擬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闊大多變化,但是都沒有他那么醇,那么練。屈原低往復,想安頓而終沒有得到安頓,他的情緒、想象與風格都帶著浪漫藝術的崎嶇突兀的氣象;淵明則如秋潭月影,澈底澄瑩,具有古典藝術的和諧靜穆。杜甫還不免有意雕繪聲色,鍛煉字句,時有斧鑿痕跡,甚至有笨拙到不很妥帖的句子;淵明則全是自然本色,天衣無縫,到藝術極境而使人忘其為藝術。
夏中義曾對朱光潛與陳寅恪這段爭論有過揣測,他說:“這與其說,朱特別青睞陶這一魏晉文化的人格符號,毋寧說,他期盼借陶的‘儒多于道’,來為其人生角色的自我品鑒,提供隱喻型鏡子。”夏中義從朱光潛的人生角色定位、選擇、自期以及演繹等四個方面論及具體的緣由,主要依據是朱光潛在1926年到1947年間撰寫的《悼夏孟剛》《談人生與我》《看戲與演戲——兩種人生理想》三篇文章,認為“朱已將其人生角色選擇置于中國文化譜系作謹慎考量”,見解是較為獨特的,是對朱光潛相關著述做了充分探究后而作出的有價值的判斷。1933年,朱光潛回國赴北大任教,后雖經歷了命運多舛、顛沛流離的生活,但其主要投身于治學和教學之中,所接觸的文化和文人也均有“中國文化譜系”的烙印。置身中國文化譜系大環境之中,朱光潛的人生角色選擇受到文化傳統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否如下文引錄所言,恐怕還需謹慎商榷。
回溯到文本,探經朱光潛與陳寅恪對陶淵明的分歧之所在,就必然要探尋其討論的出發點和結論。陳寅恪所論《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主要著眼于兩個部分的思考。第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對陶淵明之前魏晉以來清談思想發展演變的歷程。第二部分重點闡述陶淵明在以清談為主色調的社會思潮下,棄“舊自然說”而創構“新自然說”。“新自然說”的要義在于“委運任化”,即“混同自然之旨自不可謂其非自然說”,以達到“惟求融合精神于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最終將陶淵明定性為:“故淵明之為人實外儒而內道,舍釋迦而宗天師者也。”朱光潛擺明自己的立場,稱《陶淵明》的出發點是建立在“這些話本來都極有見地”的基礎之上,不是對陳寅恪觀點的全盤否定,這一點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朱光潛的批評體現在:一方面,不能簡單地把陶淵明籠統地皈依“一教”,“不是一個拘守系統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另一方面,既然不能簡單地斷定陶淵明皈依“一教”,朱光潛對陳寅恪所下的“絕對沒有”受佛教思想影響的判斷持懷疑態度,并以陳寅恪所引《形影神》詩論證陶淵明沒有佛教思想的例子反證陶氏“意識或下意識中可能有一點佛家學說的種子”。基于這兩個方面的批評,朱光潛對“新自然說”也提出異議,“淵明尚自然,宗老莊,這是事實;但是他也并不非名教”。最后認為:“在這整個心靈中我們可以發現儒家的成分,也可以發現道家的成分,不見得有所謂內外之分,尤其不見得淵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說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的傾向比較大。”從“近于人情”“富有熱情”的角度,朱光潛以“有意要做某一家”為假設的前提條件,提出陶淵明“儒家的傾向比較大”。這也是朱光潛為何沒有從社會思潮背景立意,而是從陶淵明身世、交游、閱讀、思想、情感生活以及人格與風格等入論的根本原因。因為陶淵明“是一位絕頂聰明的人”,社會思潮對他肯定有一定的影響,但不會起決定性的作用,也許這就是朱光潛稱陶淵明偉大之所在。
二、儒道泯化:是“隱喻己身”還是一片天機?
《陶淵明》的發表,其“直接誘因”是批評陳寅恪,暗含的“間接誘因”就是對魯迅批評的反駁。這段公案的直接、間接誘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朱光潛面對魯迅的批評,在十余年的時間里雖選擇“沉默”,但并不表示“默認”,更不是后來學者所認為的“心悅誠服”。朱光潛對這段過往的爭鳴經歷,有過比較客觀的認識和評價,他說:“陶淵明《讀山海經》《詠荊軻》等詩,的確也有‘金剛怒目’之態,我說他渾身都是‘靜穆’是不準確的,但魯迅說陶潛之偉大正在于他的‘金剛怒目’,我想這恐怕又是出于一種特殊的利害判斷了……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卻只能是陶詩罕見的一種變奏。我說他‘渾身都是靜穆’,是指陶詩主流而言。”這也是在與陳寅恪辯論中撰寫《陶淵明》時再次有針對性地提出“和諧肅穆”“和諧靜穆”論斷的緣由。一方面是對前期“渾身是‘靜穆’”論斷的修正,另一方面是對陶淵明個人情感、詩歌藝術主流特質的肯定和贊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更是一種對治學求實精神的執著追求。
在對陶淵明的討論上,朱光潛與陳寅恪最大的分歧在于“儒多于道”和“外儒內道”的結論性爭辯。他們看問題的視角雖有不同,但所論皆有依據,給后來學界留下了進一步思考的空間,以至于當下諸多學者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或贊成朱光潛,或贊成陳寅恪,但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兩位學者爭論的根源。是否有陶淵明式的“異化”的現象,也就是“儒多于道”或“外儒內道”還是“隱喻己身”,特別是朱光潛對陶淵明的評價“儒多于道”是否帶有自己的社會政治目的,都是值得繼續探索的問題。
通過仔細比較朱光潛對陶淵明的三種不同評價,便可清晰見出修正或糾偏的痕跡。在《說“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答夏丏尊先生》一文中,朱光潛以“情趣”入論,從欣賞和創造兩個維度剖析“《談美》里所說的話尚有不圓滿處”。這種“不圓滿”具體表現在他前期只品讀出了“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是凄涼寂寞的情感,沒有領悟到詩的佳妙——“靜穆”。于是朱光潛在“沒有很講究用語的分寸”的情況下,提出“陶淵明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的論斷。在魯迅提出批評后,朱光潛應有過反思,在《陶淵明》中刻意斟酌用詞,針對陶氏的情感生活和詩歌藝術分別提出“和諧肅穆”“和諧靜穆”的觀點,其用意在于消解或淡化“渾身是‘靜穆’”的一概而全的言論。這一點在《西方美學史》中得到印證,朱光潛說:“當時德國知識界對于希臘古典的看法,頗近似我們過去對于陶潛的看法,仿佛陶潛也是渾身靜穆,只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一面,沒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長在’的一面”。在撰寫《陶淵明》的過程中,朱光潛隱含了對這方面的深入思考,這便是“間接誘因”難尋的原因之所在。
淵明在情感生活上經過極端的苦悶,達到極端的和諧肅穆。他的智慧與他的情感融成一片,釀成他的極豐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為人和他的詩一樣,都很淳樸,卻都不很簡單,是一個大交響曲而不是一管一弦的清妙的聲響。
對于“隱喻型鏡子”是朱光潛撰《陶淵明》動機或者說陶淵明是朱光潛“自我角色隱喻”的推論,似乎是牽強的。朱光潛與陳寅恪關于陶淵明研究的爭辯學理性極強,兩位學者從各自不同的學術認同點出發,闡發各自的解讀,本是學界極為常見的學術爭鳴,若附加“隱喻己身”的含義,情況頓時變得復雜了。夏中義稱,1945—1947年,朱光潛想通過《陶淵明》表達自己社會政治舞臺“起而行道”的思想,故將陶淵明闡釋為“儒多于道”的形象,實際上不符合朱光潛為學、為人的風格和宗旨,通過此時期朱光潛的“一文兩事”即可澄清。
宛小平《朱光潛年譜長編》中收錄《談心》一文中稱,“此文未收入安徽教育出版社和中華書局出版的《朱光潛全集》,是一篇很重要的先生的‘自述’”。可以說新史料的發現,為揭示朱光潛這一時期的真實心境提供了有力的論據。朱光潛在《談心》中說:
過去的事嘗不免令人追悔,現在仿佛是一個流浪人在蹉跎許多歲月之后,漸向家園歸宿了,我以靜穆的心情憑眺我的晚景,我從來沒有經過很舒適的生活,卻也沒有經過很苦的生活,一向隨遇而安,將來簡單的生活也許還不難維持。功名事業,我素來不大感覺興趣。少壯既沒有從事于此,到老來想不會為此勞心焦慮。
由此觀之,與其說朱光潛筆下的陶淵明具有“社會—政治舞臺‘起而行道’”的隱喻性,不如說這種隱喻性是朱光潛撰《陶淵明》“觸物即發,純是一片天機”所致。“大詩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養成一首完美的詩,充實而有光輝,寫下來的詩是人格的煥發。”陶淵明如此,朱光潛亦如此。
此文發表于1947年6月的《自由文摘》,從“今年我已經快滿四十八歲”推算,應該寫于1945年,早于《陶淵明》一年左右。這段談心式的獨白,已經昭示出朱光潛內心的真實愿景。文中提及的“功名事業”即是學者所謂的“社會政治舞臺”。朱光潛明確表示,少壯時期的他對“功名事業”就不曾有想法,何況寫作《陶淵明》時,他已經步入“知天命”的人生階段。若認為在這一階段,朱光潛要在“社會政治舞臺‘起而行道’”,恐怕難有實據為證。《談心》《陶淵明》兩文創作時間如此接近,若朱光潛真想在《陶淵明》中,以陶淵明“儒多于道”來表達自己在“社會政治舞臺”上的訴求,實現“隱喻己身”的目的,又怎會有“功名事業,我素來不大感覺興趣”的直抒胸臆。此外,還有兩件事情可驗證朱光潛《談心》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一事發生在1945年,朱光潛下定決心辭去武漢大學代理校長、教務長職務。朱光潛在《我的簡歷》中說道:“1945年夏,校長王星拱生病就醫,我代理校長,因校務和工學院長鬧意見,我堅持撤他的職,我也辭去教務長職。”另外一事發生在1946年,朱光潛辭去國立安徽大學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實際上就是辭去安徽大學校長職務。“抗戰勝利后內遷的學校籌備復原,偽教育部長朱家驊接受副部長杭立武(我的同鄉和留英同學)的建議,任命我當安徽大學校長,我不愿意搞行政職務,辭了沒有就,回到北大。”雖然朱光潛在“三反”“五反”中這樣闡述辭職不就的動機:“抗日勝利后,朱家驊聽從杭立武的推薦,要我去辦安徽大學。我沒有去安大而回到北大,這有兩個動機。第一是看北大在全國大學中地位最高,而且有胡適做校長,我想靠著他,在文化教育界形成一個壓倒一切的宗派,就是造成一個學閥。其次,安徽的局面小,北京局面大,當時除南京以外,北京是一個反動政治的中心,活動的范圍比較大。”但這段迫于種種壓力所形成的文字,較《談心》而言,是不可信的,其真實原因應該是“我不愿意搞行政職務”。朱光潛堅持回到北大,刻意回避了在“社會—政治舞臺‘起而行道’”,其真實意圖誠如他自己所言:“今天的中國,已經難得有能夠安心學術研究的學校了,北京大學是唯一可以研究學術的地方,我們北大人應該承擔起中國學術的重任。”至少可以說明,朱光潛在1945年至1947年期間,階段性的人生目標是研究學術而非“隱喻己身”的陶淵明式的“儒多于道”。“我們從朱光潛對陶淵明的評價中,不難看出他的‘移情作用’,如果說陶潛在他心目中是一個非儒非道非釋的大詩人,那么朱光潛美學和中國傳統美學的關系也非儒非道非釋所能框定,倒不如是亦儒亦道亦釋的學者。”宛小平這一評價是較為合理和客觀的。
基于朱光潛與陳寅恪治學路徑、研判思維、闡釋視角的不同,對于這段公案,學界還提出另外一種質疑和判斷,主要集中在朱光潛、陳寅恪對陶淵明的思維特質是“求甚解”還是“不求甚解”的研判上。夏中義提出:“(朱光潛)認定陶淵明的思維特質,決定了他大凡讀書,必‘不求甚解’。”依據是朱光潛言及陶淵明“思想未必是有方法系統的邏輯的推理”。他認為“朱光潛是據此來微詞陳寅恪”,沒有達到“與陳針鋒對接”的效果。為深刻闡明這一判斷的合理性,夏中義從朱光潛早年述學的學理書寫入論,說道:“雖常列舉古漢詩,但看得出,這是為了潤色其學理書寫,而非以古漢詩為學術專攻,故所列舉者,大體擷取其在桐城私塾的‘童子功’”。并將朱光潛與錢鐘書讀古書的方式做比較分析,帶有一定的學術傾向性,揚錢抑朱,似可商討。他言明:“與錢鐘書相比,朱光潛之讀古書,或真稍欠火候。關鍵當對‘求甚解’之‘甚’字,作注釋。朱是草草帶過,錢卻引經據典。”在這一層面上,夏中義進一步認為“朱光潛之讀陶,不可為薄,然失之不深”,“陳寅恪視《形影神》為‘最可窺見’陶之思想‘宗旨’者,當極具慧眼”。由此映射出朱光潛與陳寅恪的陶淵明之爭,不僅論及陶淵明藝術思維特質,而且涉及朱、陳闡釋陶淵明時各自的名理思維特質。這一名理思維特質,實際上就是美學家和史學家探討同一學術問題的思維模式和思維方式。前者具有“一種哲學的意蘊”,后者以史學考證為其專長,兩者雖有學術取向上的不同,但應無價值優劣之分。就《陶淵明》與《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兩文涉及陶淵明“求甚解”或“不求甚解”的問題而言,難以延伸判定陳寅恪更為理解陶淵明。此問題可從探究《陶淵明》醞釀、創作、發表乃至收錄之艱難歷程,清晰辨明朱光潛所撰《陶淵明》,并非逞一時之能、圖一時之快的學術“快餐”,而是深思熟慮、深圖遠慮的學理論辯,在某種層面上也是力求深入理解陶淵明的一種學術路向。
三、詩學涵泳:是“不求甚解”還是蓄力已久?
日本政府促進開放式創新的政策近年來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日本政府發展開放式創新的原因除了國際性的強化企業競爭力的需要外,一方面是日本社會面臨的高齡少子化帶來的國內市場的縮小和消費階層的變化等“需求面”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供給面”問題;另一方面是發展超智能社會(Society 5.0)的需要。同時,這兩個重要原因也必將導致包括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在內的研究人員、用戶、國民的參與和企劃,這也將促進日本版的開放式創新向2.0升級。■
原料:八甲基環四硅氧烷(D4)、3-[(2,3)-環氧丙烷]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異丙醇、四甲基氫氧化銨(TMAH)、鹽酸、三甲胺鹽酸、氘代氯仿均為分析純試劑;環氧封端劑為自制。
陶淵明在朱光潛的治學生涯中分量極重。1924年,時年27歲的朱光潛在第一篇美學論文《無言之美》中,便以陶淵明《時運》《讀〈山海經〉》《歸園田居》詩作為分析“言不盡意”之美的例證,他說道:“譬如陶淵明的《時運》,‘有風自南,翼彼新苗;’《讀〈山海經〉》,‘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具;’本來沒有表現出詩人的情緒,然而玩味起來,自覺有一種閑情逸致,令人心曠神怡。”雖不是真正意義上研究陶淵明的專論,但這種信手拈來的、恰到好處的引用,非長期的詩學涵泳不能為之。如在《給青年的十二份信》《文藝心理學》《談美》等著述中,均有陶淵明詩歌作品的身影,此類例證,不勝枚舉。但需要指出的是,朱光潛論及“心界的空靈”的“靜趣”時,引用五首古詩闡述這種“靜”的具體表現時,陶淵明的《時運》《飲酒》就名列其中。這與后期朱光潛進一步提出陶淵明的“靜穆”論是不無關系的。較早投身陶淵明研究的朱光潛,1926年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中國文學之未開辟的領土》,文中以個別作者為研究中心的形式,“假想陶淵明生在英國或法國,看英或法的學者用什么方法,取什么程序去研究這位大詩人”。從后文設想的研究方法和程序來看,實際上就是后來《陶淵明》一文的大體框架,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均濃縮在了此文中,或換言之,《陶淵明》是《中國文學之未開辟的領土》中已醞釀就緒的學理構建。同年,朱光潛在《談讀書》一文中,明確將《陶淵明集》納入“老早就讀些壯年必讀書”之列。此后,在《說“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答夏丏尊先生》一文中,首次提出“陶潛渾身是‘靜穆’”的論斷,引發魯迅撰《“題未定”草(七)》進行強烈的反駁和批評。時隔多年,朱光潛就陳寅恪的《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進行回應,撰寫了《陶淵明》(上下)發表在《大公報·星期文藝》上,此文后收入1948年增訂版的《詩論》中。1956年,朱光潛發表《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一文,自我剖析了對陶淵明的重新認識,“我過去吸收書本知識,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都有這種割裂和歪曲的習慣……比如說陶潛,我把《述酒》、《詠荊軻》等詩所代表的陶潛完全閹割了”。在飽受學人爭議和詬病的情況下,這種“反思”對朱光潛晚年研究陶淵明幾乎沒有產生任何負面影響。1984年再版《詩論》時,未刪減《陶淵明》一章,也未吸納1956年“反思”內容以修正或糾正《陶淵明》中的任何論斷,可見此文重要性。89歲高齡的朱光潛,在人生最后的歲月里,在致胡喬木的信中依舊提及《詩論》,“本想寄拙著《詩論》二冊,恰遇放假,沒有取得存書,只有待三聯書店開門的時候,才能取出寄上請教”。簡要梳理以上史料可見,從1924年至1986年,62年的時間里,陶淵明不僅是朱光潛的詩學研究的主要對象,而且逐漸演化為美學研究領域的重要“意象”,即“意象化的陶淵明”。
綜上所述,朱光潛不僅醉心于陶淵明的詩、賦、文等文學作品,而且似乎更執著于文學作品背后所折射出的陶淵明的精神世界。這種持續關注的時間跨度之久、用情之深,在學術史上都是不多見的。《陶淵明》創作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朱光潛詩學素養逐漸積淀、詩學理論逐步構建的過程,似非“桐城私塾‘童子功’”擷取可以簡要概論。王攸欣在審視朱光潛寫作《陶淵明》時給予客觀的評價,他說:“朱光潛談陶淵明的身世和交游,根據陶淵明本人的詩文,顏延之所作《陶征士誄》,徐爰所作《宋書·陶潛傳》,昭明太子蕭統的《陶淵明傳》等史傳,以及梁啟超、古直等人的成果,參以自己的判斷,簡略而平實”。這種“簡略而平實”風格,既是朱光潛撰寫《陶淵明》的語言特色,也是其闡發《陶淵明》的名理思維特質。至于朱光潛在《陶淵明》中批評陳寅恪“求甚解”,是從陶淵明自己讀書喜好角度而言,“淵明讀書大抵采興趣主義”。也正是基于陶潛讀書有“不求甚解”的特點和習慣,朱光潛認為陳寅恪“把陶淵明看成有意地建立或皈依一個系統井然、壁壘森嚴的哲學或宗教思想,像一個謹守繩墨的教徒”,是一種苛刻的“求甚解”。其實質在于言明,陶淵明身上儒釋道或可兼具的特點,不拘于某一派或某一宗。此為朱光潛在全面考察陶淵明后的理性判斷。
該變壓器油箱為鐘罩式油箱,變壓器頂部為平頂結構,中性點套管布置在油箱頂部西側,套管的安裝采用在變壓器頂部焊接固定螺栓后,利用環型鋼圈將套管瓷套固定在焊接的載絲螺桿上,同時起到固定套管和對開口部位進行密封的作用。套管結構圖如下所示:
綰結而言,朱光潛撰《陶淵明》是基于兩個事實:一是直接反駁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中的部分論斷,二是對魯迅批評的回應。一明一暗的誘因,形成了陶淵明公案的兩條學術爭鳴的主線。澄清了這一問題,學界的諸多疑惑也就逐漸明晰。《陶淵明》可以說是朱光潛畢生的心血結晶,不論是篳路藍縷的研究歷程還是后期論戰的慘遭非議,朱光潛以其深厚的詩學涵養,以對陶淵明熱愛乃至“英雄般的惺惺相惜”,憑借執著追求的治學求實精神,蓄勢待發的學術積淀,與陶淵明一起在一版天機中呈現出睿智的人格魅力和多彩的精神世界。誠如宛小平所言:“陶公的人格不過是朱先生人格的反照,他們的精神境界是何等的相似。”
現代學術史上的這段公案,以及圍繞這段公案的當代學者的諸多學理闡釋,都是一筆思想深刻、內容豐富、見解獨特的文化遺產。面對如此珍貴的文化盛宴,如何從文學史、學術史、思想史等方面,科學釋讀爭鳴期間的文本,全面把握這段公案的史實,有效提煉諸家思想的精髓,仍是任重而道遠的學術難題。在浩瀚的文獻史料中,要破解難題、澄清疑惑,絕非一朝一夕之易事,還需在宛小平、夏中義、王攸欣等當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接著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