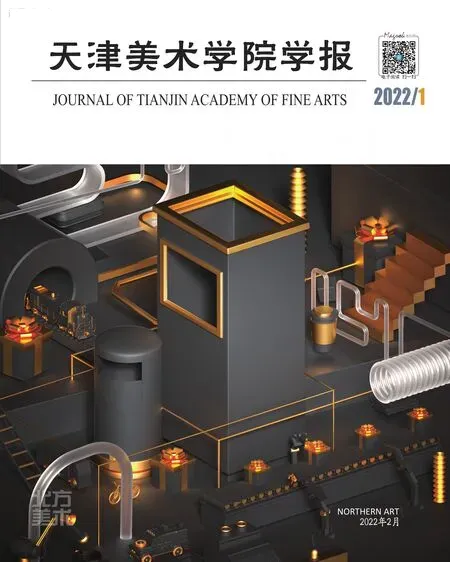以現代創作理念傳承與創新傳統藝術
一、引言
隨著新材料、新技術、新思維等各種思潮的不斷涌現,傳統的藝術創作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新的形勢。這就要求當代藝術創作者緊跟時代腳步,用個性化的創新形式和極具感染力的表現方法,用自己的藝術作品傳達出某種精神,創造出一種氛圍。其主流是東西方文化的融合與創新。為此,本文提出“通過現代創作方式傳承和更新傳統創作元素”這一課題,旨在論證如何通過現代創作方式傳承、更新并吸取有代表性的傳統文化元素。本文從藝術演變過程、創作現狀、未來發展等方面,結合作品《紅》《藍》《白》的創作,闡明只有在民間文化元素的基礎上,運用現代創作方式,不斷融合創新,將新思維、新理念與本土文化相契合,將其中的精神意蘊通過當代藝術創作手段重新組合演變成新的藝術形式,才能創作出既有文化底蘊和生活情趣,又有藝術想象空間的全新的藝術精品。
二、藝術創作的主題與時代
完整的藝術創作猶如一首優美的樂曲,或清淡,或典雅,或和諧,或對抗。即使是“休止”中的瞬間寧靜,也有著異乎尋常的美。這一切都源于藝術創作的主題與時代。
主題是藝術創作的中心思想,是創作中所顯示的總的思想意義,是創作的靈魂,是材料取舍、結構安排、線條運用、色彩構成的依據。藝術創作雖受制于主題,但并非簡單的文字解說和外包裝。它要求創作者以深刻的思想內涵展現主題旋律、節奏起伏、時空感受,運用理性化的意識展示創作中的各種要素。精準的形式選擇、嚴謹的圖像設計、時空感受中的留白處理、合理的色彩搭配、個性化的材料運用等,都是現代藝術創作的新理念、新形態。
藝術創作的主題是由生活素材所決定的。生活的豐富多彩決定了創作題材的多種多樣,題材的多種多樣又受制于藝術創作的主題。因此,藝術創作的主題必須明確、單純、鮮明、深刻,并且要新穎獨到、別具一格。為此,藝術創作者還要進一步明確藝術創作中素材、題材、主題三者之間的關系。素材是一切存在于現實生活中的原始材料。題材是在素材的基礎上,按照表現主題的需要,經過精心選擇,將用來表現藝術主題的那些材料進行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加工提煉而得來。因此,人們把題材稱為“第二現實”。
素材是題材的基礎。素材積累得越豐富,越有助于正確地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和主流,越有助于表現藝術創作的主題。積累豐富的生活素材,可以為藝術創作提供豐富的題材。如果素材范圍太小,則很難取得適用的題材。除此之外,在藝術創作過程中還要注意作品主題的深入開掘與提煉。藝術創作的主題與時代密不可分。它承載著當代社會的各種思想,生動地表現人們的審美需求、欣賞習慣以及時尚、前衛與新潮。因此,藝術創作的主題必須新穎獨到、別具一格、緊跟時代、不斷創新。
三、傳統與現代的關系
藝術創作中,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是互為制約、共同存在的。只有兼收并蓄,在傳統和現代藝術中尋找創新點,才能創作出與眾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的時代精品來。
筆者的藝術作品《紅》(圖1)主要是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融合現代藝術創作理念,讓傳統與現代相結合,從而形成新的藝術風格,并以此來展示中國文化藝術創作的傳承魅力和創新風格。

圖1 紅 李銘實設計作品
作品《紅》中出現的“門(門)”,最早在甲骨文里是個象形字,上面是一條嵌入門樞的“橫木”,下面是兩扇“門”;金文去掉了“門楣”,小篆承接金文;后來的隸書、楷書字形逐漸方整,變成了“門”。《說文·門部》:“門,聞也。從二戶。象形。凡門之屬皆從門。”可見,人類從遠古走來的時候,藝術創作就開始了,而這一切在歷史進程中從未離開過傳統。據此,筆者將“門”設計成傳統與現代的結合體,既是中國漢字,又仿佛象征著敞開著的世界文明交流之門。兩對頁中的左、右之門,既有“陰”“陽”之意,又襯托著節日中的人們團團圓圓、相互協作的和美景象。
作品《紅》中出現的紅蓋頭,最早是南北朝時齊國婦女為避風御寒蓋在頭上的頭巾,唐初演變成帷帽。唐開元天寶年間,婦女在帷帽上再以薄紗遮面作為裝飾。元朝時,為了喜慶,新娘的蓋頭一律用紅色。帶著這樣美好的歷史傳說與喜慶祝福,這種習俗一直延續到了今天的傳統婚禮中。
作品《紅》的色彩總體為紅色。紅色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寄托,以紅色為基調的藝術題材包羅萬象,如紅領巾、紅旗手、紅袖標、紅花、剪紙、窗花、紅火盆、喜字、燈籠、爆竹、紅蓋頭、紅布、紅蠟燭等。這些帶有民俗故事、蘊含歷史文化、體現時代氣象的美好事物,彰顯的是生生不息的濃厚的中華民族精神。
作品《紅》所確立的紅色調既激發了筆者在創作過程中的想象力,又調動了觀賞者的思維,充分表達了傳統題材與現代題材可以自由融合、相互滲透的創新理念。當代最受歡迎的藝術創作往往是既有傳統意蘊又富于時代特征。這就要求藝術創作者必須認真學修民族傳統文化,讓自己具有一定的傳統文化積淀;在以傳統文化為創作素材的同時,讓藝術品的形式感、造型性、色彩性、韻律性等方面能夠流暢自然地表達自己的創作理念。
以下再以筆者的作品《藍》(圖2)為例予以說明。

圖2 藍 李銘實設計作品
2008北京奧運吉祥物福娃的設計者韓美林在《人民教育》的一段訪談中說,藝術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須有“根”,而這個“根”就是中華民族之根。藝術的“根”是扎在多姿多彩的生活當中的,扎根在我們民族幾千年的優秀民族文化中的。她是撫育中華大地上每一個藝術家的母親。同時,他還非常強調藝術的個性、民族性和地域性。①
《藍》這一作品展現了民國時期女學生裝的特征:藍竹布褂黑短裙,袖短露腕呈喇叭;下擺圓弧襟邊花,衣裝盡展女風華。這種女學生服裝既擷取了傳統的民族服飾元素,同時又結合了西式服裝的特點:上衣由直筒式改為收腰式,將寬大的袖子改成上貼下散式,高領仍保留;下裳則改成縮至小腿的裙子。這種服飾剪裁簡單,既契合了中國傳統的審美觀,又展現了東方女性溫婉內斂、端莊秀麗的知性之美, 可以說既傳統又時尚。 可見, 生活和民族性是藝術創作中不可或缺的兩個因素。藝術要達到世界水平,需要依靠民族傳統和現代意識。
作品《藍》中的旗袍擷取了秦漢時“深衣”的設計元素。其一襲蔚藍承載著滿漢服飾文化,走過清朝之后的各個時代,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特色標識與品牌;又迎著新時代的春風,一次次登上世界舞臺,展示中國服裝時髦清麗、大氣婉約、深邃凝重的迷人風采。
作品《藍》中的物象以藍色為基調,如藍布,藍蓮花,藍頭飾,藍哈達,海軍服,清朝滿族的正藍旗、鑲藍旗,藍瓷瓶,京劇的藍臉譜,最初的解放牌汽車,景泰藍,以及藍色的鳥等等。由于融入了傳統文化的精神意蘊,作品的風格既傳統又現代。也正是由于吸收了傳統文化的精髓,并將其重新演繹,才有了這件既具有傳統文化底蘊又具有現代時尚風采的藝術作品。
以上兩例充分說明,傳統文化元素植根于民族性、地域性的傳統藝術淵源中。這就要求藝術創作者不僅要對傳統藝術有較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更要對傳統藝術有執著的熱情和堅持不懈的探索與追求。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才會不斷被發揚光大。
四、融匯古今,推陳出新
相對傳統藝術而言,現代創作存在著融會貫通、推陳出新等創新理念。這其中的關鍵是一個“新”字。這種“新”絕不是簡單的位移、變異及重復,而是創作者從傳統文化中提取元素,并以現代創新意識和表現手法進行再創造。這樣創作出來的作品既保留了傳統藝術的神韻,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全新的藝術形象和表達效果。
作品《白》(圖3)中的白樺林取材于現實,以現代意識進行創作,取得了獨特的藝術效果。這里利用顏料的遮蓋力和透明性來表現白樺林和周圍的景物,營造出了“山青雪野白樺,樓宇萬頂棉紗,落絮紛紛灑灑,盡染銀色光華”的光影效果。筆者以明暗和色彩為主要造型手段,既模仿、再現自然,使其更具有真實感、氛圍感,又突出了以白色為基調的空間層次。其中還有小白龍、白蓮花、白茶、白臉譜、白頭巾、白哈達等,也都在創作過程中嘗試運用不同的傳統元素,同時體現現代化風格。

圖3 白 李銘實設計作品
作品《白》中的白蓮花,是將傳統的文化之形、神、意重新演變成新的審美意象,從而創作出全新的圖案。可見,將古今中外融會貫通、推陳出新是創造新的藝術形象的有效手段。
上述創作范例給藝術創作過程帶來了啟示:不可單純地照搬創作元素,不可生硬地將傳統與現代題材的創作手法同質化。我們在珍視傳統文化的同時,也應該真正地體會和領悟其思想內涵,用獨特的智慧去感悟歷史人生、觀照大千世界,從而創作出更多的藝術精品。
五、結語
以上通過對藝術創作的主題與時代、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以及融匯古今、推陳出新等方面的論證,又結合自己系列作品的創作加以思考,深切感悟到藝術創作是人類文明的標志。它融匯古今文化元素,并把大量信息用先進的視覺表達方式、個性化的視覺語言,以其強烈的感召力,喚起人們的記憶。它要求藝術創作者必須站在時代的高度,融古創今、推陳出新,不斷營造藝術的光輝前景,為人類文明增添新的內涵。
注釋:
① 賈海紅《韓美林:艱難困苦 玉汝于成》,《人民教育》2006年第1期,第45—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