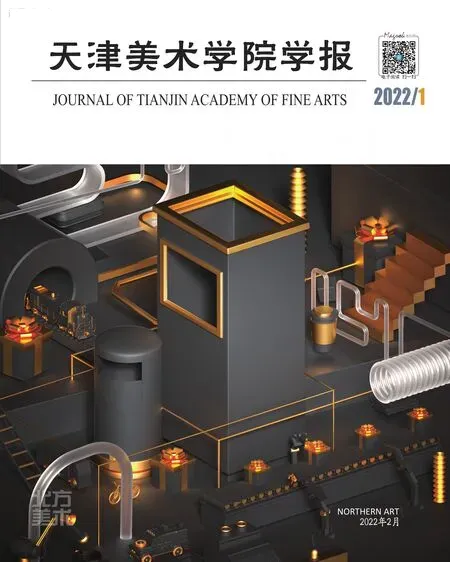“人-技術”關系視域下智能醫療監護服裝設計研究
一、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的應用現狀
近些年,智能醫療服裝市場需求顯著提升。根據美國領先的調查機構蘭德公司2015年發布的調查數據顯示,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兒童優質市場群體的擴大,加上電子元件、織物制造成本的降低和電子產品的小型化,智能服裝在醫療領域的市場需求將會大幅度提升。智能紡織品制造商為養老院、醫院等提供了一系列智能醫療服裝、智能兒科服裝等智能面料產品。比較出名的智能紡織品制造商有Clothing Plus、Camria、Hexoskin、Pireta、Stitch、Tecks等。智能醫療服裝逐漸從歐洲市場擴散到北美乃至亞洲國家。其中,亞太地區從2016年至2024年復合年增長率預計將超過35%。目前,中國智能醫療服裝市場正處于起步階段,市場需求呈現上升趨勢,但也顯現出一些現實問題,如智能醫療監護服裝市場還不夠成熟、智能醫療監護服裝設計情景和使用情景有待明確。目前市場上的智能醫療監護服裝僅限于醫院治療醫護范疇,在家庭健康監護中使用得較少。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兩點:第一,智能醫療監護服裝設計情景僅定位于醫療監護,忽略了健康監護的常規性健康概念;第二,智能醫療監護服裝市場秩序尚未形成,易與醫療保健品混淆,造成使用情景定位不明確。
二、智能穿戴服裝的階段性發展驅動
隨著智能穿戴技術的發展和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智能穿戴服裝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新需求。綜合來看,智能穿戴服裝發展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1,2,3](圖1):

圖1 智能穿戴服裝發展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技術驅動型(20世紀80年代—1997年)。在20世紀80年代,“醫療監護服裝”的概念還沒有成型,僅僅在智能可穿戴技術的基礎上孕育孵化,集中在軟件方面的傳感和顯示技術,以及硬件方面的傳感器和顯示器等方面進行探索,對于市場和消費者的使用情景未作詳細考量,屬于典型的技術驅動下的技術實驗階段。這一階段完成了產品便攜的、可穿戴的物理結構和技術結構的結合,但穿戴舒適程度和使用效果較差。
第二階段:消費社會驅動型(1998年—2000年)。隨著社會經濟和消費市場的發展,智能穿戴技術在服裝領域的應用受到關注,飛利浦、三菱、杜邦等多種類型的創新型企業拓寬了消費市場,紡織材料、智能穿戴技術、服裝設計等多學科的融入推動智能服裝設計的蓬勃發展。消費市場和新興產品的雙效驅動促進了醫療監護服裝的萌發。
第三階段:設計驅動型(2000年至今)。隨著消費市場和智能穿戴技術的成熟,醫療監護服裝逐漸向設計審美與用戶體驗方面轉換,在用戶體驗、技術功能、物理結構方面呈現大幅度提升。目前,可穿戴設備在醫學領域可應用在臨床監控、家庭監護、特殊人群監測等方面,通過信號采集和分析設備的集成,將監測結果體現在服裝及其附件上,從而使人們在日常著裝時可監測到身體的各項生理指標。[4,5]這一突破一方面使智能服裝具有了健康監護功能,尤其是在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中起到了檢測與呵護的作用;另一方面通過設計將新技術融入人們日常生活中,為人們提供了更加美觀、舒適的產品,達到了全面呵護健康的效果。
觀照醫療監護服裝的發展現狀和階段性發展驅動情況,從技術人工物內部、外部、投入和產出四個方面,可以總結出醫療監護服裝設計的四個本體要素:技術功能、物理結構、設計情景和使用情景(圖2)。智能穿戴服裝發展的第一階段是追求技術功能的提升。隨后,技術功能和物理結構逐漸走向統一。直到第三階段,設計情景和使用情景逐漸驅動技術和結構的融合。這三個階段是層層遞進的關系。

圖2 智能醫療監護服裝設計的要素
三、智能醫療監護服裝設計的技術功能與物理結構
(一)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的技術功能
技術功能可以彌合人類階段性器官的“不在場”。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的技術功能包括人體數據的搜集、傳輸和反饋。人體數據搜集主要是依靠傳感器。傳感器技術應用于醫療監護服裝的感知部分,以搜集人體的溫度、心率、血壓等多種人體健康指標數據。依據不同性能,傳感器分為運動傳感器、生物傳感器和環境傳感器等。人體數據傳輸、反饋主要依靠無線通信技術和信息反饋技術,包含開源電子平臺技術、STM32控制器技術、BLE藍牙低功耗技術、自組織低速短距離無線通信技術、無線射頻識別通信技術和近距離無線通信技術等。[6]人體生理信息通過無線通信技術和信息反饋技術傳輸到智能平臺上。根據美國技術哲學家伊德的“人-技術”關系理論,技術作為一種有待解釋的符號與我們發生關系(我們把這種關系稱為“解釋學關系”或“詮釋學關系”),即通過技術人工物的輸出與顯示設備、交互感知方式等軟硬件技術結構及功能,給予用戶視覺、聽覺、觸覺和味覺的感知,以滿足他們的客觀需求。幼兒、老人、殘疾人等弱勢群體存在人體器官的功能性“不在場”,技術化的器官對于該群體而言則屬于身體器官的延伸。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從出生到死亡均是在不斷通過技術功能尋找“身體器官”,通過器官的外化尋求某種自我的“在場”。2014年初,Mimo推出以IOS或Android應用系統結合英特爾Edison芯片的嬰兒連體衣(圖3),芯片內置在可拆卸的綠色塑料烏龜內,用以監測嬰兒的心跳、體溫、呼吸頻率等多項體征數據,利用手機App實時監測嬰兒的整體狀況,借助該裝置的技術功能彌合處在幼兒時期的人類感知器官的“不在場”,以保障新生命在這一時期順利過渡,賦予他們下一階段尋找“自我”的權利。

圖3 Mimo Edison芯片嬰兒連體衣 圖片引自http://www.redaiapp.com/1537.html
(二)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的物理結構
物理結構可謂技術設計調節的“物質性”代言人。物理結構可以劃分為軟、硬件設施兩部分:軟件部分包括人體數據搜集程序和傳輸反饋系統程序,硬件部分包括人體信息反饋部位、特定醫療監護服裝、傳感器、傳輸設備等。在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的物理結構從“想象的存在”轉變成“現實的存在”的過程中,設計是實現這一“轉變”的重要活動,而且設計本身也處于這種“轉變”的過程之中,即設計使其自身的信息存在轉變為物理存在。所謂設計的“信息存在”主張設計是構想、聯想之類的現象;設計的“物理存在”主張設計的載體是器物、產品、工程等,[7]通過設計的轉換將技術功能賦予物理結構。物理結構和技術功能不是孤立的,物理結構實現技術功能的抽象化功能,技術功能引導技術人工物的物理結構實體化,二者從認知到探索,最終形成一種依賴關系,進而達到統一,形成人與技術的“具身關系”。在此過程中,物理結構成為人體外化器官的實體,發揮著技術功能的“在場”作用,完成自我個體的回路。2014年10月,華盛頓大學蒂姆·莫里森(Tim Morrison)等研究者采用單芯片運動傳感器進行心臟監測,數據通過ISM頻段無線電和柔性天線進行加密和無線傳輸,并通過智能手機界面的詮釋,實現人類外化皮膚感知器官的真實“在場”。[8]
四、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的使用情景與設計情景
衣服是人皮膚的延伸。為實現健康生活,人們對服裝設計提出了更專業化、更人性化的要求。醫療監護服裝滿足了技術人工物與人之間的“具身關系”,促使用戶對智能醫療監護服裝提出了檢測、呵護、陪伴、時尚和智能穿戴等使用情景和設計情景的實際需求。
(一)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的使用情景
使用情景能消解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的技術性,將人的主體性拉回到日常化的“生活世界”當中。人們設計出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的目的是利用外化器官彌合個體在“生活世界”中自我的“缺席”。技術功能和物理結構產生于身體外化器官的制造過程當中,這一過程屬于技術層面的器官塑造。若缺失“生活世界”的技術消解,技術容易走向“科學主義”的盡頭,動搖“人”的主體地位,有悖于“人本”設計的初衷。因此,使用情景有助于消解外化器官的技術性,重新喚醒使用者的“自我”。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的使用情景可描述為對病、殘、幼及弱勢群體健康數據的搜集,以及對其進行健康護理和改善的生活情景。這里需要的是生活化的隱形監護服裝設計,即將外顯智能服裝逐漸內化到日常穿戴服裝生活場景中,促進智能監護服裝與人本身發生“具身關系”,并逐漸融入到使用情景中。日本化學材料企業東麗和通信運營商NTT合作的智能服裝“hitoe”品牌(圖4),針對使用者的環境進行生活化設計,采用一次性綠色回收材料,也兼顧了服裝的耐洗性和易用性,看上去與平常的同類服裝的外觀沒有太多差異。

圖4 日本“hitoe”品牌智能服裝 圖片引自http://japanese.engadget.com
(二)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的設計情景
設計情景可以調節技術與智能醫療監護服裝之間的關系。它模擬人的身體行為,以期設計出來的技術人工物在功能上可以化為身體的一部分。身體行為相對外部世界而言具有開放性和指向性,并由此構成身體意向性的知覺場。[9]因此,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的設計情景需要“以人為本”,從人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和審美需求出發,充分考慮人工物與人之間的“具身關系”:生理需求的設計情景屬于基礎需求,表現在醫療監護服裝的材質、色彩和造型等方面;心理需求的設計情景表現在醫療監護服裝的功效和作用等方面;審美需求的設計情景表現在設計風格和設計理念等方面。其中,審美需求是在第三階段設計驅動型中出現的,由審美性夾帶著功用性,與不同受眾階層的軟性需求之間形成多重博弈,不間斷地產生“流行”與“非流行”,形成間性與輪回的動態迭代,最終實現審美與功用的統一,轉化到“非流行”的行列進入尋常百姓家。[10]醫療監護服裝的發展目前處在審美與消費的設計驅動型階段,基于監護檢測功能、智能化穿戴、時尚風格理念的設計情景,滿足使用者的生理、心理和審美的需求。
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由醫療監護服裝、醫療服務機構、適用人群三部分作用主體組成(圖5)。從抽象技術到具象物體,再到人技合一的人工物工作過程,都是在設計要素和設計模式的雙重作用下完成的。醫療監護服裝與適用人群逐漸形成“具身關系”,成為人的皮膚的延伸,形成多種應激反應,不用借助適用人群的主觀意識,自主獲取身體各方面的健康數據,通過輸入設備、處理設備和輸出設備完成醫療監護服裝“上傳下達”的任務,呵護適用人群的身體健康。目前醫療服務機構包括診所/醫院/醫聯體、體檢與管理機構、醫療保險機構及其他健康服務機構,分別對應治療、檢測、預防、保險等,囊括了多元的服務主體,逐漸從單一屬性的服務機構轉向多渠道交叉的醫療服務主體,走向大健康服務設計的范疇。醫療服務機構在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數據傳輸與存儲技術等的推動下,實現了適用人群與醫療機構的雙向反饋,促進了家庭式“互聯網+醫療”監護服裝產業的發展。在設計要素為設計模式提供內部運作機制的情況下,驅動設計者、使用者和人工物三者互動,實現了智能醫療監護服裝的健康服務。日本西鐵城公司(CITYZEN)和法國國立高等工業設計學院(ENSCI Les Ateliers Paris)合作的可穿戴式智能醫療監測襯衫項目(圖6),通過醫療機構、使用者和醫療監護服裝的聯動關系,幫助心臟病患者檢測自身心率情況,完成了設計情景和使用情景的統一。

圖5 智能醫療監護服裝設計主體關系圖

圖6 可穿戴式智能醫療監測襯衫 圖片引自http://jennbagehorn.com
五、結語
從智能穿戴服裝的技術驅動型、消費社會驅動型到設計驅動型的發展來看,醫療監護服裝逐漸從技術到設計、從技術人工物到設計人工物、從消費設計到責任設計,一步步走向人本設計的方向,走向多元的智能化創新功能鏈整合。[11]正如維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在其著作《為真實的世界設計》中所說:“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為窮人、病人、老人和殘障人士設計,因為當設計師們讓他們自己忙于迎合中產和資產階級上層一時的風尚時,我們卻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受到了設計的歧視。”[12]因此,醫療監護服裝設計將是應對未來人口老齡化與低齡化極端問題的重要手段,也是社會向設計師群體提出的最真實、最迫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