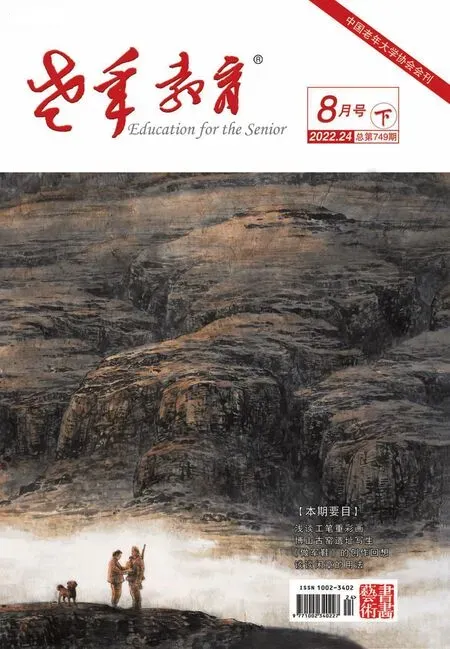圖說小楷技法(三十九)
□ 劉小晴
第六章 小楷的創作方法
寫好小楷,并非易事。歐陽修《跋茶錄》中曰:“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為難。”其實,小楷之難并非在于字小和用筆之精細,也不在于其嚴謹的法度和至到的功力,而是難在其高雅清新的氣息。
近人學書,重“創新”二字。如何去創、何以為新?則涉及眼和手兩個方面。“眼”即審美觀念,“手”即創作技巧。廖燕《二十七松堂集》中曰:“余笑謂吾輩作人,須高踞三十三天之上,下視渺渺塵寰,然后人品始高;又須游遍十八層地獄,苦盡甘來,然后膽識始定。”此論足以蕩人心魄,發人深思,令人拍案叫絕,作書亦何嘗不是如此。
書法藝術之美并非由其外在形式決定,而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內涵實質。創新,絕非單純片面地追求形式上的變異,淺顯地以為與眾不同便是“新”,甚至采用大膽變形、極力夸張的手法去表現自己。書法藝術的真正價值,在于借助外在形式顯示一種內在的個性、情感、生氣、風骨和精神。“新”固然離不開具體的、可感的、形式上的變異,但這種變異必須是一種極其微妙而合乎情理的形變。凡有志于創新者,絕不能刻意去追求形式上的新巧,而要返璞歸真,平其爭競躁戾之氣。深自韜晦,息其急功近利之風,腳踏實地,求其本質。先講筆法,次追筆勢,理法圓熟,然后伸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融之以性情,出之以自然,則不求新而自新。
一、談談創作的功利問題
書法藝術的創作,既是一個極其嚴肅、刻苦、千錘百煉的過程,又是一種消遣和游戲,是不計較個人利害得失的活動。但其同樣有著自身的客觀規律,來不得半點虛偽和絲毫投機。古代許多書家天資學力不可謂不深,道德文章不可謂不高,胸襟識見不可謂不博,然他們并不因此恃才睥睨、放浪恣肆、高自期許、目空一切。相反,他們能于超逸之中下功夫,苦殫學力,極慮專精,砥礪濯磨,篤志不分。因此,他們的作品經過一番剖洗熬煉,自然精光透露,從而達到一種爐火純青的境地。正如王宗炎《論書法》中所說:“古人作書,以通身精神赴之,故能名家。后人視為小學,不專不精,無怪其鹵莽而滅裂也。”
前人刻苦志學的故事不勝枚舉。如明代文征明的小楷之所以能風靡當時,傳美于后,與其刻苦用功是分不開的。《文嘉行略》中謂:“征明少拙于書,初模宋元,繼悉棄去,專師晉唐,自課日臨寫《千文》十本,清晨籠首,書一本畢,然后下樓,盥洗見客。”因此,他的小楷愈老愈精神,以功力見勝。他寫字極其認真,即使是信札簡帖,亦從不茍且,稍不得意便棄去重作,此即董其昌所提倡的“寫字時須用敬也”,是創作的一種嚴肅態度。周星蓮《臨池管見》謂:“字學以用敬為第一義。凡遇筆硯輒起矜莊,則精神自然振作,落筆便有主宰,何患書道不成?泛泛涂抹,無有是處。”書寫小楷,最需在用筆的精到上下功夫,若率意信筆,先不求工,則勢必不工。
書法藝術的創作雖是一種超然名利之外的藝術活動,但我們并不否認藝術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墨子》謂:“食必常飽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麗。”書畫藝術是精神的產物,但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以書養書、以畫養畫,成為現代許多書畫家進行藝術再創作的必要手段。故學書者,名利之心固不可無,亦不可過,看得淡些便可。
藝術真正的功利應該是精神的。北宋書法家蘇子美嘗言:“明窗凈幾,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之一樂耳。”一個人在空閑之時或工作疲勞之余,靜下心來寫幾行字,實在是一件愉快之事。學書可以陶養性情、接迎靜氣、破去寂寞、解脫煩悶、消除疲勞,甚至可以恢擴才情和醞釀學問。正如周星蓮《臨池管見》中所言:“作書能養氣,亦能助氣,靜坐作楷法數十字或數百字,便覺矜躁俱平。”
歷代許多書畫家多長壽,就是因為他們的書齋中有煙云供養,有翰墨寄情,眼前有無限生機,筆下有無窮受用。故而使古代許多文人雅士沉酣此道,如癡如狂,雖終老而不以為厭的真正原因。書法藝術只有保持消遣、游戲的精神,才能避免單純商業化的庸俗傾向。

《大般涅經迦葉菩薩品第十二》(局部)隋代
從創作心理來看,真正成功的創作亦應當保持一種“游戲”精神。當一個書家真正獲得創作自由時,他完全驅散了拘謹的心理,擺脫了法度的束縛。因物付物,純任自然,于不經意處隨勢生發,靈機妙緒,應腕而來,心花怒放,筆態橫生。如郢匠使斧,有運斤成風之趣;似庖丁解牛,兼迎刃而解之妙。這是一種從必然到自由,由有意到無意的“從心所欲”的境界,它無意于工,而筆筆皆工;無意于法,而處處皆法。由此,藝術創作只有保持游戲的精神,才能創造出真善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