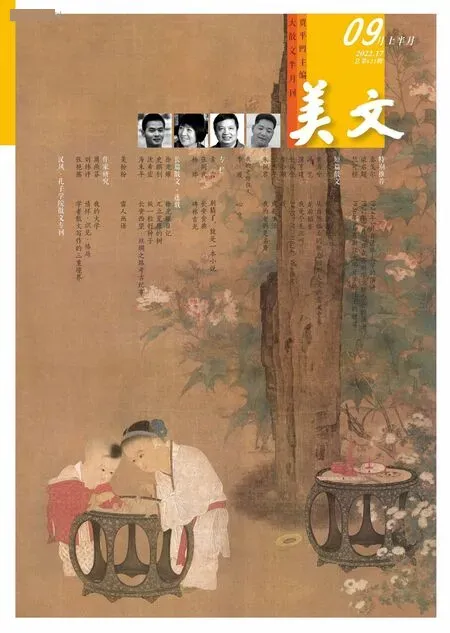從自然孤立的狀態回到人文的意義中來
◎ 黃海兮
鄉土散文寫作在中國經驗表達中已成為一曲關于農事和鄉愁的哀歌,在割與舍中,我們回望,悲憫,流連,鄉土散文寫作在一種文化留存與革新中掙扎,又被人詬病。重建新的鄉土散文寫作的現實意義,是要回到現在的寫作現場中來,在山鄉巨變中,重回人在鄉土勞作的過程顯得十分重要。那么個人如何審視新的鄉土意識,塑造自己和諧的自然觀念?我個人認為應從田園詩意中抽離出虛無的鄉土觀,將真正的敵意和分歧發生在鄉土日常中,發生在人與人的關系中。我們還需要從知識的、道德的、利己的審視中抽離出來,使之鄉土成為個人史寫作的部分。
如何優雅地表達中國經驗?在深處山鄉巨變的時代,詩意的表達曾經是我們心靈安妥的棲居地,在浪漫主義盛行的文學語境中,在重新確立新的時間觀和價值觀的過程中,過去油燈下翻書,今天手機打天下,物我相連的方式已經更變,鄉土巨變,如何將自己的生命的體驗和生活質感鮮活地表達,這是寫作者最誠實的態度。任何臣服于語言和形式的修辭,實際上缺少個人情感維系的空中樓閣,這無根之木最終會腐朽的。我們需要對新時代鄉土中國的田野調查考察,對人的境遇和靈魂進行深刻而大膽刻畫和拷問的寫作。
另外,鄉土散文寫作的現代構建是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它遠未像詩歌等其他文體那樣完成自身的現代性。這是由于傳統散文概念“文章”決定的,它背負的“文以載道”或“文質彬彬”的使命感和道德感布道天地。如何從那種古腔古調和文人氣味抽身而去,丟掉滿嘴的之乎者也。我們好久沒有說人話了,我們甚至不會使用自己本真的腔調了,我們寫作的腔調不是現代人說話的口氣,也不是我們生活中的表達。因為鄉土的復雜性,在我們隨意的光鮮的庸常的表達中,喪失力量和美感。在我看來,鄉土最重要的還是如何回到人的問題中來,把自己當人看,喧鬧的萬家燈火,內外巨變帶來的精神變遷,如何讓我們的中國經驗的表達,不那么顯得滯后和現場感缺失。
有時,我更愿意讀一段產品說明書,它有效的信息,精準的表達,像每個人的履歷表一樣審視自己來路和去向。這么來說,一個理想的讀者,不是那個你固化的假裝深刻領會文學思想的人,我對文學的理解更傾向于“人不如新”的內心判斷。鄉土在數千年的演繹中,鄉土經驗臉譜化問題如何化解?現代鄉愁、鄉情和鄉俗如何創新表達?我的理解是表達那些難以表達的問題,將這些“不像”的問題表達清晰。對自身的處境的描摹和編纂,不是立碑和立傳,它是你對自己說了什么,也是面對蒼色大地的孤獨時,你攜帶密碼有勇氣奔向遠方。當我們的寫作成為讀者的偏見、誤解和想象時,也許是個人經驗的創造性表達的轉化時。實際上鄉土散文向古典學習的不是文章的意境,不是學習對知識的正確解讀,而是對它的異質化和斑雜的不同的理解。我們需要學習的是曾經的“風雅頌”在當時所處的時代,它的當時的意義是什么?給我們后來的文學帶來了什么?現代鄉土究竟是什么?難道是因為它太中國了,我們是太熟悉了,還是太疏離了?它太復雜了,以致我們無法深入山河故里。另一方面,我們在面對正在發生著故事的鄉土時,我們心存偏見,舊的觀念和新的審美不足以解決遭遇的現實問題。今天的中國在工業化之后,我們重拾田園牧歌,自然風光,美麗鄉愁,這是人對生態和環境的覺醒,如何用中國經驗表達山鄉巨變,我想不只有向前看的眼界,也應該有向后撤的姿態。
回到羌人六的散文寫作,我喜歡他的《石頭上的樹》,這篇寓言式的散文講述的是“我”作為一粒種子在貧瘠荒蕪的環境下成長所遭遇的困境和不屈力量,他采用魔幻而又現實的擬人化對比化手法,將物和人放在鄉土的這巨大的慢速度里。每個寫作者像一位攝像師,輯錄人在大地時空的定位,承載的是我們所在的日常的生活在場表達,在變異思遷中,在物我之間的換位思考上,找到自己在空間置換的處境,把自己始終還原到人的意象。從根本上說,鄉土散文要完成現代化的寫作,是要去掉鄉土的神秘的神性符號和詩性表達,站在人的角度思考腳下鄉土思考的時空變化,鄉土中國才會從自然孤立的狀態回到人文的意義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