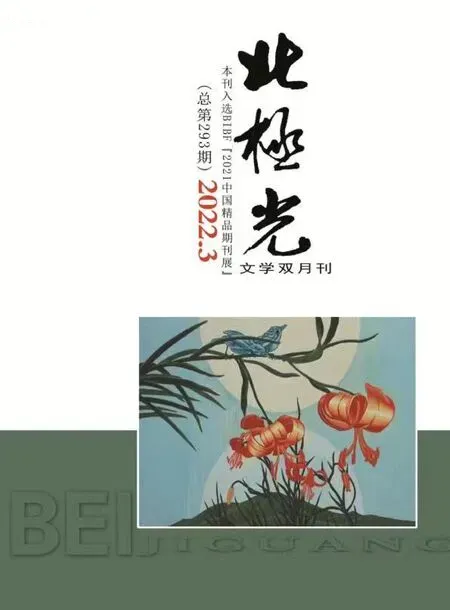歲月匆匆 情誼永恒
□璟 琛
晚上,我撥通手機,讓父親與上海的聶大爺視頻連線,五年未見面的他們終于看到了對方。之前,聶大爺一直病重,他們只能通個電話,聽聽對方的聲音,總覺得有些遺憾。
父親拿著電話的手不停地抖,對著屏幕里的聶大爺說:“我可想讓你吃我做的飯了,我們什么時候能見面啊?”
話語中,是無限的牽掛和思念……
一
父親與聶大爺相識于五十多年前。
聶大爺的老家在上海,就讀于哈爾濱工業大學,因為品學兼優,留校當了教師。文革期間,他作為“臭老九”下放到父親所在的工廠,給當工人的爸爸當起了“助手”。聶大爺生活上與妻子分居兩地,無人照顧,精神上被打壓,心情壓抑,獨在異鄉,很是凄涼。
父親遇到聶大爺,如獲至寶。能夠這么近距離接觸一個這么有文化的知識分子,是平日里想都不敢想的事,他深感榮幸。同時,對于這些被批斗的知識分子又非常同情。他想不明白,像聶大爺這么優秀的人,怎么能給他這個“大老粗”打下手。
父親16歲進廠當工人。小時候跟著爺爺做小生意,只有小學畢業。讀書少,沒有文化,是他一生的遺憾。他不吸煙不喝酒,也不會打撲克打麻將,只會顧家。工廠離家不遠,午休時間,他每天都踦著自行車跑回家,給一家老小做飯。
他有時間就自學鉆研技術,經過嚴格的考核,晉升為技師,由工人身份轉為干部。全廠兩千多人解決不了的技術難題,他手到病除。尤其是聶大爺到來后,父親還給廠里那些工程師和技術員講課,這是他一生的榮耀。
這份榮耀,當然與聶大爺有關。
父親在廠里搞技術革新,每取得一點進步,都得到聶大爺的指點與鼓勵。他說爸爸頭腦聰明,熱愛學習,可惜沒有條件念書,不然會比他還優秀。父親覺得自己成了千里馬,終于被伯樂看中,鉆研技術的勁頭更足了。
聶大爺周末多半會來我家里做客。爸爸給他做美食,媽媽承包了他的臟衣服。遠隔千里,我們在異鄉給了他一個溫暖的家。
他讓我們全家見識了什么是文化與教養。他帶著眼鏡,皮膚白凈,舉止言談,溫文而雅,從不高聲講話。他博學多識,博文強記,天文地理,無所不曉,什么問題都難不倒他。我們家那個可憐的小書架,因為他的到來變得豐滿起來,滋養著我們全家人的心靈。聶大爺一來,我們姐妹三個就央求他陪我們看小人兒書,給我們講三國,講孫悟空。講到關鍵處,他就會說且聽下回分解,我們就盼望著他下次早些來。
二
三年前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聶大爺從上海打來的電話,說我父親正在家附近的小醫院點滴,聽父親介紹癥狀,他感覺病情很嚴重,讓我盡快帶老人去大醫院診斷。我的心猛地縮緊,深感羞愧:父親居然給千里之外的聶大爺打電話,卻沒有告訴我。來不及想太多,我第二天一早就帶著父親去市醫大一院找專家診斷。果然,父親得了腦出血,幸好發現及時,手術效果很好,我們全家人都很慶幸。
父親手術后第三天,就拿起手機打電話。
我說:“爸,你要少說話,傷口怕震動。”
他不理睬我,繼續打。
我說:“你打給誰,我替你打。”
我以為他準是打給媽媽要放大鏡,他想看報紙。
父親仿佛沒有聽到我的話,對著電話:
“你好啊,聶老師你好啊。”
天啊!我竟然完全忘記了給聶大爺回電話。他之前在電話里囑咐我,一定告訴他我父親手術的結果。
父親激動地對著電話:“手術很成功,托你的福,我活的好著呢,你說什么?我聽不清,你大點聲……”
父親84歲,聶大爺86歲,這個世界的聲音在他們那里變得越來越模糊了。加上爸爸手術后氣力不足,他的聲音不斷提高,對方似乎還是聽不清楚。
我嚇得連忙搶過手機:“爸你刀口太危險了,我替你說。”
爸爸搶過電話:“我就要自己說。”
我抵不過他的任性,又為他的傷口擔憂。
三
也難怪父親任性。
當年他得到了聶大爺太多的贊揚,他太驕傲了。
在我們很小的時候,父親的廚藝就遠近聞名。一條大魚可以三吃:熘魚片、燒魚段、燉魚湯,全家人吃得噴噴香。他做的撥絲地瓜,拉出的絲晶瑩綿長,我們歡呼一般地大叫著,舍不得放到嘴里。
當然,這些美好的食物不是經常可以吃到,多半要等到聶大爺來家里共享。他興致很高地品嘗著東北菜的風味,不停地夸獎著爸爸。他也會讓妻子從上海寄來腌制的臘肉。爸爸拿臘肉太金貴了,只用一點點給我們做面條鹵兒,滿屋里就會彌漫著那種歲月沉積的濃郁的香醇,越品越香,越難忘。
只可惜,人吃得太精致,就不會長得太壯實。我們姐妹各個清秀苗條,母親擔心我們長大不能做家務活,聶大爺卻很欣賞,他說我們姐仨像極了江南女子,女孩子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聶大爺有一個照相機,他時常帶著我們到松花江邊去拍照。在那個年代,很多人的童年只有照相館里拍的一兩張照片。照相機絕對是個稀罕物。聶大爺給我們拍的那些照片,成了我幸福童年的物證。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當年小伙伴們那艷羨的目光,如同相機鏡頭一樣,把我的童年照亮。
四
聶大爺接了父親腦出血手術后的電話,又打電話給我,讓我告訴爸爸,不要再打電話,大聲說話會影響傷口康復。我聽著他的聲音依然如故,帶著江南人的溫和與細膩,帶著他陪伴我度過的童年的溫度。他好像就在我身邊,對著我的耳朵柔聲細語,而不是像爸爸那樣粗聲大嗓。
我要上學的時候,還不認識鐘表。這讓父親很不開心。他就拿過一個舊鐘表,不停地移動三個表針的位置,讓我回答時間。我由于過度緊張,完全喪失了思考的能力,胡亂地說著含糊不清的答案。
我的錯誤終于讓他的巴掌落到了我的肩上。
聶大爺來我家,看到了此情此景。他心疼地看著我,責怪爸爸說,你怎么可以動手打孩子,特別是女孩子,認識鐘表根本不用學,長大了自然就會了。此后,爸爸再沒有提起鐘表的事。
家里有個愛尿床的孩子,更是讓父親不能容忍,他覺得很丟人。并且堅定地認為,是我的懶散與遲鈍所致。夜里夢游中的我,時常會被他的巴掌激醒。
母親偷偷將此事告訴了聶大爺。他很鄭重地跟爸媽談話:這很可能是一種疾病,必須找醫生。他又幫助找了中醫給我針灸按摩,進行多方面的治療,我才終于擺脫了那個附身已久的惡魔。
后來,有一次我正在寫作業,爸爸站在我旁邊很久不說話,然后問我:“你是不是很想有個像你聶大爺這樣的爸爸?”
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好在沒等我回答,他就轉身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媽媽告訴我,聶大爺是書香門第,名門之后,曾國藩是他家的先祖,他的奶奶結婚,宋美齡做的伴娘。那時我還小,不知道曾國藩和宋美齡是何許人,但看媽媽的表情,只感覺他的身世很不簡單。后來,聶大爺的妻子來我家做客,她就像老上海電影里的大小姐,五官秀美,話音綿軟,笑起來有幾分嬌羞。我們只顧好奇地看著她,呆呆地張著嘴巴,忘記了吃飯。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不再叫他聶大爺,直接叫他大爺。省去了一個姓,親近了十萬分。
父親沒有兄弟,我們的大爺——就是爸爸的親哥哥。
五
我小學畢業時,大爺終于平反,恢復了名譽。他的精神狀態好了很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回上海探親的次數也多了,來我們家的時間自然就少了。
爸爸由衷地為他高興,又有點失落。有時候,約好的時間大爺也會爽約,爸爸就把做好的飯菜送到大學校園他的住處,大爺自然是感激不盡。
我上初三那年,大爺結束了十年的兩地分居,調回上海工作,終于可以與家人團聚,享受天倫之樂。
大爺與我們家的聯系越來越少了。
不能時常見到大爺,父親就把他掛在嘴邊,不管說起什么事情,總要提到大爺。
高考那年,父親每天晚上都給我削好蘋果皮,端來洗腳水,讓家人說話放低聲音。我吃著蘋果,泡著腳,漫不經心地看著書。沒過一會兒,就睜不開眼睛,趁他不注意鉆進了被窩。
在半夢半醒之中,我都能聽到他向我咆哮。
他與我鄭重地談話,就像當年在我的問題上,大爺與他談話一樣:
“你要是蹦著高兒都夠不著,爸也不難為你,可你一翹腳就夠著了,為什么連翹腳的力氣都不肯出,難道,你不想成為你大爺那樣的人嗎?”
我終于翹著腳走進了大學,雖然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學校,也足夠爸爸在親友面前驕傲,他自然不會忘記打電話向大爺匯報。
每次跟大爺通過電話,爸爸也會向我匯報。大爺當上了上海鐵道學院的室主任,大爺的妻子做了主任醫師,女兒在美國讀博,兒子在一家外企工作。
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家,有時也邀請爸媽來嘗嘗我的廚藝。父親不聽我的勸說,照例帶來了他做的地三鮮。母親對我的手藝贊不絕口,父親只嘗了一口,點了點頭。
母親說:“你的女兒要超過你嘍。”父親低著頭,一個勁地吃著自己的地三鮮,不停地說:“這茄子過油,我是加了糊的,一點兒都不油膩,比肉還好吃呢。你大爺什么世面沒見過,這個菜他最愛吃,說我做的比那些上海的大館子都好。”
六
有一天,我興沖沖地回家,告訴爸爸我提職的消息。他沒有回聲,媽媽向我擺擺手,我一看,爸爸正在擦眼淚。
媽媽輕聲說:“你大爺家出事了。”
我的心緊張起來。
媽媽接著說:“你大爺的兒子得了腦瘤,走了,才32歲。”
我的心一陣疼痛。
父親紅著眼睛:“老天爺對你大爺太殘忍了,不行,我得去看看他。”
我說:“爸,大爺很傷心,他一定不想見人。”
爸爸說:“可我惦記他呀。”
在我的一再說服下,父親終于放棄了去上海的念頭。
我也不讓爸爸給大爺打電話。告訴他傷痛總要自己撫平,別人的安慰有時是種打擾,可爸爸偏是不聽。大爺接了電話,簡單說幾句就放下了。爸爸更是擔心:
“他會不會生病了?”
有一次,我生氣地跟爸爸大喊:“你真是太不懂事了,別再打擾別人的生活了。”
爸爸愣在那里,半天說不出話。
他找出大爺一家四口的合影,端詳著,掉下了眼淚。半年后,大爺主動打來電話,冷靜而克制地講述了安排兒子后事的經過,告訴爸爸他已經接受了命運的安排,提醒我們不要過度工作,他的兒子就是過勞而死。
轉眼又是幾年。
爸爸和大爺都退休了,他們的通話又多起來。兄弟倆都在發揮余熱,大爺繼續做他的教授,到處講課,父親在大爺當年工作過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科技園里,與教授和博士生一起研制機器人。期間,園區的另一個教授欣賞他的技術與責任心,爸爸還跳槽一次。75歲那年,他上了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當然,這一切爸爸都一一向大爺做了匯報。
他是多么渴望能見見大爺啊。
爸爸終于把大爺盼回來了。
大爺回到哈爾濱工業大學講課。我和父親也來到講堂,等著跟大爺吃飯。因為只能停留一天,大爺沒有時間到我們家里做客。
大爺的演講不時得到聽眾的掌聲。父親目不轉睛地看著大爺,又看看目不轉睛的我,說道:“你要是有個這樣的爸爸該多好啊!”
我不大相信地看著他:“爸你說啥?”
他怔了一下,又搖搖頭:“沒說啥,我說他講課真好。”
大約又過了半年光景。
有一天,爸爸給我打電話,語氣里透著異常的興奮:“告訴你個好消息,你猜都猜不著。”
當時,我正遇上工作不順心,哪里有心思猜,便催促他快說。爸爸說:“你大爺請我跟你媽去上海啦。”這真是個好消息!我沒想到大爺會發出這樣的邀請,也跟爸爸一起興奮,同時又有幾分擔心,畢竟已經是這把年紀的人。但我又怎么好打消他的熱情,還有大爺的熱情。
爸媽到上海后,大爺打來電話,讓我放心,說老哥倆去早市買了一條大魚,爸爸做了個魚宴,還是一魚三吃。大爺終于又品嘗到久違的親情的味道了。
接下來,他們的人生出現了接連不斷的劫難。父親79歲那年得了胃癌,胃部切除了三分之二。大爺81歲那年做了兩次心臟手術,每一次都是劫后余生。加上三年前父親的腦出血手術,他們在手術后的第一個電話,都是打給千里之外的兄弟,報個平安。
爸爸老了。大爺更老了。
大爺從上海給爸爸寄來了電視機和手機。他說:電視機一定要用掛式的,老年人才好看,手機是他用過的品牌,爸爸用著才好用。于是,父親把原來的電視機和手機丟棄在角落里。
看著電視機,就是看著大爺。
打著電話,了卻兄弟間的牽掛。
父親與大爺通完了視頻電話,我帶著父親在小區里散步。
他已步履蹣跚。我不由得上前,拉著他的手,從未感覺這般溫柔。想來成年后,我還從未拉過父親的手。我假裝不在意地看了一眼父親,他有一絲不自在,又有一絲享受。
“想你大爺了。”輕風吹過,父親淡淡地說。
我耳邊再次想起視頻通話,爸爸對大爺說的話:我可想讓你吃我做的飯了,我們什么時候能見面啊?
我揉了揉眼睛,看著爸爸:“我陪你去上海看看大爺?”
他怔怔地看著我,搖搖頭。
那個視頻電話里,我不知道父親的話,大爺聽到了多少,也不知道大爺的話,父親聽懂了沒有。父親縱然任性,那個幾十年綿延不絕的溫暖的聲音,也終將漸漸遠去。
月明星稀。
前面的路,已然看到盡頭,我們拐向另一個路口。
我牽著父親的手,走過這人世間的不如意,帶著今生今世的美好,來生,與大爺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