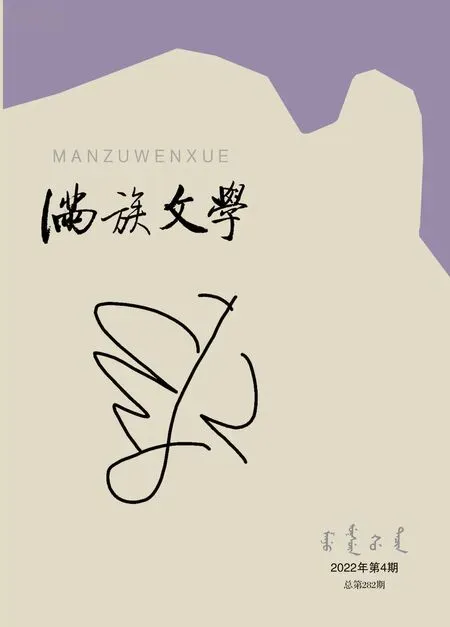肇事者
劉云芳
一
巨大的蜘蛛網掛在院墻與電線桿之間,上邊綴滿了晶瑩剔透的水珠,像一件正在晾曬的珍珠衫。一只黑綠相間的蜘蛛趴在上邊,幾條腿微微向內收著。我抬頭看它時,一枚淺淺的月亮正好粘在網上,被它據為己有。
叔叔打過電話來,問他家房子有沒有被雨水沖壞,雜草有沒有把院子完全吃掉,我順著兩扇大門的縫隙往里瞧,看見白蒿、臭蒿都已經長到半人多高了,屋檐上的一根管子正嘩嘩地往下流著渾濁的積水。我讓他放心,房子看上去沒什么問題。電話還沒掛斷,就看見爺爺從前面的小坡上走了過來,他嘴里嘟囔著,不管我也就算了,連地也荒了……等他聽出是叔叔正跟我通話時,立刻就換了神色,沖著電話喊道,沒事,都好著呢,棒子種上了,南瓜也長芽了,等秋天回來摘吧。和村里其他留守老人一樣,爺爺平時跟別人坐在一起聊天,總會埋怨孩子們出山后不回家,而在電話里,卻又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放在以前,這座院子我們都是躲著走的。
且不說,房子后邊,幾棵高大茂密的柏樹相連,遮蓋著那片古老的墳地,光是這房子本身就夠讓人疑心的。它先后死過兩個主人。村里人傳說這房子是兇宅。可叔叔、嬸嬸硬是要買下它,又找來村里的老楊,讓他幫著裝修一番。還專門貼著房檐搭了藍色的遮陽彩鋼,圍起了院墻,再把大門一裝,房子變得氣派起來。
但事情似乎真的像村里傳說的那樣,沒過多久,叔叔忽然出了車禍。就在山里的一個拐彎處,一輛三輪車把騎摩托車的叔叔撞飛出去老遠,叔叔痛苦地躺在眾人圍觀的地上。肇事者竟然是給他裝修房子的老楊。據說,老楊一直強調,當時,叔叔趴在地上苦苦哀求,只要能把他送到醫院,什么責任都不用負。而叔叔說的卻是另外一個版本,說他只是提醒老楊趕緊送自己去醫院,至于留證據什么的,他壓根就沒想過。后來,律師詢問,他直說,村里哪興這個?老楊把叔叔送到了骨科醫院,丟下二百塊錢,還沒等大夫交代什么,就急忙溜了。但令人詫異的是,只過了半天,叔叔和嬸嬸竟然也離開了那家醫院。
事故發生幾個月后,就在這座院子里,叔叔向我描述如何聽說那里治療費用高,又如何拖著那條膝蓋處骨折的腿連蹦帶跳下了二樓,上了私立醫院的汽車。說完,他拿鑷子夾了一團藥棉,在傷口里蘸蘸,疼得他直皺眉。鑷子被提起來的時候,藥棉上浸滿了紅黃混雜的血和膿水。他又說,那傷口總也不愈合,真是沒辦法。也是在那時,我們才知道,這個在煤窯起早貪黑上班的男人,竟然沒有任何保險,甚至連村里家家戶戶都會繳的合作醫療保險,他們也只交了三份,將他排除在外。就跟平時一樣,好像這個家里的每一分錢花在他身上都是可恥的,浪費的。
后來,聽姑姑們說,在私立醫院,每天睡地鋪的嬸嬸焦躁不安,叔叔腿上的傷,和村里獨自生活的女兒以及病友晚上傳出的驚人的呼嚕聲,都讓她輾轉難眠。她時不時就要給姑姑們打電話,讓她們來病房換換班,輪流看護叔叔。我從未上過學的二姑,坐著公交車從山里輾轉來到城市,在醫院一住就是幾個星期。要不是晚輩們來接,她甚至不敢走出醫院的大門,生怕因為不識字,給走丟了。再說,住院也太費錢了,她下了狠心從家里拿來的一千塊,不幾天,就花得一干二凈。
叔叔擅長修理電器。村里人來叫,他又抹不開面子,拄著拐就跟著去了。來找他的人幫忙拎著工具箱走在前邊,他在后邊跟著。
他手里還攥著一團衛生紙,不時就要彎腰擦拭一番。在膝蓋的部位,一股膿水從大片傷疤中間流出來,泉眼似的,不時往外冒著濕乎乎的東西。你看看,那里邊就是骨頭,叔叔又說。我瞅了一眼,看到糜爛的肉里顯出一絲的白,感覺渾身不自在。他輕信私立醫院大夫的話,說,還需要等,仿佛唯一能讓這傷口愈合的只有時間。
讓他更為煩心的是撞傷他的老楊遲遲不現身。叔叔氣得牙根都癢癢,發誓要將他繩之以法。因此,連老楊裝修的手藝也可恨起來。他指著地上永遠印在洋灰里的老楊的腳印說,你看看,這就是他干的活!又指著墻體說,這抹的是什么樣子,怎么看都不平整……
老楊一開始躲著,后來偶爾三更半夜回村看他老媽,像個賊一樣,騎著摩托車一閃就從門前過去了。他一向在村里以仁義標榜自己,這個時候卻耍起無賴,說,反正兒子們成家了,在外地打工,他自己又死了老婆,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要坐牢就坐牢吧。他甚至還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比如,說那天他開的不是自家的三輪車,而是老李家的,并且,他奔跑在那條路上,也是為了給老李家拉修房子用的沙子。就算賠錢,也得是老李賠。老李戰戰兢兢,跟村里人商量,要不賠叔叔兩千,哪怕三千也行。但叔叔那房子正是從老李手里買的,他短短幾年痛失兩個兒子,單靠著低保金過日子,叔叔也不忍心讓他出錢。
老楊大言不慚地放出話來:只要法院讓他出錢,他馬上就拿錢出來。叔叔聽到之后,咬著牙說,這官司,咱們跟他打,我就爭這口氣!說完,他又拿著衛生紙蘸了蘸腿上冒出的膿水。嬸嬸急忙把棉簽遞給他。我連夜聯系了一位之前認識的律師,第二天就帶著嬸嬸進城,把打官司的事兒定了下來。一大家子人暗地里祈禱,盼著法律能給老楊來個下馬威。
那段時間,叔叔總是拄著拐架跳來跳去,他也拄著拐穿過大半個村子去我們家。半身不遂的母親坐在院子里叫叔叔的名字,想起她初嫁時這個年僅五歲的小叔子如今受的傷,吃的苦,眼睛難免濕潤起來。她一遍遍囑咐:你歲數還小,一定要好好康復。一旁喂牛回來的父親,雙腿彎成了“O”型,隨著身子來回擺動著。我遠遠看著他們三個,覺得命運里充滿了荒誕和諷刺。
村里人解讀災難有他們的一套方法,有人說,叔叔出事完全是因為那套房子,誰住在那兒也好不了;也有人說,我父母和叔叔都是腿出了狀況,那或許就是我們家遺傳的問題;還有人說,沒準有截樹根因為四處伸展,正好壓住了我某位先祖的腿骨,所以,他要以這樣的方式提醒后人,就像一種怨咒。他們把風水、我們的祖先,甚至是一棵安靜生長的樹拉進來,當作一切苦難的肇事者,好像突如其來的疾病以及把車開得飛快的老楊都是無辜的。
那年春天,白蒿滿地,山風嗚咽著,從一棵柏樹上繞過去,一直沖進山坳里。我從風里找不到任何暗示。叔叔始終也沒有想到,當年那樣用心裝飾的房子如今會成了遺棄在故鄉的空殼。我再抬起頭看,房檐上那管子里的水流已經變小,像一個人終于哭累了似的。
二
那是距離叔叔出車禍大半年后的秋天,父親要做靜脈曲張手術,我不得不回到故鄉所在的小城照顧他。剛在醫院辦完住院手續,幾項檢查還沒有完成,便接到了叔叔的電話,他火急火燎地說,他就在之前治傷的那家私立醫院門前,要我馬上過去。原來,他是事先打聽好了我歸來的日期,專程選擇這一天進城的。
他拄著拐,站在一棵龍爪槐的旁邊,那張臉瘦得像被刀削過似的,旁邊的嬸嬸挎著個小包對我微笑,給他治病的那家私立醫院就在斜后方。如果不是因為我回來,叔叔找醫院解決問題的日子還會往后拖。那段時間里,他輾轉于各個小醫院,吃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中西藥和補品,沒有任何明顯的效果。問他們為什么不趕緊去正規醫院,他們不好意思地笑,這來回折騰已經花干了所有積蓄,還借了不少外債。要不是逼到沒辦法,他們也不會來找這家醫院理論。
叔叔站在那棵樹下的陰影里,等著我為他出面。這讓我忽然想起,若干年前,奶奶用土坷垃追著他打的情景。那時他只有十幾歲,不愿上學,卻喜歡將各種電器拆拆裝裝。他跑到小山坡上,又停下來,看著奶奶。奶奶卻忽然哭了。她總是擔心他惹禍,這個只大我八歲的叔叔,不知道讓她流了多少淚水。她總是渴求所有人都能保護她最小的孩子,在其他孩子面前,一遍遍強調他的弱小。后來,奶奶去世,但那份對叔叔的憐惜卻留了下來,那洶涌的淚水像一筆遺產一樣,不時從姑姑們的眼眶里流出。而等成年之后,這種對叔叔的保護,就像基因一樣融進了我們的血液里、習慣里。
叔叔盼著我為他出頭,其實這樣的事情我并不擅長,但又不得不硬著頭皮往上沖。我扶著他爬上二樓。語言的鋸子來回拉扯著,叔叔終于忍不住,大聲訴起了委屈。他的表情那么無助,幾乎要哭出來。那一刻,我感覺自己的腦袋里好像長滿了密密麻麻的刺,不斷往外扎。
經過漫長的談判,終于和院方敲定一個解決方案:由他們負責請本地大醫院的專家給叔叔完成治療。至于醫療費,院方不松口,只是說,有錢,你們就給,沒有,以后再說。
手術很快定了下來,但專家們發現,叔叔的骨頭有一小塊已經壞死,不得不刮掉。他的膝蓋關節已經完全鎖死,幾個月沒有活動,導致關節整個粘連在一起,大夫們合力都拉不開。這次手術之后,傷口倒是愈合了,不幸的是,那條腿再也不會打彎,它直戳戳地架著叔叔瘦弱的身體,走路時,不由自主地劃著圈。他每走一步,好像都在地面寫著“10”似的,“1”是左腿邁出的,“0”是受過傷的右腿劃著邁出的。同時,這條腿還變成了晴雨報告儀,每遇天氣即將降溫、下雨、下雪,關節便開始疼痛難忍。而每次一疼痛,叔叔都會想起老楊來。
有時候,親人們也會懟叔叔兩句,誰叫你們不在正規醫院治,非要逃跑的?叔叔壓低頭顱,小聲說著,我怎么知道……
快到年底,叔叔來了電話,欣喜地說,跟老楊的官司贏了,判了六萬多。這些錢大多是他的部分醫藥費,還有一點誤工補貼。叔叔雖然在煤窯上班,掙得也不算少,但他是臨時工,按照規定,這一年的誤工費只能按他農民的身份來算。賠償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法院還了他公道。在電話里,他揚眉吐氣,說話的音色也亮堂了很多。
然而,老楊卻完全不見了蹤影。聽人說,他在鄰縣一座大山里幫某個煤老板喂雞。叔叔和法院的人趕緊就去了。只見老楊在一座簡陋的房子前,正拿著一截棍子給雞拌食。看見車上下來穿制服的人,他立馬就把棍子扔遠了,說話也支支吾吾。他說自己并不是不給錢,而是太窮。但他卻又跟村里人在電話里說,有的是錢,就是不往外拿,看我叔叔能把他怎么辦。什么不讓坐飛機,他這一輩子也不可能去坐那玩意兒。不讓高消費,他老楊最高的消費無非是去醫院治病。想從他身上薅毛,等下輩子吧。
叔叔隔段時間就給法院的人打電話,唯唯諾諾地詢問。每次打電話都要跟一家人先商量好了怎么開口,反復練習幾遍,才敢把電話打出去。又問我,是不是該送送禮?是不是因為自己是個農民,人家看不起,所以不給好好辦案?叔叔還說,有次,他去法院,老楊也正好在那兒。他問法院的工作人員,他不給我錢,為什么不抓他?他們講的那一堆條款,在叔叔看來都是搪塞。我只能勸說他一頓。
幾個月后,法院讓叔叔簽訂了一份協議,說是同意老楊一個月打給他三百塊錢。村里人人都能幫他算這筆賬,六萬多,一年還三千六,那就得將近二十年,那個時候,老楊也要八十多歲了。他能活到那么大歲數嗎?但叔叔卻一臉苦笑,不作答。等人散了,他才說,我能有什么辦法呢,能要多少算多少吧。說完,他低著頭發呆。我就不再忍心說他什么了。
后來我們才知道,即使那三百塊錢,老楊也就打過一個月。叔叔把這恥辱的苦果子強咽下去,好像再把這些講給人聽,就顯得自己太窩囊了。他也想不明白,在這件事情上,理虧的明明是老楊,可最終丟錢又丟人的卻是自己,見誰都抬不起頭來。叔叔摩挲著他那條受過傷的腿,嘆息:太難了!
原來的煤窯,他是回不去了,他再也無法靠力氣干活掙錢。跟嬸嬸謀劃半天,把家搬到了幾十里地外的村子。那里有一所中學,可以一邊開店,一邊給女兒陪讀。
他們租住的房子正對著學校的大門。那是一面高高的土崖下挖的兩孔窯洞,叔叔、嬸嬸把它收拾干凈了,又在門口掛了“修理部”的牌子。土崖頂上布滿了酸棗樹、椿樹和野草。我去探望他們時,正是秋天。風一吹,酸棗簌簌地往下落。同時落下來的還有紅的、黃的、綠的樹葉,分外惹眼。嬸嬸愛干凈,不時拿起笤帚掃上一遍。
窯洞里陰冷的寒氣直往臉上撲。靠墻的一面豎著個貨架,上邊擺滿了各種零件和線圈。他說這些零件都是從網上訂購的,一個個介紹著它們的故鄉。叔叔一邊挪動它們,腿一邊在地上劃著圈。嬸嬸在一旁嗔怪:知道的說你是干修理,不知道的,以為你賣零件呢。叔叔像沒有聽到一樣,默不作聲。
他那條能預知天氣變化的腿,卻預知不了生活的變化。修理電器的生意并不好,他不得不向遠在南方打工的兒子求助,時不時要幾百或者幾千塊錢救急。原本好好的生活變成這副樣子,嬸嬸的臉色時常不好看。老楊給他帶來的傷害如同腿疾一樣,總是停放在某處,一旦生活里有什么不順,這傷害便會浮現出來。
最終,他們決定去山下投奔我大姑一家,在城邊那個小鎮上租了門面,有表弟、表妹們幫忙張羅著,生意也不會太差。叔叔連夜讓我給他的店鋪取名,又來回奔忙著搬家。
三
在“之”字形的山道上,遠遠就能看到一個瘦小的身影,他左手端在胸前,右胳膊甩來甩去。離近了看,正是老楊。
聽說,他半年前得了腦血栓,孩子們侍候了一陣子,又外出打工了。他一個人過活,吃喝都湊合著,原本就清瘦的人,風一吹過來,衣服直晃蕩,好像那衣服不是被他穿在身上,而是直接掛在了一副骨架上似的。他臉上滿是皺紋,眼睛擠在其中。算起來,他比我父親還年長,也是六十多歲的人了。
因為叔叔的關系,他看見我們家人多少都會有些不自在。這不自在讓我們覺得他似乎還略有那么一點良知。我和他都在岔路口愣了片刻,才互相問了好,之后,他便轉身從槐樹旁邊拐過去,奔向別人家。
聽說,患腦血栓之后的老楊能恢復到如今的樣子,也是吃了不少苦頭的。原本好好的人忽然失去了行動力,重新學習行走,自然是極其膽怯的。再者,得了這種病的人多少都會有些惰性,鍛煉上便不那么積極。可孩子們都有一家人要養,哪能一直守在老家,于是,想盡了辦法逼他鍛煉。他們說,最有效的莫過于把老楊扶到院子邊上,又將做好的飯放到門口,讓他自己想辦法往前挪動步子,若能回來,才有飯吃。
那雖是冬天,陽光還是穿過老楊稀疏的發絲,在頭頂上曬出了油光、汗水。他緊攥著拳頭,用足力氣往前挪動腳步,這辦法是嚴苛到有些殘忍的。在這件事情上,村里人的態度分成兩派,一派認為這么做是對的,不狠下心,怎么能練好。一派認為,這簡直是胡鬧,折騰人。那些老人從老楊身上看到了恓惶的晚年,一有空兒,趕緊往東山跑上一趟,學著城里人的樣子遛遛自己的兩條腿,順道兒甩甩胳膊。
叔叔聽說這件事后,以往一提起老楊便發狠的話反而沒有說出口。老楊欠他的錢幾乎沒有歸還的可能。他已經不想再去糾纏,有那點兒時間,還不如干點別的什么。但老楊卻成了他心里的陰影和隱痛。他總覺得老楊賴賬的事最終會變成他軟弱無能的把柄,被許多人握在手里。為此,他很少回老家,任院子里的空間被野草一點點擠滿,任田地荒蕪。
有時候,他也開著三輪車奔走于附近的各個鄉鎮與街道。嬸嬸在家里看門,她開始熱衷于直播、發視頻,用各種網絡上傳誦的雞湯文吐槽命運的不濟。那因為美顏過度表現出的我們未曾見過的姿態,顯出一種陌生感。然而叔叔卻從未察覺,他能將一件件電器無師自通地修好,卻不知道世界上很多東西是一旦壞了就無法修復的。他整天忙碌,似乎卻總是入不敷出。
去年秋天,店鋪房租忽然漲價,他們權衡半天,打算搬家。他獨自轉移空調外掛機時,那條受傷的腿沒能支撐住,整個人從梯子上重重摔了下去,導致手腕粉碎性骨折,腰部也受了重創。
醫院好像一個魔咒,讓嬸嬸看到就想逃避。兩天之后,叔叔被扔在醫院,無人問津。我們表兄弟姐妹幾個趕緊湊夠手術所需的錢,又幫著找好了護工。就在那段時間里,嬸嬸在視頻網站上記錄著自己的生活,任親戚朋友們怎么勸說,她都無動于衷。而他們的兒子再也不愿接聽叔叔的電話,也不再接我們的,他像暴風中的風箏一般,被干脆地扯斷了與家族的聯系。
等叔叔出院回家的時候,發現嬸嬸將原來的家分裂出兩個來,她想跟叔叔分開過。她一口咬定,叔叔曾多次罵過她,還沒給她道歉,沒有下跪請求原諒。叔叔卻說,你也罵我了,夫妻吵架的時候,哪有什么好話!但幾經折騰,嬸嬸還是卷著鋪蓋走了。戶口本里,剩下叔叔孤零零的那一頁。
親人們經常想,假如叔叔的腿沒有被老楊撞傷,他還像那些年一樣在煤窯辛苦上班,一家人在那套新買的房子里安心過活,他們的生活會不會是另外一種樣子?我苦想了半天,也說不出什么來。在復雜的生活大網里,誰又能說得清造成今天面目的肇事者究竟是什么人,或者是怎樣一件事情。
聽說,老楊在去年又病了一次,還做了回手術。叔叔沒能從他身上討要到的錢,一次次分期送到了醫院。這讓他們家也常過著火上熬油的日子。但叔叔似乎不太怨恨老楊了,至少很少再提起。他在那座小鎮上一個人生活著,自己做飯,自己修理家電,生意竟比原來好了很多。甚至在去年秋天,還破天荒地把爺爺接到山下住了好長一段時間。
他偶爾會跟我聯系,一看到他的號碼,我心里還是會忽然一緊,琢磨著,他是否又出了什么事,或者是否要借錢。視頻那頭兒,那張瘦削的臉上綻放著微笑,問我最近忙啥呢,然后看著我的孩子們,臉上是長輩看到晚輩才有的慈愛。我每次都要對他說,你照顧好自己。說完,便忍不住哽咽了。我明顯感覺到,奶奶給后輩們的淚水遺產在我身體里洶涌著。并且,我心里常會升騰起一種內疚感,覺得自己沒能照顧好叔叔。但同時也會有另一種聲音在此時冒出:你大可不必。這兩種聲音糾纏在一起,讓一切變得更加含混。
關于嬸嬸,人們說,在城市里的火鍋店見過她,也在川菜館里見過她。叔叔聽了,沉默了一會兒,說,可是,她不能吃辣。我們讓叔叔去把她找回來,他卻說,算了,一個人也挺好。但他依舊不斷給兒子打電話,一次次發去信息說,我不朝你要錢,只是想知道你過得好不好,卻始終沒有得到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