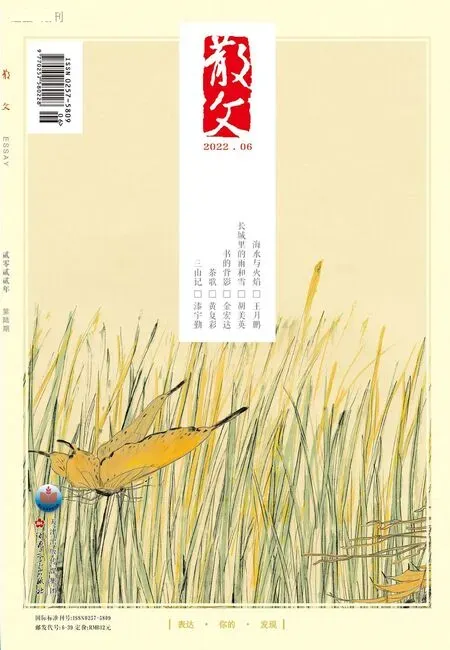依靠
周榮池
一
我和父親彼此交流很少,雖然時而見不到他我也慌張。他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用血紅的油漆寫在墻上,這是獨居多年的他應對訪者不遇的一個好辦法。我對于他以及村莊,有時候也像是訪者。他有一群我永遠搞不清楚數量的鴨子,在他認定的河流里跟著他來來去去。河水在他的叫喊聲里流淌,就像村莊蒼老的血管,也是帶著酒味的。他常常戲稱,在這個家以及村莊,“畜生是比人多的”——那“一大趟”魯莽聒噪的鴨子,也是他一生的依靠。倔強的父親沒有什么朋友,他“一大趟”的兄弟姐妹已遠去城市很少來往,他們當然也有各自要依靠的生活。但父親每一段時間總會有一個很好的酒友,這個人是誰也并不固定,每個人不同的年紀也有不同的依靠。他曾經有個面容清癯的酒友叫黎先生,只是個劁豬的獸醫,酒量大且喜歡吃劁豬所得的穢物。那時候家里總要養豬,黎先生拎著皮包來做完“手術”,父親拿香皂給他洗手上的血污,然后用一頓酒抵他的工錢。父親后來講,有一次中午他們就著一只小公雞喝了五斤酒,喝完在門口草堆邊睡到天黑——說這話的時候,黎先生已經不在人世,父親也沒有什么悲傷,但總記得和他喝過的酒。這個性格暴躁的男人,認定酒是他的命數,能和他喝酒的人,才算是他的朋友。
我到家常見到門開著,他對這個依靠了一生的村莊毫無戒備。見他的車不在,就知道人也出去了。現在,三輪車代替了他放鴨的獨木舟。本族的大伯母坐在門口,就像守著自己家門一樣親切。這些老得忘記了過去的人們,把這個村落的每一處都當成自己的依靠。他們沒有了悲傷或者喜悅的情緒,過去曾經有過的親近或惱怒也像從未發生過一樣——他們和土地一樣,終于變得沉默寡言。
二
隔壁鄰居老正松早就故去,留下院子里的草木枯榮沒有了任何實際意義。這曾是村子里最令人羨慕的人家,也是我見過的最為“細作”的村戶。令村民羨慕的是,老兩口皆是早年去上海討生活又退休回來的,每個月郵電所的人都送來一筆不菲但不知道究竟多少的“勞保”。這筆被村里人看成“不勞而獲”的收入是令人眼紅的。寒暑假期時,他們的子孫從滬上回來,帶著一口上海腔和一些后來才知道并不昂貴的小物件分給鄰里。比如上海牌的肥皂、大白兔奶糖或者木頭制的搓衣板——有些甚至可能只是某個村莊遠銷城市回流的手作。
鄰里們的關系并非完全如人們說的“鄰居好,賽金寶”,實際上,大家多少有著彼此的不滿。這戶女主人會背誦“老三篇”的人家總是關著門,人們稱他家的院門“關得鐵桶一樣”。不過即便是他家的門開著,也沒有太多人愿意光顧,因為那門內的生活和村里是不一樣的。他家的院子地上是用青磚鋪的,種的是據說北方才有的蘋果樹,這些在村子里也是罕見的。菜園子里的菜是本地的,但打理得過于井井有條的樣子也很令人隔膜。大多數村民在菜地里并不花太多心思,很多時候不過是撒些“懶棵子”任由它們生長,人們更在意莊稼的豐歉。這就像人們并不關心自家孩子讀書的事情,而更在意孩子們什么時候能成為田地里的“大勞力”。所以,老正松家將種果蔬作為一種正事盤算,是令人非常不滿意的。更為惱人的是,因為老正松很有些侍弄花木的手段,果樹的長勢又非常喜人,每到收獲的季節有鄉里賣水果的人來收,這又是一筆讓人覺得非常不合理的收入。人們不愿意吃他的果子——當然也吃不到,所以就偷偷地在背后說,這些果子是“換了錢打藥吃的”。說這些話的,不僅有我父親及鄰人,還有老正松自己的親兄弟們。
孩子們總是不信邪的,趁著老太婆打盹時,去摸幾個果子回來嘗一嘗也算解恨。而后自然是莊臺上響起一頓帶著上海口音的謾罵。他家的罵聲并不會令人們不安,大家會都偷著高興,還有人不屑地說:“都是孩子摘的,孩子不頑皮那就要裝在‘盒子’里去!”這里人說“裝在盒子里”,就是死去的意思,死人才不會頑皮。他的孫子從上海回來,在村子里到處好奇地轉悠,卻沒有孩子和這個穿著涼鞋的上海人玩。他站在豬圈邊盯著那肥長的絲瓜發呆。我們就悄悄在絲瓜上掐幾個深深的印痕。老正松發現的時候,我們都佯裝無辜說是他孫子自己掐的。那個說上海話的孩子和我小名一樣,叫“小兵”,但并沒有和我們任何一個人成為朋友。
我親眼見過父親和老正松抄著農具打架的樣子,他和自己的親兄弟也有這樣的場面。不過那時候農人打罵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日子太憋屈了,打罵或成為一種辛酸的解壓方式。其時,我覺得他們永遠不會再來往了,然而他們還是一起堅定地生活在這個乏善可陳的村莊里。
我喜歡老正松家的院落及菜地。
他院子里種的是青皮的蘋果,春天會開那種優雅淺白的花朵。不同于路邊鄉氣的野花,那些花朵像是聽不懂意思的上海話,總給人一種很高級的感覺。他在樹下的墻邊種了幾叢枝枝蔓蔓的菊花,那些花朵很干凈也很貼切,讓人想到陶淵明的詩句——這些是父輩們無從理解的高妙。他家還有一棵蓬徑巨大的桂花樹,那是我聞到過的最深切的香氣。老正松曾經講過菊花的很多種類,他比其他農民更細致而優雅,這也是他無法被理解的原因之一。
老正松家屋后有一個不小的方塘,四周的埂子都仔細整理過,岸坡用水泥板牢靠地護著。塘里養的是常見的魚種,但總讓人覺得像公園里的水池。那些魚會在令人氣短的晨昏浮出水面四處游弋,看了讓人無比地心靜。日后我見過很多景觀里的錦鯉池,都覺得沒有那口池塘使人心醉。岸邊種著幾叢月季和萬年青,根邊泥上還有鍋灰的痕跡。村里人知道鍋灰是極好的肥料,對于月季和萬年青尤是不二選擇。伸出枝頭向水的柿子樹,偶爾有掉一兩個果子在水里,就有魚兒不停地追逐著嬉戲。
他的菜地在門口,與院門隔一條東西向的莊臺路。這是村莊里大體一致的格局,而他家菜地是可以當著景觀來看的。他不用蘆葦做籬笆,因為久了朽壞會生難纏的灰黑。這和鄰居們也是不一樣的,并非全是因為蘆葦輕賤。他在菜地的周圍隔段種上榆樹小苗,半人高的時候便“殺頭”留樁,這樣用網子圍起來一勞永逸且干凈。這種“活樁”上生長著郁郁蔥蔥的生機,就像是主人細致悠閑的心思。老正松菜園里的部署是整齊劃一的,就像我們后來說的“網格化管理”這個詞一樣嚴密而精致。韭菜的行列就像用尺子量過一樣,讓人一看就無比舒心,似乎他的土地里不是生長而是列隊。夏天生長最豐茂的時候,自成小林的辣椒、茄子與豆科一類,伏地冬瓜、南瓜和菜瓜一類,架子上牽藤的豇豆和黃瓜又是一類——他又在靠水的護坡種上忘憂草和菊花,這無人問津的一切有著詩意,是對一個孩子意外的美學啟蒙。
桂花開時,我心里總是癢癢的。母親給我買過一種廉價桂花香味的梳頭油,那種味道鄉氣而又頑固。我不知道聽誰說這些細碎的花瓣可以泡酒,便偷偷踮著腳扯住幾根出墻的枝條,一把薅下來想拿來泡父親視之如命的“糧食白酒”。因為緊張倉促,枝上的花瓣被震動得所剩無幾,但那種香味仍令人興奮無比。我把這些細碎的花瓣帶著塵土塞進了玻璃瓶,草草地埋進自家屋后的泥地里,就像是把沒有完成的作業藏起來一樣。
這些自然會引來爭執和不安,好在“三要不抵一偷”的俗話,還是讓我“逍遙法外”,好在吵鬧曾經一直是南角墩有趣的日常。
三
老正松斷氣的時候,我在城里忙碌未能歸來。我知道父親幾次打電話告訴我,是想讓我回去磕個頭的,除此之外并沒有什么更要緊的事情。父親也許還有一種隱秘的情緒,那就是他對自家子孫的提醒。他覺得有出息的子孫在外面再風光,最后卻不能在父母身邊,這到底不是什么周正的事情。父親是想以自己的這些行動告訴我們,子孫是他最終的依靠,只是倔強如他說不出煽情的話語。
父親的蒼老是從酒量上顯出來的,雖然他堅持不聽醫生的話斷了“一頓二兩五”的念想。我知道煙酒的危害是真實的,但也不曾斷過對他的“孝敬”。老正松走后,自家門口被他用水泥澆筑成平地,作為鴨子們的“作場”,而老正松的菜園子成了他無可爭議的領地。那些已經蒼老的樹樁每年依舊長出新芽,只是園子里的菜蔬都是父親一貫粗糙的手筆。他沒有耐心像老正松那樣伺候泥土,只是隨心所欲地撒上一些頑強的種子,任那些菜蔬瘋長在四季的輪回里。老正松家的院子也永遠關門上鎖,銹跡斑斑地守候著一段早已經結束的光陰。
我時常帶女兒推一推那扇已經朽壞的門,里面的生長已經放肆得失去了過去的體面,而我講的事情,孩子也沒有什么興趣了解。那些樹木已經蒼老得不再掛果子,瘋長的雜樹驕傲地占據了一切,它們竟然成為這個院落最后的依靠。屋后的塘口也被填上大半,殘余的水邊被父親隨意種了幾叢茭白,和野生的蒿草一起望天收地生長。水邊的那棵柿子樹也無人問津,掛了幾個有氣無力的果子更沒人留意。到了快熟的時候,父親就摘回來放在自家的米缸里催熟,等我和孩子回家的時候給我們“殺饞”——這里的一切,某種程度上已經都是父親的了,但他也并未顯露過一點興奮。
早年老正松把自家院子里桂花樹賣掉的時候,我就體會到了一個老人的灰心喪氣。我知道,他并不缺這幾千元的“外快”,但當我看見他數錢時候嘴角的蒼老笑意時,心里也就明白這一切是他對這個村莊最后的滿意,除此之外,他不再有任何依靠。看著他把一樹芬芳賣了,我就知道,一個老人決心不再留戀過往的時候,一切是誰的都已經不再重要,他也已經不再指望和依靠誰,毫無情緒可言的票子,用手帕卷著塞在腰包里,也許更為可靠。
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我見到狗在屋后跳躍,它是沒有任何情緒的。父親原先只覺得這不過是些畜生,可養狗之后他又像變了一個人,每次出去吃酒席都會像帶著孩子一樣,讓它坐在自己的三輪車上。當一個男人變成老人,一切好像都不需要再去爭取與解釋。他們可以把過去歲月里的血性和倔強全然放下,就由著一個牲畜蹦蹦跳跳而樂在其中。突然有一天,父親黯然地打電話給我,說小狗丟丟走失了。他圍著三蕩河沿線找了半個月,只找到了半根繩子,斷定它是遭遇了不測。我也回去找了很久,也看見了父親悵然的表情。我知道在他的心里,丟了狗就是丟了某種依靠。后來丟丟居然又跑了回來,他激動地打電話給我,說它回來的時候像個失魂落魄的孩子。他給它下面條吃,埋怨地咒罵它不知好歹——大概他心里也會想,這里,才該是這只狗的依靠。
村子里的房屋越來越少,而失去更多的是曾經辛勤而熱鬧的人。過去那些赤膊爭斗的人們,現在和手里蒼老的拐棍一樣倚靠在墻邊。他們不問親疏,不問恩怨,不問男女,甚至不問人畜,都成了彼此最后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