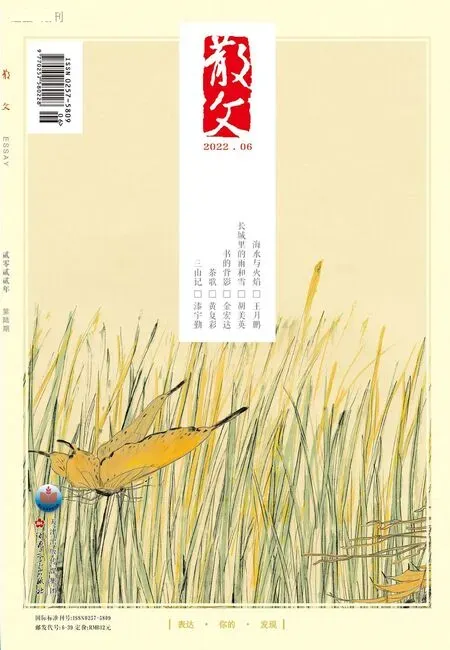讀書,而且勞作
劉學剛
我在菜園邊讀《工作與時日》。作者為古希臘赫西俄德,農耕時代的詩人,天堂世界的記錄者,黎明時期的歌手,人類文明的傳遞人,用勞動和大地發生關系的實踐者。
天空何其敞亮,蔬菜何其鮮亮。赫西俄德的好句子一行行地鋪展,如同蔬菜,鋪展著它們的莖葉花果。記不清讀過多少遍了。每一次讀,都像一場告解,帶著我的疲憊和煩憂,把赫西俄德讀給蔬菜聽,讀給昆蟲聽,讀給從體內的黑暗中奔突而出的另一個我聽。
有些人說我太執拗,不合群,他們的嘲笑有胳膊,有腿腳,也有翅膀。我依舊要矯正我的姿勢,完成一種簡單、質樸、緩慢的生活。我想,如果他們能夠細心地讀《工作與時日》,這些文字就會開口說話,響亮如清晨的雞鳴,深沉如黃昏的炊煙,把他們從紅燈停綠燈行的時間或地鐵報站的時間中牽引到《工作與時日》的時間中來。
《工作與時日》的時間不是單調的羅馬數字,它有氣息,有色彩,有聲音,有味道,時間感與宇宙感相交融。譬如,第一次鳴叫于橡樹間的布谷鳥是一種時間(陽歷2月),從地下爬到植物上的蝸牛是一種時間(5月中旬),天空中出現的獵戶座是一種時間(7月)。與這些時間相呼應的是,人們要進行從容不迫、細心縝密的應對,達成人類生活和自然節律的同步:2月,地上水深剛好齊牛蹄,晚耕;5月中旬,磨礪鐮刀,開始收獲;7月,貯藏谷物,為牛騾備足飼料和褥草,卸下耕牛的軛頭讓牛休息。
《工作與時日》的發生地波俄提亞,那里有一座海利肯山。赫西俄德在山上放羊,也寫寫詩。海利肯山是傳說中詩神繆斯的住地,居住著蜜蜂、葡萄藤的夢和許多的神靈。赫西俄德參加詩歌比賽,得過大獎,獎品是一只三腳青銅鼎。長詩《工作與時日》是一首訓諭詩,是赫西俄德對懶弟弟佩耳賽斯的一次“精準扶貧”。扶貧的重心,是指導生產技術和訓誡倫理道德,《工作與時日》,是文學具有救贖力量的一個可靠的見證。
我想說的是,被赫西俄德訓誡的,還有一個我。我與赫西俄德的遇見,是我生命中的一次立春,猶如經受嚴寒的樹木,竭力讓繁枝茂葉從一些米粒大的嫩芽上起身。那些年,就像一只在城市的霓虹燈下上蹦下跳的灰螞蚱,我神情倉皇,手腳忙亂。在清晨的微光中,追趕著急促的上班鈴聲。捧著母親的病歷,在街角診所和專科醫院里滿臉堆笑,人也矮了半截。寒冷的冬夜,去超市購物,看見光鮮的草莓、葡萄,身體突然僵在了中央空調的暖風里。赫西俄德的聲音響起了:
他們快樂地做自己想干的活計,土地為他們出產豐足的食物。山上橡樹的枝頭長出橡實,蜜蜂盤旋采蜜于橡樹之中;綿羊身上長出厚厚的絨毛;婦女生養很多外貌酷似父母的嬰兒。
改變竟然來得如此突然。我想放慢生活節奏、向后撤退的時候,讀到了《工作與時日》。這個“后”,不是落后,而是后面,是根部的所在。譬如,故鄉是我們的后面,土地是植物的后面。有了這個“后”,我們才能自在自足地前行。如同牧羊人赫西俄德的陳述,人們過著體面的幸福生活,這體面來自與土地的交往。土地是人性的主要貯存器,勞動培育勤勞、公正的美德。《工作與時日》用六音步詩行寫成,共八百二十八行,讀一遍無須很多時間,即使讀二三十行,我收獲的亦是無法言說的安寧和幸福。我是《圣經》的葡萄園里許多工人中的一個,我們每天勞動時間有長有短,所得報酬卻都是一樣。
我的耕讀生涯也始自與赫西俄德的遭逢。讀書,而且勞作,是我聚攏生活碎片的一種方式,我的體面而幸福的生活也由此開始。我在城郊一個廢棄多年的小工廠開墾了一塊荒地,種花種菜種春風,讓去年的種子以青菜葉或紫色花的樣子出現在暮春的陽光下。《工作與時日》反復述說的自然節律需要落地,與我的當下發生關系,開出幸福的現實之花。菜園以西是一個雞鳴喔喔、炊煙裊裊的村莊,那里生活著很多勤勞樸實的赫西俄德。偉大的荷馬以眾多盲樂師的模樣在無數的村莊吟唱,彈奏著月光的絲弦。兩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既牧羊又寫詩的赫西俄德不在別處,他以好鄰居的身份站在我的菜地上,教我如何制作土肥,如何識別黃瓜的謊花。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個赫西俄德式的父親或長兄。要是沒有他的勸誡,我們要如何在荒蕪上看見葳蕤,如何像莖葉花果那樣有條不紊地展開自己的未來,還有,如何懂得敬畏,懂得節制?一株黃瓜苗,谷雨移植,小滿開黃花,芒種結綠瓜,處暑葉子枯黃。我的菜在生長,赫西俄德的好句子也像蜜蜂一樣嚶嚶嗡嗡的,成為青菜的畫外音。
當我刨好小土坑,撒播了蘿卜種。赫西俄德說:“用泥土蓋住種子,以免鳥兒啄食,因為管理得好是凡人的至善。”許多這樣的時刻填充著我的菜農生活。我在菜園西南挖了一口井,用一個抽水泵把井水升到高處,又在菜畦里流成小溪,溪水中閃閃發光的凈是赫西俄德的好句子:“你的眼睛看著美好的河水做過禱告,又在此清澈可愛的水中把手洗凈之后,才能蹚涉這條常流不息的潺潺的流水。”
奔波半生勞碌半生之后,我用“頭伏蘿卜二伏芥,三伏有雨種蕎麥”這樣的時日來安排工作,在菜園里養育著如此眾多的小生命,像赫西俄德那樣活著。也寫詩文,讀給我的青菜們。如同赫西俄德稱頌的文藝女神——正是她們,在這山上首次指引我走上歌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