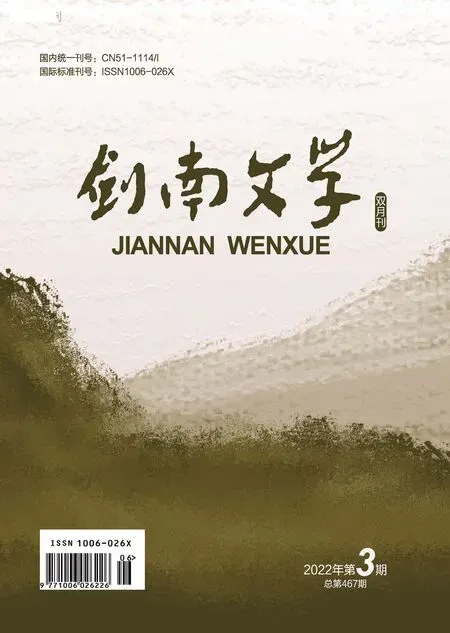跳沙坑的男孩
□ 楊啟云
讀五年級的時候,屈平原從會仙村小學轉到了鄉小。鄉小是個老叫法,實際上官方都稱鎮中心小學了,但老百姓就是不改口。
第一天上學,屈平原就把一個假期積攢的新鮮勁兒消耗掉了。一個是路太遠,一個是路太爛。桃源鎮倚著涪江,半山半壩,會仙村在最偏遠的山里。早上五點過,爺爺就把他從床上叫起來了,到新學校的興奮始終撐不起沉重的眼皮,早飯幾乎是閉著眼睛吃完的。換新衣服的時候,雞終于打鳴了。半夜才停的雨仿佛被雞鳴喚醒,唰唰唰又來了。爺爺倒是習慣了,四川的氣候嘛,八月底九月初打稻谷,天老爺是不會給好臉色的,得搶,搶晴的間隙。一路泥濘,屈平原腳下的水靴被扯掉了好幾次。一直下到壩子邊緣,上了石子路,才好些。十二里路,爺孫倆走了三個小時,幾乎算是最后一批到學校的。好在第一天是報名,沒人批評屈平原遲到了——當然,后來兩年時間,屈平原就沒有這么幸運,因為遲到罰站、罰搞清潔的時候就沒少過。
小孩子的熱情不容易被打壓。幾天之后,屈平原就恢復了熱情,這個動力既不來自于高大明亮的教室,也不來自各式各樣的新鮮面孔,它來自于操場角落的沙坑。因為下雨的緣故,整個九月的體育課幾乎是內堂,莫說學生郁悶,連老師都上得百無聊賴,干脆將體育課時間贈送給語文、數學老師。沙坑因此就空閑了下來,四周長滿了雜草。屈平原是拔雜草的時候發現沙坑的。哇!他很興奮。他們村上有人修新房,而且是那種砌磚的房子,才能看到河沙。在沙堆上滾來滾去,那是何等的愜意!唯一遺憾的是這里的沙坑不是用來滾的,那些老資格的鄉小學生像模像樣地奔跑、跳起來,然后落進沙坑,屈平原的興奮一下子就被抑制了。好在像他一樣的學生還不是少數,當時為了提高升學率,所有村小五年級的學生都集中到鎮上上學。幾個膽大的學著奔跑、跳躍,奔跑雖然別扭,但差距不大,跳躍簡直就難看了,頂多只能叫跨,有些人干脆就是跑進沙坑的。屈平原壯著膽子跑了一回,他不算最糟糕的,勉強算跳起來了,但是地心引力好像對他矮小壯實的身體特別偏愛,“跳了可能有一鳰高”。這是他后來回想起這段生活的自嘲。而且,落入沙坑后,他根本沒站穩,估計也不想或者不習慣站穩。他斜跌進去,然后打了一個滾——很愜意,他真想多滾幾下,可惜,后面的人像下餃子似的跳過來了,有人就撞在他身上,并且覺得抱歉,自己爬起來,還非要把他拉起來,不經意就壞了他的美夢。
沙坑有些潮濕,沙子沾了一身,有人還吃進嘴里,那種硌牙的感覺就不好了。不少人吃過一次虧就不跳了。國慶節一過,體育課正常了,沙包、跳繩、乒乓,還有各種球類,沙坑就愈發被人疏遠了。然而,總有那么一小群人,喜歡嘻嘻哈哈在沙坑邊亂跳一氣,并借機在沙坑里打幾個滾。屈平原就是這群人中的一個。
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初二。屈平原的個子并沒有往上長多少,跟他的成績一樣。這個真不能怪屈平原,不管是長個子還是讀書,他覺得自己都是努力了的,無奈先天不良。沒到鎮上讀書的時候,他還不知道有人居然能奢侈到每天吃肉。每周吃一次肉,他覺得這就是美好生活的上限了。至于成績,他倒也不慚愧,他們村上的第一名,下課都不出教室,不也是排在十名以后嗎?
然而,偏偏有人為他的成績著急。初二的時候新換了班主任,叫吳娟,是個漂亮的女老師,短袖襯衫牛仔褲,齊肩發,短劉海,一副眼鏡襯出文質彬彬的颯爽氣。吳娟是本地人,以優異的成績從本地初中升入縣師范學校,今年畢業就分配回來了。漂亮的新老師通常都有特別的親和力,吳老師對他們是真心的好,特別希望每個學生都優秀,包括身體,包括習慣,包括成績。
吳老師是溫柔而嚴厲的,她和男生打乒乓,和女生跳繩、踢毽子,有時候體育課打籃球,她也敢加入進來。但是,有人違反紀律,她就不客氣了,會用一根黃荊條打手心。鄉下孩子皮糙,頂多呲一呲牙,也就過了,下了課依舊嘻嘻哈哈。屈平原自然挨過手心,有時候走神,還被吳老師擲過粉筆頭,但大多數時候都沒有打中他,不是打空,就是打到旁邊人身上了。這時候,教室里一片輕笑,并沒人覺得是受了侮辱。
屈平原屬于“踩線生”。“踩線生”這個概念是他初三才聽說的。顧名思義,努力一點,就在線上,懈怠一點,就在線下。屈平原懈怠了很多年,早已經把自己定位為線下的那一部分人,初中畢業,學個磚匠或者木匠的手藝,然后就可以出去打工了。爺爺奶奶無所謂,他們認為只要身體健康,哪里都可以找飯吃。父母出去打了兩年工,深知知識的重要性,每次回家,都表達了希望孩子將來讀大學的殷切希望。
將來怎么樣,這個有點遠,不如在沙坑里打個滾來得輕松愜意。吳老師跟他私下交流過幾次,每次的鼓勵大概能管半天。屈平原也想努力,但一想每年能升學的,也就三分之一都不到,自己就是中下水平,大家都努力了,自己還不是中下水平?這就是眼界,他只是著眼本校,沒有高瞻全縣,升學的名額是可以爭奪其他學校的。
吳老師雖然年輕,但深諳心動不如行動的道理。她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有二十多個人,每天中午午飯后到下午1:40 上課前,到教室上一節自習。成績好的,自己會找事,成績實在差的,反正也沒有什么希望,反而得以僥幸維持快樂的學校生活。
效果自然是明顯的,到期末考試的時候,他們班的總成績就躍居全學區的第一名。屈平原也慢慢習慣了午休時候關在教室里,雖然習慣性地被操場上午休學生的熱鬧牽動眼球,但內心漠然,早已沒有了剛開始的焦躁。
第二年春天的太陽開始變得濃烈的時候,效仿吳老師的班級就多了。操場里從容的學生少了,很多學生就趕在午間進教室之前瘋狂一把。和屈平原滾沙坑的學生大都被壓縮到了這個時段,時間忽然變得緊迫,滾沙坑變成了一場資源搶奪戰。
那天不知道是搶奪得太忘形忘了時間,還是吳老師提前到了教室。總之,吳老師在教室里清點了一圈,然后站在教室的后窗望向沙坑的時候,屈平原還在沙坑里瘋狂打滾。
有人使勁拉扯了他一下,指著窗口對一臉懵逼的他說:“喏,你們老師在叫你。”他扭過頭,看見吳老師額頭抵在窗欞上,眼神刀一樣從鏡片后刺出來:“你!站那兒,別動!”吳老師一只手伸出窗戶,指點著他,聲音有點歇斯底里,透著一股狠勁。
他望了望四周,還有很多人在操場里悠閑地晃蕩。他定下心來,撣撣身上的沙粒,抓起丟在沙坑旁邊的棉襖,慢慢往教室走。
吳老師把他堵在了教室轉角。臂彎里夾著棉襖慢吞吞走過來的屈平原把吳老師惹火了,她逼視著他的雙眼,他發鬢下垂的汗滴、眉毛上夾著的幾顆沙粒硌疼了她的眼睛,憤怒瞬間湮沒了她。“回去,繼續跳。”她冷冷的語氣中夾著不由分說的堅決。
屈平原垂下頭,沒有動。他心里有些不以為然,應該還沒有遲到,就算遲到,也不是學校規定的上課時間,是被老師占用的休息時間而已。他只是在老師的侵犯下稍稍掙扎了一下而已。況且他的低頭就算是默認了自己的錯誤——本沒有錯誤,給老師一個面子而已。
屈平原的理由只是用來支撐自己的不以為然的,吳老師除了體會到他的抗拒,顯然無法感受他內心的想法。“回去!繼續跳!”吳老師一把抓住他的肩頭,針法粗糙的家織混紡毛衣輕松地被拉出一個三角形。他感受到頸部被線條拉扯的疼痛,他不想動,但頸部更大的力量傳來,讓他的頭逼著偏向發力的方向。看似文弱的年輕女老師的爆發力量不可小覷。屈平原放棄了掙扎,被頸部的毛衣重新拉回到沙坑邊。
“跳!”吳老師松開手,簡潔地發布命令,語氣中透著一股狠勁。
他沒有動,他還沒有發覺老師的異樣。
“跳!”吳老師一腳踢在他的腿彎里。他趔趄了一下,借機跨進了沙坑。臥在沙坑里的孩子翻身起來,退出了沙坑,遠處正準備奔跑過來的孩子止住步伐,他們在遠處圍了一個圈,成為沉默的看客。
“去,從那邊跑過來,跳!”吳老師指著跑道遠處,眼神里似乎彌漫著無窮無盡的悲哀與憤怒。
他垂著頭,緊抿嘴角,無聲地站在沙坑里。
“快去跳!”吳老師手指戳著他的額頭,有些歇斯底里。這時候,他感受到了老師的惡意。
絕大多數的農村孩子其實都是在打罵中成長起來的。這些打罵主要來自于父母。沒有精力,沒有文化,打罵是最簡單有效的教育方式。但是,他們只有對孩子不爭氣的憤怒,他們的打罵會適可而止,那些不受控制的責打,往往都包含著父母的傷心和絕望,最后的結果,常常是母親抱著孩子一起哭。
愛之深,責之切。有傷害,但是沒有惡意。
但這不意味著屈平原沒有感受到人的惡意。他五歲多的時候,參與了一次瘋狂的游戲。村落邊的李家兄弟,人雖吝嗇,但種得一手好桃。桃子臨近上市的時候,他們組織了一場游戲。那天剛好是雨后,桃園旁邊的排水溝里集了半溝水,七八個小孩子挽著褲腿站在水溝里蓄勢待發,他們的目標是水溝盡頭的一根木柱上擺放的一枚白里透紅的桃子。規則很簡單:李家兄弟喊“跑”,孩子們沿著溝沖過去,誰先搶到就是誰的。屈平原沒有任何收獲,他最接近勝利的一次是手指已經觸及桃子了,但是,因為用力過猛,插在水里的木柱被撞歪,桃子掉進了水里,按照規則,必須重新開始。一個小時后,有三枚桃子成為獎品,屈平原的母親忽然殺出,一把將他從水溝里拖起來,惡狠狠地瞪了李家兄弟一眼。李家兄弟因此訕訕地宣告游戲結束。
屈平原渾身泥水跪在堂屋里,他心中還殘留著盎然的興趣,也有些遺憾:只差一點,只差一點就搶到桃子了!他以為罰跪的原因,只是因為弄臟了衣褲。
母親燒好一盆熱水,就將他從堂屋里叫出來,讓他脫光了泡在熱水里。母親一邊幫他洗掉頭上的泥污,一面潸然淚下。這時候,屈平原才知道,這件事還有比弄臟衣服更嚴重的后果。
“娃啊,人窮志不能短。你想吃桃子,媽趕場去給你買。”母親的話里滿是酸楚。
現在,屈平原從吳老師惡狠狠的命令中感受到了和當年李家兄弟恣意的笑聲中相似的味道。沉默委屈的土壤中漸漸滋生了憤怒,他依然垂著頭,但骨骼、肌肉甚至于臉皮,都有一種繃緊的感覺。
“快去!”吳老師忽然一抬手,一耳光扇在他臉上。她的臉有些扭曲,一副惱羞成怒的樣子。
猝不及防的耳光帶來莫名的恐懼,死死壓制了屈平原的憤怒。就像夏天的驟雨,第一滴掉下來,第二滴第三滴馬上就緊跟其后,耳光失了控,接二連三扇到臉上,屈平原伸出雙臂抱住了自己的頭。
驟雨很快停歇,吳老師看起來比屈平原更痛苦,她喘著粗氣,右手掌通紅,嘴角溢出泡沫,幾縷發絲披散在臉上。圍觀的學生默默散去,他們教室的后窗,不時出現幾張震驚的面孔,靜默中夾著驚恐、疑惑、不安、哀傷,停留片刻,趕緊閃過。
屈平原在辦公室站了一下午,吳老師一直沒有出現。既沒有來批評他,也沒有來給他一個挨打的充足理由。上課下課的老師、抱作業本的值日生來來往往,屈平原收獲了不少好奇或者憐憫的目光,還有好心的老教師的幾聲嘆息:“娃呢,又不聽話了。”
到下午課外活動的時候,辦公室只剩下他一個人,他下定了決心,昂然離去,混在通食生的隊伍里出校門回了家。
正是桃花謝菜花初放時,一路都是蜜蜂嗡嗡裹挾著花與青草蓬勃的氣息,走著走著,屈平原緊繃的身體松弛了,恨意漸漸消退,離家愈近,腳步反倒遲疑起來。
磨磨蹭蹭到了家,爺爺正在院壩邊喂牛,聽見腳步,一回頭,滿臉都是疑惑:“你怎么回來了?”
“不想讀了!”屈平原努力裝出氣沖沖的樣子。
“不想讀了?”爺爺很詫異,聲音一下子就高起來了。他丟下手里的牛草,跟著屈平原進了屋。奶奶也從灶房里過來。“孫兒,在學校受氣了?”她的緊張語氣觸動了屈平原心里的委屈,他的眼圈一下就紅了。
“誰打你了?這么狠,你看這臉上的手指印。半邊臉都腫了!”奶奶眼尖,驚詫詫叫了起來。
“吳老師。”屈平原忍住眼淚。
爺爺奶奶愕了。“老師也不能這么打,學生又不是罪人,哪個都要犯錯的。”擠牙膏一樣從屈平原嘴里擠出事情經過,奶奶憤憤不平。
“快去燒水,給娃兒熱敷一下。”爺爺顯得冷靜些。
奶奶心疼的抱怨、妹妹放下作業跑來圍觀的震驚和憐憫所帶來的尷尬,完全壓倒了屈平原臉上的疼痛。
“都莫說了,煩不煩!”他自己的英雄氣概倒出來了。
這事真不能善罷甘休,一次遲到,也被打得這樣,那今后怎么辦?真的不上學了?那是萬萬不行的——如何面對兒子媳婦!爺爺奶奶在飯桌上商量了一晚上,決定明天一早就去找吳老師的父母,畢竟直接跟吳老師掰道理風險太大,萬一年輕人氣勢太盛不講道理怎么辦?還是迂回吧,讓她父母管教,這是最好的辦法,也算給了吳老師面子。
早上屈平原睡了個自然醒——其實也比放假時候醒得早多了,畢竟習慣了在學校上早自習。剛吃過早飯,爺爺回來了。
“談得咋樣?”奶奶心急如焚。
“哎!”爺爺嘆口氣,把手里提著的一只用稻草縛著雙足和翅膀的老母雞丟在地上,自去階沿上抽出插在土墻裂縫里的煙袋,裹了一鍋,深吸一口,這才開口。
說起來,吳老師的爸爸跟爺爺算是熟人,他是個編竹器的手藝人,爺爺趕場還買過他編的背篼、撮箕。所以,爺爺表達得很委婉。吳老師父母也是明白人,她爸爸陪著爺爺抽悶煙,媽媽則不停地在旁邊賠不是。“娟女子最近完全變了個人。脾氣暴躁,三兩句就吵,連我們都要吼。以前有空就回家,現在倒好,起碼有一個月沒回來,去學校看她,她還不耐煩。我們找旁人問,才聽說是感情出問題了。”
吳老師初中畢業后,和一個男生好上了,她讀師范,男生就在斜對面的縣高中。她爸爸媽媽本來是反對的,自己的女兒畢業就是教師,是鐵飯碗,讀高中考不上大學回來還不是農民?無奈女兒堅決要喜歡,把學校發的伙食費和父母給的零用錢省下來給斜對門的高中生。這男生還硬是爭氣,去年高中畢業考上了北京的大學,可惜,才讀了半年書,就給吳老師寫了分手信。說是跟吳老師一直只是同學情誼,感謝吳老師的支持和幫助。
“你說都是本鄉本土的,感情我女兒是熱臉貼在了冷屁股上。你讓孩子今后怎么見人?”吳老師的媽媽眼圈一紅,眼淚就出來了。
話說到這里,爺爺心里也明白了,人家女娃子遇到這么大的事情,心情不好發點氣也正常,都怪自己娃娃運氣差。吳老師的父母恐怕也只能旁敲側擊,希望今后吳老師不再亂發脾氣。吳老師的父母滿懷歉疚,非要捉一只雞,讓爺爺帶回去給孩子養養身體。
關鍵是——娃娃覺得這個面子丟大了,怎么做工作讓他去讀書?兩位老人倒真是頭疼。
“先放一放吧,讓他在家里吃幾天苦,把事情淡忘了,自然就想去學校了。”爺爺也只有出此下策。
屈平原既然不告而別,也就打定主意,讀不讀書無所謂。不讀書也沒有什么不好,幫忙放牛砍柴,他還是能做的。所以,他也懶得多想,干脆獨自跑后山上掏鳥窩去了。
偏偏車到山前自有路。等屈平原從山上屁顛屁顛跑下來,猛然發現院壩里停著一輛自行車,原來是教數學的趙老師來了。
趙老師是代吳老師來道歉的。趙老師說,吳老師是個好老師,責任心強,工作努力,雖然處理問題有點過激,但確實是為娃娃好。她打了娃娃,自己關在寢室里哭了一下午,等她發現屈平原離開學校了,也很著急,可是,天晚了,路遠,又不熟。要不是今天一上午的課,吳老師就親自來了。
爺爺奶奶一面歡喜事情意外解決,一面又覺得麻煩老師上門,實在過意不去,非要從柜子里翻出一塊臘肉,扯了幾根萵筍,留趙老師吃午飯。午飯后,屈平原坐趙老師的自行車回學校,爺爺奶奶把他們送上機耕道,直到他們背影消失在山灣處。
好像昨天什么也沒有發生——如果你不注意屈平原剛踏進教室時大家偷偷瞟過來的眼光的話。晚上讀報時間,吳老師走到屈平原面前,見他一直垂著眼簾,遲疑了一下,也沒有說什么。
從此之后,屈平原像變了個人,除了悶坐在教室里讀書,就是悶坐在教室的后階沿上,和幾個耍得來的小個子男生下“六子沖”(一種棋類游戲)或者“狗卵子”棋,沒人的時候,他就自己跟自己下。除了上課答問,他再沒有跟吳老師說過話。
在爺爺奶奶看來,重新進學校的屈平原變乖了,兩個老人很高興。上街趕場的時候,屈平原爺爺背上吳老師家的老母雞,又從自家柜子里撿了二十個雞蛋,從地里扯了一捆萵筍,送到吳老師寢室。吳老師紅著臉推拒,他爺爺按住老師的手說:“小孩子皮糙,打幾下沒事的。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不自在。”吳老師囁嚅著,終于沒說出什么。老母雞物歸原主,爺爺也就如釋重負。
初三畢業,屈平原順利踩在了線上,可惜只考上了縣里的三流高中。父母心里面遺憾,但電話里的聲音還是很高興的。為了兌現這份喜悅,父母特地趕回來,要請老師吃飯,以示感謝。這個時候屈平原剛躥了個頭,長得和他父親一般高,嘴角有了髭須,不再是小孩子模樣。他自然是不贊同父母意見的,父母只好折了中,背著他買了禮物去見吳老師,還帶回了吳老師回贈給他的一只英雄鋼筆、一個漂亮的筆記本。“你們的老師好客氣哦,你真是遇到了一個好老師。”母親把鋼筆和筆記本給他送到房間的時候,激動得臉色發紅。他挨打的事情沒有人告訴父母,除了他,估計家里人都忘了。母親出門后,他就把桌子上的筆和本子丟在一個舊鞋盒里,然后扔到了床下。
屈平原就讀的五中在縣城以北四十多公里的山里,算是最偏遠的高中。去了之后,居然很快有了優越感,原來來自壩里學校、又靠近縣城的學生,在山里孩子眼里,都是些見過世面的。
高一上了一學期,老師就開始給學生精準定位:哪些是重點照顧對象,哪些是踩線生,哪些是能忽悠畢業的,哪些是提前要攆走的。屈平原就像春天里拔節的麥苗,個頭偷偷地又竄了一截,壯實的影子雖然不見了,但看著還結實,加之有速度,彈跳也不錯,老師就跟他談,要他加入學校運動隊,當體育生,將來走體育專業還是很有希望的。
畢竟大學的誘惑在那兒擺著,但是進訓練隊要交訓練費,還要買運動服,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屈平原心里就有些打鼓。老師為了幫助他實現心愿,讓他把電話給父母打通,自己幫著給他爸爸媽媽做工作。父母希望他上大學的心情自然比他還迫切,當時就答應寄錢回來。
根據他的身體素質,老師給他選的體育專項是跳高。訓練跳高的是高三的謝教練,謝教練是個老資格的體育教師,四十多歲,身體壯實,眼神凌厲。熱身跑的時候,他的目光在屈平原身上掃過幾次,讓屈平原如芒刺在身。接下來是每個人試跳,動作各式各樣,有跨過的,有滾過的,有翻過的,甚至于有人一腳踢翻了木質的立架。學生們嘻嘻哈哈,教練的嘴角緊抿,板著一張生鐵似的臉,眼神在沙坑邊編織出刀光劍影陣。
屈平原是最糟糕的那一個,沒有之一。他在跳高桿面前劃了兩次弧線,都沒能跳起來,那根細細的斑竹桿像是橫亙在他面前高不可攀的陡壁,他輕松的助跑就成為最后落荒而逃的反諷。第三次他終于撞進了沙坑,周圍無形的壓力就像推土機,而他,像被推進沙坑的一堆土,斑竹的橫桿自然跟他一起跌落沙坑。
謝教練估計也是忍無可忍了。他剛從沙坑里坐起來,謝教練就遠遠地指著他說:“那個學生——你那叫跳高?你那叫豬拱白菜地。就算你沒學過,前面那么多人跳,沒吃過豬肉你還沒見過豬跑?別跳了,跑五圈!”
周圍一陣哄笑,屈平原臉騰地就紅了。他慢慢從沙坑里爬起來,走上跑道,然后慢慢開始跑起來。不是他笨,也不是他不想跳,是沙坑拒絕他。他每一次跑近沙坑,就心生怯意,仿佛沙坑變成了一堵巨大而堅實的墻,他跳起來,就會撞得頭破血流。
他有些郁悶,自然在跑道上邊跑邊走神,在教練偶爾瞟過來的余光中,他懶洋洋的身影刺激著教練的耐心。
“滾過來!”跑到第三圈的時候,他聽到了謝教練的吼聲。他自然不會滾過去,一個高中學生應有的尊嚴他還是要堅守的;而且,他并沒有像小學時候,一聽到老師的吼聲就趕緊奔跑過去,他是走過去的,他的高而略偏瘦的體型成功地制造了誤會,他并不慢,但關健是步幅大而節奏慢,全沒有矮小學生走路時看起來快速積極的樣子。
“看你龜兒那懶洋洋的樣子,你是被人抽了腳筋還是夢游沒醒?老子最見不得你這種又散漫又自以為是的學生!你這個樣子要是能訓練出來,雞公都會下蛋了!”謝教練沒等他走到面前,一頓怒罵已經劈頭蓋臉而來。
我怎么了?你憑什么罵我?屈平原抹掉濺在臉上的口水,直視著教練,滿臉的不服氣。
“你還不服氣?你這個態度,還訓練個屁,滾!”謝教練話音很冷,聲調卻并不高,明顯控制了自己的暴怒。伴隨著一個“滾”字,屈平原感覺大胯上挨了一腳,力量不大,卻讓他打了個趔趄。
學生們都沒吭聲,高二高三的學生知道謝教練從前是練足球的,曾代表縣足球隊到省上參加過比賽,這一腳,算是客氣的了。
但屈平原不這么認為。有什么了不起,不練就不練,老子還不稀罕呢。說實話,屈平原對自己升大學的事情沒有那么執著,愿望主要是父母的,如果說他還抱了一點希望,大約也就像夏天的晨霧,若有若無的,風一吹,也就散了。
所以,屈平原冷冷地瞟了教練一眼,扭身就走了。
“回來!”謝老師一聲悶喝。他沒想到屈平原真敢“滾”。按照以往的模式,學生低著頭挨訓,等到老師脾氣發完了,訓練繼續。說實話,農村學生考大學實在不容易,老師也不愿意輕易就剝奪了他們的機會。屈平原不按套路出牌,謝老師面子上就掛不住了。
屈平原站住了。
“訓練隊不是茶館酒店,想來就來,想走就走!這五圈跑不好,就一直跑!”謝老師見屈平原停下,心里也松了口氣。他的語氣依然強硬,但其實已經色厲內荏。
可惜屈平原沒聽出來,他聽到的依然是威脅,所以,他遲疑了一下,并沒有回頭,直接回教室了。
晚自習的時候,班主任把他叫到了辦公室。
“你有好多羊子吆不上山(土話,意思是好多驕傲的本錢)?”班主任語氣不善,“學校、老師想方設法給你們創造條件,希望你們能考上大學,改變命運,結果呢?你們一點也不領情!教練脾氣直,偶爾懲罰一下不努力的學生,也是正常的。你倒好,脾氣比教練還大!”
老師時而呵斥,時而語重心長,說了半天,無非教練很生氣,只是看在和班主任多年同事的份上,同意接受屈平原道歉,然后讓他回到訓練隊。
屈平原不想道歉,就算他不努力,也不該換來羞辱。如果這事情都不再提,他還可以勉強接受重返訓練隊。
班主任盯了他半天,像看怪物似的。
“我懶得跟你說,你好好反省。”班主任把他扔在了辦公室里。
這是一個初春的夜晚,屈平原孤零零地站在老師的辦公桌前,四周陣陣涼意傳來,也夾雜著山區里各種野花和青草的氣息,不自覺喚醒了屈平原身體的記憶,那個沙坑邊挨打之后站在辦公室的下午。他的心里彌漫著心酸,與那次不一樣的是,他長大了,變得更果決。
半個小時之后,屈平原離開了空蕩蕩的辦公室,他在寢室里簡單收拾了衣物,穿過老師宿舍樓下時,一腳踢翻了謝老師的蜂窩煤爐子,在學校門衛專注看電視劇的側影映襯下,昂然離去。
他半夜到家的時候,爺爺奶奶嚇得不輕。但這一回,爺爺束手無策。放在從前,高中生都該算秀才了。秀才的老師,你如何找他理論?老師的父母,爺爺當然更是無緣相識。
父母專門趕回來,要送他回學校,還四處托人去斡旋。屈平原堅決不回學校。父親忍無可忍,將就房背后的黃荊條一頓抽,又喊他在堂屋里跪了一夜。天亮的時候,屈平原雙目凜然,神情決絕。母親撫著他背上的淤青,大哭了一場。一家人從此斷了再讓他去上學的念頭。
從此,屈平原的生活在學技術和打工之間轉換折騰,幾年之后,他同億萬農民工一樣,擠上漫長的綠皮火車,在打工的軌道上漸行漸遠。
耍朋友、結婚、生孩子,他繼續踏上父輩的道路。爺爺去世,奶奶佝僂著身子,再也帶不動孩子,母親從打工者隊伍中退出來,肩負起帶孫子的重任。
如果說有什么不一樣的,那就是屈平原夫妻都算是有一點文化的人,更加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孩子一定要讀書,讀大學——這點早已成為家庭的共識,毋庸置疑。但是,屈平原還有個要求,那就是不受氣。他要強調這個,母親自然就想起他小時候,難免心酸,帶孫子的時候特別注意。有一次,孫子在學校跟一個小女孩拉扯了幾下,臉上帶著抓痕回來了,他母親是個老實人,多年的打工生活養成了埋頭苦干、任勞任怨、不與人爭吵的好習慣,孫子受氣,急在心里,輾轉一夜,天明的時候想了一個笨辦法,把孫子的指甲剪尖,期望下一次抓扯的時候是對方受傷或者起碼持平。結果第二天就被老師發現了,打電話給他,他哭笑不得,又加了一條——基本的道理還是要講。
兒子漸漸長大,一起長大的還有屈平原心中的痛點。牛奶、水果只是讓兒子身體強壯,但內心的強大、知識、能力和未來卻縹緲難測。他知道,孩子跟在父母身邊、上好學校預示著最好的結果,但以他羞澀的收入,不過是在糾結之中,兒子從鎮中心小學畢業,然后進入了鎮初中。
屈辱之余,他也找到了欣慰點:兒子不僅有著超越同齡孩子的強壯,而且成績也比他從前好很多。母親說,按老師的說法,只要孩子成績不滑坡,畢業考上縣中是沒問題的。
縣中是國重,換在以前是不敢想的。屈平原讀初中的時候,學校要隔一兩年才會有一個學生考上縣中。這幾年鎮中與時俱進,學校管事的找過好幾次風水大師,后來校門改向西方,再后來又向著東方。估計要不是南邊是櫛次鱗比的居民,校門還得向南改一回。然而,改過之后,學校果然一帆風順,年年都有升上縣中的學生,后來愈來愈多。校門一改,屈平原每年春節回家的時候,就只能看看學校的側影。學校是屈平原出遠門的必經之道,從會仙村出來的公路抵達學校面前,然后拐上縣道,奔縣城。學校校門先前向北的時候,屈平原抵達鎮口,迎面給他的,就是學校的正臉。
不過,管它正臉側臉,屈平原畢業之后就從未再踏進校門。每次經過學校外的時候他心里都是疙疙瘩瘩的,但又忍不住會向里面瞟幾眼。他讀書的兩層木樓早已經拆除了,替代的是一幢高大敞亮的四層磚混大樓,明晃晃的玻璃窗映照著藍天白云。香樟樹被砍掉了,替代的銀杏樹高聳出圍墻,可惜每年春節回家,只看到光禿禿刺向天空的丫杈,從未見過一地金黃。
既然兒子大概率能上縣中,他的心中也就釋然了不少,對鎮中多多少少增添了一點親切感,甚至于對妻子手機上的微信家長群偶爾也關注一下。
春節回家的時候,母親希望他去拜訪一下老師——他兒子都初三了,還有半年就畢業了——重要性不言而喻;況且,班主任很關照孩子的。他本能地拒絕了。母親說這話的時候本身就遲疑,像是鼓足了勇氣,他的回絕似乎也在母親的意料之中。
其實,他看似不假思索的回絕背后,是難以言說的煎熬。以他對孩子的期望,見老師、送紅包應該是必經之道,然而,他的面前橫亙著一座山,這座山就是孩子的班主任——那個曾經打他耳光的吳娟老師。得知吳娟教他的兒子,他憎恨過“無巧不成書”“緣分”“命運”等扯淡的詞語,甚至思考過轉學轉班。然而統統不成立,況且,他也聽到過各種有關吳娟老師的描述:學校最好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市優秀;性格溫和,對學生好;有好多次調進城的機會,甚至新成立的外國語學校專門請過她,她都拒絕了。
他選擇了沉默和回避。
母親早已在他床下的鞋盒里發現了丟棄的鋼筆和筆記本,但她不相信歲月不能讓兒子釋懷。她不挑破,但會故意向兒子轉述吳老師的種種好。兒子保持了沉默,話說得多了,他就煩躁起來。
然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春節出門不到一個月,屈平原膽囊發炎,回家做了膽囊切除手術,休養的時候正值兒子二診考試后的家長會。母親這回有些生氣,一個大男人,屁大點事情老是藏在心里,難道比孩子升學的事情還大?母親說,你兒子初中都快畢業了,父母就沒去開過一次家長會,沒在家還可以理解,在家也不去,讓兒子怎么想?我一個老太婆,每次去見了老師都唯唯諾諾,老師說什么也不懂。你一個當父親的,就不能給你兒子點面子嗎?
母親是真氣了,眉頭緊皺,額上丘壑縱橫,頭上花白頭發紛亂。屈平原猛然發現,母親真的老了,已經不是當年那個依從他,帶著他進城買鞋買衣服,抱著他哭的年輕女人了。他眼里有些酸澀,知道這回是無法逃避了。
踏進學校大門,他的眼里自然全是陌生,房屋自不必說,原來的前后操場連成了一片,泥地變成了混凝土的籃球場。他的眼光定格在操場一側,那里曾經有個沙坑,現在立著籃球架。
他松了一口氣。二十五年未進校門,內心里疙里疙瘩的感覺是有點,但并沒有一直繃著的那種緊張。
人更是陌生,老師大都是新面孔(對他而言),偶爾看見個老教師面貌依稀,但看他時眼神漠然。他自然也就心安理得不打招呼,免得對方去強力搜尋可能不存在的記憶。
“你是當年那個……那個……”他偶爾也能看到這樣的一幕,他有些憐憫這樣的尷尬場面。
兒子領他進的教室。家長坐自家孩子的座位,學生們都擠在教室后。
吳老師站上講臺的時候,屈平原心中喀喇一聲,就像冰層解凍,完全釋然了。臺上這個四五十歲的女人,完全被歲月折騰得面目全非。依然是齊肩發,但染過的黃色并不能掩蓋鬢邊額前蜿蜒的白發。個頭全然不是當年印象中的高挑,是矮而微胖。瓜子臉被皮下脂肪撐得微圓,變成了被焦慮長期烘烤的土黃色。修過的眉毛像一條僵直的黑蟲,臥在溫和而疲憊的雙眼上方。
吳老師的語氣中充滿堆砌起來的熱情,溫軟空乏,讓屈平原神情恍惚,完全無法還原出當年乒乓臺邊那個黑發飛揚笑聲清脆的美麗女子,那個戳著他額頭恨鐵不成鋼的颯爽形象。
“后面的同學,請安靜點。”吳老師忽然提高了聲音,溫和中透著一點嚴厲。家長們忍不住往教室后望去,擠在一起的學生嘰嘰喳喳,有些騷動。
“你是不是給臉不要臉!”一個高挑時髦的漂亮女生忽然給了她旁邊一個高個子男生一耳光。聲音不響,馬上就被周圍同學的驚叫聲和噓聲掩蓋了。
“在干啥……在干啥!”吳老師怒氣沖沖地從講臺上沖下去,屈平原的目光跟隨她急促而微微笨拙的腳步向后移,自然就看見他的兒子一只手捂著左臉。
“杜巧玲,你發神經啊!”他兒子右臉一片急紅。
他有些意外,他沒有想到杜巧玲是這樣一個早熟的漂亮女生。兒子跟他說過杜巧玲,初一就給他遞過紙條,被他拒絕了。“成績差,不講理,聽說她爸還是操社會的,喜歡拿刀砍人。讀小學時,跟人吵架,動不動就威脅說要叫她爸來把人殺了。跟個女操哥似的,誰敢跟她耍朋友!”他當時暗暗感慨兒子懂事,還忍不住調侃了兒子幾句。
他不知道兒子跟杜巧玲發生了什么矛盾,但肯定是小事,按他的經驗,老師已經急匆匆出面了,這個事情暫時就按了暫停鍵。
事情超越了他的經驗。
“我就發神經,你能把我怎么樣?”杜巧玲抬手又是一耳光。
要干啥?!他有些憤怒,他看見兒子伸手一推,杜巧玲一個趔趄,周圍的學生往后一退,杜巧玲就跌倒地上。
“你們在干啥?!”吳老師避開幾個后退的學生,聲音急巴巴的。
一個矮瘦的男人忽然間從后排座位上站起來。
他手上有刀!屈平原心里咯噔一聲,他看見那個男子面色陰沉,手一揚,就向自己的兒子撲去。糟了!他本能地一蹬腿,就要往后沖,胯骨忽然撞在左右的課桌上,哐啷啷一片響,腳下凳子一帶,差點摔倒。
完了!他心里滿是絕望和憤怒。
一片驚叫聲中,他跳過凳子,看見吳老師伏在他兒子身上,后背上插著一把匕首,那個矮瘦的男人兔子一樣跳出人群,眨眼間消失在門外。
這時候,屈平原才感覺到自己的兩胯、腳踝疼痛,還有切掉膽囊的那個位置,那種沉悶的、被拉扯的、難以言說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