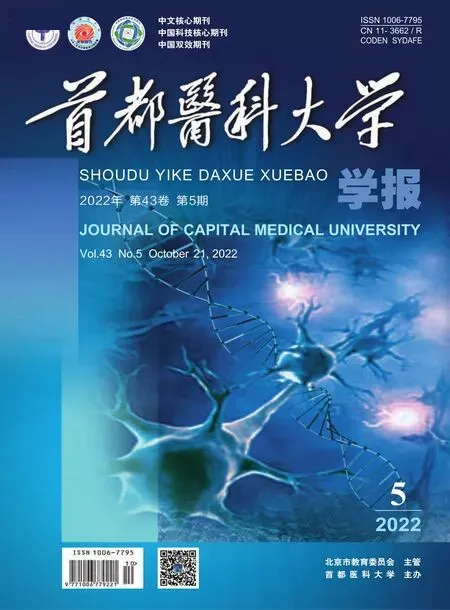“Chinese way”在關節鏡下處理巨大肩袖損傷中的作用及臨床療效
張 博 林 源 任世祥 陳 彤 于 洋 賈佳霖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骨科,北京 100020)
巨大型肩袖損傷一直是肩關節鏡手術中最具挑戰性的話題,治療方案眾多,較為棘手。根據患者術前的臨床癥狀及影像學表現很難完全預測肩袖修復的可能性,患者年齡、活動要求、撕裂類型及殘留肩袖組織質量、手術技術熟練程度均影響著手術決策的制定。以往有研究[1-2]顯示,通過肩峰成形、大結節成形及肩峰下組織清理減壓治療巨大肩袖損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這些術式均無法改善肱骨頭的上移及肩峰下間隙的不斷減少,而肩峰下間隙保留是肩袖修復術預后良好的預測指標。隨著肩關節鏡技術的不斷發展,巨大肩袖損傷的鏡下縫合及重建已經成為可能。Mori等[3]及Lee等[4]的研究表明,巨大肩袖組織的邊緣修復縫合可重建肩袖組織的力偶平衡及力學傳導,術后肩關節疼痛緩解及功能評分明顯改善。但損傷導致的脂肪浸潤,肌腱結構的退變或收縮,會導致撕裂的肩袖修復難度加大,修復失敗率升高,一直是臨床治療的難題之一[5]。
近幾年,“Chinese way”作為一種鏡下修補巨大肩袖損傷新的固定方式,已經逐漸應用于臨床,并取得了較好的治療效果[6]。它是一種利用肱二頭肌長頭腱(long head of biceps tendon,LHBT) 轉位固定于岡上肌腱足印區,以替代重建上關節囊 ( superior capsular reconstruction,SCR) 修補巨大肩袖撕裂的方法。Kim等[7]的研究顯示,采用“Chinese way”的方法,不僅能對肱骨頭產生向下壓的作用,還能避免因使用其他移植物帶來的感染風險。但該術式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可能引起肱二頭肌止點疼痛或者陣攣痛,并且會加重肱二頭肌退變程度。本研究擬通過隨訪來評價“Chinese way”在關節鏡下處理巨大肩袖損傷中的作用及其治療效果。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期間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收治的運用“Chinese way”方法治療單側巨大肩袖損傷患者的臨床資料,符合納入標準的患者共42例,其中男性23例、女性19例,年齡45~76歲,平均年齡(57.2±6.3)歲。右側30例,左側12例。術前均以“關節疼痛伴或不伴活動受限、外展乏力”為主訴就診,術前癥狀持續時間3~25個月,平均(11.6±4.2)個月,均保守治療無效。術前完善肩關節正位、Y 位(岡上肌出口位)片、肩關節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檢查。癥狀、體征及影像學檢查均支持肩袖巨大撕裂診斷,術中進一步確認并測量。手術的實施以及術后隨訪工作已經獲得了患者的知情同意,并且經過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倫理編號:2017-科-213)。
納入標準:①患者具有或不具有外傷史,有疼痛、活動受限等肩部臨床癥狀,術前查體符合肩袖損傷表現,如Neer征陽性、Hawkins征陽性、落臂征陽性等;②MRI 檢查提示肩袖巨大損傷,即多根肩袖撕裂( ≥2 根) 或肩袖撕裂口寬度在 5 cm以上,Goutallier <3級,X線片提示Hamada分型 1~3 度;③關節鏡下探查確認巨大肩袖撕裂,岡上、岡下肌腱撕裂嚴重,退變明顯伴有回縮,有一定張力,伴有或者不伴有小圓肌、肩胛下肌腱部分或完全撕裂;④關節鏡下確認肱二頭肌長頭腱在關節腔內質量良好,無縱向撕裂,可伴有輕度退變。
排除標準:①診斷為風濕性、類風濕性關節炎或色素沉著絨毛結節性滑膜炎;②巨大肩袖撕裂翻修者;③既往有其他肩關節手術史或關節感染史;④患者既往存在腋神經損傷或三角肌功能不良,嚴重的肩關節不穩;⑤心肺功能較差不能耐受手術;⑥患者有精神病史不能很好配合;⑦無康復意愿或無法隨訪的患者。
1.2 手術方法
手術由同一位高年資醫師完成,所有患者采用全身麻醉,沙灘椅位。常規消毒、鋪巾后,由肩關節后方軟點將關節鏡(30°)置入關節腔,腰穿針定位下建立前上工作通道。常規關節鏡探查關節腔有無合并損傷及肱二頭肌長頭腱關節內部分連續性及質量。對合并關節粘連的患者行關節囊松解術;對合并肩胛下肌腱撕裂者,根據撕裂大小選擇關節腔內修補肩胛下肌腱;然后建立肩關節外側入路及前外側入路,將關節鏡置入肩峰下間隙,清理肩峰下滑囊,成形肩峰前下方骨贅。
清理肩袖表面滑膜組織,充分顯露肩袖前外后側間隙,鏡下觀察評估肩袖撕裂及回縮情況,術中確定:肩袖均為巨大撕裂,累及2根及以上肌腱且肌腱回縮明顯,難以拉回足印區或雖可拉回足印區但張力較大。損傷情況確定后開始進行修補手術:①首先徹底松解回縮的肩袖組織,離子刀切斷肩峰下以及關節盂上方粘連結構;然后將肩袖離斷面新鮮化,如果肩袖分層則需清理上下層間隙,保留質量較好的肌腱組織,如果存在縱裂,則需要清理裂口邊緣;離子刀清理肩袖足印區以及螺釘置入點的軟組織,必要時將置入點適當內移至肱骨頭軟骨面(本組患者有2例需要內移,內移距離5 mm),用磨刀磨除肱骨大結節骨贅,打磨足印區骨面至少許血液滲出(打磨不宜過深,否則影響錨釘的穩定性);②將肱二頭肌長頭腱轉位至岡上肌腱足印區近關節面處,一般后移1~1.5cm(位置不應偏后,可適當偏前,避免肱二頭肌長頭腱張力過大,導致術后疼痛加重),置入1枚直徑4.5 mm內排錨釘(Twinfix Ultra PK Suture Anchor,Smith&Nephew公司,美國);錨釘的每組尾線分別穿岡上肌腱偏前方組織以及肱二頭肌長頭腱,然后分別與同組的另外一條尾線打結固定;③根據肩袖撕裂的范圍來確定錨釘數量并選擇合適固定點置入內排錨釘盡量使尾線由前向后均勻穿過全層的肩袖殘端組織(距離離斷邊緣約1.5 cm)并兩兩打結;最后將尾線分組,盡可能使肩袖殘端組織完全覆蓋于大小結節表面,使用直徑5.5 mm無節外排釘(Footprint Ultra PK Suture Anchor,Smith&Nephew公司,美國)將尾線拉緊后分別固定在肱骨大結節下方,鏡下確認肩袖殘端與其足跡貼附緊密。
1.3 術后處理
術后即給予患者阻滯鎮痛、預防感染、消腫等對癥治療。所有患者術后均按照統一的康復手冊進行功能鍛煉,具體的計劃包括:①術后即給予患肢佩戴肩關節外展包,保持在45度外展 、0度外旋及 0度前屈的位置;②術后第1天開始主動行腕關節和前臂肌肉收縮訓練,禁止主動屈肘活動訓練以防止牽拉肱二頭肌長頭腱;③術后2周進行肩關節肌肉等長收縮、肘關節屈伸等鍛煉;④術后6周以內進行被動功能鍛煉,主要以鐘擺樣運動為主,適當進行外旋及肩部前屈上舉活動;⑤術后6周后開始輔助性主動功能活動,如患者無不適主訴可停止佩戴肩包;⑥術后3個月開始肌肉力量的恢復訓練,適當增加抗阻練習;⑦術后 6 個月開始進行對抗性訓練。
1.4 觀察指標
所有患者的指標觀察點為術前、術后6個月、1年、2年,由同一非參與手術醫師記錄、評估并統計。具體觀察指標包括:①患者手術基本情況,術后是否出現切口感染、神經血管損傷、大力水手征、陣攣痛、關節粘連以及錨釘松動,甚至錨釘脫落移位等并發癥;②記錄患者術前、術后6個月以及末次隨訪肩關節活動度,包括:前屈上舉、外展上舉和體側外旋角度;③采用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對所有患者術前、術后6個月以及末次隨訪疼痛進行評價;④比較患者術前、術后6個月以及末次隨訪的功能評分,包括:美國肩肘外科協會評分(America Shoulder and Elbow Surgeons Score,ASES)[8]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評分(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UCLA)[9]。ASES滿分為100分,分數越高代表被檢者肩關節功能越好。UCLA評分最高為35分,優:34~35分,良:29~33分,差:<29分。⑤根據術前及末次隨訪X線片和MRI檢查結果,觀察重建組織結構的完整性。
1.5 統計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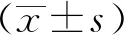
2 結果
2.1 患者基本情況及合并癥
本組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手術時間70~90 min,平均(81.7±6.8) min。未出現臂叢神經或腋神經等重要血管神經損傷,未出現氣體血栓、負壓性肺水腫等嚴重術中并發癥。術中鏡下探查發現42例患者全部存在岡上、岡下肌腱撕裂,5例患者合并小圓肌撕裂,2例患者合并肩胛下肌腱嚴重撕裂,術中均行肩胛下肌腱修復術。所有患者均獲得隨訪,隨訪時間6~24個月,平均(13.2±4.2)個月,其中嚴重關節粘連患者4例,通過康復醫院輔助治療均恢復良好,術后切口均一期愈合,未出現感染、陣攣痛、大力水手征及術后錨釘松動或脫出等并發癥及不良反應。
2.2 關節活動度、疼痛及功能評分
患者術后肩關節活動度均較術前明顯改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詳見表1。所有患者術后各項評分均較術前明顯改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末次隨訪時關節活動度、疼痛及功能評分較術后6個月均有所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詳見表2。末次隨訪時UCLA評分,優20例,良17例,差5例,優良率 88.1%(37/42)。

表1 術前與術后及末次隨訪時肩關節活動度比較

表2 術前與術后及末次隨訪時VAS 評分、ASES評分、UCLA評分比較
2.3 影像學檢查結果
所有患者術前及術后X線片檢查均提示肩關節退變未見明顯進展;MRI檢查提示6例患者重建的肩袖組織再次損傷撕裂,發生率為14.3%(6/42),其中3例發生在術后6個月,2例發生在術后1年,1例發生在術后2年,活動不當造成再撕裂患者4例,無明顯原因者2例,但6例患者功能恢復良好,未訴明顯不適,因此未行翻修手術(圖1)。

圖1 患者肩關節斜冠狀位MRI影像
2.4 典型病例
患者男,62歲,右肩部疼痛伴關節功能明顯受限,MRI診斷為巨大肩袖撕裂,后在全身麻醉下行關節鏡下雙排縫線橋技術聯合“Chinese way”處理損傷的肩袖。術中所見及手術前后影像學資料見圖2,3。

圖2 典型病例,患者術前及術后1年隨訪時的影像學結果
3 討論
肩袖損傷是導致肩關節疼痛和功能喪失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巨大肩袖損傷患者保守治療效果差、恢復時間長,故手術成為其主要的治療方法。主要的手術方式包括:①單純肩峰下清理和減壓;②肱二頭肌長頭腱切斷或固定;③肩袖修復;④肌腱轉移;⑤人工關節置換等[10-11]。隨著關節鏡技術的發展,鏡下修復巨大肩袖損傷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具有手術創傷小、術后恢復快、治療效果好的特點[12]。朱以明等[13]對77例患者進行了長達2年的隨訪觀察,研究顯示,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術是治療巨大肩袖損傷的有效方法,即使對術中肩袖肌腱僅部分修復,其肩關節功能仍較術前有顯著改善。盡管如此,鏡下修補巨大肩袖損傷仍然面臨著諸多難題,如何降低修補術后再撕裂的發生率,得到更優的臨床效果,成為目前臨床的焦點問題。

圖3 典型患者術中鏡下操作圖
肱二頭肌長頭腱與肩袖對肱骨頭有協同下壓作用,如何對巨大肩袖撕裂患者中無明顯病變的肱二頭肌長頭腱加以利用,值得進一步研究。“Chinese way”即是保留肱二頭肌長頭腱關節盂和/或上盂唇止點,而遠端轉移至岡上肌腱足印區進行固定,同時可以橋接部分修復得肩袖。該方法的原理是借用肱二頭肌長頭腱提供減張支架,加強肩袖前方組織力學強度和前上阻擋效應,輔助巨大肩袖修復,減少縫合肩袖組織的張力[14]。此方法無需通過其他部位獲取額外供體肌腱,簡化了手術程序,減少內固定耗材使用,降低了手術成本。Cho等[15]將68例巨大肩袖撕裂患者分為兩組:37例肩行肱二頭肌長頭腱增強修補術,31例行常規肩袖修補術,研究顯示:前者術后功能評分以及前屈、外旋和內旋肌力均較后者明顯改善,MRI提示,前者肩袖愈合率明顯高于后者(58.3%vs.26.3%)。余電柏等[16]的研究顯示,巨大肩袖撕裂患者行“Chinese way”修補術后功能恢復良好,患肩疼痛明顯改善。術后肩袖再次撕裂率低,該術式不僅避免了取材引起的額外損傷,而且可縮短手術時間和減少錨釘的使用量,與其他常規修補方法相比更具有優勢,值得臨床推廣。本研究結果與上述研究相似,患者術后隨訪的結果在活動度、功能評分及VAS評分等方面均明顯提高。
另外,巨大肩袖撕裂往往伴隨有不同程度肩關節的退變以及肌肉的萎縮、脂肪浸潤,Hamada分型3度以上的病例往往因為關節退變嚴重,間隙會出現明顯的狹窄,大結節的增生會非常嚴重,肌腱松解難度和重建點的處理難度也會明顯增加,因此必須對患者嚴格按照手術的適應證進行篩選,本研究中筆者通過術前的X線片檢查觀察患者肩關節退變情況,排除了肩袖關節病[17]的病例,選擇了成功率更高的Hamada分型 1~3 度的輕度退變患者;利用術前MRI,排除了嚴重脂肪浸潤[18](Goutallier 3~4級)的病例,降低了再斷裂發生率。除了患者本身因素,手術技巧也是成功的關鍵。撕裂肌腱回縮粘連、瘢痕纖維化較為嚴重,直接牽拉往往不能達足印區,這就需要術者進行廣泛地松解。前方需要松解的部位包括肩袖間隙、肩胛下肌,后方需要松解的包括回縮組織與岡下肌、小圓肌形成的粘連,肩袖上表面往往會與肩峰下表面、三角肌腱膜及三角肌形成粘連,肩袖下表面常常與上盂唇及肱二頭肌長頭腱粘連[19-20],均需一一松解。若仍不理想,可采取肩袖間隙滑移技術或固定點內移技術。有些仍難以覆蓋,就要采用邊緣集合技術,即邊對邊縫合,將U形撕裂轉變為T形撕裂或新月形撕裂,降低縫合張力,將撕裂肩袖復位固定[21]。另外,雙排錨釘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肩袖肌腱在大結節區域的接觸面,提供了更大的初始生物力學強度,使肩袖與骨面之間的間隙縮小,從而促進腱-骨接觸面的愈合[22]。Chung等[23]對272例關節鏡下肩袖修補術的患者平均隨訪1年的結果顯示,再撕裂率為22.8%,他認為與再撕裂相關的危險因素包括較低的骨密度以及術前脂肪浸潤和肩袖回縮程度。本研究隨訪顯示,6例患者出現了術后肩袖再斷裂,分析發生再撕裂的原因,除了與自身肌腱質量差及損傷程度重有關之外,還與患者存在骨質疏松以及術后劇烈活動相關。但本組患者再撕裂的發生率僅為14.3%(6/42),明顯低于其他研究者[24-25]的報道,這可能與本研究嚴格控制病例納入標準,術中注重松解和錨釘固定縫合技巧以及術后規范化的功能鍛煉密切相關。
綜上所述,“Chinese way”修補巨大肩袖損傷的方法更能夠降低患者疼痛癥狀、改善關節活動度、恢復關節功能,且并發癥及結構失敗率更低。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納入的病例數量較少,缺乏大樣本多中心的研究;遠期效果也有待進一步觀察。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張博:研究設計、撰寫論文;林源、任世祥:研究設計、修改論文;陳彤:研究實施、數據采集;于洋、賈加霖:數據統計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