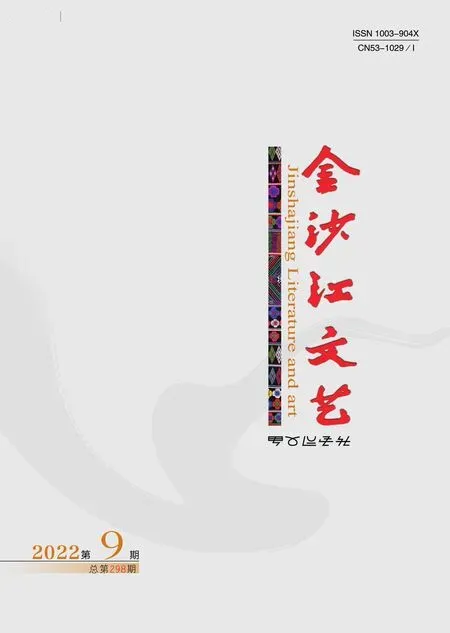糖 鎮
◎李躍慧
法納禾最早出現在糖鎮,是多年前的事了。
那時,她不過十四五的模樣,洗得稀薄的粉色頭巾蒙住了烏黑的發和頎長的脖子,只把青稚的眉眼露在初冬微凜的風里。她挽著韁繩,一匹高大的騾子溫順地跟隨著她。一人一騾,自鋪滿白霜的狹窄山路下來,經過立在潺潺河流上的木橋,進入糖鎮寬闊的青石街道。
她一路打聽至高家的糖攤前,站下,張眼細瞧。
糖鎮以色如琥珀、散著糧米醇香且纏綿唇齒的麥芽糖聞名四方。那糖有論斤稱的糖塊,也有論罐賣的糖稀。糖塊有粘花生的,也有粘核桃的,用小錘子敲擊有清脆的聲響,扯在手里和嚼在嘴里卻又筋道柔軟。罐裝的糖稀明凈剔透,可以在筷頭上千回百繞,又能入口即化。糖鎮有許多熬糖人家,這其中,高家的糖在色澤上、口感上又更為精道。
但法納禾的目光卻并沒有叫那令人垂涎的麥芽糖粘住,她打量的是賣糖的人:二十來歲的小伙,敦實的身板,一張被煙火熏燥的臉,安靜的小眼睛和微張著嘴時露出的小虎牙。
法納禾有點羞澀,卻不慌張:“我問一下,這是高家的糖攤嗎?”
被問到的小伙高柏,見有了生意,順溜應:“就是了!山里頭的親戚,就只認我家的糖,逢街天趕集沒有不帶的。妹妹要罐裝的糖稀,還是稱斤的糖塊?”
“我這下子不買糖,”法納禾脆聲說,“我找你家拿錢呀。”
“拿錢?”這沒頭沒腦的話,把高柏說得一愣,好性子的人也冷下臉,“什么錢?我家哪時差你錢?”
法納禾不瞧臉色,直直說:“差呀!阿爸說過的,你家還有幾回柴錢沒結給我們。”
柴錢。高柏漸漸緩了慍色。麥芽糖至要緊是“熬”,而熬糖所需的硬實木柴只深山里有,熬糖人家都有熟識的人砍柴送柴。山里不通車,運送木柴的人全靠自家養的幾匹騾子,一趟一趟馱出來,先記賬,等湊成個數目了,再一總結賬。
高柏問:“你阿爸是法大叔?”
法納禾說:“就是的。”
“賬目在呢,錢該給。不過我要親手交給法大叔。你,招呼得了恁多錢?”
法納禾臉色一黯,她倒不氣這樣的輕看,只是——
“阿爸不在了。”
高柏吃一驚:“法大叔過世了?”
“嗯。”
“難怪,這么久都不見他送柴來,也不來拿錢。唉,他是得了什么病?”
“哪曉得呵!”法納禾也茫然,“夏天的事了,阿爸正鋤著地呢,一下子淌一身汗,衣服都濕了,他說:‘沒力氣了,歇歇’,就到樹蔭底下躺著,再喊就不應了。”
旁邊有個賣香紙的老人嘆息:“那算有福啊,吃一輩子苦,走得倒撇脫。”
一時都沒話,留著段靜默給逝者。過一晌高柏說:“這么樣的話,錢就給你。還不曉得呢,妹妹是叫——”
“我叫法納禾。”
這是一個彝語名字,高柏的奶奶和阿媽都是從山里嫁到鎮上的彝家女,一輩子也只用彝語名字。法納禾這名字,高柏也曾聽老法提起過的。
“你上我家吃中飯吧,法大叔來也是在我們家里吃飯的。來,我給你把騾子牽到我家院里——”
高柏要帶路,法納禾卻握緊韁繩:“飯不吃了,我還有要緊事情呢!”
“要緊事,”高柏打量她,“妹妹有啥子事情,要緊到連吃飯都顧不上?”
“我想把好力帶到牛馬市場,找個人家養著它。阿爸不在的時候,我們把家里別的騾子都賣了,用來打酒買米、買豬買羊,砌墳安碑。只有好力,村子里的人誰也不肯要,都嫌它歲數大,說它越往后越馱不起了,只能長久把它養著,白費糧草。好力是在我家里苦老的,我該養它的老,可我一個人也養不了它。鎮上地方大,人多,會有人愿意養個乖順的騾子吧,它聽話,不作怪,老人小孩都騎得,貨物也還馱得起的。”
高柏曉得了,這樣的騾子,通常只有一個去處。不過,他不忍說出來。但愿吧,但愿會遇到不懂行或是心腸軟的人。
牛馬市場就在街尾那片空地上,高柏指給了,又不無擔憂地說:“你恐怕要慢慢等。”
下午就有過路的熟人來給高柏說稀奇:“今天牲口市場上,哈哈哈,有個笑死人的事情!”
高柏敲著糖,心里卻一動:“啥事情,你說說。”
“有個小女娃兒嘛,牽匹老騾子守一天,逢人問價她只一句話:‘你能好好招呼它么?’哎呀,怎么講!一頭騾子嘛,哪家不是那樣待,難道還把它當小娃養,當祖公供起?哈哈哈!笑死我!”
高柏沒笑:“那就沒人買?”
“不不不,有人買,”熟人搖著手,笑得喘不上氣來,“你猜賣了多少錢?”
“多少嘛?”
“恁多!”熟人伸出一根手指。
高柏嘆著氣:“一千塊確實太便宜了,不過能有人幫她養著那騾子,倒也還好。”
熟人瞪起眼:“哪里一千?是一百。跌下崖子的騾子毛驢馬,散了架,館子里一百塊兜走,那憨娃兒,把活牲口賣了個死牲口的價。”
高柏霍地站起來,好比割了自己的心尖上的肉,疼得蹦起。早曉得他就買來。
旁邊擺攤的也叫:“天吶,這不是跟白撿一樣?就沒人爭著買?哪怕一百五、二百五買來也劃算啊!”
“爭,哪個爭得著!”老熟人說,“一個老獨人,他講我買騾子做個伴,除了喂草料,我吃啥子也給它吃點啥子。你爭?你舍得給騾子吃飯吃肉嗎?”
高柏慢慢坐回去。真要那樣,誰能不服氣。
過些日子,高柏才曉得法納禾賣掉騾子是因為她沒打算回家。她在鎮上最大的火鍋店“魚羊鮮”找得個洗菜剖魚的活。老板原是安排她在前面端菜抹桌,可是她不大會瞧勢頭,嘴巴又直,就叫她在后廚做。這活冬天遭罪,手總浸在冰冷的手里,凍得緋紅,手背裂開細口,手指長了凍瘡,不會彎曲。一浸油鹽汪出她淚來,旁人瞧了覺著不忍,勸她戴上膠皮手套,她輕輕甩著自己的手:“想戴,可是戴去上手笨得很,擇不好菜,刮不凈魚鱗甲”。
法納禾有時在午后來找高柏。開館子賣飲食都忙兩頭黑,好在午飯與晚飯之間有那么點空閑,法納禾就出來溜一轉,透透氣。糖鎮就那么一條街,也沒多大去處,她就找高柏。高柏平日不是話多的人,劈柴、生麥芽、磨粉、攪糖,法納禾就在一旁靜靜瞧,有時也搭把手。高柏得了空閑,把老姜拿火上烘熱乎,切了片給她貼在生了凍瘡的手指上。有時也給她些邊邊角角的糖,她喜滋滋拿去分人吃。
有回法納禾往灶里添著柴,問正在煙火繚繞中忙活的高柏:“高柏哥,你不怕我瞧你熬糖,瞧著瞧著學會了,也賣糖,搶你的飯吃?”
高柏額頭鬢角都是汗,只笑笑,有絲驕傲:“要下功夫的,你以為看看就會?”
法納禾撇嘴:“那么了不起喲。”
有陣子法納禾沒來,再來的時候還沒到晌午,她急赤白臉跑來了,結結巴巴說:“高、高柏哥,我……我惹下大禍了。”
高柏穩一穩神,把散著清香的麥芽端到太陽底下鋪開。
“莫慌,慢慢講我聽。”
法納禾猶自魂不守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呵!”
“說么。”
“我會不會被抓進牢房,關個十年八年?”
高柏自己拉了個竹凳坐,也遞一個給法納禾:“坐著說,究竟哪樣事?”
法納禾手撫胸口,按住那怦怦的心跳。
“你到底弄壞東西還是傷著了人?事大不過如此。”
“不是的,我……欠了話費,人家都催上門啦!說啥子限時繳費,不然要追究法律責任。”
高柏一掌拍腿上,“我以為什么大事!”
“欠了很多!”法納禾急哭了,“兩千多哪!”
這數目把高柏也驚著了:“這么多話費!你是打到外國去了?”
“我把你給那柴錢,買了個小靈通,五百八。他們說小靈通是白送的,五百八全算成話費,到年底打不完就作廢了。我想我哪里打得完嘛,就借人打,一起做活的小張小馬、賣菜的姚大媽、打辣子面的蘇老板、送酒水的小陸,還有……記不清了,我叫他們打電話都拿我的打。用了這久都沒事的嘛,誰曉得今早上電信局的人就找來了。”
高柏指著法納禾,真想把手指頭鑿到她腦門上,又不知說她什么好。想了想,咬牙忍住:“那你是來找我借錢?”
“我,我只想喊你幫忙出主意!”法納禾絞著手指。
“簡單呀!”高柏說,“要是叫我拿主意,我叫你莫管它,躲一陣子好了。其實欠話費的人多呢,把卡扔了也得,換個電話也得,這么點事情他也夠不上告你抓你。”
法納禾說:“我不躲!”
“那就叫用你電話的人幫你湊。你不好意思開口,我幫你說,那些人我都認得。”
“我不是那樣人!”法納禾漲紅了臉,“說好白送人打,這下子又跟人家要錢。自己吐口水自己舔的事情,我不干!”
“嘿嘿!”高柏氣笑了,“那你硬是要出這筆錢呀。”
結果是高柏和法納禾坐車到縣里電信局辦公室,做了擔保,立下字據,分期還款。
法納禾又找了一份工,在燒烤店幫忙。每天火鍋店收工就到燒烤店去,生火、穿串、煎炸烤、洗碟子拖地,一直忙到凌晨兩三點,回去躺不了兩小時又該起床了。到底年紀小,這樣都撐得下來。
可法納禾還是嫌錢來得慢。一有空閑就拿個煙殼紙,蹲在旮旯里寫寫畫畫算錢賬。燒烤店老板看她那么心急,就額外開恩,準許她把客人扔下的塑料瓶拿去賣錢。那時候廢品行情好,一個瓶子能賣一毛錢。法納禾嘗到甜頭,又多干了一份工作:利用中午休息那一小會兒的時間到街上撿塑料瓶子和紙殼。糖鎮還不大有人撿廢品,偶爾有,要么是瘋子,要么是花子,像法納禾這樣清爽的小姑娘撿廢品,而且還撿得兩眼放光毫不羞慚的,還沒有過。于是法納禾在糖鎮就成了有名的人,人們老在談笑間說起她。
法納禾花了三個月零五天的時間來還清欠款。
最后一次還款,法納禾要高柏跟她去。手續并不煩瑣,一手交錢,一手打出票據。法納禾把票據上的數目一瞧再瞧,確定沒錯了,才折進衣兜,噔噔噔下樓,快步走出電信局大門,一屁股坐在了馬路邊的水泥臺階上。高柏當她累了,站著等一會兒,待側頭細瞧,才發現她竟然是哭了。
她瞪大雙眼瞧著馬路上人來人往,緊緊咬住的嘴唇把哭聲擋住,淚水卻大顆大顆落下,把她撲了塵泥的臉攪得斑駁。
她哭得雙肩聳動,卻無聲無息。
高柏從來沒有遇到過哪個人的哭,會讓他這樣心軟無措。他想給她拿點紙,捏在手心又放回兜里。說句安慰的話吧,也難以出口。最后他在離她不遠的地方坐下,替她接受不時有行人投來的異樣目光。
法納禾終于哭得痛快,用袖子揩了臉,朝高柏笑。糖鎮人形容一個人笑得甜,老愛說笑得跟麥芽糖一樣;笑得好看,就說笑得像喇叭花,高柏這時候覺得法納禾笑得像一朵沾了麥芽糖的喇叭花。
在法納禾離開糖鎮那些年里,高柏時時想起這笑容。給麥子灑水催芽的時候,背谷米上樓的時候,煙火繚繞嗆得涕淚齊下的時候,擺攤稱糖的時候,甚至,吃飯喝水的時候。
法納禾是在和高柏從縣城回家不久后的一天突然離開糖鎮的,“魚羊鮮”和燒烤店里都還有半個月的工錢沒結,這是老板按行規暫扣的,只要說明不做了,待找到替工,老板就會清結工錢,好聚好散。可是法納禾沒來得及跟老板請辭,甚至也沒有花一點點時間來跟高柏告別。
有人說法納禾被人販子拐跑了,人販子穿著西裝,開著小車,長得俊俏,嘴巴蜜一樣甜。有人說法納禾到福建鞋廠做鞋去了。也有人說不是去福建,而是去廣東,做的也不是鞋,是當小姐掙大錢哩。還有人說夢見法納禾被人打暈了裝進麻袋里,扔進了糖鎮那條河。
只有與法納禾住一屋的小姑娘,在高柏問到她的時候,很羨慕地說:“她啊,跟人看火車去了。”
“到哪里去看?”
“鐵路上呀,”小姑娘奇怪地看一眼高柏,“除了鐵路上,別處哪里還看得到火車?”
這真是無可辯駁,高柏就又問:“那她咋會突然想去看火車?”
小姑娘笑一聲:“才不突然呢。那天有群外地人來吃飯,當中有個穿制服的,說是在鐵路上工作。那眉眼比我們老板娘的都細致,一雙眼睛老是笑,閃著亮。偏生說話也好聽,又清亮又綿軟,不像我們這些地方的人粗聲大嗓的。他講了好多火車上的事情,他說火車上南來北往的人各各不同,有北京人、上海人、香港人,還有金色頭發的外國人。我們都支著耳朵聽,我瞧法納禾真的聽迷了。我們幾個都有事,端菜、收碗并碗、抹桌子倒茶,法納禾殺好了魚洗完了菜,后廚就不拿著她喊了,她竟悄悄拿個凳子坐旮旯里聽。后來客人多了,我們忙起來,就沒細估那桌外地人啥子時候也結賬走了,法納禾也不見了。”
“那你也沒瞧見她跟外地人走啊?”
“沒有,可我就是曉得。她收走了她的毛巾、梳子牙刷。”
高柏不信那些聽上去有鼻子有眼的閑話,因為他自小生活在糖鎮,曉得在這個平靜無波、雞犬安寧的地方,許多人都是會編故事的,包括他的奶奶和阿媽。眼前這小姑娘說的他也不全信,不過,他聽進了最后那句話。還能帶上洗漱用具,至少說明法納禾走的時候是自由的。
走就走吧!高柏同自己說。那些用過法納禾小靈通的人,一個個都裝聾作啞,讓法納禾白白替他們出錢,到底叫人冷心。
糖鎮還是那樣,趕集天喧喧嚷嚷,車鳴馬嘶。閑天站在街頭一眼望得到街尾,風吹得路兩旁的香樟樹枝葉亂晃,火紅的攀枝花噼里啪啦掉下來。
小小的變化也是有的。“魚羊鮮”老板把店開到了縣城,高柏家把土房換成了磚房,建起了兩層小樓,并且他還相了幾回親。準確地說,是媒人帶著女方到高柏家來“相家”,女方都覺得高柏家底過得去,也算有樣手藝在身,父母老人瞧著也實在,問題在于高柏本人,他老是淡淡的,問他什么他只是笑笑,要說他怕羞吧,他又那么自在,叫那些“相家”的姑娘也難把熱臉往他身上貼。都是伶俐人,誰沒點眼色呢。
爹媽見兒子這個模樣,也愁。可彝家人最愛是自由,兒女大了父母便敬他(她)成了人,不會再比手畫腳拿重話來說了。
高柏倒是平心靜氣,育麥芽,磨玉米,磨糯米,浸泡,蒸煮,大火熬小火熬,每道工序都一絲不茍,每個細節都做得怡然自在。做糖,自然是要好看,要清香,要甜蜜。從口里,到心里。糖不容雜質,心不容雜念。
閑的時候,高柏會陪著他的新伙伴靜靜待會兒。他坐著,它站著。有時他默默抽支煙,它悠然嚼著草,有時他不抽煙,它也不吃草,一人一騾相對無言。
它就是那匹被老獨人從法納禾手里一百塊錢買走的騾子。老獨人喝酒過量,死了。他侄子把騾子一千塊賣到驢肉館,鎮子就那么一條街,什么事也藏不住,大家不顧驢肉館老板的驅趕,嘻嘻哈哈去瞧那匹“有故事”的老騾子。騾馬壽命長,在農家里還可過得長久,可是家沒有了,屠宰場便成了它最后的唯一的去處。高柏在屠刀之下,花兩千六百塊錢把老騾子救了回來。
高柏還記著那匹騾子的名字,好力。
但是好力一年比一年老,牙不行了。高柏只能割草尖上最嫩那截葉子給它,把苞谷面拌了豬油喂它,它有時吃一點,有時只是望望。
高柏就跟它說:“好力啊好力,你怎么也要等到法納禾回來吧!”
一個街天,高柏正應了顧客要求拿小錘子敲花生麥芽糖,隨著每一聲力道適中的“嗒”,麥芽糖勻成拇指大的小塊,這時一只胖胖的小手忽然伸過來,抓起一塊糖,要不是高柏及時收勢,那一錘子非敲壞了骨頭不可。高柏要把那孩子吼幾句,可待他瞧清楚,又噤了聲。
那是一個八九歲的男孩,眉眼似曾相識,神色卻是蒙昧的,他把糖放在嘴里使勁嚼著,臉上露出癡拙的笑。高柏另撿了兩塊大些的給他,揮手叫他走。那孩子卻不走,站在一旁吃得稀里呼嚕。
“樂樂,你怎么曉得跑這里來!”
一個女人氣喘吁吁跑過來,她肩上挎一個大大的藍白雙色格子布包,另一只手還拖著一個大拉桿箱。穿一件白色的薄外套,蠻精神,一頭短發卻給風吹得亂蓬蓬,大眼睛里含著無所畏懼的笑意,眼角已有了隱約的細紋。
高柏把糖遞給顧客,收了張百元鈔,卻老是找不對數目,落了顧客輕聲地埋怨。
“高柏哥,你這朝急躁了,賬也算不對。”
高柏沒出聲。他只覺鼻子酸澀,眼眶發熱,真怕淚水涌出。
有人湊過來:“啊呀!這,這模樣怎么有點像法納禾?”
女人笑笑:“我是法納禾呀。”
好些人就攏來,擺攤的,趕集的,也有找柴割草的。
“啊呀,我們的法納禾回來啦!”
“這是你娃兒吧,長得恁壯實,咋不讀書去呢?”
“你男人哩,也跟來哦?”有人伸著脖子四處望。
有人瞧出不對勁:“這娃兒莫不是哪不好,不聲不響的?”
“你這問的啥子話?人家娃兒有病礙著你了?”
法納禾放下行李,摟過那孩子,笑笑同大家打招呼:“你們也瞧出來了,樂樂有智力殘疾,讀不了書。不過他聽話呢,哪時候都笑呵呵的,最可愛。”
大家也就說:“是呢,最可愛。”
“到我家里歇吧,”高柏一手一只搶過行李,“我先把東西拿回家。”
“等一下,高柏哥!”法納禾把手輕輕搭在高柏手背,溫暖柔軟,卻有不容推卻的堅持,“我這次回來不同以往,拖家帶口,還要長住,我要先各人找地方落腳。”
高柏悶聲說:“各人住,你住哪里?你家老房子前幾年就被雨水沖垮了。”
法納禾問:“你咋曉得?”
“山里親戚說的么。”
法納禾默一晌,說:“也沒法,我一早把它舍下啦!”
“也是,”高柏說,“你是啥子都舍得下的。”
說了這話,高柏覺出了心里的苦澀,可是又寬慰著自己,管他管他,只要法納禾能回到糖鎮,她想要怎么樣也都好。他問:“那你想在哪里落腳?”
法納禾說:“就在這鎮子里吧,找一找。”
高柏就陪她找。臨街的村子找到一處閑置的小院,面積不大,有些年頭了,可是法納禾愛那紅磚青瓦,大門兩邊的墻上爬滿橘黃的炮仗花兒,院子里的月季開得正旺。
高柏問:“租金怎么算呢?”
“不,”法納禾說,“我要買下來,長久住。”
房主說:“知根知底的老熟人,我也不喊高,十萬零八千,大家一起發嘛。”
“成!”法納禾竟不還價,“寫了協議,我馬上過錢給你。”
房主眉開眼笑:“好好好!”
這么一筆大買賣,高柏竟沒來得及插上話。
屋子早是搬空了的,簡單灑掃,買來灶具,煮了一鍋飯,燉了一只雞,高柏又買回些鹵肉涼菜。樂樂見有這么多吃的,歡喜得不停往嘴里塞,他不曉得吃多少是個飽,任法納禾苦勸不聽,直吃得吐了才算。
法納禾抱著吐過之后沉沉睡去的樂樂,看高柏掃凈地下,她說:“高柏哥,別忙了,坐下向火,說會兒話。”
高柏于是走過去,在火塘邊坐下來。他曉得法納禾有話要說。
“高柏哥,你沒有問我離開糖鎮這些年的事情。”
高柏苦笑:“你不說,問了白問。你要說么,我不問你也會說。”
“嘿!”法納禾笑了一下,那神色似在品咂著過往的甜蜜,又像在咀嚼眼前的苦澀,“樂樂的爸爸,我后來才曉得,他并不在鐵路上工作,那身衣服是一個親戚穿舊了送他的。不過他真帶我去看了火車,不止這樣,他還帶我去過北京,到過布達拉宮,去過天涯海角,也見過了大理的風花雪月,東西南北,冷的地方,熱的地方,都走過了。我們多數靠他賣襪子掙的錢過活。到冷的地方就賣棉襪,到熱的地方就賣絲襪,一兜襪子,一只喇叭,在他手里就能變出錢來。他長得好看,口才又好,陌生人都信他的話,愛買他的襪子。我原來想,這輩子就跟著他,順著他,他想咋辦就咋辦,他說去啥地方就去啥地方,直到……”
法納禾穩一穩心緒,高柏傾耳靜聽。
“幾個月前,他領樂樂去買雪糕,回來只一個人。我問樂樂呢,他說不見了。我一聽嚇瘋了,遍大街去找。我叫他也找,他說他不找了,丟就丟了吧,我們再生一個聰明的,老了才有靠。我千辛萬苦把娃兒找回來,就清醒了,樂樂是我的命,比起樂樂,他啥子也算不上。我要跟他分開,他把攢下的十萬塊錢給了我和樂樂,叫我們永遠不要再找他。”
法納禾緊緊抱著樂樂,凝視著他平靜安睡的臉:“樂樂是我的寶,我要領著他好好過日子。他不像別的娃兒,長大可以四處闖蕩,掙錢吃飯,他只能待在家里——我總得給他一處自己的地方。”
高柏明白了她那么急于買下房子的原因。
高柏說:“在糖鎮過日子不會咋樣難的,我,我在著呢。”
法納禾說:“我曉得,所以我回來了。”
“你把娃兒放睡,我帶你見個老朋友吧。”
法納禾抽著鼻子:“我現在難過,不想見人。”
高柏說:“要見見,你才會曉得你沒有白白回來。”
法納禾有點詫異,可是她一直信著高柏,就放了娃兒,隨高柏到他家。
高柏領她到一處地方:“喏,你瞧。”
騾廄前,法納禾慢慢看清楚,月光人靜靜望著她的,真的是她的老朋友,原以為再也不會相見的老朋友。
“好力!”法納禾跑上前緊緊摟住好力的脖子,把額頭抵在它額頭上,深深聞著它的青草氣和汗腥氣,淚水流了滿臉,她又把臉貼在好力順滑的鬃毛上蹭干。
“好力!好力!你還在!你還在!”
法納禾歡喜極了。
高柏覺著能換法納禾這片刻歡喜,啥子都值得了。
法納禾在糖鎮新大街賣起了襪子,她用不著大喇叭,因為幾乎人人認得她,很快也曉得了她的襪子賣什么價錢,不必多費口舌。她把樂樂帶在身邊,一遍一遍教他說話,教他認人識物,給他唱歌講故事。雖然樂樂學過就會忘記,但母子倆還是樂此不疲。
有時樂樂調皮,趁媽媽不注意從街頭跑到街尾,回來的時候手里總會多些東西:烤苞谷、米花糖、小氣球,毛茸茸的小雞小鴨……開頭法納禾打過他,以為他拿了別人家的東西,后來才發覺都是送的。
有一天,樂樂嘴里含含糊糊蹦出三個字,法納禾側耳細聽,終于聽明白。
樂樂說的是:“麥芽糖。”
他站在灶臺邊看高柏熬糖,隨著火勢變化,糖面時而平滑如鏡,時而噗出無數朵金色的花,時而如風掀過湖面,云翻浪涌。他看得那么入神,那么歡喜。
法納禾瞅著他,眼里晶光流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