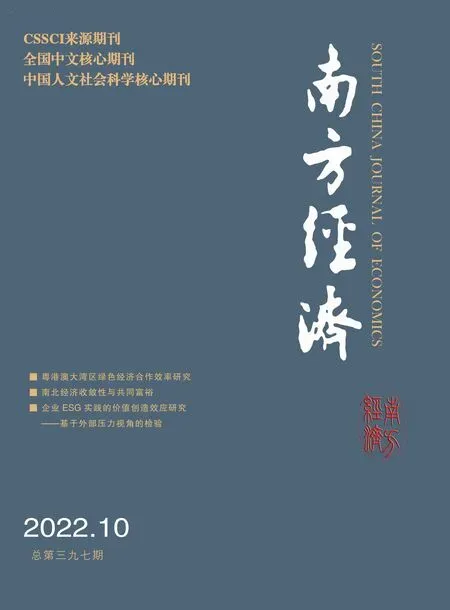《會計監管風險提示第8號
——商譽減值》的政策效果研究——基于業績補償承諾的視角
徐婷婷 柳建華 陳 果
一、問題提出
并購重組是上市公司迅速擴大規模、提高市場集中度和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渠道,也是企業優化資源配置,實現轉型升級的重要經濟手段(Ahuja and Katila,2001)。盡管已有研究肯定了并購的重要作用,但也有文獻發現,我國并購企業與標的企業之間存在著較嚴重的信息不對稱(Fuller et al.,2002;Masulis et al.,2007;陳仕華等,2013)。即便上市公司在并購之前已經對標的企業進行了盡職調查,但是由于文化及地理上的差異,或是出于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等問題,仍會影響對標的企業估值的準確性。為此,證監會于2008年規定采取收益現值法等估值方法的并購重組交易,并購雙方企業必須簽訂業績補償承諾(1)具體可見證監會2008年4月16日發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換言之,標的企業需就未來的盈利能力進行承諾,當沒有達到承諾額時需對并購企業給予相應補償。據統計,2013年至2017年,業績補償承諾的簽訂比例從10.74%升至40.50%。隨著政策導向和市場慣性,業績補償承諾在并購重組活動中日漸盛行(王建偉、錢金晶,2018)。
理論上,業績補償承諾的實施具備信號傳遞作用,有助于緩解并購雙方的信息不對稱(Datar et al.,2001;呂長江、韓慧博,2014;楊超等,2018;毛倩等,2021)和道德風險(Kohers and Ang,2000;Cain et al.,2011),提高估值的準確性,還可以激勵標的企業提高業績(潘愛玲等,2017)。然而近些年來,業績補償承諾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的弊端卻頻頻暴露。有大量研究發現,并購雙方企業的大股東具有合謀簽訂不合理業績補償承諾的傾向,即利用高溢價并購(徐莉萍等,2021)和高業績承諾(李晶晶等,2020a)故意抬高公司股價從而謀取個人利益。也有研究發現,標的企業為了避免履行補償義務,或盡可能地減少補償金額,具有在承諾期內通過盈余管理調高利潤的動機(盧煜、曲曉輝,2016;謝紀剛、張秋生,2016;柳建華等,2021)。由于高溢價并購會產生高商譽,一旦標的企業沒有達到承諾業績或是不履行補償義務,上市公司就會面臨巨額的商譽減值風險。過高的商譽減值不但會增加上市公司的股價崩盤風險(王文姣等,2017;韓宏穩等,2019;李晶晶等,2020b),還會嚴重損害公司價值(王建偉、錢金晶,2018)。更值得關注的是,上市公司還普遍存在以業績承諾期為由故意不進行商譽減值,而是在承諾期結束后才進行商譽減值的利潤調節行為(王建偉、錢金晶,2018)(2)例如受到媒體廣泛關注的東土科技(300353)收購拓明科技事件,交易雙方約定拓明科技在2015年至2018年期間扣除非經常損益的歸母凈利潤分別不得低于4000萬元、5200萬元、6760萬元和8112萬元。在業績承諾期的前三年,拓明科技均完成了業績承諾,然而到了2018年,其業績卻突然“變臉”,當年僅實現凈利潤4912.65萬元,業績承諾完成率僅為60.56%。為此,東土科技當年對該公司計提了高達8164.33萬元的商譽減值準備。諸如此類案例數不勝數。。一方面是由于業績補償的承諾期往往長達三至四年,一旦在承諾期內沒有完成承諾業績,標的企業將面臨補償責罰,而進行高溢價并購的上市公司也將面臨通告批評(3)例如,光洋股份于2016年4月16日通過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方式購買當事人合計持有的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權,因未完成2017年度承諾業績,深交所對業績補償義務人給予了公開譴責和通報批評的紀律處分。,給公司聲譽和業績帶來不利影響。另一方面,由于商譽的確認與計量只能依附于總體資產或者資產組公允價值的評估進行,其公允價值很難被證實(謝紀剛、張秋生,2020),這就使得商譽減值的操控空間較大(4)《會計監管風險提示第 8 號——商譽減值》也特別提到:“在實務操作中,公司在商譽初始確認環節,往往存在合并成本計量錯誤(如未考慮或恰當考慮應計入合并成本中的或有對價)、未充分識別被購買方擁有但未在單獨報表中確認的可辨認資產和負債(如合同權益、客戶關系、未決訴訟、擔保)等問題”。(Massoud and Raiborn,2003;杜興強等,2011),上市公司大股東有動機確認更多的商譽資產(Filip et al.,2015)。因此,在業績補償承諾的“催化”下,上市公司高商譽及高商譽減值現象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據Wind統計,2012年至2017年,A股上市公司商譽減值總額從10.48億元一躍至368.20億元,其增長速度令人震驚。
為強化商譽減值的會計監管,進一步規范上市公司利用業績補償承諾進行跨期商譽減值從而損害中小投資者利益等問題(毛群,2019),2018年11月證監會發布《會計監督風險提示第8 號——商譽減值》(以下簡稱“8號文”),明確提出“對企業合并所形成的商譽,公司應當至少在每年年度終了進行減值測試”,并且不得“簡單以并購重組相關方有業績補償承諾、尚在業績補償期間為由,不進行商譽減值測試”。這意味著,上市公司無法再通過以承諾期為由跨期計提商譽減值的方式調節利潤,繼續進行高溢價并購和高承諾業績補償協議的成本將大大增加,因此上市公司采用高溢價并購和高承諾業績的意愿可能會相應減少,這也有利于公司更加謹慎地對標的企業進行選擇。與此同時,媒體監督已經成為市場糾正機制的重要形式之一(周開國等,2016)。頻繁的商譽減值“爆雷”本就引起了媒體新聞的廣泛關注,“8號文”作為新一輪并購潮興起后首個針對商譽減值計提時點進行規制的政策,其實施效果也必將成為媒體的重點關注對象。因此,“8號文”之后上市公司管理層出于輿論壓力也會盡量降低商譽減值發生的可能性以防止向市場傳達公司“盈利能力下降”的不利信號,進而使上市公司的長期績效提高。
鑒于上市公司并購時所簽訂的業績補償承諾是巨額商譽減值的重要來源(李晶晶等,2020a),本文基于業績補償承諾的視角考察“8號文”政策的實施效果,包括對上市公司商譽減值、并購估值及長期績效等的后續影響。具體地,本文通過雙重差分法對2016年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實證研究后發現:“8號文”有助于降低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的商譽減值水平,加強媒體對簽訂業績補償承諾公司的關注與監督,但存在2018年突擊計提商譽減值的現象。此外,“8號文”能夠降低上市公司對不合理業績補償承諾的使用傾向,降低并購溢價并提高長期并購績效。最后,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并購企業在“8號文”之后沒有顯著提升盈余管理水平和股價崩盤風險。本文總體表明,“8號文”有助于上市公司在并購過程中合理使用業績補償承諾,降低商譽減值水平。
本文的主要貢獻為:第一,首次檢驗了商譽減值政策的有效性。盡管已有文獻探討了商譽減值的發生、處理以及商譽減值與其他因素的影響關系,但少有文獻考察商譽減值政策的影響效果以及其對上市公司業績補償承諾使用的影響。本文從“8號文”的提出到實施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發現其不但能夠有效地降低上市公司的商譽減值水平,還能促進上市公司對業績補償承諾的簽訂更加合理。尤其是,在“8號文”實施之后,盡管上市公司的并購次數沒有明顯降低,但是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比例已大大減少,這對商譽減值的監管者以及業績補償承諾的制定者均提供了具有切實意義的參考。第二,本文深入考察了商譽減值政策能夠降低簽訂補償承諾上市公司商譽減值水平的內在機理。從增加媒體監督和促進合理并購和等角度進行詮釋,揭示了“8號文”政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商譽減值的確認及發生時點,并且從市場的角度對管理層施加壓力,是對已有文獻的重要補充。第三,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創新性。雖然現有文獻已經證實業績補償承諾可以引發巨額商譽減值及股價崩盤風險,但是由于商譽減值的影響因素眾多,模型往往具有較高的內生性。本文基于“8號文”這一外生事件,通過雙重差分模型的檢驗,能夠更具有針對性地揭示業績補償承諾與商譽減值的內在影響關系。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014年,受我國經濟轉型調整與宏觀環境轉變的影響,許多行業選擇通過并購重組進行轉型升級,并推動了新一輪并購潮的興起。這一現象導致A股存量商譽迅速積累,為巨額商譽減值提供了潛在空間。與此同時,業績補償承諾在并購雙方企業中日漸盛行,而未達到承諾的業績補償協議成為了上市公司商譽減值的重要動機。在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業績承諾的設計缺陷使得業績補償承諾引發了“高溢價、高承諾、高股價”的利益鏈條,逐漸成為了并購企業與標的企業大股東之間進行利益輸送的工具(李晶晶等,2020a)。當承諾期結束后標的企業無法完成承諾業績或是不履行補償義務,上市公司將面臨“業績變臉”,之前向市場釋放的盈利信號也將不復存在。更需要重視的是,許多上市公司管理層為了“洗大澡”、避免聲譽受損或者股價下跌的風險,還存在故意推遲確認或者擇機確認商譽減值的行為(Massoud and Raiborn,2003;Henning et al.,2004;盧煜、曲曉輝,2016)。尤其是以業績承諾期為理由不進行減值,而是在承諾期結束后才一并進行商譽減值(5)證監會在《2018年上市公司年報會計監管報告》中也指出,存在“部分上市公司商譽等資產減值準備計提隨意,利用會計估計或會計政策變更跨期調節利潤,選擇性確認與披露以及構造交易等,財務信息未能真實反映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的現象。,而此時的商譽數額已相當巨大。正是由于商譽減值不斷“爆雷”已經嚴重威脅到了中小投資者的切實利益,為此監管層十分重視,并于2018年11月16日發布了《會計監管風險提示第8號——商譽減值》,對商譽減值的會計處理和信息披露、減值事項的審計、與減值事項相關的評估等方面都進行了更為明確的要求。
從“8號文”的內容中不難看出,該政策的目的是規范上市公司商譽減值的信息披露質量和計提時點,加強對潛在商譽減值的審計與評估,對未來的業績補償承諾簽訂給予風險警示和防范。因此,該政策的提出具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對沒有計提商譽減值但是存在高額潛在商譽風險的上市公司起到風險警示的作用,二是對上市公司不合理使用業績補償承諾的行為起到震懾和抑制作用。首先,“8號文”提到在監管工作中應重點關注“公司是否定期或及時進行商譽減值測試,是否在此過程中重點考慮了特定減值跡象的影響”,而特定減值跡象就包括“現金流或經營利潤持續惡化或明顯低于形成商譽時的預期,特別是被收購方未實現承諾的業績”的情形。這表明,由于不合理的業績補償承諾而導致高額商譽減值的現象已經受到監管層的廣泛關注,并且在政策中一再強調要從評估、審核以及監管等多個層面加以防范。其次,“8號文”中提到“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的規定,公司應當在資產負債表日判斷是否存在可能發生資產減值的跡象。對企業合并所形成的商譽,公司應當至少在每年年度終了進行減值測試”,并且“不得以業績補償承諾為由,不進行商譽減值測試”。這一要求意味著上市公司無法再通過承諾期結束后計提商譽減值的方法調節利潤,從而使得商譽減值的操作空間變得更為有限,因此上市公司利用業績補償承諾和商譽減值發生機會主義行為的動機可能會相應降低。不僅如此,當并購后難以創造出足夠的價值彌補溢價,并且跨期商譽減值無法為業績承諾的未完成和不補償“兜底”時,繼續進行高溢價并購和虛高業績承諾只會帶來比之前更高的成本。因此從長遠來看,對于上市公司而言更好的選擇是盡量減少不合理的業績承諾簽訂,避免高溢價并購或高業績承諾,進而避免巨額商譽減值帶來的更高風險。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1:“8號文”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的商譽減值水平。
近年來,觸及商譽減值風險的上市公司眾多,對中小投資者利益的影響也較大,因此上市公司商譽減值“爆雷”事件一直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例如天神娛樂、聯建光電以及天山生物等巨額商譽減值事件已經被多次報道,并成為業內典型案例。“8號文”是自2014年并購潮以來首次詳實而全面地就商譽減值的會計處理、計提時點以及監管細節做出要求,并且在多個層面明確了不合理的業績補償承諾已成為高額商譽減值的重要原因。因此,媒體在“8號文”發布之后對上市公司業績補償承諾實施效果的報道與關注可能會進一步加強,進而對計提了高額商譽減值的上市公司以及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形成監督效應。并且,在“8號文”下發不久后的2019年1月4日,財政部下屬的會計準則委員會針對商譽應該采取“減值測試”抑或是“商譽攤銷”的處理方式展開了激烈討論,這也進一步引發了投資者的關注及相關財經媒體的報道。
已有研究證實,媒體監督已經成為市場糾正機制的重要形式之一。管理層作為商譽減值與否的決定者和主要策劃者,其商譽減值行為必然會受到不同媒體監督程度的影響。于忠泊(2011)發現媒體監督會對管理者形成強大的市場壓力,抑制對企業長期業績影響較大的基于實際經營活動的盈余管理水平。周開國等(2016)認為媒體作為信息收集、處理與傳播的重要媒介,能夠彌補法律與政府的不足,對公司治理起到積極作用,具體表現為降低公司發生違規行為的概率。Joe et al.(2009)的研究也表明,媒體監督能夠改善管理層的無效率行為,進而提升公司的長期績效。由于商譽減值本身就是企業“可持續盈利能力”下降的信號,一旦計提過高的商譽減值,公司將面臨股價下跌及聲譽受損的風險。因此,出于輿論壓力和監管壓力(Dyck and Zingales,2002),管理層會盡量避免發生高額商譽減值的可能性,利用業績補償承諾進行高溢價并購和虛高承諾的傾向也將大大降低。結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2:“8號文”有助于提高媒體對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的關注,監督其商譽減值水平。
由前文可知,2014年以來的商譽減值爆發主要源于業績補償承諾的不合理使用。一方面,并購雙方故意抬高并購溢價,并設置虛高承諾,想利用業績承諾向市場傳達標的企業未來盈利狀況良好的信號,從而提升公司股價,再坐收漁翁之利。另一方面,當標的企業的實際能力無法達到承諾要求時,上市公司通過幫助標的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等利潤調節行為(劉浩等,2011;劉向強等,2018;柳建華等,2021),從而掩蓋其真實的盈利水平。然而,通過盈余管理所調節的利潤無法長期維持(Teoh et al.,1995;逯東等,2015),大量的商譽減值會導致“業績變臉”的發生,損害公司價值。已有研究發現,政策實施有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如會計準則制度的實施能夠有有效改善上市公司研發信息的披露狀況(梁萊歆、金楊,2010),監管政策也可以影響公司的現金股利及企業價值(楊俊等,2015)等。不難推斷,當“8號文”施行之后,一定程度上可能會遏制上市公司對不合理業績補償承諾的使用傾向,并加強并購估值的謹慎性,減少盈余管理操作,進而提升公司績效。此外,媒體報道對上市公司管理也具有監督作用(王云等,2017),上市公司可能會努力提高績效水平以提振股價,彌補商譽減值帶來的潛在損失。結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3:“8號文”降低了上市公司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傾向,并且有助于并購合理估值,提高上市公司并購績效。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由于“8號文”于2018年11月16日發布,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外生事件前后時間的對稱性,本文選取2016年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并購事件作為研究對象,以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并購公司作為實驗組,以未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并購公司作為對照組。具體地,考慮到上市公司2018年以后的商譽減值也可能是由于2018年之前并購簽訂補償承諾所積累下來的,因此為了確保結果更加準確,對于2018年以后的實驗組樣本,本文僅保留在2018年之前的并購中未簽訂業績補償承諾,而是在2018年之后才首次簽定業績補償承諾的樣本(6)事實上,2016年至2018年簽訂過業績補償承諾,且2019年至2010年間再次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樣本較少。。業績補償承諾數據由Wind數據庫手工匹配獲得。除此之外,本文還依據以下標準對原始數據進行了篩選:(1)剔除股權收購比例為30%以下的并購樣本;(2)剔除交易未完成的樣本;(3)剔除金融類企業樣本;(4)剔除同一家公司同一個月內發生多次并購事件的樣本;(5)剔除財務數據缺失的樣本。最終本文得到2199個并購事件樣本。為了避免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連續變量均進行了1%水平上的縮尾處理。其他變量數據來自于Wind數據庫與國泰安數據庫。
(二)回歸模型與變量的度量
首先,為了考察與未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企業相比,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在“8號文”之后是否降低了商譽減值水平,本文具體采用如下雙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進行回歸:
GWloss(DeltaGWloss)=α0+α1Treated+α2After+α3Treated×After+α4ROA+α5Size+α6Leverage+α7Growth+α8TOP1+α9CFO+α10Loss+α11∑Industry+α12∑Year+ε
(1)
其中,被解釋變量為商譽減值與總資產的比值(GWloss)和本期商譽減值與上一期商譽減值的變化值(DeltaGWloss)。Treated是指示變量,以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并購公司作為實驗組,取值為1;以未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并購公司作為對照組未實驗組,取值為0。After是區分“8號文”實施前后的指示變量,令After在2018年及其之前等于0,在2018年之后等于1。在該模型中,本文重點關注Treated×After的系數,且預計其符號為負,表明與未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并購公司相比,相比于“8號文”實施前,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并購公司在“8號文”之后會降低商譽減值水平。此外,基于上市公司發生商譽減值的常見動機,選取控制變量包括總資產收益率(ROA)、總資產規模的自然對數(Size)、資產負債率(Leverage)、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經營性現金流與總資產的比值(CFO)以及是否有“洗大澡”動機(Loss)等,具體的變量及其說明如表1所示。
其次,為了考察“8號文”是否增加了媒體對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的關注與監督,將模型(1)中的被解釋變量替換為媒體監督指標,利用CNRDS數據庫中的網絡新聞情感得分數據庫,采用上市公司當年在報刊中的情感得分絕對值加總(7)按照CNRDS數據庫中的網絡新聞情感得分數據庫衡量標準,報刊情感得分取值為1的表示“正面評價”,為0的表示“中性評價”,為-1的表示“負面評價”。本文將每個公司當年收到的多個情感評價得分取絕對值后加總,表示正面或負面的評價越多,受到的媒體監督相應就越高。作為媒體監督1(Media1)指標,用媒體監督1指標的自然對數作為媒體監督2(Media2)指標,其他控制變量不變,模型如下:
Media1(Media2)=α0+α1Treated+α2After+α3Treated×After+α4ROA+α5Size+α6Leverage+α7Growth+α8TOP1+α9CFO+α10Loss+α11∑Industry+α12∑Year+ε
(2)
最后,為了考察“8號文”對上市公司簽訂業績補償承諾意愿的影響,本文將并購次數(MA_times)和是否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虛擬變量(VAM)依次作為被解釋變量,僅以After作為主要解釋變量,其他變量不變,具體如模型(3)。同時,為了檢驗“8號文”對上市公司并購估值與長期績效的影響,將模型(1)的被解釋變量替換為并購溢價和并購績效,其中并購溢價采用“Premium=(交易總價值-賬面價值)/賬面價值”衡量,此外還采用行業調整的平均并購溢價(Aju_Premium)作為替代檢驗;并購績效采用并購后一年的ROA和ROE的變化之衡量,具體如模型(4)。
MA_times(VAM)=α0+α1After+α2ROA+α3Size+α4Leverage+α5Growth+α6TOP1+α7CFO+α8Loss+α9∑Industry+α10∑Year+ε
(3)
Premium(ROA,ROE)=α0+α1Treated+α2After+α3Treated×After+α4ROA+α5Size+α6Leverage+α7Growth+α8TOP1+α9CFO+α10Loss+α11∑Industry+α12∑Year+ε
(4)

表1 變量定義表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圖1列出了自2012年至2020年以來業績補償承諾簽訂比例的趨勢圖。可以看到,業績補償承諾的簽訂比例從2013年開始大幅上升,至2017年達到最高,為40.50%,之后又迅速下降至2020年的16.44%。圖2列出了2016年至2020年簽訂與未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商譽減值總額(億元)變化趨勢圖。可以看到,“8號文”發布后,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的商譽減值占比在2018年集中爆發,然后迅速下降至之前的水平。相比之下,未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其商譽減值占比在2018年后下降得更為平緩。這也說明對于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2018年之前高溢價并購和高業績承諾所積累的商譽減值大部分都集中在2018年進行了計提。

圖1 業績補償承諾簽訂比例趨勢圖

圖2 簽訂與未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商譽減值占比(%)均值變化趨勢圖
表2列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看到,Treated的均值為0.293,表明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平均占比29.3%,共644家。

表2 描述性統計
表3為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并購企業在“8號文”實施前后商譽減值水平的均值差異。數據顯示,在“8號文”實施前, 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與未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相比商譽減值顯著更高;當“8號文”實施后,兩者的商譽減值水平不再顯著,并且此時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商譽減值水平更低。

表3 “8號文”發布前后主要變量的分組描述性統計
(二)實證檢驗
首先,本文檢驗“8號文”對上市公司商譽減值影響,表4為對應的回歸結果。第(1)列至第(3)列的被解釋變量為GWloss;第(4)列至第(6)列的被解釋變量為DeltaGWloss。其中,第(1)列和第(4)列為不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第(2)列和第(5)列為不加入時間和行業虛擬變量的回歸結果;第(3)列和第(6)列為加入控制變量和時間、行業虛擬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除了第(5)列之外,Treated×After的系數均為負顯著。這表明,相比于未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并購企業,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并購企業在“8號文”之后降低了商譽減值水平。
由于《會計監管風險提示第8號——商譽減值》政策于2018年11月發布,而2018年的年度財務指標于2019年一季度才正式公布,因此不排除2015年及之后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在2018年集中進行突擊商譽減值的可能性。從圖2也可以看到,2018年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的商譽減值占比明顯提高。為了進一步對此進行檢驗,首先本文將政策時點改為2017年重新進行回歸,也即將2018年的商譽減值視為在“8號文”政策發生之后。具體地,令政策指示變量After在2017年及其之前等于0,在2018年及其之后等于1,并重新構造交乘項,回歸結果如表5的第(1)列和第(2)列所示。可見Treated×After的系數不再顯著,這表明“8號文”政策對上市公司商譽減值的作用效果確實會受到2018年簽訂業績補償承諾公司集中進行突擊減值的影響。
此外,考慮到業績承諾的期限一般是3年,那么2018年之后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于2019年、2020年尚且處于業績承諾期內,因此難以區分商譽減值的降低到底是“8號文”政策的效果還是上市公司故意選擇不在承諾期內計提商譽減值,而是在承諾期結束后才一并計提商譽減值的原因造成的。為此,本文補充了2021年的公司財務數據(8)對于2019年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2021年為其業績承諾到期年份。,將基本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替換為并購后兩年(承諾期內)及并購后三年(承諾期結束)的商譽減值總額與總資產的比值,分別定義為GWloss2和GWloss3。同時構造商譽減值相應年份的變化值,即令DeltaGWloss2=GWloss2-GWloss,DeltaGWloss3=GWloss3-GWloss2,其他變量不變。回歸結果如表5 的第(3)列至第(6)列所示。可見此時Treated×After對GWloss2在1%水平上負顯著,對GWloss2在10%水平上負顯著,盡管對DeltaGWloss2和DeltaGWloss3不顯著。結合表4結果,這表明,不論是在業績承諾期內還是在業績承諾期結束時,“8號文”政策之后上市公司的商譽減值均降低了,說明“8號文”確實能夠降低上市公司的整體商譽減值水平,并不受是否處于業績承諾期內的影響。

表4 “8號文”對并購企業商譽減值的影響
其次,本文檢驗“8號文”是否加了對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的媒體關注度,從而監督其商譽減值水平,對應結果如表6所示。第(1)列至第(3)列為以媒體監督1(Media1)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第(4)列至第(6)列為以以媒體監督2(Media2)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不加入控制變量時,Treated×After的系數不顯著。當分別加入控制變量時間、行業固定效應后,Treated×After的系數對Media1在5%的水平上正顯著,對Media2在10%的水平上正顯著。以上結果說明“8號文”確實增加了媒體對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的關注與監督。以上結果共同證實了本文的假設2。

表5 “8號文”對并購企業商譽減值的影響——考慮突擊減值的可能性
最后,本文檢驗“8號文”是否降低了上市公司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傾向,以及其對并購溢價和并購績效的影響,結果如表7和表8所示。表7的第(1)列至第(3)列為對并購次數回歸的結果,第(4)列至第(6)列為對是否簽訂業績補償承諾這一虛擬變量回歸的結果。可以看到,僅有第(2)列After對MA_times的系數為10%的負顯著,而不加控制變量【第(1)列】和加入時間和行業固定效應后【第(3)列】After對MA_times的系數均是不顯著的。相比之下,第(4)列至第(6)列顯示,After對VAM的系數顯著為負。以上表明,當“8號文”實施后,上市公司的并購次數沒有降低,但是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意愿大大下降。
表8的第(1)列至第(4)列為并購溢價的回歸結果,第(5)列和第(8)列為并購績效回歸結果。可以看到,Treated×After的系數對并購溢價為負顯著,而對并購績效顯著為正。這表明,“8號文”實施之后,相比于未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不再傾向于進行高溢價并購,同時長期的并購績效表現更好。

表6 “8號文”對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媒體監督的影響

表7 “8號文”對并購次數及業績補償承諾簽訂意愿的影響

表8 “8號文”對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并購績效的影響
(三)進一步檢驗
1.“8號文”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
前文表明,“8號文”能夠降低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的商譽減值水平,提高媒體監督,從而降低上市公司不合理的業績補償承諾簽訂意愿,提升長期并購績效。由于在“8號文”之前,上市公司具有通過跨期計提商譽減值從而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同時為了幫助標的企業完成承諾業績,避免公司股價下跌及聲譽受損,并購企業也有強烈的動機進行盈余管理。因此,為了進一步考察“8號文”的實施效果,本文將檢驗“8號文”是否抑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提高。具體地,本文將基本回歸中的被解釋變量替換為未修正的Jones模型計算得到的殘差絕對值(DA)和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計算得到的殘差絕對值(EM)以刻畫盈余管理指標,其他變量與模型(1)相同。具體結果如表9所示。第(1)列至第(3)列的被解釋變量為由未經過修正的Jones模型計算得到的殘差絕對值所衡量的盈余管理指標(DA),而第(4)列至第(6)列的被解釋變量為由經過修正的Jones模型計算得到的殘差絕對值所衡量的盈余管理指標(EM)。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到,除了第(1)列Treated×After的系數在10%的水平上負顯著異外,其他列Treated×After的系數對DA和EM均不顯著,這表明,相比于未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并購企業,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并購企業在“8號文”之后沒有顯著提高盈余管理水平。這也可以進一步表明,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并購績效并不是由于進行了盈余管理的結果。

表9 “8號文”對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
2.“8號文”對股價崩盤風險的影響
當業績補償承諾無法按時完成或是標的企業不履行補償義務,公司股價可能面臨下跌風險(李晶晶等,2020b)。如果“8號文”能夠有效抑制不合理業績補償承諾的簽訂,那么“8號文”之后上市公司發生股價崩盤風險的可能性應該會有所降低,或者至少沒有顯著增加。因此,表10進一步考察了“8號文”對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股價崩盤風險的影響。其中,股價崩盤風險參考彭俞超等(2018)的做法由NCSKEW和DUVOL兩個指標衡量。可見,Treated×After的系數均不顯著,這表明“8號文”實施之后,是否簽訂業績補償承諾對上市公司的股價崩盤風險不再有差異影響,即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不再引起過高的股價崩盤風險。整體而言,“8號文”后上市公司對業績補償承諾的簽訂更加合理化。

表10 “8號文”對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股價崩盤風險的影響
(四)穩健性和內生性檢驗
針對表4的基本模型,表11的第(1)列和第(2)列為加入公司聚類穩健標準差后的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可見Treated×After的系數仍然為負顯著。此外,本文增加了與公司商譽減值相關的其他控制變量,包括交易規模(取交易總價值的對數,TV)、商譽與總資產的比值(GW)和盈余管理水平(采用經過修正的Jones模型獲得,EM),回歸結果如表11第(3)列和第(4)列所示,此時Treated×After的系數仍然為負顯著。以上表明表4模型的穩健性較好。
針對表6的基本模型,本文用新的被解釋變量變量“媒體監督程度”這一虛擬變量替代原來的被解釋變量。具體地,將Media1的數值在四分之一分位數以上的定義為媒體監督程度高,令“媒體監督程度”等于1,否則為0。此外,還加入了表11中提到的三個其他控制變量,結果如表12所示。其中,第(1)列為不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第(2)列為加入控制變量但不加入時間和行業虛擬變量的回歸結果,第(3)列為加入控制變量和時間、行業虛擬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第(2)列和第(3)列中Treated×After的系數仍然為正顯著,以上表明表6模型的穩健性較好。

表11 穩健性檢驗:“8號文”對上市公司商譽減值的影響
針對表7和表8的基本模型,與表11相似,本文增加了相應控制變量,結果如表13及表14所示。由表13可見,After對MA_times的系數不顯著,對VAM的系數在不加入時間和行業虛擬變量時為負顯著,加入時間和行業虛擬變量時不顯著。以上結果與表7結論并無矛盾。由表14可見,除了第(3)列以外,Treated×After的系數對并購溢價仍然為負顯著,而對并購績效仍然為正顯著。以上結果與表8結論仍然一致。
最后,考慮到表4的結果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表15采用PSM+DID模型進行檢驗。經傾向得分匹配后,表15顯示Treated_PSM×After的系數仍然為負顯著,與基本結論一致。

表12 穩健性檢驗:“8號文”對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媒體監督的影響
五、結論與啟示
近年來的商譽減值“爆雷”事件頻頻出現,引起了監管層和資本市場的廣泛關注。為了防范和降低商譽減值帶來的損害,證監會發布《會計監管風險提示第8號——商譽減值》一文,要求上市公司至少每一年進行商譽減值測試,且不得以業績承諾期為由不進行測試。由于業績補償承諾是高溢價并購和高商譽減值的重要誘因,因此這一政策無疑會對上市公司的商譽減值及業績補償承諾的實施效果產生影響。本文通過雙重差分法對2016年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實證研究后發現:“8號文”有助于降低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的商譽減值水平,加強媒體對簽訂業績補償承諾公司的關注與監督,但存在2018年突擊計提商譽減值的現象。此外,“8號文”能夠降低上市公司對不合理業

表13 穩健性檢驗:“8號文”對并購次數及業績補償承諾簽訂意愿的影響
績補償承諾的使用傾向,降低并購溢價并提高長期并購績效。最后,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并購企業在“8號文”之后沒有顯著提升盈余管理水平和股價崩盤風險。本文總體表明,“8號文”有助于上市公司在并購過程中合理使用業績補償承諾,降低商譽減值水平。但從長遠來看,由于我國的法律法規尚不健全,而“8號文”也僅僅是對相關風險進行警示,因此仍然需要從完善業績補償承諾設計機制、健全法律法規約束等角度考慮遏制商譽減值的潛在風險。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以得到如下啟示:首先,上市公司應該更加謹慎對待業績補償承諾的簽訂,合理設置承諾業績,理性預測標的企業未來償還能力,避免高溢價并購。其次,監管方應重點監督上市公司的機會主義行為,防范“高溢價、高承諾、高股價”鏈條的形成,制定更為有效的政策促進上市公司利用業績補償承諾合理估值。同時進一步加大對“不計提”或“亂計提”商譽減值行為的懲罰力度,形成監督與懲罰相對應的配套措施,真正對管理層施加壓力。最后,中小投資者應該合理看待業績補償承諾的簽訂,不要盲目跟風,避免利益損失。

表14 穩健性檢驗:“8號文”對簽訂業績補償承諾上市公司并購績效的影響

表15 內生性檢驗:PSM+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