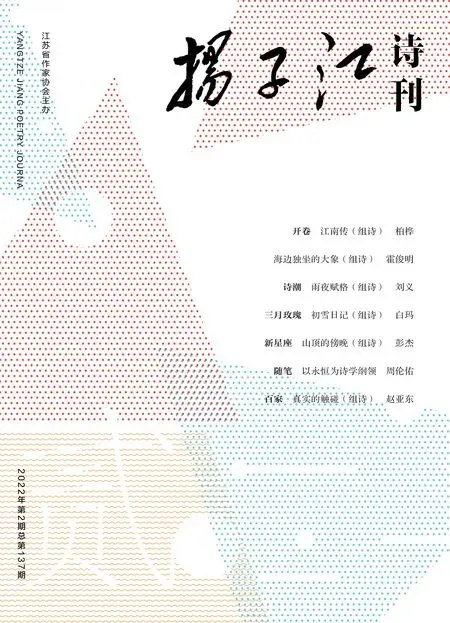南疆木器(組章)
蔡 淼
沙棗木:花瓶
沙棗木做的花瓶,用來裝沙棗花,一種帶著隱喻的命運被反復提及。
在南疆,沙漠的邊緣,沙棗搖曳,燈盞解構。
書桌之上,一種木頭被另一種木頭指認、接納。
沙棗木做的花瓶,并不需要什么花朵裝扮。
它越過疲憊、蒼涼,高擎秋天的體香,在書房分娩。
一個空花瓶,木質的紋路指向源頭。
空,一種啟示。
靈魂泅渡,寓言空置。
枯坐。對視。高貴者的天空擺渡在春天的門口。
好多年了,我們從頭到尾沒有說過一句話。
時間的縫隙里落滿了塵土,夜晚安靜下來,整個房子都住在一棵沙棗樹里。
楊木:燭臺
他的身體也和眼前這燭臺一樣,輕飄飄的,懸浮在塵世之上。
泣血般的吶喊從細小的事物中傳來,那些經過鐵烙的紋飾在燭臺上呈現出故鄉和穹頂。手持楊木燭臺,紅色的蠟燭讓原木的燭臺有了靈魂。一只燭臺叫醒了整個夜晚,微弱的燭光一層一層地剝落下來。落在阿里木身上的,不只有光,還有無盡的往事和記憶。
制作燭臺這門技藝即將在家族內消亡,這或許是時間的選擇。阿里木背負著愧疚、衰老,卻無法替代傳承。黃色的絹布包裹了整個房間,與楊木結緣成就了阿里木一生的必修課。
燭臺只有在夜晚才能發揮作用,而阿里木卻傾注了整個白晝的時光。
還有一些愛沒有來得及說出,還有一些技藝沒有來得及傳承,還有一些楊木躺在院子里等待著阿里木的刀斧。
榫木穿插,隨手賦形。
阿里木說,左手活成了一把刻刀,右手活成了一把楊木。
燭臺上的燈光逐漸矮下去,燭臺沉浸在黑色之中,靜寂,偉大的虛空。
胡楊木:根雕
從沙漠中走出的圣雄,寧可把自己渴死也絕不低頭。
死而不朽,時間會生出青苔,為大地留下伏筆。
把心掏空了,時光才能慢慢靜下來。
在公園里走進一座陳舊的房子,展廳里擺著比房屋更陳舊的胡楊根雕。胡楊木上隨意地掛著幾個葫蘆,是搬運的人為自己留下的借口嗎?
我們是否足夠了解一株胡楊?時間的回聲似乎在提醒著什么。
胡楊木從不缺少贊美之詞,皸裂之聲敲響歷史的肋骨。
每一件根雕都注入了現代人樸素的審美意識。
他們從沙漠里拖回一截截干枯的胡楊,把它改造成茶桌、木墩、椅子,甚至是花盆。旋刀和斧子調整了胡楊的語序或邏輯。刻刀開刃,以一種疼痛的姿態重建內在的階梯。
他們說,每一件胡楊根雕都是絕世孤品。
棗木:木枕
亞力坤熟練地將木枕分出十余個部分,兩頭布以魚鱗,中間是各種花卉、草木、山石等,每一組圖案都呈現出一種安寂和對生命的寬解。電烙鐵在木頭上吐出特有的紋理,焦灼的木炭以一種氣態的方式追溯和詮釋著這門獨特的藝術。
以木為質,鋪開大千世界的精彩,一種浸淫于生活的藝術已經傳承千年。
在時光的隧道里,木枕的技藝不僅凝結著亞力坤對祖先的懷念,更傳承著一種生活的智慧。
電烙鐵已經在木枕上完成了逡巡,對時間的抗爭讓我們游走在藝術的邊緣。粗細方圓、疏密虛實、濃淡干濕都將在我們的頸下治愈白晝的勞累。
回到家中,亞力坤那張瓷實的臉孔延伸進夢中。三更醒來,用手輕輕地觸摸木枕的表面,那里回旋著森林和棗木的氣息。
只有在做夢的時候,我們才一遍又一遍重返故鄉。
木枕在黑夜予我以跋涉之語,在白晝予我以滄浪之音。
木枕始終以夢境的方式接替它身上的紋理,在每個深夜醒來。
馕戳子是木頭與鋼針的結合,馕戳子尚未問世的時候,維吾爾族人束緊一把雞毛扎向馕胚。馕戳子是打馕過程中給馕的表面拓印花紋的工具,印制花紋不僅美觀,還能讓馕餅入味,透氣,避免中間隆起。
一根樺木在木匠的手中很快旋成一根有凸凹起伏的把子,上下刻成幾圈平行的圓圈,中間刻上花紋,鋪上油彩。底部繞上一層碎布,裝上馕針,按在木柄上,晾曬三日,加固即可。其大小形態各異,可實用亦可收藏。
走出馕坑的每一個馕在享受高溫的同時,也用清油、牛奶、芝麻的芳香治療傷口。
在南疆,我們吃的每一個馕餅,都少不了馕戳子的點綴。
馕戳子,是一種木器,一種工具,也是一種生活表達的儀式。
在南疆,幾乎每一個打馕人用過的馕戳子都超過三十年,從來沒有人會扔掉一個年邁的馕戳子,就像從來沒有人會掉下一粒馕渣子。
我望著書柜上的馕戳子,一種負罪感在心頭奔涌。每一個馕戳子都應該奔赴馕胚而不是空守書房。
小小的馕戳子,簡單,卻又日復一日地奔走在腸胃與馕餅的兩端。
梨木:木杯
用梨木做的木杯,在盛夏盛上冰塊和石榴汁,整個夏天都涼爽無比。
梨木,有韌性,無毒,無異味。無論是裝滾燙的茶水還是凜冽的冰泉都不會走形。每一個木杯的誕生都凝聚了匠人的思想,每一只木杯都有一個獨特的造型。
伐倒一棵梨樹,要經過砍、旋、摳、挖、磨、雕、燙等工藝才能有木杯的雛形。
木杯雖小,卻是飲水的關鍵器物。
做一個木杯,極需耐心,杯沿和杯身要薄如蟬翼,同時還要接受電烙鐵的燙畫。多一寸則顯累贅,少一厘就會被燙穿。杯子的底座和杯把用砂紙一遍一遍打磨,直至如皮膚般輕柔可彈,再用小刀鑲嵌上瑪瑙、羊皮、牛骨,一個木杯才算徹底完工。
維吾爾族匠人要用半個月的時間才能打磨一個完整的木杯,每一個木杯少則可用幾十年,多則百余年,在歲月中裹滿了包漿。
木杯被各種液體沖刷浸泡,滋潤著我們內心的干旱。
當用杯子的人離開了這個世界,還有一只木杯會記得他曾經的容顏。
還是一千年以前的技藝,木器巴扎上擺滿了耀眼的木盤。
先祖傳下來的木器制作技藝,已化作維吾爾族人血脈里的基因,世代相隨。
泡桐木,耐腐爛耐酸堿耐磨損,紋理優美、細膩。
泡桐木做的木盤,輕盈,如一張張木質的速寫紙,以一種流暢的線條把生活場景搬運到盤子里。
那些凝固的線條開始在春天復活。
深褐色,抖動著光影的花朵和深情的舞蹈。
木盤中有四季,有鳥獸,有懸崖,也有深夜的暴雨和自我的省視。
凝視,被時光過濾的木盤以一種游子的身份回到故鄉。
當銼刀緩緩地研磨出木盤的曲面,木頭涅槃,另一重使命就開始蘇醒。
木盤,放牧靈魂的叢林,古老而現代。
它沉默不語,拉低了時間的轉速,以對抗膚淺的節奏。
其實木盤并沒有什么復雜的工藝,但它始終以永不改變的方式出現在南疆人家的生活中。
柳木:盤式肉墩
十五歲的柳木尚且無法打磨成一個盤式肉墩,十五歲的人生卻已經走到盡頭。與厄運抗爭無效,歲月與病魔同行。
木盤和肉墩的完美結合,在一動一靜中抵達和諧。
盤式肉墩,呈圓盤形,中間有一凸出的圓柱形的墩子,上大下小,四周凹陷。
走訪得知,中間的肉墩可以用來切肉,切蔬菜,切水果。切畢,自然落入四周凹陷的盤面,極為便利。也可以用來做木制壺承,中間凸出的部分放壺,凹陷處放木制的杯具。
兩種不同的生活儀式,在一個盤式肉墩中聯誼。
炊飲皆在方寸之間,回憶無法填滿一個盤式肉墩。
快樂和憂傷同時到來,萬縷心結,被一寸一寸切斷,拉長。
妹妹再也不可能醒來,所有的語言卡在喉結處。盤式肉墩里的食物,成了被滯留的晚餐。
執念,只能被掛在天空。
院前的柳葉在風中謝幕,大地的劇場之上同時舉辦著兩場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