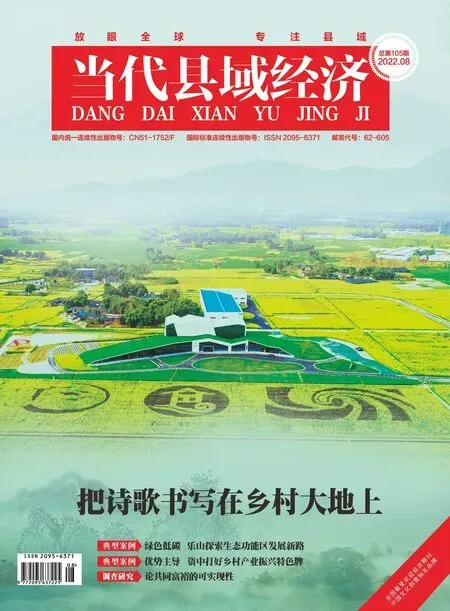金融助推四川省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思考
□高波
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石,金融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縣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配套的金融支持,同時也面臨著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主要舉措
縣域經濟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和城鄉一體化程度是四川省實施“一干多支、五區協同”“四向拓展、全域開放”戰略部署的底部支撐。金融支持不足是縣域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四川省委、省政府歷來高度重視金融服務縣域經濟發展,金融機構也積極貫徹政策導向和監管要求,進行了一系列探索。
自2004 年以來,四川省連續19 年以省委“一號文件”形式部署“三農”工作。其中,2022 年“一號文件”提出,加大對“三農”領域的信貸支持力度,保持同口徑涉農貸款余額和普惠型涉農貸款余額持續增長;引導在川大中型商業銀行提升縣級機構授信放貸能力和效率,督促指導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強化支農支小市場定位。《關于推進“5+1”產業金融體系建設的意見》(川府發〔2019〕2 號)提出,推動金融資源向農產品加工園區匯聚,引導金融機構對接農產品加工園區金融需求。
當前,四川省已形成了類型多樣、結構較為合理的多層次縣域金融服務體系。截至2020 年末,四川銀行業金融機構數量為228家。其中,主要定位為服務縣域經濟的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等小型農村金融機構的法人機構101 家,分支機構5808 個,從業人員50067 人,資產總額20980 億元;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和小額貸款公司等農村新型機構的法人機構56 家,分支機構303 個,從業人員4474 人,資產總額807 億元。2022 年,金融機構新增涉農貸款2086.1 億元,占全部新增貸款的24.4%。
成都市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試點為四川省其他地區金融支持縣域經濟發展提供了先行先試的可借鑒經驗。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多層次農村金融組織體系不斷完善。成都市銀行機構已普遍設立“三農金融部”或“普惠金融部”,互聯網銀行、金融租賃公司、涉農征信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多元化新型金融組織逐步建立。第二,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日益深化。依托農村產權和現代農業制度賦能,探索了近20 種農村產權抵押標的融資模式;圍繞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模式創新,開展農業職業經理人貸款、農產品倉單質押貸款等業務。第三,農村金融核心基礎設施建設效果突出。“農貸通”村級服務站持續完善,創新“線上+線下”融合模式,較好解決了農村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難題。
制約因素
主要表現在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迅速、規模壯大,資金需求由小額信貸向大額貸款轉變;以農業產業化經營、休閑農業、“互聯網+農業”為代表的農業發展方式,延長了農業經營周期,使得資金需求由短期貸款向中長期貸款轉變;依托產業園區推動工業向園區集中,發展產業集群,使得工業園區對于貸款的需求增加。
本文選取四川省2020 年GDP 排名前40 名且非地級市主城區所在地的縣域2020 年末存貸比情況(剔除缺少2020 年末存貸款數據的縣)進行分析,包括仁壽縣、成都市青白江區、彭州市、廣漢市、江油市、威遠縣、金堂縣、大竹縣、射洪市、都江堰市、南部縣、瀘縣、什邡市,共13 個縣(市、區)。其2020 年末的平均存貸比僅為54.13%,大大低于全國的81.69%和全省的76.93%。縣域存貸比偏低的情況,在全國其他省份也普遍存在。為此,銀保監會要求對縣域存貸比進行監測分析,加強考核引導,合理提升資金外流嚴重縣的存貸比。
縣域金融機構雖多,但真正設在鄉(鎮)上、服務“三農”的金融機構較少且還有減少趨勢。在金融業務開展中,“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縣域中小微企業普遍面臨著“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大中型金融機構的縣域分支機構權限普遍較小,產品不夠豐富。
原因分析
在金融科技大發展背景下,部分商業銀行陸續退出縣級行政區,引發了縣域金融服務渠道不暢、服務體系不健全、金融服務縣域經濟的功能弱化、金融產品創新不足等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相比大中城市的經濟發展,縣域經濟較為脆弱,縣域金融機構經營風險較高。以重點服務于縣域經濟的農村商業銀行為例,其不良貸款率高于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而撥備覆蓋率、資本充足率均低于后三者。根據銀保監會公布的數據,2021 年末,農村商業銀行、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3.63%、1.37%、1.37%、1.90%;撥備覆蓋率分別為129.48%、239.22%、206.31%、188.71%;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2.56%、17.29%、13.82%、13.08%。考慮到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等監管因素,農村商業銀行能夠用于投放的信貸規模有限。
四川省大多數縣的當地產業具有先天弱質性,支柱產業尚處于起步階段,產業化程度低且以中小微企業為主,受經濟周期影響較大。中小微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容易出現因市場變化而業務大幅波動、資金鏈緊張等問題,進而導致信用風險上升。銀行為控制信貸風險,對縣域中小微企業的信貸準入門檻較高,形成“融資難”問題;按照收益覆蓋風險的原則,要么直接提高貸款利率,要么要求融資擔保機構提供擔保,又形成了“融資貴”問題。
部分縣級政府偏重于金融機構對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持,缺乏對縣域生態信用建設的整體考量,使得銀行在維護金融債權過程中,面臨著起訴難、判決難、執行難等困難。反過來,出于對信用環境的擔憂,銀行在發放貸款時會更加謹慎。另一方面,縣域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一般規模較小,擔保能力有限;因風險收益不匹配等原因,商業性融資擔保公司提供擔保的積極性不高。
銀行實行高度統一的信貸資金管理機制,其縣級分支機構主要功能是吸收存款、銷售理財產品和發放貸款。為控制信貸風險,銀行在發放貸款時強調擔保、抵押和貸款風險責任追究,使得縣域中小微企業獲得融資的難度增加。另一方面,因縣域金融人才匱乏,金融機構信貸產品研發權主要集中在省級分行乃至總行,對縣域支行授權小。這使得縣域金融機構難以結合實際需求,研發多樣化、個性化的金融服務。
對策建議
金融支持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政府、金融機構、中小微企業的多方聯動,構建起完善、高效的金融服務體系。
一是優化信用體系建設。以大數據為基礎建立和完善金融信用信息數據庫,實現縣域企業及個人信用、政府與征信機構、金融機構、行業協會商會等組織的信息共享。通過持續加強信用信息的綜合運用,促進政務信用信息與社會信用信息互動融合,最大限度發揮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作用,營造守信受益、失信被懲戒的氛圍。二是優化金融法治環境。嚴厲打擊非法集資、金融詐騙等非法金融活動,以及企業、個人惡意逃廢債行為。加大依法審判、執行金融訴訟案件力度,維護金融機構合法權益。加大金融類案件審理、執行力度,清理財產保全障礙。對于金融涉訴案件,在法律允許范圍內優先受理、優先審理;對于債權債務關系清晰的金融涉訴案件,盡量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提高效率。三是加強政務誠信建設。健全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機制,進一步提升縣級政府公信力,引領其他領域信用建設。將縣級政府所屬職能部門在履職過程中因違法違規、失信違約被司法判決、行政處罰等信息納入政務失信記錄。建立公務員誠信檔案,將公務員在履職過程中因違法違規及受到開除以下處分的相關信息,納入政務失信記錄。四是建立財政支持機制。縣級財政按照“政府引導、市場運作、風險共擔”的原則,將對于中小微企業、科技等財政直接補助,轉變為財政貼息方式,通過激勵與約束機制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對縣域經濟發展具有重大作用且需政府加強引導的貸款項目采取專項財政貼息,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同時,還要更好發揮融資擔保公司在中小微企業融資中的“放大器”和“穩定器”作用。
一是持續完善普惠金融事業部機制。商業銀行可將普惠金融事業部機制與縣域金融服務需求深度對接,整合監管機構關于提升小微不良貸款容忍度、涉農和中小微企業貸款核銷處置、普惠小微貸款增量獎勵、存款準備金激勵、支小再貸款等相關政策,下沉服務重心,將金融資源向縣域傾斜,充分利用監管政策紅利。二是加大信貸產品創新力度。商業銀行可針對縣域中小微企業財務信息不完善、缺抵押、缺擔保等特點,加強對工商信息、工資發放情況、社保公積金繳存情況、納稅記錄、水電氣繳費記錄、涉訴信息等政務或公開信息的挖掘利用,輔以縣域支行的當地人脈信息獲取便利,為企業進行“畫像”,設計適用于縣域中小微企業的信貸產品,緩解“融資難”問題。三是優化授權審批模式。發揮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科技優勢,促進銀企信貸業務的高效對接、精準風控、實時貸后管理。在提高審批效率的同時,減少人工參與度,彌補縣域高素質金融人才匱乏的劣勢,降低人工成本,進而降低銀行獲客成本和企業貸款成本,緩解“融資貴”問題。
一是注重自身信用維護與積累。中小微企業要按規定繳納稅款、社保公積金、行政事業性收費等費用,及時執行法院終審的生效法律判決文書,按時還本付息,珍視企業信譽,一點一滴積累自身信用。二是主營業務向當地優勢產業、龍頭企業靠攏。商業銀行為控制風險,往往圍繞當地優勢產業和龍頭企業,設計標準化的信貸產品,對縣域中小微企業實行批量準入、批量授信。三是經營場所向產業園區集中。當地政府為發展產業,將優惠政策、財政資金向產業園區集中,吸引企業投資。金融機構在政府支持下,信貸資金也會向產業園區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