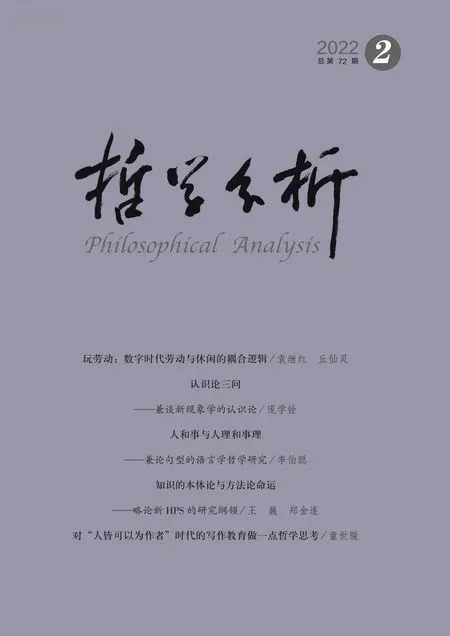認識論三問
——兼談新現象學的認識論
龐學銓
認識就是獲取知識,知識是真實確信的判斷,明證性則是真實確信的依據和保證,因而也是認識的目的。這是一般認識論涉及和涵蓋的基本問題。西方哲學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眾說紛紜,對認識論的討論迄今仍在繼續。對其中的不少重要問題,筆者依然覺得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梳理和研究,本文將其概括為三問:認識的對象是什么?如何認識對象?如何確信所獲得的認識?德國新現象學家赫爾曼·施密茨(Hermann Schmitz)對這三問提出了不同于以往哲學家的思考和回答,所以,本文同時重點考察新現象學的有關觀 點。
一、 認識的對象是什 么?
認識的對象是什么?不同的哲學派別和哲學家有不同的說法,但貫穿西方認識論始終的基本觀點有兩種:認識論的實在論和整體 論。
認識論的實在論(Realismus)認為,任何一種形式的事物都是認識的對象,認識就是對象化的認識,無論是實際存在的還是意識構建的對象。傳統哲學的唯物論或唯心論,理性論或經驗論,都主張這種認識論的實在論。德國實在論哲學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說:我們一旦能夠想象出一個事物,就意味著認識了它。胡塞爾認為意識總是關于某物的意識。海德格爾批評傳統認識論把認識當成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一種關系,結果使整個認識論糾纏到認識主體如何從內在世界到達外在對象的這一難題中去了。他本人將認識奠基于存在論上,指出認識是此在在世的一種存在方式,此在并不是首先囚禁在內在世界中的認識主體,認識著的此在是在世界中存在的;傳統認識論的命題不是原始的而是派生的認識,純粹的更原始的認識是對命題和命題所及東西(是否符合)的證明,“證明涉及的只是存在者本身的被揭示的存在,只是那個‘如何’被揭示的存在者”。傳統的真理符合論便是以這種實在論為依據 的。
認識論的整體論(Holismus)則主張,認識的對象是無所不包的整體。德國古典哲學所推崇和強調的理性便是指對整體的領悟。黑格爾是這種整體論的典型代表,他主張真理就是整體,在《精神現象學》序言中指出:哲學不能像解剖學那樣,采用歷史性的無概念的方式,給哲學的趨勢和觀點、一般內容和結果作一種歷史性的敘述,或作一種兼容并蓄的羅列。哲學的認識必須從獲得關于普遍原理和觀點的知識開始,按照一般思想的規定去理解它的具體和豐富的內容,并能夠對它作出有條理的陳述和嚴肅的判斷,這才是哲學的認識和知識。奎因獨立于黑格爾,是整體論的另一位代表,他接受迪昂(Dehem)的觀點,認為不可能驗證一個孤立的假 說。
施密茨對上述兩種觀點提出了批評。他指出,認識論的實在論包含著兩個層次的會讓人誤入歧途的立足點:首先,認識必定有相關物,認識就是對象化的認識。實際上,是否與事物相關,并不是認識的本質。在普遍否定的存在斷言中,就根本沒有相關物,例如“不存在20 面以上的歐幾里得正多面體”這個重要的數學定律,無疑是一種認識或知識,卻看不到任何相關物。其次,在談到對事物的認識時,人們并不滿足于獲取該事物的個別或某些內容,而是認為獲得與該事物全貌對稱的認識,或至少應與其全貌相符。然而,怎樣才算是完全“認識”了事物?事物由多方面的內容或要素構成,我們對它們的認識是不可能達到窮盡程度的,“因為沒有明確的依據能夠說明這一點:人們獲取某物的多少知識以后,才算真正認識了它”。認識論的整體論的主要誤區則是把關于對象的個別或部分確信認識/知識嵌入整體之中。這種“嵌入”實際上是一種錯誤的“推移”“推論”,好像對象的具體內容都包含在普遍原理或一般思想之中,都籠罩在概念或理論的光芒之下。而作為整體的對象,它或者是一種或多或少混沌多樣的整體,或者是包含著無數事實的整體,根本無法被完全陳述,沒有人能夠看清他所認為的對象的全部,對象的內容也不可能全部蘊含在普遍原理或嚴肅概念之中。“知識是在認識過程中積跬步而來,每一步,即便是極小的一步,也都有可能出現失誤或錯誤。”
施密茨主要通過深入考察和批評認識論的實在論,闡述了他自己關于認識對象的觀點。按照心物、心身二元論的西方哲學傳統,實在論的認識對象實際上歸結為兩種:客觀事物和主觀經驗。傳統哲學是怎樣理解這兩種對象 呢?
施密茨指出,傳統哲學的心理主義感覺論將認識看成是感官受到外界事物(包括事件和物)的刺激,然后被傳遞到大腦形成感覺或感覺的復合。因此,感覺實際上是與感官能力相適應的有限的刺激反應,這就大大限制了認識的通道;而且,由于還原主義,客觀事物/世界的豐富內容被還原、過濾成了某些只能被感官感知到的要素或特征,成了認識中一些內容貧乏的表象乃至抽象的觀念/概念。胡塞爾的意識意向性所構建的對象,也有別于通常意義上的客觀事物。與此同時,按照內攝性思維范式,客觀事物除了被還原、加工而留下的那些基質性特征,其他性質和特征,如顏色、硬度、味道等,都被作為純主觀的經驗或觀念,從而否定了它們具有事實的存在 性。
在施密茨看來,這種支配歐洲二千年的傳統思維范式,不僅誤解了客觀事物,否定了主觀經驗的事實性,而且造成了嚴重的后果——未經意識加工的原初生活經驗(primitive Lebenserfahrung),部分幾乎被完全忽視了,部分被錯誤地解釋成主觀的經驗、錯覺或臆想,部分被歸入感官知覺而隱匿于生理學和心理學的邊緣。新現象學正是要揭示原初生活經驗世界,將它作為自己研究的對象領域。相應地,在認識論上,一方面,要消除傳統思維范式所導致的對事物的扭曲,另一方面,要把被傳統哲學所忽視的那些事物納入認識論視野,恢復它們作為認識對象的權 利。
具體說來,新現象學所恢復和確立的認識對象 是:
1. 主觀事實
盡管以往的哲學都重視研究人,討論如何認識人自身的問題,卻沒有真實地回答古希臘德爾菲神廟中那句著名的哲學箴言:“認識你自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直受到傳統思維范式的束縛與影響。現象學試圖重新在我自身中發現自己真實的當下,發現概念和語言所要陳述的我的意識之事實性。在施密茨看來,老現象學家們所說的人(主體)始終沒有完全脫離傳統的主體性觀念,這樣的主體性實際上是真實主體性的退隱性異化,盡管在胡塞爾、海德格爾、薩特和梅洛—龐蒂那里表現的形式和程度不同。因此,要真正認識人自身,就要重新揭示和認知主觀事實,了解真實的主體 性。
通常人們應用“主觀的”一詞,是指從主觀角度看待個人的感受和情感等,如人身上經常會出現的當下感知到的悲傷,愉快,疼痛、饑餓,等等。這些發生在可看、可觸的軀體(K?rper)上,但不需自己去看、去觸就能感覺到的感受,施密茨稱之為身體(Leib)。身體不同于軀體。軀體的主要特征是在空間上受到平面/表面的限制,可以用地點和距離關系來確定軀體各部位的位置,這叫相對位置。身體在空間上沒有平面/表面,也沒有清晰的界限,但有不可分割的、前維度的體積/容積,不能用地點和距離來確定其位置,這叫絕對位置。“在絕對位置上發現的感受,就是。”身體感受一般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局部的感受,如局部性的刺痛感或騷癢感、麻木感或疼痛感,叫身體島。另一種是擴散性的整體的身體感受,如全身泡在浴缸里的那種愜意感。第三種是氣氛性的身體感受,如愛一個人或被一個人愛時的愉悅感,在悶熱的夏日所感受到的天氣,人仿佛是被漫無邊際地涌出的氣氛所把 捉。
傳統哲學往往把諸如此類的身體感受歸入主觀經驗或心理體驗的范圍,不具有事實性存在的特征。但是,它們實際上是個體當下直接感受到的事實,施密茨用“主觀事實”這一概念來標識這類事實。“主觀事實是那些最多能以自己的名義說出的事實。”例如“我悲傷”的陳述。當我本人就是這個“我”時,這個陳述就是指悲傷正襲擊著我,我正沉浸在悲傷中,悲傷是我切身感受到的。這就是主觀事實。主觀事實是當下發生和被感知著的,表現出內容的鮮明性和豐富性,在真實性程度上超過對象化的陳述所指稱的客觀事實。這樣的主觀事實構成的主體性,叫作具體主體性(konkrete Subjektivit?t),它顯然比傳統的主體性更真實更具現實性,后者是它的隱退性異 化。
施密茨將主觀事實作為新現象學基本的認識對象,并進行了廣泛探討。由此,既為認識論發現和增添了一個無窮盡的對象領域,也在哲學上將對自我、主體的認
識提升到新階段。2. 類物
傳統認識論將物簡單地二分為實體與屬性,對物的認知似乎就是對這二者的感知,從而長期忽視或無視了如風、聲音、目光等這類被稱為“類物”(Halbding)的實際存在。施密茨對類物及對它的感知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在他看來,類物既不同于物的實體,也不同于物的屬性,而是居于二者之間,與這二者的區別,既明顯可感知,又非總是一目了 然。
一般來說,在持續性上,物是持續存在的,物的特征可能會變,但物還是同一個。我們可以問:某個人或動物,在我們沒有感知到他或它時,是什么?存在于何處?怎樣存在?而類物卻不具有這樣的持續性,它們會消失,并可以同樣重新出現。假如我們問:風或聲音,在它消失的這段時間,是什么?存在于何處?怎樣存在?這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會被當作一個笑話。類物雖然不像物那樣具有持續存在的特征,但在其存在期間也有其不變的特性,這種不變的特性同樣會出現變化的形式。比如風,在人們順風或逆風而行時,對它的感覺是截然不同的,就是說,它也會表現出不同的感覺屬性,但它是同樣的風。在表現特征上,物本身與它對他物施加影響的力量是不同的,如一只擊打著他物的手,對被擊打的他物施加和產生影響的,是擊打的力量而不是手本身。類物則不同,類物在發出力量的那一瞬間,本身就這這種力量,比如電擊,絕不會將它感知為由一個正在擊打他物的物(電流)產生的結果,因為電擊是一個物理的感覺過程,這個過程同時也就是電流本身。
將類物作為認識的對象,對于認識論而言意義非凡,因為,“若不對類物展開獨立論述,感覺學說便始終是不完全的”。
3. 源自情境的事實
“情境”(Situation)是一種對象型式,它“由事態,大多數情形中還有計劃和問題,在內部以一種或多或少模糊的方式構成的、整體地組合在一起的多樣性事物的富有意義的暈圈(Hof)”。這個定義明確概括了情境的基本要素或特征:首先,它由事態、計劃和問題等構成。事態是新現象學原初生活經驗的基本構成要素,它可以是通常可感知到的事實(Tatsache),如住所的舒適、春天早晨的清新等,也可以是非事實,如愿望、想象等;其次,它是前語言、非陳述、非命題性的,其中的事態、問題和計劃等要素,不是單個的或在空間上被分割的存在,也不能用語言將它們個別地陳述出來,而是混沌多樣地彌漫式地存在于情境內部。再次,它是富有意義的整體,其中的要素錯綜復雜地糾纏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富有意義的暈圈”(Hof);“暈圈”沒有清晰的邊界,但意味著一種組合,也就是一種模糊的整體性,有點類似于海德格爾的“意蘊整體”。在情境中,主觀和客觀、主體和客體處于彼此關聯未分的狀態。施密茨喜歡舉技術熟練的司機避險的例子來說明情境的這種意蘊:在遭遇危險的時刻,司機面臨的那些事態/事實(如突然出現的行人或障礙物等)、問題(如繼續行駛或剎車避讓等)和計劃(如踩剎車或轉方向盤等),包括主體(司機)和客體(事態/事實),都沒有單個清晰地凸顯出來,而是混沌多樣地處于一個情境的暈圈中。司機從感知到危險的事態/事實,到迅速采取恰當的應對動作,沒有思考或/和推論的時間,而是“一下子”自然地協同配合發揮作用,這種自然協調,類似于海德格爾說的當下“上手狀 態”。
情境既是一個存在論的事實概念,也是一個認識論的對象概念。施密茨說:一方面,情境本身是認識的對象,情境中多樣性要素構成的意義通過情境“暈圈”整體地顯露出來,“當意義一下子(瞬間)顯現出來時,情境就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源自情境的事實是認識的對象”。施密茨把情境和源自情境的事實作為認識的對象以及關于它們的認識,稱為認識論的解釋論(erkenntnistheoretische Explikationismus),以區別于傳統哲學認識論的實在論和整體 論。
歐洲古代哲學一般認為,物的自身結構構成了它的存在,物的存在就是物本身,正如經院哲學所說:“各個存在者都是單獨的”(omne ens unum)。近代哲學,尤其是在康德那里,物是被表象的存在。這種表象性思維,實際上也和古代哲學一樣,把物看成單個的存在,“把世界理解成單個對象構成的關系之網”。施密茨把對物和世界的這種理解稱為“素群主義”,它不了解單個物的意義是在情境的整體意蘊中顯現出來,而是試圖打破這種整體意蘊,將情境分解為單個的物(事態/事實)或規則。這是一種目光短淺,但在今天已成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世界觀。“這種致力于將情境分解為單個元素組成的素群或網絡的素群主義,是很現代的;然而,作為一般的世界觀,它顯然是虛構的,因為總的來說,為了發現單個元素,我們需要情境。”胡塞爾雖然是在意識范圍內談物/對象,但他對物的理解沒有離開傳統哲學的立場——“在這種最廣泛的意義上,‘事物’是對于最終存在著的東西,‘具有’最終的屬性、關系、相互關聯的東西(通過這些東西,事物的存在最終得到展示)的一種表達,而事物本身則……是最終的基體”。海德格爾反對包括胡塞爾在內的對物和世界的上述素群主義理解,認為存在者之為存在者,向來就有因緣關聯。錘子所以為錘子,因其自身同錘打有緣;因錘打,又同修固有緣;因修固,又同防風避雨之所有緣。這種原始的因緣關聯形成源始的整體,“我們把這種含義的關聯整體稱為意蘊[Bedeutsamkeit]。它就是構成了世界的結構的東西,是構成了此在之為此在向來已在其中的所在的結構的東西。”不過,海德格爾不是從認識論的對象上,而是從世界結構上來理解這種因緣關聯的整體性,他反對傳統認識論的概念和思考方 式。
二、 如何認識對 象?
西方近代認識論用表象來表示主體對物的認識,認識被規定為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一種關系。這是傳統認識論的基本立場。按照這個立場,主體處于內部世界,要認識作為對象的客體,就得超越內部世界,就好比一個住在洞穴中的人,想要了解外部世界的某個對象,就必須鉆出洞穴,到外面去捕獵這個對象。由此便產生了一個引得無數哲學家探索的認識論難題:主體是如何從內部世界到達外部世界并認識對象的?康德在1772 年2 月21 日給M.赫茨(M. Herz)的一封信中明確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問我自己,我們稱為表象的東西和對象的關系,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的?”施密茨稱康德的這個設問是為近代認識論奠基,也是他后來“先天綜合判斷是如何可能”這一設問方式的首次基本表 述。
康德試圖通過先驗感性論和先驗分析論來回答這個問題。在施密茨看來,康德依靠先天直觀形式和范疇概念獲取知識的認識論,是“錯誤地把認識理解成一場自帶知識的旅行,不管這場旅行始于洞穴還是主體,認識都不需要從內而外的過渡”。實際上,康德認識論的對象,不是與主體無關的物自體,而是主體在認識過程中形成的。換言之,康德是試圖通過本體論與認識論統一的途徑來解決傳統哲學的認識論難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認識論是近代認識論向包括胡塞爾意向性理論在內的現代認識論轉變的樞紐。然而,在康德的認識論中,主體絕沒有超越自身通達外部世界認識物自體的能力:“如果我們把外部的對象當作物自體,那么就完全不能理解,我們是如何只通過我們內部的表象而獲得外部現實的知識的。因為……所有的自我意識傳達的就只是我們自己的判斷而已。”也正是主體能力自身的這種限制,在先驗辯證論階段,康德通過二律背反的論證,在經驗和物自體、現象和本質之間劃了一條鴻溝,回到了二元論的傳統,仍停留于近代認識論表象思維的基本立 場。
胡塞爾解決傳統哲學認識論難題的路徑和方法是意識的意向性理論。意向性理論涉及三個方面或層次。一是如何解決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的關系?在胡塞爾那里,意識是建構所有現實性意義的基礎,具有意向活動—意向相關物的一般結構。處于意識結構最底層的感知具有意向能力的意向行為,它構造作為表象的客體,完成意識的表象性客體行為。正是這種感知的客體性行為,使主體與對象內在地關聯起來。可見在胡塞爾那里,表象作為本體論意義的對象是意識建構起來的。他顯然是在意識范圍內解決傳統認識論難題的。二是主體如何達到對客體的整體認識?按胡塞爾的觀點,感知有內感知和外感知之分。在外感知和感知“對象”的關系中,包含著本真被感知之物和非本真被感知之物的區別。前者是“對象”當下被給予主體的內容或方面,這是原本意識;與此同時,該“對象”中沒有被當下給予主體的內容或方面,會以映射方式一起被給予主體,即主體通過“共現”(Appr?sentation)而獲得非本真被感知之物,這是非原本意識。共現意味著通過一個被經驗(被給予)的東西的聯結,設定(想象)一個未被經驗(被給予)的東西也是當下的。意識的超越性感知,必然并且始終是由當下被給予和共現共同組成的。原本意識和非原本意識這二者的共同進行,保證了意識對客體的整體認識。三是如何建立本己的自我意識與陌生的自我意識之間的聯系?這是胡塞爾交互主體性現象學討論的問題。這時,傳統的主客體關系問題被轉化為主體間的聯系與交往問題。對他人的感知是以“同感”(Einfühlung)方式進行的。同感也即對他人、陌生主體的感知。同感是怎樣在這種感知活動中起作用的?胡塞爾說,如果我感知一個事物,那么,我就同時也設定了這樣的可能性:我可以從這一個事物的感知過渡到其他事物的感知。同樣,如果我們感知一個被理解為意識之載體的身體,那么,我們就同時設定了這樣的可能性:可以從這個身體的感知過渡到陌生身體的感知,也就引發了對“陌生的自我意識”的設定,而“這種引發是以一種不易加以描述的‘同感’的方式進行的”。這個意義上的同感,實際上與共現同義。同感使主體間的聯系與交往成為可能,是胡塞爾交互主體性現象學的核心概 念。
歸結起來,胡塞爾解決傳統認識論難題和對他人、陌生主體的經驗問題,不是走傳統經驗主義或理性主義那種從自我/主體超越內部世界外部世界的事物和陌生主體的路徑,而是描述“他人以何種方式被給予”“陌生經驗是如何可能的”。按倪梁康轉述耿寧的說法,胡塞爾是從“原本性”的三個層次上描述他人、陌生經驗/主體的被給予方式的,這里不作詳述。根據意向性理論,自我與他我的“被給予”“被建構”處于普遍的相互作用的關系,交互主體性關系及世界經驗便是如此建立起來 的。
按照胡塞爾的觀點,作為意向活動的意識,是意向體驗的組合,人們所體驗到的一切,都是意識的構成物;“被給予”、共現、同感、想象等,也都屬于意識本身的結構與功能,都具有先驗性。意識的這些結構與功能,真的是先驗的或者說具有本質直觀的明證性,還是哲學家自己的“預設”?這個問題需要證明嗎?又何以證明?倘若果真是先驗的絕對存在,那么,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即使胡塞爾在解決傳統認識論難題時走的不是傳統經驗主義或理性主義的路徑,他最終能夠避開或解決傳統主體性哲學的認識論難題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也因此,海德格爾、梅洛—龐蒂離開胡塞爾的思考軌道,另外尋找解決這一難題的路徑。限于篇幅,這里簡略闡述海德格爾而不涉及梅洛—龐蒂在此問題上的有關觀 點。
海德格爾也從批判傳統認識論入手討論認識與真理問題。他指出,傳統認識論習以為常地把認識當作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主體是主要的一方,客體是外在的。于是就產生出這樣的問題來:主體是如何實現從其內部世界向外部世界超越的?人們在這樣討論認識問題時,往往只是滯留在認識的“入手處”,卻沒有進入認識的“源本”。從“源本”上考察認識,認識就是此在“在世的一種存在方式”。“操勞活動的尋視(Umsicht)、操持的顧視(Rücksicht)以及對存在本身——此在一向為這個存在如其所是地存在——的視(Sicht),這些都已被標明為此在存在的基本方式。”此在并不是被囚閉于內部世界中的主體/先驗自我,它本身就是按日常生活的樣式活動在世界中,是一向已經“在外”存在的,此在這種“在外存在”是真正意義上的“在內”。所以,在感知某某東西時,此在并不是要從它被囚閉于其中的內部世界范圍中“出去”,然后帶著贏獲的知覺轉回那個內在的意識的“密室”。此在整個認識活動中都是“作為此在而在外”。海德格爾就是循著這樣的思考,試圖從認識的“源本”上“消除”主體意識如何從其所在的內部世界通達外部對象這個傳統認識論的難 題。
海德格爾要找到一種比傳統認識論所強調的“看”“直觀”這種認知方式更原始的認知方式。而將認識奠基于此在在世存在的一種方式,就可以找到這個更原始的認知方式。所有的看、直觀,都植根于原始的領會——尋視(Umsicht)。尋視是如何原始地領會世內事物呢?海德格爾說,此在與世內上手事物打交道,在使用著上手事物時,就包含著尋視的尋問:“這個特定的上手事物是什么?對這個問題,尋視著加以解釋的回答是:它是為了作某某東西之用的。”此在這種尋視活動原始地把上手的東西某種東西,如桌子、門等等。這種“作為”含著屬于因緣整體的指引關聯,尋視著的領會是以因緣整體為背景揭示上手事物的。某種上手的東西何因何緣,這向來是由因緣整體性先行描繪出來的。嚴格地說,沒有用具這樣的東西存在,只有在用具整體中那件用具才能夠是它所是的東西。例如,鋼筆、墨水、紙張、桌子、窗、門,這些“物件”都不是首先獨自顯現出來的,然后作為單個實物塞滿一房間。所以,對世界的揭示,總是先整體,再個別。“因緣整體性‘早于’單個的用具。”“用具的整體性一向個別用具就被揭示了。”而尋視的這種“揭示/領會”正是通過原始的“作為”結構進行的,命題是把原始的“作為”結構明確化,也即把得到揭示的存在者傳達出來,命題傳達出來的存在者,就成了一個世內存在者,也即傳統認識論說的被認識的對象。如果被揭示的存在者與真實的存在者是同一個東西,那就意味達到了真理性認 識。
施密茨明確指出,從根本上說,胡塞爾的意識現象學沒有離開傳統主體性哲學的立場,也就談不上對傳統認識論難題的真正解決。在施密茨看來,傳統哲學所謂的心靈、心理,是一種虛構之物:“所有心理分析理論不可動搖的前提是,這些個體經歷和行為之‘源’應當如一場演奏會中的不同樂器,‘匯聚’于一個唯一的靈魂(心理)之中。然而在我看來,為每個人‘配置’這樣一個由他的種種思想、知覺、想象、情感、決斷、本能和追求等組成的‘聚寶盆’,這種直至康德依然持守的傳統看法,既沒有現象上的依據,也缺乏確鑿論證,根本不足采信。……類似的還有19世紀以來一些人習慣談論的意識、意識流之類的東西——他們不信任自然而然的經驗,欲以‘意識’取代變得令人懷疑的所謂靈魂”。所以,靈魂、心靈及其替代物,即德文Bewu?thsein、英文mind、法文conscience 表達的所謂“意識”,皆為多余,必須予以摒棄,代之以身體的被觸動狀態這種個人經驗之場域及其集中點,而情緒被觸動狀態是不能不意識到的屬于本己的東西,它們是人的本己現身情態,也即主觀事實。“主觀事實‘點燃’了主觀性,由此而使人產生意識并成為有意識的人。”因此,“有意識”“思想”并非某種以“心理”或“意識”為名的“設備”所具有的功能,而是身體被觸動狀態“呈現”的事態,“思”本身就是一種身體上發生的事件。
施密茨肯定海德格爾的觀點是一種試圖打破傳統認識論的內在世界教條魔咒的構想,但認為這種構想“太籠統了,甚至只是暗示性的”,需要加以具體化,必須揭示指向與存在者照面和所遭際的存在者之重要性的動機,要描述“尋視”究竟怎樣在與世內上手事物打交道中以因緣整體為背景“指引關聯”地揭示存在者的?對此,海德格爾沒有給出具體回答,因為他沒有從人(此在)與其身體被觸動狀態的關系中去解釋個體,忽視了身體性。由于忽視了身體性,也使他描述的原初時間變得沒有價值,因為時間與身體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而海德格爾“”
的說法,顯然意味著此在在與存在者世界的關系中,實際上充當了類似于胡塞爾意識主體的角色,表明了他最終還沒有徹底擺脫傳統哲學的立 場。
施密茨正是以身體為中介,描述了如何認識對象的三種途徑與方 式。
其一,通過身體動力學機制規定和感知主觀事實。前面說過,施密茨要恢復和確立的認識對象之一是身體感受也即主觀事實。關鍵是要找到一個范疇體系或他所說的身體性“字母表”(Alphabet)來描述主觀事實的基本特征,這些基本特征體現和標識身體現身情態,而身體現身情態的學說是新現象學身體理論的核心。這樣的范疇有三個:狹窄(Enge)、寬廣(Weite)、身體方向(leibliche Richtung)。“狹窄”與“寬廣”是身體現身情態最重要的維度,其真實含義只有在本己身體感受中才能領會。在狹窄與寬廣之間起居間協調作用的是身體方向,它由狹窄導向寬廣,但不能反過來從寬廣返回狹窄。通過狹窄、寬廣和方向三者不同方式的相互作用,就像由字母組合成單詞那樣,組合、重構著身體感受,即主觀事實,這是靜態角度的身體性,即身體靜力 學。
從身體靜力學衍生而來的身體動力學(leibliche Dynamik)更為重要,它實際上決定了身體性存在的命運。所謂身體動力學,也就是身體的狹窄與寬廣這兩個維度、傾向之間的競爭性“對話”。施密茨將處于動態的競爭關系中的狹窄稱為緊張(Spanung),將寬廣稱為膨脹(Schwellung),二者間競爭性對話的不同狀態,規定著不同的身體現身情態,形成不同的主觀事實。或者反過來說,不同的主觀事實、身體現身情態反映、表現著緊張與膨脹二者間的不同對話狀態。例如,正常的呼吸屬于二者力量大體平衡的狀況;喘息則典型地表現了二者的自節奏狀態,即一會兒緊張占上風,一會兒膨脹居主導;焦慮時,表明緊張居主導;當緊張和膨脹間“對話”的紐帶斷裂而彼此分離時,生機原動力也隨著消失了,例如,驚恐就是極度的私人狹窄/緊張的體驗,陶醉則是極度的私人寬廣/膨脹的體驗。還有另外一種特別的“對話”狀態,即緊張和膨脹兩種傾向牢牢地粘連在一起,彼此間不能再進行平衡的競爭性“對話”,這時,生機原動力實際上停滯了,例如饑渴就屬于這種狀態。狹窄/緊張和寬廣/膨脹的這種競爭性對話關系,也被稱為身體經濟學(leibliche ?konomie),它“構成仿佛如蒸汽那樣的生機原動力,一個人就像在蒸汽推動下運行的鍋爐”,“生機原動力以其敏感性和可變性構成了完美的生命狀態”。身體動力學機制描述的是身體與主觀事實的關系。一方面,它形成了人的本己身體性的存在及其特征,規定著本己的身體現身情態;另一方面,它又覺知作為對象的身體感受/主觀事實。這兩方面是同時的、當下的。于是,以身體為中介把作為對象的主觀事實的形成與對它的感受(認識)統一了起 來。
其二,通過感知情境和解釋情境中的事實獲取對象的認識。按照施密茨的觀點,對情境的感知不是分別感知其中的單個事態/事實、問題和計劃,因為在情境中,主體和客體、事態、問題和計劃,或多或少在混沌多樣的整體中交融共生,甚至根本不曾個別地顯露出來。這樣的情境不只是作為認識對象出現在主體面前,而且是將主體和客體動態地涵括于自身之內,引發身體上的運動反應,實現主客體的交互協同作用,也即身體的入身作用。通過入身作用,情境的整體性明顯呈現出來并為主體所感知,這時,情境中的單個事態、計劃和問題,隨著情境的整體呈現一同為主體所感知。例如,善于察言觀色的婦人就能看出回家的丈夫情緒有些激動,技術熟練的司機在突然遇到危險時,無需思索便能靈活地避免了一次交通事故,這便是入身的感知。婦人之所以能一眼看出丈夫有些激動的情緒,司機之所以能即刻感知這(危險的)情境并采取相應行動,是因為他們具有一種理智的知覺(das intelligente Wahrnehmen),這也就是在公元前5 世紀前荷馬、巴門尼德、恩培多克勒等希臘詩人與哲人那里所說的“νοε?ν”(直覺,一種特殊的知覺洞察力)。
情境中的事態/事實不是“自身被給予”認知主體的。在施密茨所說的情境中,事態/事實處于互相關聯而非單個存在的狀態,而“自身被給予”這些說法都只是對物的素群主義理解的空洞隱喻。情境中的事態/事實也不是依賴言語才得以成為人們認知的對象,而是在主體言說它們之前便已浮現于人的眼前。因何會有這種浮現?在這里,格式塔心理學的凸顯(Abhebung)概念提供了關鍵的指引。例如,在視覺領域,形狀從背景中凸顯出來;在聽覺領域,音樂中最高音聲部從旋律中凸顯出來;在思想發展過程中,主題從主題域中凸顯出來,主題域從無關的背景中凸顯出來。人們要問:事態/事實又是如何從其實際現身的作為背景的現實(情境)中凸顯出來呢?施密茨說,一方面,事態/事實的凸顯并不是由這個作為背景的現實決定的,而是通過對情境中的事態/事實進行解釋而實現的。這種解釋好比農夫的收獲,既關乎農田,情境就好比農田;又關乎果實,即獲得對這些事態/事實的認識。這種認識的獲得應該有解釋/認識的技巧。所謂解釋/認識的技巧也就是處理解釋者和事態/事實之間的關系,其中主要的是分析性的解釋/認識技巧,它是對重要事態最大化的解釋和對個別事態進行關聯、排序的技巧,讓它們浮現、凸顯出來,使主體可以言說,從而獲得關于它們的認識。這就是施密茨所謂“認識論的解釋論”所關涉的認識途徑和方法。另一方面,盡管作為背景的現實(情境)并不決定事態/事實的凸顯,但是隨著情境的整體凸顯、呈現并為主體所感知的同時,情境中的事態/事實也必然同時為主體所感知,換言之,它們的凸顯具一種明證性。“不管是通過解決問題的方式,還是以無所可問的明證性的方式 ,相關事實都從這個‘事態之暈圈’中凸顯出來。”
其三,通過身體交流解決主體與他者的關系。所謂主體與他者的關系,包括主體對物特性的認知和交互主體性的關系。西方哲學長期以來在如何解決這個關系問題上有過無數探索,但由于身心二元論的思維,一直沒有找到有說服力的答案。施密茨試圖以身體交流(leibliche Kommunikation)理論來解決這個問 題。
先說如何通過身體交流獲得對物特性的認知。斯賓諾莎說,物質有無數的特性,人們只知道其中某些特性,其他的特性都隱藏于它們的背后。康德認為,只有在與主體(先天直觀形式和范疇)相關聯的條件下,才能獲得關于物的經驗知識,而物自體或物的本質則在經驗領域之外。康德這種建立在主體與對象相關聯基礎上的認識論,到了胡塞爾那里,發展成一種系統的關聯性思維方式。施密茨認同這種關聯性思維方式,即“只有與我們自身相關,我們才能刻畫物的特性”。不過,在他看來,這種“相關”,并非主體與對象(物)的關系,而是身體與作為身體交流“伙伴”的物的關系。當身體與物構成交流的伙伴關系時,人就能獲得對物(的特性)的認知,這種伙伴關系的缺失則導致對物(的特性)認知的缺失。他引用心理學家克萊恩特(Kleint)的轉椅實驗來說明這個觀點:坐在轉椅上的受試者,在蒙著眼睛不知情的情況下快速旋轉,停下轉椅,“他在重新睜開眼睛的瞬間會感到十分驚訝。通常情況下,起初眼前的所有物體都變得非常混亂和分散,讓人感覺如夢初醒。眼前的空間布局顯得十分陌生,不真實,不真切,如同舞臺布景一般,有時候會有混亂的印象,如同與物和對象無關的沒有輪廓的色彩雜燴,所見物之間沒有太多距離,更像是連成一體的。過了一會,才恢復了符合正常物之特性的正常定位”。這個實驗告訴我們:蒙著眼睛和轉椅的快速旋轉導致了身體與物之間交流的缺失,從而感官喪失了對物(的特性)的融合和組織力量,直到重新建立起身體與物之間的交流,才恢復了對物(的特性)的正常感 知。
再說如何通過身體交流解決交互主體性的問題。胡塞爾提出“交互主體性”問題,并對解決此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解決這一傳統哲學難題的研究中具有經典性意義。可是他為解決這個問題設定的出發點仍然是先驗意識。這又使問題回到了原點:一個先驗的主體意識如何超越自身而與他者或另一個主體建立聯系,從而排除唯我論?施密茨認為,一般通過如下兩個途 徑。
一是通過身體性對話的傳遞。前面說過,身體的現身情態就是狹窄/緊張與寬廣/膨脹的身體對話。一旦身體被觸動,便會出現這種對話狀態。通常有兩種原因會引起身體被觸動:一是他物/他者。比如,我們身體上可以毫無遮蔽地感知到天氣,天氣作為某種他者的東西,向我們的身體涌來,把捉、觸動著人,使人處于情緒被觸動的狀態。我們就是以這種方式體驗著他者的存在,勾連起與他者的關系。施密茨稱這種情形為在“反轉性知覺”(Wahrnehmeung mit verkehrten Fronten)中體驗他者存在。二是身體性對話被傳遞到對話伙伴身上。這種傳遞,有時通過軀體直接接觸的方式實現,最典型的例子是摔跤;有時不需要軀體上的接觸,例如兩人對視時的“目光交流”。人的目光對動物也有相似的作用。
二是通過身體交流。無論是軀體直接接觸或非直接接觸,身體性對話傳遞到對話伙伴身上便自發形成了主體與他者或另一個主體的準身體的一體性(quasileiblicher Einheiten)情境,這便構成身體交流。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的身體交流是入身(Einleibung)。入身的基本特征是主體在準身體的一體性情境中,能夠通過自然的迅捷的協調行為應對面臨的各種情形。人們正是在這個入身的過程中,與他人打交道,發現同伴,有了“他人之明證性”的意識。入身的形式多種多樣。最普遍的形式是交互式入身,如:相互注視、握手、交談,表情的暗示與吸引、雙人鋸木,等等。人與動物或無生命物體也可以有交互式入身行為,如賽馬過程中騎手與馬在相互激發中沖刺最后的目標,賽車手在人與車的相互激發達到運動的極致。還有單向式入身,如演講者的演講吸引了全場聽眾,臺上魔術師的表演吸引了觀眾等。歌曲、器樂、拍手、叫喊等一切有節奏的聲音,都能引起入身行為。此外還有“共舉性入身”(solidarische Einleibung),如劃艇、合唱等。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身體交流中,主體(的身體/軀體)如何能夠與他者或另一個主體發生“自發的”協調、協作?施密茨認為,這源于主體自身的身體被觸動狀態,所謂意識也即是這種身體的被觸動狀態。顯然,這依然涉及意識的存在狀態及其本質這個意識論、認識論中難以回避的問 題。
三、 如何確信所獲得的認識
這個問題休謨已經提出來了:“我們很可以問,?但是如果問,?那卻是徒然的。那是我們在自己一切推理中所必須假設的一點。”在休謨那里,這個假設指的是自然信念,同時又是將這種信念與推理本性相連接的某種形式的必然性,或稱先驗必然 性。
黑格爾將知識理解為關于一個對象的意識。圖根哈特在批評這一理解時提出了他自己關于知識特征的理解:不是每種與一個對象的意識關系都是一種知識,知識是那種認之為真的與一個對象的意向關系;知識獲得者對它的真(實性)確信不疑;不僅確信它是真的,而且能理性地給予論證。圖根哈特確信知識需要也能夠從理性上加以論證的主張,顯然不同于休謨只需假設某種先驗必然性的觀 點。
施密茨指出,圖根哈特將知識理解為對于真實斷言之真理性的確信,這顯然是準確的,可是第三個特征卻疑竇重重:要創立一種能夠理性證實知識的普遍認識論并不現實,因為論證知識有效性并非易事,也沒有統一不變的標準。近代歐洲主體性哲學對知識有效性論證的結果,可以作為施密茨這一觀點的佐 證。
我們知道,笛卡爾把認識論的提問方式從古代哲學追問“世界是什么”轉向了“你怎么知道世界是什么”,由此而將哲學探索從外在世界轉到主觀領域,創建了主體性哲學的理論形態。主體性哲學的根本特征是在理性中尋求哲學的最終基礎和知識的確定性,把主觀性和確定性并列。因此,黑格爾說,自笛卡爾以來哲學轉入了確定性的領域。按照主體性哲學,只有主觀意識、理性思維才是自明的確定的。笛卡爾明確將主體(我,自我)與思維等同起來:“嚴格地說來我只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也就是說,一個精神、一個理智、或者一個理性。”他認為人們通過反思自我意識就可清晰明白地顯現的觀念知識,如幾何和邏輯公理,具有必然的確定性,而來自外部經驗世界的觀念和心靈想象虛構的觀念,都是不確定不可靠的,必須予以清除和否定。這種以意識的自明性論證知識有效性確定性的觀點,經康德和胡塞爾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 展。
康德的先天綜合判斷提供了證明或衡量科學知識的標準,他的批判哲學就是以先天綜合判斷為中心﹐從純粹理性﹑實踐理性和判斷力三方面展開討論。《純粹理性批判》探討的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之可能,《實踐理性批判》討論的道德意志先天法則的客觀有效性,《判斷力批判》闡述的情感判斷的普遍必然性,都是以先天綜合判斷為依據的。在先天綜合判斷中,康德強調具有先天自明性的思維形式對感覺經驗的綜合作用,沒有這種自明性,感覺經驗就不可能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確定的知識。施密茨指出,康德提出的先天綜合判斷為解決經驗論和理性論的片面性和構建確實可靠的知識“立下了巨大功勞”,“強調先天綜合判斷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斷言,這種定義上的界限劃分是康德的一大貢獻”。但他同時對此提出三點質疑:一是康德提出先天綜合判斷時沒有提到證實其普遍必然性的特殊情形。實際上,有些符合思維自明性的公理、原理,并不一定是從先天綜合判斷導出的;有些判斷、命題,被先驗地認定為真理,但當人們可以輕易復制它們時,其真理性便受到了動搖。比如,平行公理、空間的三維性等這些被萊布尼茨認為是顛撲不破真理的幾何定律,以及很容易通過先天綜合判斷得出的排中律、時間的無限性等,會漸漸消逝,因為諸如此類需要我們(而且我們也有能力)根據康德意義上的分析判斷的公理,對于皮亞諾公理而言,只需要通常用來計數和計算的(自然)數字就足夠了。二是并非只是先天綜合判斷才有明證性。還有可以通過觀察、感性直觀獲得的(后驗)判斷的明證性,例如,當一個人盯著一張剛被他用黑色墨水寫過的白紙,明證性讓其確信,這張紙上的白色和黑色是不同的。這個例子顯示,并不是每一個明證性都需要與一個先天(判斷)形式緊密相連,(后驗)判斷的明證性是很容易實現的。而與通過后天感性經驗獲得的明證性相比,先天判斷形式反而具有劣勢,它的“說服力比較僵硬,因為它們至少不能被驗證,所以更加可疑”。再說,那些看起來無可爭議的先天判斷,出現明證性假象的例子卻比比皆是。例如,按照形式邏輯,“無物存在”的假定必然導致邏輯矛盾。然而,將“非存在”判給對象,實際上并無邏輯矛盾,因此,“無物存在”在邏輯上是可能的。三是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實現?按照康德的思想,先天綜合判斷既包含(后驗)判斷即經驗,又具有必然性確定性的明證性,那么,它是如何實現呢?在康德的先驗分析理論中,只有虛妄抽象的自身被給予和直觀性。但是,這并沒有給先天綜合判斷的明證性提供合法性。
胡塞爾用“明證性”(Evidenz)來證明意識的意向行為所構建的知識具有普遍必然性和確定性。明證性是胡塞爾現象學的中心概念之一,它的基本含義不同于心理主義感覺論所說的感覺上的清楚明白,也不包含證明、論證的意思,而是指意識對意向對象的當下擁有。一方面,意向性以與其豐富多樣的意向相關項相符的多重方式,在先地指明了“明證性”;另一方面,意向性在其所有變化形式中都預設了與這些形式相符的當下擁有的種類,所以,意向性又返回地指明了“明證性”。顯然,胡塞爾的明證性是意向性所具有的“普遍凸現的形態”,“明證的判斷是原本的被給予性的意識”,意識相關項自身給予意識的各種方式,都只是明證性的各種復雜樣式而已。靜態的和發生的現象學分析的任務,就在于回答明證性認識是如何得以可能 的。
施密茨指出:胡塞爾雖然沒有陷入非理性的片面,卻依然處于理性主義和先驗主義傳統的懷抱之中。他主張哲學思維要批判地反思認識的可能性問題,這是回到康德認識論的起點;他認為思維必須將某個東西設定為明白確定的前提,這又是吸取了笛卡爾的思路。他反對在認識中預先設定存在,但又必須承認有絕對被給予的存在,他“把明證性理解成所指對象的自身被給予性,結果,他用明證性判斷對象X 時總是強調,X 必須自身被給予”。在胡塞爾那里,是什么在向人們保證這種事物的被給予性?是思維的明證性即本質直觀。施密茨進而指出,這種本質直觀,對象自身的被給予性,無非是指在判斷對象時,對象明白無誤地呈現在判斷者的意識中,是判斷者所熟悉的,而“所熟悉”的恰恰要通過判斷獲得,可見,胡塞爾企圖借助于無可爭辯的明證性進行先驗的本質直觀達到對事物的確定性認識,是缺乏根據并難以成功的。不僅如此,胡塞爾在要求把一切假設都懸置起來時,唯獨不把意識的存在這一假設懸置起來,實際上一開始就作出了純粹意識及其活動存在的預設,從而與其他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家殊途同歸,使理性和非理性(感受)的“分裂達到頂峰”。
在主體性哲學家看來,客觀性、確定性也就是普遍性必然性,普遍性必然性與意識的內在明證性密切相關。對胡塞爾來說,唯一的確定性是意識自身的確定性,唯一的普遍性必然性是觀念的本質的普遍性必然性。對于這種以意識的明證性論證知識有效性的觀點,阿佩爾曾批評道:“在笛卡爾,康德甚至胡塞爾意義上的意識明證性,不足以論證知識有效性的基礎,這一事實已經獲得了證實。”同樣,先天綜合判斷是建立在依據個人直覺明證性之上的,“它還不足以對歐幾里得幾何學和色彩陳述的作出基礎論證”。
本文第二部分指出過,海德格爾反對傳統認識論把認識看作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試圖打破內在世界教條的魔咒,從存在論上考察認識。同樣,他反對主體性哲學從意識的明證性論證知識的有效性、認識的真理性,也從存在論出發回答“如何確信所獲得的認識”,證明認識的真理性問 題。
傳統真理觀把真理標畫為命題、判斷與其對象相符合。海德格爾說,符合這個術語究竟是指什么?一切符合都是關系,但并非一切關系都是符合,例如一個符號指向被指的東西,這種指是一種關系,但不是符號與被指東西的符合。也有相同東西的符合,如6 與16 減10 相符合。傳統真理觀所說的“知”和“物”的符合指的顯然不是相同東西的符合。那么,是指它們相似?哪方面相似?如何證明這種符合或相似?實際上,符合論或相似論所說的“知”是一種命題、判斷,“物”則是命題所揭示的對象,換言之,要證明的是命題和命題所揭示的對象間的符合或相似。或者,從意識的明證性來證明?正如阿佩爾所說,這種主體性哲學的證明方法是無效的;或者,以命題、判斷的真假來證明?但是,“就判斷而言,必須把判斷活動這種的心理過程和判斷之所云這種內容加以區分”,這樣,就還必須證明究竟是判斷活動還是判斷內容與對象(物)的符合或相似。若是后者的符合或相似,還得弄清楚,這種符合或相似究竟是實在的還是觀念上的,抑或既非實在又非觀念的?兩千多年來這個問題不曾有分毫進展,反而變得這么復雜和混亂,肯定是哪里出了問題了。海德格爾認為,問題就出在傳統認識論從主客體關系展開問題的討論,出在把命題、判斷與所揭示對象的符合或相似當作真理的原始所在。因此要重新解釋“認識本身的存在方式”,要發現真理的原始所在。在展開主客體關系的認識活動之前,有一個“把存在者從晦蔽狀態中取出來而讓人在其無蔽(揭示狀態)中來看”的“去蔽”活動。“去蔽”使存在者進入主客體的認識論關系,也派生出命題、判斷的意義,因此,它既為主客體關系的認識活動奠基,也是真理的原始所在。所以,要證明認識的真理性,不是去證明命題、判斷與其所揭示對象的符合或相似,而是去證明命題、判斷揭示的就是存在者本身。例如,設想一個人背對墻說出一個命題:“墻上的像掛平了。”說出這個命題的人轉過身來看見了平掛在墻上的像,這時他的知覺證明了這個命題。“知覺”證明了這個“命題”的什么呢?證明了:“命題中曾指的東西,即存在者本身。……命題之所云,即存在者本身,顯示出來。”之所以能夠依據存在者的顯示進行證明,是因為:“道出命題并且自我證實著的認識活動就其存在論意義而言乃是實在的存在者本身的存在。”這就是認識本身的存在方式。所以,說某個命題是真的,意味著:它就存在者本身揭示存在者,在對存在者的揭示中展示存在者,讓人看見存在者。這就是作為真理的原始所在。顯然,(原始的)真理根本沒有傳統真理觀所說的那種認識和對象之間相符合的結 構。
施密茨認同海德格爾的上述觀點,指出他的生存論分析提出了此在的“在世存在”模式,促進了主體性哲學的終結;他強調世內存在者的存在與顯示依賴于整體意蘊的指引關聯,為新現象學情境存在論的提出作了準備。這是生存論分析的巨大成果。但是,生存論分析同樣存在明顯的問題。其一,沒有說明此在究竟如何“遭遇”指引其可能性的(其他)存在者,致使此在對(別的)在世存在者的去蔽失去了實際的指引關聯;其二,在《存在與時間》之前,尤其在1919 年至1920 年冬所作的幾個報告中,海德格爾認為此在具有“向來我屬性”,此在所遭遇、糾纏的實際生活經驗便是此在的世界,即是說,此在由主觀事實構成,這樣的此在,是具體主體。但生存論分析把向著世界的沉淪和自身的瓦解作為此在在世生活的基本傾向,此在的“向來我屬性”即主觀事實由此而失去并被客觀化了,這時,原先那個作為具體主體的此在,成了隱退型異化的主體,即被剝離了主觀事實的沒有規定性的形式存在,此在的實際生活也便只是“嬉游于虛空之中”。其三,關鍵的問題還在于:此在的展開、籌劃、去蔽以及全部在世內的存在,都沒有基礎性的要素——身體。按新現象學的理論,在揭示和證實人的現身情態即人的本己感受和與他者的關系中,身體才是關鍵和基 礎。
那么,對于“如何確信所獲得的認識”即如何證明認識的真理性這個認識論的重要問題,施密茨的新現象學又是持什么樣的觀點 呢?
首先,明證性所證實的主要是事態的事實性而不是真理。胡塞爾斷言:“明證性無非就是對真理的‘體驗’而已。”施密茨指出,這并不完全正確。因為,人們在面對有關事態的信息時,首先感興趣和想要弄清楚的是這些信息中哪些事態是事實?只有在被告知所面對的有關事態的信息都是事實時,才會在明證性中首先想要弄清哪個(被告知的)事實才是真相/真理。需要指出的是,施密茨區分了事實性與真實性。他認為,有許多事態,不是事實,卻是真實的。例如,任何目標都是有目標內容的,任何希望也都是有希望內容的,目標內容和希望內容對相應的目標和希望而言,是真實的,但并不是事實。又如,“無物存在”這個斷言,本身也是一個事態,就其不存在邏輯矛盾而言,它是真實的,但并非事實。因此,“不是每一個明證性都需要與一個正確或錯誤的斷言緊密相連。在明證性中,真相(真理)是次要的事情,最主要的是事態的事實性”。
其次,如何確信所獲得的認識是與事實相符,即具有事實性?生活中,事實性的所在就是明證性。在明證性中,人們一定把事態當作事實,這是因為,“明證性是具有能夠將事態標識為事實的現實權威的帶有確信的責成性強制”。這里的所謂權威是這樣一種力量,它責成主體服從具有約束力的計劃。那么問題來了:在明證性中主體的這種“服從”是如何體現呢?施密茨說,這種“服從”不是主體對事實性的“確信”,而是事實性向主體索取的“同意”即確信,主體對事實性不能或至少不能不受約束地直接逃避。這樣就有了進一步的問題:“同意”的究竟是什么?不可能是對明顯地呈現出來的事實(以T 表示)的“同意”,因為這樣的“同意”意味著:這個同意T 的人,至少承認T 是一個事實(T*表示);而要承認T*,又必須承認T*和T 一樣是一個事實,這樣又得承認T**,如此便陷入了循環論證。所以,事實性向被觸動者(主體)索要的“同意”不可能是對明顯呈現出來的事實之同意,因為被觸動者與(觸動他的)事態/對象建立關系,并不取決于事態/對象是否(作為事實)單個呈現出來,而是對事態/對象的一種“有意識”的同意。這種“有意識的”同意具有雙重結構:作為由于被觸動而有意識的感受者,他是被動的接受性的,接受明證性中所凸顯的事態/對象的降臨,這種降臨具有權威性;但作為感受者,他同時又持有讓自己去感受即讓自己與事態/對象交往的態度,這表明其被觸動又具有主動的意味。這種狀態,就是事態/對象通過其在明證性中凸顯的權威而向被觸動者要求的東西,即被觸動者以確信的方式承認或認為自己就是被事態/對象的事實性所觸動的人,并確信自己由此而擁有了一種相應的主觀事實,這種主觀事實在明證性中一定以(服從事態/對象降臨的)權威性的方式存在。這便是施密茨的明證性所體現的“帶有確信的責成性強制”。
對于認識論上“確信”問題的回答,施密茨顯然不同于包括胡塞爾在內的傳統主體性哲學。他以(被觸動的)身體為基礎和中介,將真理概念置于(事態的)事實性基礎上,強調真理是對事實性的直接斷言:斷言所描述之物就是被證實為事實的事態,如此而已,這叫。在這個意義上,相對真理的命題就變成:一個事態不總是,也并非對所有人都是事實,一個事態在此刻和彼時,對一個人和另一個人而言有時具有事實性,有時卻不然。傳統主體性哲學忽略事態/對象的事實性的權威,關注對象的自身被給予性,強調真理是所描述之物和描述它的語言所陳述的內容之間的符合,這叫。
四、 結語
至此,也許可以對本文討論的問題說幾句結論性的話了。認識論問題屬于哲學的根本問題之一,任何哲學流派和形態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貫穿于以往哲學發展的全過程,也仍將在未來哲學的道路上延續;它是開啟性、開放性的,在探討和論辯中不斷發展深化,關于認識論的探討和論辯不會終結。認識論總是與哲學流派和形態及其相應的思維范式息息相關,屬于不同哲學流派和形態的哲學家,必然會有不同的認識論觀點;不同的認識論觀點匯聚成的思想河流,奔流向前,其中只有前浪與后浪、繼承與超越之類的關系,不宜絕對區分誰對誰錯,更不可隨意判定哪個進步哪個反動。認識論必然涉及意識問題。意識具有先天的結構與功能嗎?意識是作為內在世界獨立于身體/軀體的存在嗎?關于意識的本質及其存在方式,歷來是哲學討論的中心話題之一,也是神經科學和腦科學的重要研究領域。盡管對意識的科學研究不斷取得新成果,對意識的哲學思考在不懈進行,但解開意識之謎的道路依然漫長而遙遠。僅就以往的認識論探討而言,這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如何理解意識,決定了哲學家會提出什么樣的認識理論,也決定著我們如何評價有關哲學家的認識理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