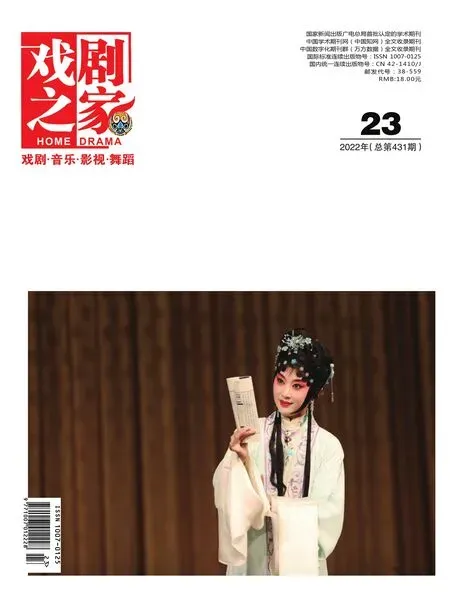朱載堉樂舞理論對舞蹈教育的當代價值
李曉楠
(山東藝術學院 山東 濟南 250300)
在我國古代社會中,有一位“讓國高風”的聞名藝術家,他就是被當時的人們稱為“布衣王子”的端清世子——朱載旸。他自幼受到父親朱厚烷的影響,對音樂、數學有極高的興趣,且聰明好學,畢生致力于研究學術,并撰寫了大量著作。作為一代文化巨人,他不僅開拓了近代科學的先河,而且在音樂和舞蹈理論等藝術領域的研究也造詣頗深。朱載旸最偉大的成就,是在律學史上創建了十二平均律,為中國乃至世界音樂藝術所作的貢獻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他的著名代表著作《樂律全書》中涉及的內容包羅萬象。他精通天文歷法、數學珠算、音律樂譜以及舞譜和繪畫等。在他的14 部書中,有關于舞蹈的內容在其中占據了一定的比重,分別有《小舞鄉樂譜》(不分卷)、《六代小舞譜》(不分卷)、《靈星小舞譜》(不分卷)、《二佾綴兆圖》(不分卷)。此外,在《律呂精義·外篇》中朱載旸系統地論述了和舞蹈理論相關的研究成果。而在《論舞學不可廢》中,朱載旸又首次提出了“舞學”一詞,他認為,應該把傳統的舞蹈從古“樂”中分離出來,獨自成立一門新的藝術學科,并加以系統地研究論述。可見,朱載旸在舞蹈藝術方面的成就為中國舞蹈界開創了歷史之先河,并且成了中國舞蹈理論研究的先行者之一。
一、朱載堉的“舞學”新解
朱載旸創建的“舞學”理論,有著完整的構想大綱和嚴格意義上的理論支撐。他對“舞學”思想所應研究的具體內容劃分為十個方面,稱為“舞學十議”:一、舞蹈學校;二、舞人;三、舞名;四、舞器;五、舞佾;六、舞表;七、舞聲;八、舞容;九、舞衣;十、舞譜。朱載旸十項問題概述的研究范圍覆蓋廣闊,對每一方面都進行了針對性的評論和解說。
朱載旸樂舞理論批判地繼承和吸收了儒家正統的樂舞思想觀,他沒有盲目地沿用古代“樂”“舞”一體的空泛之說,而是在深受儒家樂舞思想影響的基礎上,對樂、舞之關系進行辯證地論述。他認同禮樂同政治相連,在社會中的地位及政治作用都極其重要。朱載旸將我國古代傳統的樂舞體系與自己對舞蹈的獨特創見相融,形成了一套新的具備科學化、系統化的舞蹈教學理論。所以,他的理論是按照“先引古制,后附新說”的方法來建立的研究體系,有承有創。在當時純舞蹈逐漸衰落的藝術大背景下,朱載旸對舞蹈的起源、分類、藝術特性、社會作用等等論述的內容進行精辟地論證和總結。這類成熟的見解,使得舞蹈有了新的定義,對舞蹈藝術今后的發展定位奠定了基礎。例如,他在《論舞學不可廢》這篇著作中提到的:“蓋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足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而在儒家的《樂記·樂本》篇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朱載旸的樂舞思想相承于儒家的正統觀念,閱之而述:在我們的日常活動中,外在的客觀現象由于觸動人內心產生了一種情感,人們為了充分表達這份感動之情,不覺而動,隨之產生的自然行為稱為舞蹈。朱載旸的理論固然與儒家正統思想下的樂舞觀有相似之處,在此基礎上,他又在另一層面發展創新并表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同舞蹈起源于外界事物對我們的影響、起源于多元未知的生活環境,同時他還認為,舞蹈藝術會根據不同生活環境下人群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舞蹈樣貌和藝術風格。其次,他十分重視舞蹈對治國安邦穩定社會的政治作用,積極強調樂舞對人的教化作用。可見,從歷史的維度來審視當時的文化語境,朱載旸的“舞學”思想放之藝術行列之中已極具時代先進性。
二、朱載堉樂舞教育的先進功能
啟于明代強烈的專政統治特權,朱載旸從多種層面引發了對舞蹈理論、舞蹈教育、舞蹈表演等藝術形式的思考,他的“舞學”便著重強調舞蹈作為一門從“樂”中劃分出來的“新興”藝術所應發揮的重要作用。
(一)“身”“心”兼備
舞蹈是一門身體行為藝術,由人外在的“形”(肢體語言)來表現內在的“情”(心靈和情感)。朱載旸在《樂律全書》的“舞學”思想中就體現著“身心觀念”的指導原則。他認為傳統的古樂舞可以“以之治己”又可“以之事人”,舞蹈可以作為一種純粹的藝術來修身養性,人們通過習舞“修身”“修心”,從而達到陶冶情操、修身養性的目的,幫助人們提高完善道德修養,實現舞蹈對人的教化作用,這也就說明了舞蹈對于人體本身的發展和身心健康的培養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作用。不僅如此,朱載旸還將古代樂舞分為文舞和武舞兩大類,分別對應不同的季節變化來學習,以便順應自然之規律。他在舞學中強調,身體的律動應該在人體接受最大范圍內遵循自然的運動規律,舒而緩,保持適度的身體狀態,才能“身”“心”兼并。現代學者對此也有相同觀點:“舞蹈作為一種高級的運動狀態,雖以身體形態為表達方式,但它的前提、過程、效果、境界恰恰是由人內部而來的并高度性的被心理控制和制約。”朱載旸站在“天人合一”的角度,將舞蹈置于宇宙的宏觀審視下,強調舞蹈在自然萬物中和諧發展的運動規律,體現了一種生命力的傳承和延續,它的發展符合時代的規律,且具有永恒的藝術特性。
(二)“德”“育”雙行
古代的禮樂體制中,以“舞”來強化“育”是十分顯著的。“內外兼修、形神兼備”是舞蹈育人的最終目標。古代社會極為重視樂舞的教育,起于儒家思想的陶染,朱載旸的樂舞理論中同樣強調樂舞對培養人類優良品質的美育作用。禮樂之教在使一個人達到德行標準的基礎上,施以美的教育,有助于其審美內涵的提高。“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良好的文化素養是體現一個人“德”育的最有力的支撐。舞蹈不僅要求形體美還要求內在美,人們通過習舞,可以逐漸完善一個人的道德品格,可以從中學習儒雅、隨和、謙遜,以禮待人的處世態度,只有內心的不斷豐盈,才能協調身心的全面發展。
三、朱載堉舞蹈教育理論的當代價值體現
自人類文明誕生起,舞蹈就成了人類最早創造的藝術形式之一,她穿越了萬古千秋,仍然以一種生生不息的姿態生長,發展至今。在當代,舞蹈作為一個民族文化象征的符號已經成為大眾用來消遣娛樂的藝術形式之一,她豐富的形式內容承載的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內涵和文化底蘊。她可以無限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陶冶人們的藝術情趣,表達人們的思想感情。這種綜合的發展藝術在眾多藝術門類中其位置已無可取代。
回溯古今,舞蹈教育從萌芽形成到成熟發展再到完善制度,其體系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從娛人、娛己到育人、育己的發展流變,時代賦予了她生命可以不斷延續的先進的思想性和功能性,使其具備了理論與實踐雙標的作用條件。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就倡導“有教無類”的教學理念,提倡教育不分貧富貴賤。到了明朝,朱載旸也指出:“古人自天子至于庶人,無有不能舞者”。作為貴族身份的他提出這樣的思想理念,其意識思維是極為敏銳的,人人都有享受平等教育的權利,這是不為貧富、階級權利所束縛的,此觀點不具有偏頗性。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封建社會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思想家們所表露的“以禮救世”的態度,正是趨于對自身的價值觀念有著正確的定位。朱載旸的教育觀中還提出習舞者需品行端正、身心兼備,與志同道合的人集體而舞不受外界干擾,強調學習舞蹈應該專心致志。他編制的擬古舞譜具備完整的舞蹈隊形場記、舞姿動作變化等,內容豐富翔實、清晰明了,甚至于今,我們仍可以依照“舞圖”來編排,其準確性及精密度令人咋舌。朱載旸所形成的舞蹈教育理論體系放于幾百年后的今天,仍與我們現代素質教育的觀念有許多相似之處,有些結論也不謀而合,盡管在當時特殊的時代下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他對于樂舞的認識和體悟已經是超越時代的了。
在中國古代階級社會中,舞蹈教育作為社會教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育人、育才的積極作用,古人的教育思想、實踐內容、行為方式等也都緊跟時代的更迭,完成蛻變使之越來越完善。而在現代教育中,舞蹈教育的價值和理念也逐漸成為舞蹈學科建設的風向標,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領著她的前進方向。舞蹈教育在我國尤未普及。近年來,舞蹈教育備受社會關注,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舞蹈教學的培養原則、舞蹈教育的受教育平等度以及舞蹈教育的完善標準等都是社會對舞蹈教育多元化的需求體現。新時代的舞蹈教育在培養我們對于美的認知、體驗、感知的過程的同時應該兼具以文化育人的目標,培育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舞蹈人才。對中國舞蹈的發展而言,理論的修正既是批判的也是繼承的,使其不斷注入新鮮的血液,具有時代的審美風尚則是舞蹈藝術在社會文化中不斷前進的活力源泉。
四、結語
明代朱載旸創建的“舞學”教育思想體系所蘊含的人文觀、家國觀、世界觀、宇宙觀等一系列的形而上的中國古代哲學范疇內的價值觀念,對今天舞蹈學者研究史學、美學等基本理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他對舞蹈教育理論的全面認識、細致整理及不斷考據,為中國古代乃至今后的舞蹈學術體系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研究空間和深層的理論價值,其中,所蘊含的多層哲理仍需我們后輩不斷地挖掘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