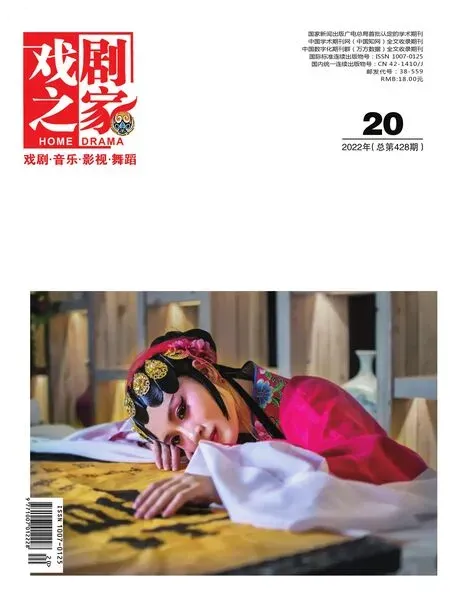嶺南海絲文化的推廣與傳播
——以世界級非遺廣東粵劇為例
李燕霞,曾衍文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 旅游商務學院,廣東 廣州 511483)
粵劇是海內外粵地僑胞們文化同源、民心相通和人緣相親的藝術載體,承載著他們的婉婉鄉情、悠悠鄉韻和綿綿鄉愁。客居海外的華人華僑最具鄉土意識和尋根情結,嶺南文化瑰寶——粵劇也因此成為眾多華裔互致親情、遙寄相思的獨特文化載體與情感寄托。以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和廣泛國際影響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傳承保護為切入點,如以粵劇藝術的情感語言促進海內外僑胞、華裔在文化相通、文明交流互鑒中尋求更多共識,不僅能夠促進彼此間的情感相連、民心相通,也有助于提升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增強民族文化自信。
一、廣州海絲時期嶺南粵劇藝術的海內外傳承與傳播
粵劇,又稱“廣東大戲”,是以唱念做打、樂師配樂、戲臺服飾及抽象形體等表演藝術演繹當時嶺南地區勞動人民生活場景的地方戲劇。粵劇廣泛吸納外來劇種、中外唱腔甚至外國文藝形成自己的風格,比國劇——京劇更早走向世界,歸因于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廣州擁有優越的地理環境和悠久的對外貿易。早在兩千多年前,廣州便開放埠口,開放貿易,通過海上貿易與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和地中海沿岸地區互通往來,成為最早親密接觸西方文化的港口城市。中外文明在此互通交流,匯聚積淀,賦予廣州“兼容并包,開拓創新”的文化基因,也直接影響了粵劇藝術與海外文明的對話交流,促進了戲劇文化的海內外傳承與傳播。筆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追蹤中國完全對外開放前,嶺南粵劇在兩廣、港澳地區的流傳印記以及粵劇隨著廣府移民的活動軌跡向海外東南亞、北美的傳播軌跡,探尋粵劇如何以“互通鄉音,聯結性情”的藝術特性融入西方的主流文化。基于史料研究,粵劇藝術的海外傳播大致經歷三個階段:
(一)清朝時期的萌芽生根階段
清朝道光、咸豐年間(19 世紀40-60 年代),粵劇第一次走出國門,在海外“開疆拓土”。中外貿易在廣州頻繁交流,滋生了販賣中國勞工的黑暗交易,人口販子以“看戲”“演戲”為餌誘騙嶺南地區社會底層人民,如農夫、漁民等去北美洲及東南亞等地從事采礦、修路這類苦力勞動,其中不乏粵劇藝人被騙。彼時,來自家鄉的戲曲音樂成為背井離鄉的粵籍華工悲苦清貧、思鄉念祖生活里的唯一消遣。這無形中為戲曲(實際為粵劇)在海外的傳播奠定了堅實基礎。1852 年,據美國《阿爾塔加利福尼亞日報》記載,廣東粵劇團“鴻福堂”在舊金山為開拓金礦的粵籍華工演出傳統劇目《六國封相》;粵劇還活躍在東南亞及北美的粵語華人聚集區,深受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地區粵語華人移民的喜愛。它們被廣為傳唱,奠定了粵劇藝術以新加坡為中心,向東南亞其他周邊城市輻射傳播的基礎,因此,新加坡是“粵劇第二故鄉”。晚清王韜《漫游隨錄》中記載,清朝同治六年(1867 年)第二屆巴黎世界博覽會上粵劇的演出盛況。“有粵人攜優伶一班至,旗幟新鮮,冠服華麗,登臺演劇,觀者神移,日贏金錢無算。”此舉使得粵劇“Cantonese Opera”為西方歐洲人民所知悉。
(二)近現代時期的逐漸式微階段
20 世紀20 年代末至30 年代是粵劇藝術發展的第一次高峰時期,粵劇語言從“戲棚官話”變為“廣州白話”,粵劇唱腔由假嗓改為平喉,粵劇表演從全男班、全女班到男女同臺,粵劇曲調從單一到多元,從以弋陽腔和昆腔為載體的簡歌易語到融本地南音、粵謳、咸水歌等歌謠小曲的淺唱輕吟,既呈現寫意派的空靈唯美,又具有寫實派的動感輕快。此后幾十年里,粵劇主題圍繞年節演出及演酬神戲展開,主要目的是供鄉民休閑娛樂或撫慰思鄉,而后發展成為宣傳國內民主事業的革命題材劇,以粵劇的群眾影響力傳播革命進步思想。20 世紀40-70 年代,粵劇發展經歷抗日戰爭、國民黨內戰、解放戰爭等一系列歷史事件,內容形式也因時勢的變化不斷變革創新,粵劇藝人為了尋求生存,使得粵劇的傳播軌跡從國內逐漸轉向國外。歷史的變遷直接推動了粵劇在海外的傳播與發展,這也是粵劇在國內從興盛到衰落,在國外逐漸風生水起的主要原因。20 世紀初,粵僑開始活躍于新加坡、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以及美國、加拿大等北美地區,粵劇也因此得以推廣,深受當地粵僑的歡迎。東南亞粵劇戲班隨勢而起,興建戲劇院,并從國內聘請專業的粵劇“大佬館”和“名角”前往當地進行粵劇表演,粵劇的海外傳播漸入佳境。然而,隨著40 年代二戰爆發,粵僑流離顛簸、食不果腹、忙于生計,粵劇在海外傳播自然而然地進入了衰落式微階段。
(三)現代時期的復興繁榮階段
20 世紀70 年代末,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備受群眾歡迎的粵劇,呈現“萬家燈火萬家鳴”的盛況,迎來復興。粵劇界一改之前以劇團演戲為主的推廣狀態,轉而在國家政府“弘揚傳統文化,振興粵劇藝術”的文化政策下,多樣化創新粵劇的推廣形式,如舉辦粵劇名伶個人藝術展演,其中,1984 年“紅線女獨唱會”是首創;推廣普及粵劇的“羊城群眾粵劇大聯展”;選拔粵劇青年人才演藝大賽;舉辦以“粵劇傳承保護”為主題的紀念會、研討會。每四年一屆的“羊城國際粵劇節”及每年上百次的出境出國演出從根本上促進了粵劇的國際化交流,為“中國精品戲劇走向世界,西方優質戲劇引入中國”搭建了交流合作的平臺。1990 年12 月12 日-20 日舉行的首屆“羊城國際粵劇節”吸引了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香港、澳門等在內的國家和地區共38 個社團,參演人數2100 多人,影響意義深遠。
二、粵劇在海絲文化起點——廣州的傳承與傳播現狀分析
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是我國在21 世紀初提出的文化建設方針,它為非遺文化發展帶來機遇,也為助力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去”邁出關鍵步伐。然而,起源于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廣州的非遺粵劇如何憑借“走出去”文化建設提供的重要契機鑄就新的輝煌呢?2009 年9 月30 日,粵劇經由粵港澳三地聯合申報,成功獲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國際影響力也與日俱增。
(一)以廣州的地緣優勢促進粵劇海外傳播
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源地,從古至今,它作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窗口,見證了中外文明的交往。“不可否認,興盛期的‘絲綢之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大走廊,東牽亞太經濟圈,西系歐洲經濟圈,貫通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部分區域,借此絲路沿線的物質及非物質文化產生了大范圍的交易、交流和互動。”西方文化借助海上絲路在廣州登陸,中國文化也借道廣州流往海外。各國文化在此地匯聚沉淀,深入民心。廣州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特殊歷史地位及其對粵劇海內外傳承與傳播的重要影響,使得優秀繁榮、醇厚堅實的非遺文化典范——粵劇完全可以率先破題,當先鋒,走在前,以情感語言、文化記憶的方式書寫“文化出海”的歷史新篇章。根植“千年商都”廣州兼容并包、華洋雜處土壤的粵劇,因其悠久的歷史和廣泛的受眾,成為海內外人民文化溝通,情感寄托最為有效、最受歡迎的藝術載體之一。在增強文化自信,文化出海建設過程中,粵劇理應代表嶺南文化承擔起對外文化交流的責任,幫助粵港澳地區在國際上提升形象、樹立品牌,持續擴大粵劇的境內外和海內外的影響力。2017 年,第七屆國際粵劇節,東南亞地區及英國、法國等海外粵劇社團來到廣州展演優秀劇目,海內外展演劇目超過50 臺。新加坡的粵劇社團還表演了形式新穎的“英語粵劇”。除了粵劇展演,羊城粵劇節期間,各種粵劇研討會、粵劇名師講座、藝術沙龍等活動為海內外粵劇從業人員提供了相互交流探討的機會,擦出新時代粵劇多元化傳播發展的靈感火花。
(二)以粵劇的受眾力量促進粵劇海外傳播
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粵劇的傳播形式、傳播手段與傳播環境均受到當今社會多元文化,如“快餐文化”“科技文化”等的沖擊,正面臨巨大挑戰。粵劇傳承近400 年歷史,能夠兼容并包地吸收本地劇與外地劇的藝術精華,形成自己的傳統特色,此外,它主要立足于市井文化與大眾生活,具備通俗曉暢、平易淺顯的特征,符合世俗大眾的平民心態,迎合了他們的消遣需求,因而,這種藝術形式廣受市場歡迎。然而,受到新媒體的沖擊,這種傳統表演性質的藝術正逐漸衰落,年輕人對這種藝術普遍感到陌生。堅守在粵劇一線的觀眾群體和在演職員,很多人普遍在50歲以上,呈現老齡化趨勢。“45 歲以上的中老年群體,是我們非遺項目保護和傳承,最忠實的粉絲,最天然、最可靠的同盟軍。他們既是非遺保護和傳承最穩固的受眾,也會是非遺保護和宣傳最好的宣傳者。”公園或廣場的粵劇戲臺、粵劇戲園常常座無虛席,粵劇依然是老年人的主要休閑娛樂之一。因而,弘揚和推廣粵劇藝術的引導者是活躍在“戲劇舞臺”的老年人。2007 年,姚冠冰老奶奶創辦小紅豆藝術團,該藝術團于2011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粵劇中國保護中心推廣基地”的榮譽。她組織志愿者免費教授孩子們粵劇知識,悉心培養至少400位小紅豆粵劇新苗。2015 年,小紅豆藝術團受邀廣州南方劇院,參演“2015 年海內外華人粵劇粵曲展演晚會”,并與全球粵劇愛好者交流學習;同年11 月,受邀參演了“2015 年穗港澳桂粵劇活動日晚會”。2017 年1 月,到北京參加“黨旗下的盛世中國——2017 我愛祖國青少年文藝展演”,該藝術團演繹的《我是一顆小紅豆》榮獲曲藝組金獎。
跟國內情況相似,海外粵劇社團也以代際間的“大手牽小手”形式推廣傳播粵劇,讓年幼觀眾親近粵劇文化。眾所周知,“粵劇已成為以粵語為母語的華人之間的文化紐帶,從某種意義上講,粵劇戲劇藝術是一種凝聚力,看粵劇和唱粵曲不僅是一般的觀賞娛樂,也是外籍華人保持自己祖國文化的一種途徑或者方式。”粵劇于粵僑而言,是懷舊思鄉的個人記憶、血脈相連的歷史傳承,粵僑對保護和傳承粵劇非遺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與非遺文化的保護會讓他們覺得“老有所樂、老有所為”。例如,新加坡敦煌劇坊每年均前往新加坡的學校開展粵劇講座;新加坡徐家班戲曲藝術團時常舉辦戲劇化妝、戲劇武術、身段表演、音樂演奏等“親子”班;新加坡藝聲粵劇團每年均為民眾舉辦兩場大型的公益性粵劇展演……這些粵劇表演團體為獻力粵劇發展,傳播非遺文化營造了良好的文化生態環境,為粵劇藝術培養人才、凝聚觀眾、創作精品、傳播國粹及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貢獻了無形的社會力量。
三、結語
粵劇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承載著粵港澳三地及海外華人的個體記憶與民族情感,也承載著廣府文化的深厚底蘊與歷史價值,它抑揚頓挫的韻律,古典清麗的唱詞深情演繹出嶺南文化的獨特風采,吸引、浸潤并滋養著粵港澳大灣地區及珠三角九市及美洲、歐洲和東南亞等地海內外華人僑胞們的心靈。保護和傳承這顆在浩瀚如海的歷史河流中仍獨樹一幟的“南國紅豆”,是華夏子孫義不容辭的責任,推動粵劇的境內外和海內外傳承有助于民眾在文化交流與融合中實現情感互鑒、民心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