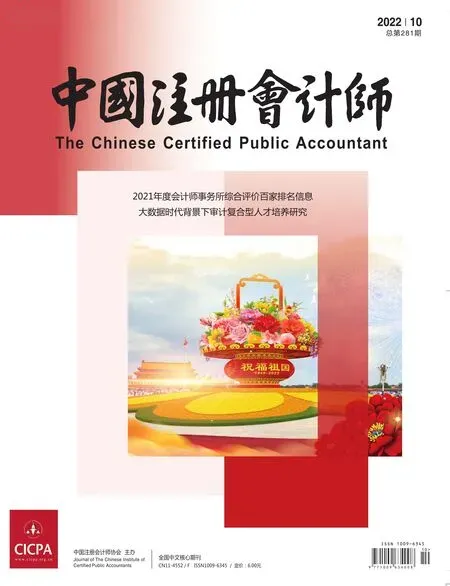分步收購與商譽規避問題研究
| 顧水彬 曹陽
一、引言
企業合并是企業謀求外延式增長和獲取協同效應的重要路徑與戰略,是行業整合和產業升級的重要推力。據Wind統計,我國企業合并規模已從2012年3172.65億元上升至2020年的12111.77億元,企業合并已成為我國企業資源重組與優化配置的重要方式。然而,近年來資本市場中出現了一種先收購目標企業控制權,再收購剩余股份的“分步收購”現象。2017年12月科斯伍德收購龍門教育49.76%的股權,又于2018年開始收購龍門教育剩余股權;2019年4月,光韻達份收購通宇航空51%的股權,又于2020年6月收購了通宇航空剩余49%股權;2019年10月,麥迪科技收購海口瑪麗51%股權,又于2020年11月開始收購海口瑪麗剩余49%股權。緣何在原則導向的會計準則下,市場上仍涌現“51%+49%”的分步收購現象,企業是否存在利用會計準則規避商譽之嫌?
從2 0 1 8 年證監會發布的《會計監管風險提示第8號——商譽減值》,到2020年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發布的《企業合并——披露、商譽和減值(討論稿)》、到2021年中評協發布的《關于關注企業商譽減值測試評估業務風險的提示》,再到2022年國資委發布的《關于加強中央企業商譽管理的通知》,折射出商譽問題的現實重要性與政策關注度。本文在此背景下展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貢獻與政策價值。
二、分步收購與商譽規避的理論關系
企業合并是指將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單獨的企業合并形成一個報告主體的交易或事項。從收購次數來看,企業可以通過一次收購或分步收購取得被合并方(近似)所有股權。與一次收購不同,分步收購先購買被合并方部分股份以獲取控制權,其后再收購被合并方(近似)剩余股份。雖然兩類收購的次數與會計處理存在不同,但是實質效果可能一致。
《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合并》第十三條指出,對于取得控制權的股份收購,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購買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差額,應確認商譽。然而,《企業會計準則第33號-合并財務報表》第四十七條又指出,母公司購買子公司少數股東擁有的子公司股權,在合并財務報表中,因購買少數股權新取得的長期股權投資與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計算應享有子公司自購買日或合并日開始持續計算的凈資產份額之間的差額,應當調整資本公積和留存收益,不確認商譽。綜上可見,會計準則對企業合并中控制權獲取之前與之后支付溢價的會計處理要求截然不同,對于同一對象全部股份的收購,企業可以通過“分步收購”方式來規避控制權取得之后的商譽確認。具體原理如圖1所示。

圖1 分步收購與商譽規避理論關系
三、分步收購與商譽規避的現實關系分析
現實中,企業采用分步收購獲取全部股份的現象并非個例。筆者搜集整理了2018年至2020年采用分步收購方式的A股上市公司(主合并方第一次收購股權比例在50.00%左右,最終直接控股比例在99%以上),共發現40家公司。如表1所示,大量上市公司將首次股權收購比例設定為51%,隨后又收購剩余49%股份,對同一收購對象,高度一致的收購比例與兩步安排折射出“分步”的刻意性與目的性。

表1 分步收購上市公司的收購比例與分步安排
筆者從40家樣本中挑選了數據最為完整的6家公司進一步開展比較研究,試圖揭示分步收購與商譽規避的現實關系。表2Panel A匯報了6家樣本公司如果采用一次收購全部股份應確認的商譽情況。由第④和⑤列可見,6家樣本公司利用分步收購規避掉的平均商譽要高于實際確認的商譽,其中“麥迪科技”規避的商譽為實際確認商譽的3倍。

圖2 科斯伍德分步合并龍門教育流程圖
表2Panel B匯報了依據企業業務類型和收購標的資產類型配比的一次收購對照組與分步收購樣本組的比較結果。由表中數值可見,一次收購對照組每一元支付對價所含商譽比例是分步收購樣本組每一元支付對價所含商譽比例的2倍以上。綜上可見,企業采用分步收購規避商譽的現實效果較為顯著。

表2 分步收購與一次收購的商譽比較(單位:萬元)
四、分步收購與商譽規避內在關系的案例研究
為了進一步發現分步收購與商譽規避的內在關系,本節以科斯伍德合并龍門教育的案例開展研究。該案例采用兩步法收購(近似)全部股份,收購標準特殊,時間跨度恰好,具有較強的典型性和時效性。
(一)公司簡介
主合并方:蘇州科斯伍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2011年3月22日登陸深交所創業板,是一家秉承高創新能力發展戰略的國際知名環保油墨制造商,也是國內環保膠印油墨行業的龍頭企業之一。
被合并方:陜西龍門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2016年7月28日登陸新三板,是一家面向初高中學生提供短期集中式培訓、K12課外培訓以及教學軟件及課程銷售,集教育培訓、產品研發、教學研究于一體的綜合教育服務機構。
(二)收購過程分析
第一階段:獲取控制權。2017年5月3日科斯伍德首次提出擬收購龍門教育51%的股權,12月27日,科斯伍德以7.49億元現金完成收購龍門教育49.76%的股權,另與龍門教育相關股東簽訂《表決權委托協議》,獲取額外2.629%的表決權,最終實現實質控制龍門教育,其中超過被合并方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5.96億元支付溢價確認為商譽(歸屬于合并方的商譽,在合并財務報表中列報),歸屬于少數股東的商譽為6億元(不在合并財務報表中列報),全部商譽為11.98元。
第二階段:收購剩余股份。2018年10月9日科斯伍德與龍門教育及其主要股東馬良銘簽署《意向性合作協議》,擬收購龍門教育剩余50.24%股權。2019年7月24日,科斯伍德以發行股份、可轉換債券及支付現金的方式收購龍門教育剩下的股權50.17%,交易總金額為8.13億元。由于此次收購視同購買少數股東權益,股權交易對價與按得的股權比例計算的龍門教育凈資產份額的差額6億元計入資本公積(股本溢價),不確認商譽。
(三)分步收購的基本動機分析——轉型并表
1.產業轉型。從行業性質來看,龍門教育是教育培訓行業,屬新興產業,自2016年《民辦教育促進法》修訂出臺后,公司發展更是迅速,而科斯伍德主要經營油墨與印刷,屬傳統行業,隨著新媒體、互聯網盛行,以及原材料價格上升,行業整體收縮,公司營業收入與利潤出現持續下滑,尋求產業轉型成為該公司的迫切任務(如圖3所示)。科斯伍德收購龍門教育,由印油墨行業跨界教育市場,旨在實現產業的強勢轉型,盡享教育業務的高速發展與豐厚盈利,類似跨界教育的合并還有豆神教育(前身為立思辰)和凱文教育(前身為中泰橋梁)等。

圖3 合并前油墨與教育市場規模增長率(左)、科斯伍德分步合并前后凈利潤變化趨勢圖(右)
2.并表輸血。在業績為王的資本市場,龍門教育并表“輸血”成為科斯伍德合并龍門教育的另一重要動機。由圖4可見,近年來科斯伍德的營業收入與凈利潤出現持續下滑,其中2017年凈利潤較2016年同比下降了90.10%,而龍門教育的營業收入與凈利潤卻持續高速增長。自龍門教育并表后,合并營業收入由2017年的4.72億提升至9.59億元,同比增長103.2%,合并凈利潤由2017年的587.7萬元上升至2018年的8941.75萬元,2019年更是達到16842.12萬元,凈利潤增長了近30倍,可以說龍門教育并表“輸血”對科斯伍德功不可沒。
(四)分步收購的深層動機分析——商譽規避
1.從收購間隔來看——規避“一項”交易。《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上市公司在12個月內連續對同一或者相關資產進行購買、出售的,以其累計數分別計算相應數額。規則越清晰,交易越易構建。從形式上看,科斯伍德的二次收購的完成時間間隔大于12個月,但實質上科斯伍德早于2018年10月(離第一次收購完成小于12個月)就公告了其繼續收購龍門教育剩余股份的意向。綜上可見,科斯伍德對龍門教育的兩步收購安排可能刻意迎合“12個月”門檻,規避“一項”交易與“完全”商譽的確認要求。
2.從公告內容來看——實屬“戰術”安排。企業戰略理論指出戰略具有穩定性、長期性、重大性。科斯伍德于2017年7月28日發布的《重大資產報告購買書》中公告稱“收購龍門教育是為了戰略布局教育服務產業”,同時指出“未來不排除將購買龍門教育剩余股權”。龍門教育自2016年登陸新三板,股價曾高達365元,一度超越貴州茅臺,盈利空間大,發展快速。王化成(2018)指出對主合并方的經營具有重大影響或盈利貢獻大的標的資產應全資控股。綜上可見,科斯伍德對龍門教育短期內的兩步收購屬于“同一”戰略的戰術安排, 旨在規避商譽。
3.從收購溢價來看——凸顯“剛性”收購。科斯伍德《2018年年度報告》顯示,龍門教育關鍵業務K12(中小學)課外培訓業務營業收入僅為1.56億元,遠低于此前預測的2.76億元,且產生了1834萬元的凈虧損。然而,在龍門教育主營業務業績未達預期的情況下,科斯伍德仍以高于第一次合并(11.95元/股)的價格(12.56元/股)于2020年3月收購剩余股份,體現出繼續收購龍門教育的“剛性”。由被收購主體的股份出讓名單來看,科斯伍德前后兩次收購的股份出讓方(龍門教育大股東:馬良銘、明旻、董兵、 馬良彩、方銳銘等)的高度重疊性,凸顯出兩次收購的“連貫性”。深交所專門對第二次收購目的及價格下達問詢函,提出“各年總體業務收入預測值較前次大幅降低的情況下,本次收購少數股權的交易作價明顯高于前次收購控股股權交易作價的原因”。
4.從商譽占比來看——迫切“規避”商譽。我國上市公司合并普遍存在“三高”現象,即高估值、高業績承諾、高商譽。由于高額商譽存在巨大的減值壓力且需要合并后大量的利潤吸收消化,因此商譽就像懸在上市公司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由科斯伍德的資產結構可見,科斯伍德分步收購形成的商譽占據總資產的35.03%,是固定資產與無形資產合計的2.5倍,如若采用一次合并,其形成的商譽將占據總資產的73.80%。“超高比例的商譽”不僅形成了巨大的商譽減值與利潤吸收壓力,而且還不利于股票流動性與外部融資。綜上可見,科斯伍德具有強烈的商譽規避動機與需求。
(五)分步收購與商譽規避的經濟后果
筆者認為比例商譽法是分步收購規避商譽的直接原因,該方法將導致歸屬于少數股東的商譽無法列報,造成商譽“低估”(IFRS3 BC 217)。在完全商譽法下,分步收購與一次收購確認的商譽是一致的。其實,我國在商譽減值測試時一直采用完全商譽法,即將比例商譽還原成完全商譽后再計提減值,但在合并財務報表中未使用。建議我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參考國際做法,在合并財務報表列報中采用完全商譽法,減少分步收購的商譽規避問題,提升合并商譽反映的完整度。
為了呈現科斯伍德分步收購的商譽規避經濟后果,筆者進一步模擬了“新冠疫情”和“雙減政策”下科斯伍德分步收購與一次收購龍門教育股份的商譽減值情況。
1.基于新冠疫情的商譽減值測試。科斯伍德于《2020年年度報告》和《2020年度商譽減值測試報告》指出,2020年度線下培訓教育業務因新冠疫情受到較大的影響,因此對龍門教育的合并商譽計提了3615萬元的減值。如科斯伍德采用一次收購獲取龍門教育全部股份,其商譽減值額或將達到7258萬元,將占合并凈利潤的52.8%。
2.基于雙減政策的商譽減值測試。科斯伍德于《2021年年度報告》指出,受2021年“雙減”政策影響,線下培訓教育業務受到重挫,因此對龍門教育的合并商譽計提了4.79億元減值,導致公司凈利潤虧損4.5億,較上年下降491.35%。如若科斯伍德采用一次收購獲取龍門教育全部股份,其計提的商譽減值額或將達到9.6億元,將導致合并凈利潤出現巨虧。
五、觀點爭鳴與改進建議
為何分步收購能規避商譽,是分步收購產生了不同性質的經濟業務,抑或實務在會計準則應用時存在誤解?本文認為,對分步收購的認識,應該從少數股東權益的計量基礎與商譽的列報模式切入,從分步收購業務的本質予以認識。
1.比例商譽法導致分步收購商譽規避。《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企業合并》IFRS3-32段指出,商譽是合并日支付對價和少數股東權益合計數與合并日凈資產公允價值之差。依此定義,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提出了完全商譽法和比例商譽法,即當合并時少數股東權益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合并財務報告列報完全商譽(Full Goodwill),而少數股東權益采用可辨認凈資產份額計量時,合并財務報告列報比例商譽(Partial Goodwill)(IFRS3 19段)。IFRS3允許報告主體在兩種商譽法中自由選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SFAS 141(R)要求完全商譽法,而我國會計準則要求比例商譽法,即僅合并財務報表、僅列報與合并方持股比例對應的商譽部分。
筆者認為比例商譽法是分步收購規避商譽的直接原因,該方法將導致歸屬于少數股東的商譽無法列報,造成商譽“低估”(IFRS3 BC 217)。在完全商譽法下,分步收購與一次收購確認的商譽是一致的。其實,我國在商譽減值測試時一直采用完全商譽法,即將比例商譽還原成完全商譽后再計提減值,但在合并財務報表中未使用。建議我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參考國際做法,在合并財務報表列報中采用完全商譽法,減少分步收購的商譽規避問題,提升合并商譽反映的完整度。
2.對商譽的誤解導致商譽規避誤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合并財務報表》IFRS10-BCZ168和BCZ173段指出:“獲取控制權是一項重要事件,主合并方在獲取控制權的時點已經控制了被合并方資產與負債,且所有獲取資產與負債已重新確認與計量,控制權獲取之后的剩余股份收購不新增資產和負債或影響資產和負債的確認與計量,僅增加了收益份額,因此無需確認商譽”。我國《企業會計準則33號—合并財務報表》第四十七條也有類似表述。
筆者認為,對于“無需確認商譽”的誤解存在兩方面的偏差,一是忽視了完全商譽法的列報背景,二是前述“無需確認商譽”是“新增”商譽。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企業合并》IFRS3-10段指出合并商譽在合并(控制權取得)時即已形成,控制權取得后的剩余股份收購并不新增資產和負債,因此無須重估資產和負債及重新確認可能比原來“新增”的商譽。在比例商譽法下,合并時少數股東權益公允價值難以估測以及相關股份未實際發生購買,相應的商譽未在合并財務報表中列報,但未列報并不否定少數股東權益相應商譽的存在性。當少數股東權益被主合并方購買時,交易實際發生,而且購買價款中包含了合并時歸屬于少數股東權益商譽的對價,此時控制權取得后的繼續收購需要將原合并時歸屬于少數股東權益的商譽予以入表列報(IFRS3 BC213段)。在公平交易模式下,支付對價超過交易對象公允價值部分為商譽,外部投資者需要了解整體支付與被合并方評估價值的關系,科學評估合并績效與合理性,以及發現被合并企業未來的增長前景。
3.業務實質穿透不足導致分步收購商譽規避。分步收購規避商譽不是一個計量問題,而是一個確認問題。分步收購的確認實質是“一攬子交易”抑或“多重要素安排”的識別問題,其識別的關鍵在于各收購交易步驟是否屬于整體籌劃、實現同一交易目的或互為前提條件。目前我國會計準則僅對多次交易獲取控制權和多次交易處置喪失控制權的“一攬子交易”進行規范,但并未對分步收購是否屬于“一攬子交易”予以明確規范(CAS20第十一條,CAS33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一條)。
筆者認為,合并次數和合并時間間隔不是判定一項或多項交易的關鍵因素,合并交易安排的商業實質才是。企業合并是企業的重要戰略,具有穩定性、重大性和長期性。短時間內對同一標的資產多次收購更符合同一合并戰略的階段性執行或合并的戰術安排,應界定為“一項合并”。原則導向會計準則注重業務實質,反對準則套利。在控制權收購與少數股權權益收購的商譽確認存在差異的情況下,理性經濟人會利用會計準則間隙,安排“鏈式收購”,規避商譽,并對資本市場系統風險埋下隱患。建議會計準則制定機構與證券監管機構從嚴規范分步合并,將同一標的資產的分步合并視同一項合并,輔以例外原則,以減少商譽規避,抑制管理者蓄意抬高估值與過度自信等非理性合并行為,提高企業合并信息的相關性與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