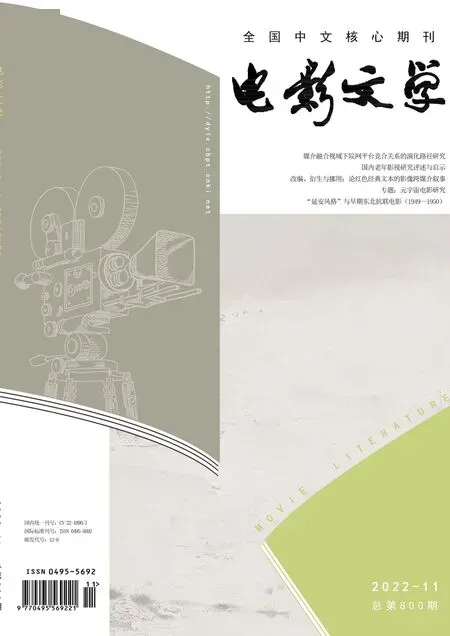數字奇觀電影生態美學內涵之生態審美本源性
方 麗
(北京師范大學數字創意媒體研究中心,北京 100091)
一、何為生態審美本源性
在我國著名的生態美學學者曾繁仁看來,生態美學的重要內涵就是生態審美本性。生態問題如此重要,它關系到人類如何定義自我,從根本上來說,是屬于人之生態性哲學本質的追問。在西方認知論哲學的語境中,人的抽象本質被先哲們定義為“理性的動物”“感性的動物”等,恩斯特·阿西爾將人的本質定義為“勞作”,將人抽象為符號創造者和使用者,但這種定義似乎仍然不能完全覆蓋人的生命本性。海德格爾基于存在論現象學的方法,直面人的“存在”這一基本理念,指出存在并非在二元對立基礎上而成的認知,其本質體現了生命和自然的交互融入關系。羅爾斯頓強調,人性并不是存在于自身,“而是在于我們與世界的對話中”,完整性主要是指利用與環境的多元化交互,不管環境是敵人還是朋友,由此才能稱之為完整性——依托環境才能實現真正完整。所以,個體基本特性就是其生態本性。當生態本性進入審美領域,東西方美學領域皆產生了獨具特色的生態審美本性,在東方傳統中主要表現為中和之美和生命之美,在西方較為突出的是自然生態審美的本源性和身體美學。
二、自然本源與返魅之美
以生態為主題的數字奇觀電影濃墨重彩地刻畫出真實自然景觀與虛擬自然景觀,將自然作為展現生態意識、討論人與生態關系的重要手段。《百變貍貓》《獅子王》《雄獅少年》等奇觀電影中無不展示出生生不息、萬物蓬勃的自然生態之美。《百變貍貓》中郊外自然環境與不斷擴張的東京城市風景形成鮮明的對比,貍貓們原本徜徉生活于綠色友好的自然中,他們隨著天地自然四季運行的規律而休養生息;《獅子王》(2019)的故事發生地就具有自然生態基因,大草原草木蔥蘢、生命多樣,一派祥和安寧的生態之美。《雄獅少年》中通過場景主色調冷暖對比的手法,刻畫出繁榮蓬勃的嶺南鄉村風光——火紅的木棉花是角色精神覺醒內在涌動的外化,三人在湖泊、原野、自然風光中尋找舞獅導師的場景切換突出了人與自然之和諧乃至親近自然本源生發出追尋過程的美妙,最終冰冷暗調城市印象的描摹更加襯托出自然審美才是人類的生態審美本源性。
對于自然美的表現是古往今來藝術家們重要主題,在美學發展的早期階段,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哲學家們認為自然美是層次很低的美,只有藝術美才能稱為真正的美。自然是人類始終根深蒂固的作為一種客體的想象,是人的內在精神的外化。站在生態美學的視角來看,自然不是審美的對象,反而成為審美的主體,布伊爾就曾指出:“生態審美表現自然本身的美。”并不強調其中人的思想的重要性,也不是以人的角度出發去衡量對自然的抽象認識。自然成為一種審美的主體,不僅承擔“工具化”的輔助功能。在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生態主題的數字奇觀電影中,創作者們注重自然美的主體性呈現,將其提升到了一個重要的藝術高度上來。自然美與藝術美的融合升華是值得肯定的美學嘗試。
在里程碑式的數字奇觀電影《阿凡達》中,卡梅隆導演邀請保羅——南加州大學的語言專家,擔負起創造納威族語言系統的創作任務,同時逐步給動植物取名。另外,還讓朱迪·霍爾特全面編制出數十種植物的譜系說明。導演對于自然的藝術化呈現基于嚴謹的科學研究之上,足見其對于生態之美的重視程度。影片中大多美輪美奐的自然場景都是基于實景景觀采樣,經過數字技術處理后,表現出一種超真實的虛擬自然生態美感。潘多拉星球的主體真相峰原型是中國著名的黃山,東方的奇幻場景在科技元素的加持之下,構成了影片中的虛擬自然景觀——堪稱本片最重要的主角。在這個星球上,天地自有其運行的規律,萬物皆處于生態循環之中,納威人本身也具有強烈的生態審美情趣,他們對于自然美的認識不是停留在把自然簡單地作為一種工具或征服的對象,而是對于自然美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和認可。電影中納威人居住的星球展現出一番人類伊甸園般的富饒美麗景象,山川秀麗,海河奔涌,植物繁茂,野獸多樣。在茂密而深不可測的雨林里,圣樹傳遞著來自遠古祖先的信息,天空中飛舞著熒光閃閃的圣樹種子,這個古樸、奇異、自然的星球儼然是基于復興希臘萬物有靈說的生態有機論的奇觀展現。這里所有的樹木都通過根系彼此相連,整體生態中的所有生命元素都像大樹一樣構成了一個交織運行的生命之網。通過納威人與動植物的互動,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去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正如納威人公主向杰克所做的闡述:“能量在生物間流動。”能量如原子的力量是源自大自然的,在將來某個時刻會歸還給自然。天地萬物生而平等,并處于一種平衡而多樣的生態系統中。影片成功地傳遞出潘多拉星球的生態美感,同時也蘊含著豐富的東方古典生態審美內涵。納威人與潘多拉星球家園的關系是一種“天人合一”之美,他們的生命與大樹、動物、翼獸都處于一個能量流動的網絡中,仿佛每一個細胞都與這個綠色的家園融為了一體。這種人與自然圓融會通的境界,也正是中國傳統生態美學的核心。當人將自己看作自然天地的一部分時,才能真正領悟到生態世界的美麗。
類似的生態系統之美在《獅子王》中也有很好的體現,木法沙曾對辛巴說道:“你要懂得這種平衡,并尊重所有的生物,不管是螞蟻還是羚羊。雖然我們吃羚羊,但是我們死后身體會變成草,而羚羊吃草。”也就是說,自然中人們的所見所聞所想均處于極為細微的平衡關系之中,生命始終是在循環聯系之中。在《飛屋環游記》中,自然生態得到了充分的美化,卡爾帶著充滿回憶之愛的小屋投入自然的懷抱。不僅實現了生命的回歸,更是一種靈魂的撫慰與救贖。天地之大美中昭示出人與生俱來的生態審美本性。這些電影中的生態之美與東方美學體系進行了遙望與呼應。
《周易》中將符合生態規律的天地自然運行視為一種“美”。這種“中和之美”就是我國早期對于人的生態審美本性的認識,陰陽乾坤“正位居體”,因而“上下交而萬物通”,“天地變化,草木蕃”,人與萬物生命力蓬勃生長,于是暢于四肢,發與事業,成為至高之美。人的生態審美本性深深地蘊藏在東方美學體系中,數字奇觀電影的呈現將其進行了形象化的呈現。我國動畫電影《夢回金沙城》就是一部獨具東方風情的影像作品,其中展現了江南水鄉、九寨溝等具有民族特色的自然之美,唯美而清新的視覺風格讓人領略到東方生態美學的意蘊。但值得惋惜的是,電影的生態敘事意識淡薄,情節設置得欠缺邏輯,使得美麗的東方風景淪為一種簡單的風光場景轉接,未能真正成為推動敘事的美學基礎,但是電影在東方美學的藝術表達上還是值得肯定的。
在一些數字奇觀電影中,人們對于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的想象通過數字化的方式呈現為生動、直觀的動態影像,創作者們依靠非凡的創造力將對于自然和生命的想象轉化為一種推動人們改變環境的塑造力。生態美學中對自然的“返魅”不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一種討論和理想,而是在數字構建的可視化的虛擬場景中得以實現。所謂“魅”是遠古時期由于人類認識局限和科技的欠發達所形成的自然神秘感以及人類對自然的敬畏感和恐懼感。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進程后,“人為自然立法”“人定勝天”等觀念深深植入主流社會思潮,是一種人類對于自然的“祛魅”。但是發展帶來的人類對于自然的毀滅性破壞引發了一輪深入的思考,通過部分的恢復人類對于大自然的審美力和神圣化成為解決危機的途徑,這就是對于自然部分的“返魅”。數字奇觀電影具有先天的優勢,將對自然的“返魅”形象化地呈現出來。例如在《阿凡達》中,“建構于科技文明基礎上的人類社會為了在潘多拉星球建立礦藏開采基地,研發化身人阿凡達接近納威人,并最終采用武力對其進行狂轟濫炸,充分體現出‘祛魅’的地球文明對潘多拉星球帶來的災難,也可看作人類在利益驅動下,現代工具理性對于原始地球生態的大肆破壞。潘多拉星球美輪美奐,是導演對于原始地球美好意境的想象與升華。虛擬仿真建構的萬物皆遵守真實世界中的自然法則。借助數字特效技術,創作團隊設計出參天大樹組成的原始森林,虛擬CG植物和造型奇特的各類猛獸。藍色納威人的外形設計具有人的身體和似貓的頭部,具有人獸合二為一的多樣雜合風格。外形設計的多樣性指向文化的多樣性——在納威族的價值觀設計方面,他們秉持‘心物一元’論,將自己看作星球的一部分,能聽懂自然的呼吸,接收到自然之神‘伊娃’的旨意。影片特殊的光影設計將植物與地下網絡形成一個有機整體,通過布滿發光鏈條的圣樹,納威人向祖先和神靈祈福,甚至聽到逝去的族人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聲響與回應。文學觀念中抽象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環構成了一個數字建構的可視化能量場。在潘多拉這個能量場中,所有植物以及智慧生命都對自然萬物懷有敬畏之心,呼應著生態美學中的‘返魅’觀念。當然,這種‘返魅’并不是暗示人類回歸到原始蒙昧的生存狀態,而是部分地恢復自然的神秘性與人的生態審美本性”。納威人在神秘的自然面前,也表現出對中國古典生態美學中道家的“無為”思想和儒家“仁愛”觀念的契合。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人應該遵從自然的規律,人的血脈與自然經絡交融流動,從而熱愛自然、融入自然。“無為”就是要避免人類對自然的過度索取與開發,通過精神自由的生存境界實現人在自然中的超然灑脫。納威人對與自然始終抱有著“仁愛”的審美精神,他們懂得去回報大自然的恩惠,秉承著仁愛、寬容和良知踐行著與天地萬物的良好生態關系。
自然是在恢復人的生態審美本性時,起到了本源性的作用,人類是自然孕育而生的,作為人類的棲息之地,雖然有時為繼母,沒有善待好家園。而文明的發展與延續,會持續向前,正如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學家杜威所說:“證明人類的希望和目的在自然中找到了基礎和支持。”
三、身體美學與生命之美
身體美學的提出是一種統一了感官與哲思的生命美學。從哲學演變的視角來看,哲學家們對于身體和感官的認知走過從主體性意識美學的對身體與欲念的忽視向注重主體身體性特征的身體美學的轉變過程。尼采倡導的超人,不僅是具有強力意志的主體,而且要有強壯身體作為基礎,強調了身體性。海德格爾的存在論中注重“此在”,預示著身體是構成此在主體的重要部分。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的知覺現象學,更是強調主體的身體性知覺,并提出了“世界之肉”的思想——人與世界不是意識或物質的簡單區分,而是一種身心一體的“肉”,也就是說,身體與世界是一體的。由此開始,身體美學進入人們的視野。正如《阿凡達》中納威人具有連通自然和祖先神靈的身體設定,構成一種介于精神與物質之間的靈性的存在。人對于自然的審美不僅是一種精神性的認識,更是一種身體性的行為,是梅洛·龐蒂所說的身體和世界有著相同的肉身性,其并沒有二元對立的聯系,體現了一種可逆性關系,其特點為相互融合、反射、對抗以及僭越。潘多拉星球上的萬事萬物是納威人身體的擴展,另外,納威人的身體同樣為外部生態世界的擴展,利用此類交融的關系,生態系統與納威人的身體具有一體性。作為異類的化身人杰克,當意識進入化身人的形體之后,實現了一種從人類中心主義觀念到生態整體主義思想的轉變,他的身體既是一個觀看潘多拉星球的看者,同時也是一個被看者,身體成了看者和被看者的集合。因而,人對于外界生態的認知得到了一次升華。正如梅洛·龐蒂所說:“神秘之處在于:我的身體同時是能看到的和可見的。”我自己的身體能夠被看見。身體關注著所有事物,也能關注著自身,所以在其所見中能夠捕捉到它自身“能夠看見”自身的意味。外部全新世界——潘多拉星球因為這種肉身性的審美能力,鑲嵌在杰克的化身人肉身之中,世界與身體由相同的材料所構成,兼具物質性與精神性的靈性肉身真正地實現了自然與人的水乳交融,仿佛回到了自然的子宮之中。
異曲同工的是在動畫奇觀電影《百變貍貓》中有一場非常震撼人心的貍貓游行情節,在這場令人嘆為觀止的場景中,動畫利用其假定性的特點極盡變形之能事,貍貓們借助其身體化身為種種形態,有具象的動物、抽象的自然神靈等視覺元素,令影片中的人類觀看者產生了奇異的審美體驗。這一場象征著萬物有靈的表演,正是基于身體美學的夸張化與想象力。很遺憾的是,電影中的貍貓們未能通過這樣的方式令愚蠢的人類幡然醒悟,但這樣的視覺奇觀嘗試構成了這部生態主題動畫的重頭戲,令畫框外的觀眾陷入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沉思。貍貓們在電影中有著多次身體變形,他們不得不異化自我融入人類社會,或者化身神怪去給人類以教訓與提醒,只有在自然中,他們才能恢復自我作為貍貓的形象,在春夏秋冬的四季時空中堅持著與自然萬物的交融生息。當其置身在生態自然環境中時,其內部的審美體驗會伴隨生態意識實現喚醒。觀者也能意識到貍貓與環境的一體性,他們不是凌駕于自然之上的異己之物,在居于城市的“變身”人類肉身的對比之下,處于自然中的肉身乃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仿佛回到了自然的母體之中,自然也不再是沒有生命的客體,兩者融合成為富有靈性的肉身。這種介入式的審美經驗,克服了人與自然的疏離和對立,形成物我一體的生態審美本性。如同我國美學家劉成紀所言:“一種理想的審美狀態,應該是人與自然在身體層面同稟物性、在感覺層面產生生命的交感、在價值層面命運相通的狀態。”
如果說身體美學在數字奇觀電影中通過角色的身體呈現出一種顯性的審美特點,那表現生命力、生命之美是大量具有生態意識的數字奇觀電影的美學核心。藝術就本質而言就是藝術家延伸自己的精神生命,對自然本源保持關注,進而實現理想化與精神化。數字奇觀電影的創作者們所秉持著的對生命的熱愛不僅停留在對人類生命的熱愛,更體現為一種具有生態整體觀的宇宙大愛,是一種對生態環鏈中所有生命之美的欣賞與愛護之心。對生命美好的歌頌正是人的生態審美本性在電影中的重要體現。首先,在女性為主角的數字奇觀電影中,體現出突破身體奇觀審美的精神生命之美。創作者開掘出基于女性生態主義審美觀的女性形象塑造,打破了英國電影理論家勞拉·穆爾維所提出的銀幕上的女性身體是為了滿足男士窺視欲的審美偏見,反而專注于女性精神生命之美的塑造,實屬難能可貴。這些女性角色在常規意義上的審美標準來看或許并不是“女神”的形象,但卻傳遞出女性深層次的精神理想和生命追求。比如《海洋奇緣》中的莫阿娜、《美人魚》中的珊珊等角色。她們的生命之美體現出強烈的生態審美使命感,莫阿娜為了歸還象征著綠色自然女神的特菲提之心而勇敢地踏上冒險旅程;窘態百出的珊珊為了保全人魚族的生命而臥薪嘗膽。其次,科幻奇觀電影基于宇宙觀基礎上展現出對所有生命的大愛。 創作者們表達著對外星生命的熱愛,對人工智能短暫生命的反思,誕生于理性科技想象的敘事中,充滿對生命詩意的贊嘆。在《E.T.外星人》中,孩子們拼盡全力也要保全外星生命的延續,對于與地球個體生命具有顯著差異的外族生命形態,激發起內心中強烈的生態審美本性,不以常規的眼光去看待生命的美與丑,而是建立起跨越時空界限的友誼。最后,這種對于生命之美崇高感的審美體驗,更突出地表現在災難奇觀電影中。為了強化人們認識到生態危機的嚴重性與緊迫感,災難奇觀往往采用極端化的視覺效果呈現出破壞性極強的場景和情節。通過逆向思維以對自然面貌的負面刻畫——地震的巨大破壞力、火山噴發的火光沖天、龍卷風呼嘯而來、氣候災難的步步緊逼等突出生命美感被極度破壞,試圖激發觀者強烈的生態自覺性。此外,在動畫奇觀和魔幻奇觀電影中,創作者們往往直接歌頌生命的多樣性。諸多動物形象登上動畫奇觀電影成為主角,從現實中取材的老鼠、河馬、兔子到暢想遠古題材的劍齒虎、猛犸象,再到真人動畫結合電影中的純數字虛擬生命構建,如《長江七號》七仔、《捉妖記》中的胡巴,構成了一個動物的繽紛奇觀世界。這些角色中不僅包括著傳統觀念上可愛、美麗的動物,也包含著具有生態環鏈之美卻曾被賦予“丑陋”定義的動物們,如《蟲蟲特工隊》中的各種蟲子、《料理鼠王》中的老鼠們等。站在生態美學的立場來看,生態審美的標準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生態系統中曾經丑陋的事物也是生態環鏈中最重要的生命環節。電影中這樣的表現契合于“自然全美論”的觀點,單獨的審美對象,均會表現出高度一致的極致美感,讓自然元素產生更大價值,而并不是一種凌亂與丑陋狀態。“也就是說所有的原始自然,必定均存在審美價值”,這意味著原生態本原的事物極具審美價值,能夠被用來鑒別與欣賞,對這種自然之美予以否定屬于不理智片面的行為表現。這要求我們轉換電影美學構建時的創作視角,不能只關注傳統意義上具有價值或者美好的生物形態,“同時也關注著早已被賦予消極審美價值的各種生物”。在魔幻和奇幻電影如《納尼亞傳奇》《指環王》《哈利·波特》中,導演們構思出充滿想象力的人與動物的結合體,比如半羊人、精靈人、半獸人、亡靈族等,諸多復雜等生命形式共同組成電影中的自然世界,他們甚至具有人類所不具備的魔法和力量,成為電影敘事中不可或缺的生命元素。這些魔幻電影具有相對復雜的世界架構和故事邏輯,但往往表現出一種對現代社會的厭倦和對自然世界的向往,為現代人尋求突破現實困頓處境找到一個想象的出口。這些影片中對與生命多樣之美的呈現,是人類探索并認可非人類生命的嘗試,突破了傳統意義上以人類為中心的生命認知。《指環王》中人類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反而由精靈、霍比特人、巫師等一同構成正義的聯盟,為突破代表貪婪欲望的邪惡勢力索倫而集體奮戰,反映出人們對于和諧世界、社會平等及生命自由的追求。
結 語
在數字奇觀電影中,生態審美本源性主要表現為自然本源和返魅之美、身體美學和生命之美。生態美學視角下的生命之美是萬物構成的整體生命的和諧、穩定和美麗,所有能量流動中的生物均平等地分享著一個整體的生態系統。著名美學家柏林特也指出:“全部生命都需要我們基于尊重與關愛,秉持敬畏之心與自然生態系統進行聯系,而對于生態電影而言,其審美必須建立在遵循自然這一前提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