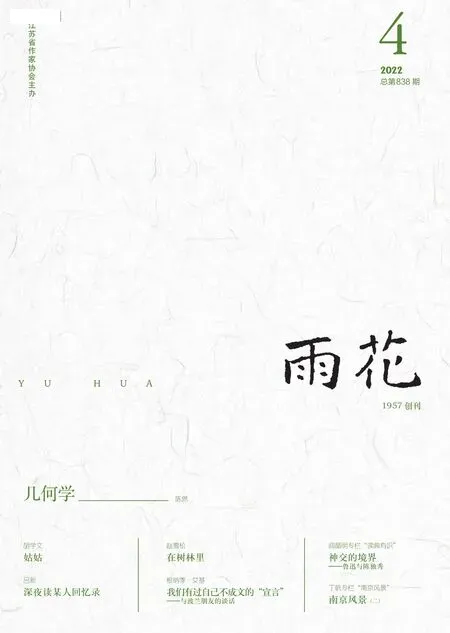素面人對一枝花
孔 灝
同此水中天
“我”之一字,自西風東漸以來,為現代人所最愛。但是,除了大家都明白的、作為第一人稱代詞的“我”之外,其實“我”字的本義是一種進攻型武器,按象形字的特點分析,是為長柄和三齒鋒刀相背狀;另一說,是象形為一人手持大戌,作吶喊示威狀。還有一種解釋是:“我”字,即古之“殺”字。根據相關學者的研究結果:“吾”和“我”,雖然都是第一人稱代詞,但是“吾”只可作主語,不可作賓語;而“我”則既可作主語,亦可作賓語。并且,“吾”是一種普通指代,呈現為一種客觀化陳述;而“我”是一種特殊指代,其重在表明個體的特殊性,是一種情意性表達。僅僅通過在字形和字性上的如此分析,就可以說明一旦對于“我”有所冒犯,必定會引起攻擊——我們的老祖宗又有智慧又有遠見,他們早早就提醒后世的子孫們:偏執于自己的“我”或侵犯別人的“我”,都是兇險的;一定要跟“我”保持適當的距離。
當然,俗語又常說: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所以,刀叢劍雨之中,也往往可以有詩情畫意在。比如,王國維先生之《人間詞話》中,就專門對詩詞中的“無我之境”與“有我之境”做過精彩的論述:
我觀王先生高論,精彩是精彩,卻還是“方便說”:因為,不管是“無我之境”還是“有我之境”,若真沒個抒情敘事的“我”和感動理解的“我”在,那么,詩在哪里?讀詩的人又在哪里?又何況,王先生所用的“無我”概念,本系佛教之專有名詞,若按佛教經典之意,那個或“有”或“無”之“我”,不過是“地、火、水、風”這“四大”假合之身的“假我”而已,因此,那虛幻假合之“我”的或“有”或“無”,又有何意義呢?
不承想,蘇東坡先生卻提前了一千年的時光隔著窗戶預先搶答說:有意義!當然有意義!
這窗外,應當是公元1081年的三月了。時年四十四歲的蘇東坡,被貶黃州。那幾年,他過得很苦、很艱難,但是,比起前幾年的牢獄之災、差點丟了性命而言,卻是不幸中的萬幸了。這一天,他的學生、也是他的親侄女婿王子立同學千里迢迢專程來看望他。老蘇大喜過望,立刻屁顛屁顛地帶著小王到處走走看看,把那當地僅有的名勝算是玩了個遍。可是,所謂“天底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啊,人小王也還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啊,終于,他來向自己的老師兼大爺告辭了。老蘇本是曠達之人,雖心中不舍,似亦并不為意,忽想了想,說:對了,還有個地方你沒去過。于是,第二天,就把這孩子帶到了當地西山的菩薩泉邊,并作詩一首《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
此歌有點民謠風,好像還有點饒舌在里面,換用今天的表演方式大致相當于:你大爺我無酒是也無錢啊,只好送你一杯菩薩泉。菩薩泉,菩薩泉,菩薩泉啊菩薩泉,是從此以后從此以后是從此以后啊,你在哪里低頭是看不見個我,你在哪里抬頭是看不見這水中這水中的天?
這樣的曲風,那自然是熱鬧之極、好玩之極的!重點是:且看這里面是“有我”還是“無我”,是不是不可不究、茲事體大?細品此詩,再想象著老蘇在自己的晚輩面前無酒無錢而又泰然自若之姿、之色,真是讓人心中不由得一動——卻原來,這家伙師出名門啊!那《論語·衛靈公》記載:
君子也會無酒無錢嗎?那是當然!但是你可知道:君子即使到了無酒無錢之時,卻仍然能夠堅持不懈地做好自己,仍然能夠堅持不懈地持菩薩心、行菩薩道、飲菩薩泉。如果一個小人到了無酒無錢的境地,那可就一定會成為一個下三爛了!
如此境界,即便面前是“淡出鳥來”的白水,也讓人想要痛飲三大杯啊!何況,這“何處低頭不見我?四方同此水中天”兩句,雖明白如口語,卻又天人合一、含義雋永,所以后世的紀昀紀曉嵐讀到此句激賞之,推其為“竟是偈頌”。照我看,“偈頌”不“偈頌”的,并不打緊,難不成和尚說話、作詩就一定高明?關鍵是:難得老蘇如此心安啊!人家不羞不臊,不卑不亢,不怒不郁,不矜不狂……
而且,還不僅僅是任性。這里面,也確實如紀曉嵐所悟,真有著一種“外不著相為禪,內不動心為定”的“硬核”在。按《楞嚴經》載:“有佛出世,名為水天,教諸菩薩,修習水觀,入三摩地。”“三摩地”者,心不散亂也,也即禪定之境。一位名叫“水天”的佛,來教導諸位大菩薩們,讓他們修習觀水之法,從而因定生慧。所以,一句“四方同此水中天”,那也可以好比是降級干部蘇大爺哄自家的小孩兒,唱了一首民族風給他聽:菩薩泉水清又清,我捧泉水送親人。飲了此水心安定,菩薩保佑你事事成……
但是我表妹說,蘇大爺這一手,可能不是學自《楞嚴經》,而是學自五代時后梁的高僧——自稱“契此”的布袋和尚。這位和尚出身農家,十八般農活那是樣樣精通。農忙之時,大師慈悲,分別答應了多戶農家助其插秧。結果,各家都看到這位大和尚在自己的田里干活,并且,當天就圓滿完成了任務。到了晚上,各家為了表示感謝,都來請他吃飯。結果,他也分身而去,欣然用餐。這時,大家才知道這位和尚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就有人請他就插秧這事做“開示”,這和尚一笑,隨口吟出一首《插秧歌》:“手捏青苗種福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凈方成稻(道),后退原來是向前。”我表妹還說,所謂“種福田”云云,也是“方便說”,說到底不過是“種心田”而已。布袋和尚的意思是,塵世中人學佛修道,無非是要保持一顆如水一般的清凈心。當一個人去除了各種欲望、各種妄念,真正“放下”,那種返璞歸真的看似“后退”才是真正的大成就!
我當然覺得我那集美貌與智慧于一身的表妹說得完全正確!比如,人問布袋和尚法號如何稱呼,布袋和尚答以偈頌:“我有一布袋,虛空無掛礙。打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又有人問布袋和尚可有行李,布袋和尚又以偈頌作答:“一缽千家飯,孤身萬里游。睹人青眼在,問路白云頭。”聽其言、觀其行、察其意,明明白白可以知道這是一位佛菩薩再來嘛!可是,當時的紛紛世人,又有幾個能夠認識到?后來,直到后梁貞明二年(公元916年)三月三日,布袋和尚圓寂于奉化岳林寺東廡下石凳上,并留有辭世偈:“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大家才知道:這和尚,原來是彌勒菩薩再來啊。
如此推衍,若依我的淺見,當不管是“水天”佛的教導也罷,還是以水為鏡觀“心”之清凈也罷,這個“水”的存在應該才是更加重要的。為什么?著名禪師趙州有名言:“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有學僧問:我看師父已經成佛了,但師父你老人家自己認為自己還算不算一位凡人呢?趙州道:我當然只是一個凡夫俗子而已。僧又問:那禪師你又是如何做凡人的呢?趙州答道:我也沒有什么玄旨,只是每天徒勞地念佛求靜罷了。學僧緊追不舍,再問:您既提到了“玄旨”二字,“玄”且不說,那究竟什么是“旨”呢?趙州道:我從不追根問底。學僧繼續追問道:禪師所說還是“玄”的問題,我現在問如何是“旨”。趙州一笑,如弟子回答老師問題一般謙虛作答:我現在正回答您的問題,不就是奉“旨”稟報嗎?趙州禪師如此言句,或許,差不多也可當作一泓清水看?
元初書畫大家趙孟頫有才女妻子管道升,見老趙有納妾意,遂寫一《我儂詞》請老趙指點:“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我觀這首《我儂詞》,就寫得比較全面,把個蘇大爺、布袋和尚和趙州禪師他們幾個反反復復、顛三倒四所說的什么“你”“我”“菩薩”“水”之類的種種名相,全都一網打盡了。
也是!當年布袋和尚圓寂后,就有人以這位老人家的生平來設問:“日日攜空布袋,少米無錢,卻剩得大肚寬腸,不知眾檀越信心時,用何物供養;年年坐冷山門,接張待李,總見他歡天喜地,請問這頭陀得意處,是什么來由?”我想:且把那個“你”或“我”,都老實認真地當作“眾生”看,再把那“眾生”都老實認真地當作“菩薩”敬,何止是答這“何物供養”“什么來由”的問題?又何止是尋那蘇大爺“四方同此水中天”的境界?你就是要達到同此“天外天”乃至同此“天外天之天外天”的境界,又有何不可呢?
成長多煩惱
釋迦牟尼佛在成佛以前,身為迦毗羅衛國太子,也是個有妻有子的世俗凡人。當年,釋迦牟尼的夫人耶輸陀羅生子羅睺羅,既是整個釋迦族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整個迦毗羅衛國的一件大事、喜事,關鍵是,羅睺羅的出世更是當時的迦毗羅衛國太子釋迦牟尼個人的一件大事、喜事!這喜悅在于——太子釋迦牟尼終于有后了!這,就算是太子給了他老爸凈飯王一個交代:咱做太子的,既然已經為你老人家的江山社稷續了香火,也就是盡完世間人子的責任了;那么,咱再正式出家修行,你做老爸的也就不能再阻撓了吧?
由此可見,所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確實是“然哉然哉”啊!而且,這故事的兩面性到這里還不算完,更大的負面在于:羅睺羅出生前的六年時間里,太子釋迦牟尼一直在外參訪修道,根本就沒有回到宮殿與太子妃耶輸陀羅同居過。那么,這孩子是怎么回事?自然,王宮內外生起各種議論,釋迦牟尼的父親凈飯王也是心中沒底,那時候,還不興什么親子鑒定之類的辦法,就只能請來一位相師入宮鑒定。這位相師很有辦法,見到這剛出生的孩子便問:“你叫什么名字啊?”那孩子竟像是這位相師的老朋友一般,不慌不忙地開口答道:“我叫羅睺羅啊。”“羅睺羅”,是梵語譯音,漢語之意即“障礙”。相師聽了大驚,忙道:“對對對,你老娘懷胎六年才生下你,你豈不正是被胎所障礙了嗎?你自己說的這個名字,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相師說完這番話,心知宮廷之事極復雜、眼前之事極難辦,一個不小心就會掉腦袋,只好又向凈飯王東拉西扯地說了幾句云山霧罩、不著邊際的廢話,連忙告退。這時,邊上立刻有大臣向凈飯王進諫:“這個孩子是他媽懷胎六年才出生,并且一落地即會說話,恐怕不祥,應該把她們母子燒死。”考慮到事情太過古怪,恐出妖孽,考慮到懷胎六年出生這事于常理實在說不通,何況家丑又不可外揚,老國王只好狠下心來,安排人挖了火坑,準備將耶輸陀羅母子推入坑中燒死。這時,太子妃耶輸陀羅合掌向天祝禱說:“這孩子真是在我腹中六年才得以出生的,如果是我說謊,理當被火燒死。但是如果有冤情,火坑中一定會生出蓮花來救我。”然后,她就抱著孩子毅然決然地跳入了火坑。片刻之間,見證奇跡的時刻到了:火坑當即變成了水池,水中生出青蓮,托住了耶輸陀羅母子。于是,太子妃的貞潔和王孫的身份終于都得到了證明!于是,天下太平,萬事大吉……這個故事,如果是讓一個搞孩子早教工作的人來講,他就可以除去羅睺羅身上的神秘光環不計,直接得出如下結論:成長這件事,絲毫耽誤不得!否則,就算你是耽誤在娘胎里,也有可能掉到火坑里去!
當然,要說這有些古代印度人的想法,那還真是腦洞大開啊!其實,根據相關記載:咱們中國的道教祖師爺老子,他的老娘更是懷了他整整八十一年才生下這孩子;而中國禪宗六代祖師慧能,也和羅睺羅一樣,在他老娘的腹中待了六年,才來到世上。這兩位在中國出生的老人家,既沒造成恐慌,也沒造成猜疑,全家人都高高興興的,將孩子視若珍寶。像那位印度大臣所說把娘兒倆都推入火坑中燒死之類的做法,是太沒有人性、太匪夷所思了……好在,時隔不久,在外參學的太子釋迦牟尼也回到家中,對此異事,即將成佛的太子運起神通一看:原來,羅睺羅的前生有一世是個頑皮的孩子。這個孩子曾經水淹老鼠洞,把幾只老鼠困在洞中六天才得以逃生。于是,今世就必須受到在娘胎里困住六年才能出生的果報。這一解釋,令朝野上下皆大歡喜,迦毗羅衛國臣民們心中最后的那塊石頭,終于落地了。
由此還可見,所謂“君子慎乎其德。有德斯有人,有人斯有土”之說,也確實是“然哉然哉”啊!即使從現代醫學的角度看,每一個人之所以能夠成其為人,也都是由數千萬乃至兩億個精子之中的一個與卵子結合,發展而來,這里面的偶然和必然,與水淹老鼠洞的故事一樣,那是有著非常相似的離奇曲折和非常明白的因果歷歷呢。同樣,人們對于自己子女的成長問題,也自然表現出了相同的重視,和因人而異的不同角度。北宋元豐六年(即公元1083年),蘇東坡剛剛擺脫牢獄之災后,貶謫黃州期間喜添了他的第四個兒子。在這孩子的滿月洗兒會上,年近半百的中年男人蘇東坡即席喜作《洗兒戲作》詩一首:“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這首詩,直寫自己對于孩子成長的祈愿,看似輕松,其實沉重;看似愚蠢,其實聰明;看似俚俗,其實深刻……有那么多摔跟頭的教訓在里面,有那么多觀世情的通達在里面,這時候的蘇東坡,真是文化精神和思想境界方面完全打不倒的“小強”啊!可惜的是,這位九月二十七日出生的孩子于次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作為父親的蘇東坡只能飽含熱淚寫下了“哭兒詩二首”,悲傷地嘆息道:“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兒,眉角生已似……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薪那免俗,變滅須臾耳。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中年喪子,悲從中來!“老淚如瀉水”之余,如何自我開解?只有宗教,只有宿命,只好面對自己空空的懷抱,檢討和反思著自己前世的“惡業”深重。
想那孩子出世之初,蘇東坡曾經對他抱有多么大的希望啊——“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熟讀《論語》的人自然知道:這“愚且魯”,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呢!說是有一天,孔子突然評價了自己的四個學生高柴、曾參、子張和子路:“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即高柴愚直,曾參遲鈍,子張偏激,子路粗魯。被孔子他老人家評定為“愚”的高柴,是東周春秋時期齊文公十八世孫,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據說,高柴身高不滿五尺,卻在魯、衛兩國先后四次為官,做過多地的縣長和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是孔門弟子中從政次數最多、時間最長的人。《禮記·檀弓上》記載說,這孩子為去世的父母守三年之喪期間,情真意切,悲哀至極,從不曾表現過半點喜色。《孔子家語·弟子行》中更是記載說:“(高柴)自見孔子,出入于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這孩子自從進入孔門學習后,言行舉止從不曾有過越禮之事,走路的時候連留在地上的人影都不曾踩過。至于曾參,則更加廣為人知。他和自己的爸爸曾點,都是孔子的學生。曾參更是直接參與編制了《論語》,親自撰寫了《大學》《孝經》等,成為儒家學派重要的代表人物,被后世尊奉為“宗圣”。就是這么一個被孔子他老人家評定為“魯”的學生,卻有著非常強烈的自省精神:“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與朋友交往,他要求自己做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對自我修煉,他立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聽老師講課,當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時,他能非常從容地應對:“唯。”然后,告訴自己的學弟們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此之“愚”人,如此之“魯”人,哪一個不是圣賢之人?哪一個不應該師以事之、終身受教?
如是觀之,所謂成長,所謂長大,那個“大”字,必定也是了不起的一個評語呢!大概,《易經·文言傳》里的一段話,或許能有所定義或者闡述吧:“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真正長“大”的人,從天地化生萬物中,想到要為人民服務;從日月星辰的燦爛光明中,想到人格要光明磊落;從四季流轉的輪回中,想到要掌握自然規律、用好自然規律;從親見親聞親歷的旦夕禍福中,想到“人在做、天在看”,所以要“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然哉然哉”!果然,要說這長大,實在是一件極難之事啊!所以,自古成長多煩惱、自古成長多曲折。但是,我們來此世間一遭,真要說這百年時間總也不能長“大”,或者說是不能往“大”處長,那,真是心中有一千個不安、心中有一萬個不甘啊!
對夏蟲語冰
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小時候不容易看到非戰爭題材的外國電影。所以,當我們在十來歲的年紀看到印度電影《流浪者》和德國電影《英俊少年》時,那樣的故事和那樣的插曲,真的是讓人驚艷不已、記憶深刻。
《流浪者》給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句話和一首歌,即“法官的兒子永遠是法官,賊的兒子永遠是賊”,以及那首“阿巴拉古(到處流浪),嗚……”;而《英俊少年》,讓我通過一首歌《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在懵懵懂懂之中,對歲月、憂傷、愛情、幸福……有了一些最初的體會、向往和感動。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這首《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源出于一首古老的愛爾蘭民歌《年輕人的夢》。在歷史上,這首歌還曾被人重新填詞,改作《布拉尼的小樹林》。到了19世紀,愛爾蘭著名詩人托馬斯·摩爾又根據這首歌的旋律,另作了一首詩歌,命名為《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詩句反復詠嘆,輕聲訴說,低回婉轉,深情追問:“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在陽光下漸漸枯萎/愛情曾輕輕拂過我的心扉/為何卻又獨自風中憔悴”“也曾綻放過最美的花蕾/也曾流露過最美的淚水/為何春天一去再也不回/為何來不及后悔心已碎”。再以后,這首歌又得到過維也納古典樂派代表人物之一、世界音樂史上最偉大的著名音樂家貝多芬的親自校訂;而德國浪漫樂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被譽為浪漫主義杰出的“抒情風景畫大師”的作曲家門德爾松則依據這首歌的曲調寫過鋼琴幻想曲;法蘭西科學院通訊院士、在法國培養起來的德國作曲家弗洛托,更是在自己的歌劇代表作《瑪爾塔》中,讓劇中人兩次演唱這首民歌……由此,《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在世界范圍內受到了人們的喜愛和傳唱。一個最顯而易見的例證就是,這首歌被用在了多部影視劇中:在電影《英俊少年》之前,一部美國故事片《三個聰明姑娘的成長》就曾選用這首歌;在電影《英俊少年》之后,日本電視劇《阿信》里,逃兵俊在雪地里為小阿信吹奏的口琴曲,也是這首歌的旋律。
沈從文說:美麗總是愁人的。這“愁”,是來自美麗的不易把握、不能長久。在沒有各種“反季節”作物的從前,過了夏天,就再也看不到“玫瑰”了!于是,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順理成章地就成了“愁”的化身。當然,這種感嘆不僅發生在西方,也不僅作用在植物身上,即在東方、對于動物來說,也是同樣。不過,東方的思想家似乎更超然、更灑脫。《莊子·秋水》里記載:北海之神認為,對于井底之蛙就沒必要與之討論海的事情了,因為它的眼界被狹小的居處所局限了;對于只能存活一個夏天的蟲子也沒必要與之討論冰雪的事情,因為它的眼界被短暫的時間所制約了。莊子他老人家的高明在于:他不愁!他不僅不愁,而且,他壓根就不理睬這回事!在莊子看來,既然玫瑰本屬“夏花”,那么,玫瑰的凋零豈非和莊子夫人的去世一樣,都是值得“鼓盆而歌”的喜事嗎?特別是,如果再有人不理解,那又有何可說呢?所謂“夏蟲不可以語于冰”啊!
這邏輯,用《論語》上的話說,就是孔子他老人家兩次長嘆過的那個現象:“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而佛教的《維摩詰所說經·觀眾生品第七》上,說得更加好玩:
話說佛教界的大德居士維摩詰長者身體有疾,文殊菩薩受釋迦牟尼佛委托前往探訪,表示慰問。一時之間,八千位菩薩、五百位阿羅漢和成千上萬的天人,都跟隨文殊師利菩薩來到了維摩詰家中,認真聽取維摩詰居士和文殊師利菩薩關于佛法的精妙絕倫的對話。這時,維摩詰的房間中有一位天女,因為歡喜贊嘆,便現身于空中,以天上的鮮花撒在各位大菩薩和佛陀座下已經證得阿羅漢果位的五百弟子身上。那些花朵落到菩薩身上后紛紛落地,但落在各位羅漢身上后,緊緊地吸附在衣服上。所有的佛弟子們各自暗暗運起神通之力,卻無法擺脫這些鮮花。于是,天女便問佛陀座下以智慧第一著稱的舍利弗尊者:“我說大羅漢啊,你干嗎要去掉衣服上的這些鮮花呢?”舍利弗尊者回答說:“出家之人,身上沾著這些花兒可就犯了儀律,失了咱佛門的威儀了啊!”這天女便說:“別扯犢子說什么這些花兒有違佛門儀律吧,花是花,佛門儀律是佛門儀律,這兩者又有什么相違之處呢?說到底,就是因為你心中有分別之念而已!如果依照佛教的儀律出家,心中仍存著鮮花和佛門儀律這兩者有區別的想法,這才是真正地不符合佛法呢!只有當鮮花和佛門儀律在心中都已沒有了分別時,這才是真正地符合了佛法!你看,各位菩薩身上都不沾著鮮花,那不就因為他們斷除了一切分別的念頭嗎?這也好比有人心中有不安之事,才會怕鬼。同樣的道理,如果佛弟子心有所懼,自然會有煩惱。煩惱積聚成的習氣不能除盡,那天上的鮮花就會沾在身上;如果把煩惱積聚成的習氣全部除盡,這花兒自己想要沾在你的衣服上,那也是沾不住的。”總而言之吧,一句話:羅漢不知菩薩的境界!
但是,由“夏蟲不可以語于冰”,進而“羅漢不可以言菩薩”,以此推演下去,天底下,還需要交流和溝通嗎?還需要理想和憧憬嗎?那么夏蟲怎么辦?那么羅漢怎么辦?就真的如印度電影《流浪者》中那句著名的臺詞所說“法官的兒子永遠是法官,賊的兒子永遠是賊”?所以,我還是固執地以為:必須對夏蟲語冰!必須對羅漢說菩薩!必須對好色者說好德者!
實際上,對夏蟲語冰,就是當年的釋迦牟尼佛告訴弟子們:“一滴水,只有把它放進大海里,才能永遠都不會干涸。”就是當年的孔子告訴弟子們:“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是當年的曾子告訴弟子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就是當年的孟子告訴弟子們:“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就是當代作家王蒙在其小說《風箏飄帶》里通過主人公在告訴我們:“人應該是世界的主人,職業的主人,首先要做知識的主人。您修傘我也修傘,您掙十八塊我也掙十八塊;但是您懂得恐龍,我不懂,您就比我更強大,更好也更富有。是嗎?”
當然,對夏蟲語冰,同樣需要條件。比如,“語”的動機、過程和后果,自然是需要考慮清楚的。又比如,在“語”和“不語”之間的取舍,自然是需要合乎法律、合乎道義、合乎習俗的。就以《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這首歌為例,唱,還是不唱,那是講究得很呢:據說在羅馬神話之中,荷魯斯偶然撞見了“維納斯”與別人婚外戀,“維納斯”的兒子丘比特為了幫自己的母親保持名節,于是贈給荷魯斯一朵玫瑰,請他守口如瓶。這位荷魯斯老兄收了人家的玫瑰之后,果然就緘默不語,最終成為“沉默之神”。這,就是拉丁成語“在玫瑰花底下”這個詞的來源。所以,在西方,玫瑰花除了表達愛情,也是嚴守秘密的象征。到別人家里做客,若是看到主人家桌子上方畫有玫瑰,就應當知道在這桌上所談的一切都不可以外傳。同樣,古代德國的宴會廳、會議室以及酒店餐廳,天花板上也經常畫有或刻有玫瑰花,也是意在提醒與會者們守口如瓶、嚴守秘密,不可以把玫瑰花下的言行透露出去。
這樣一說,似乎又把這玫瑰說得太煞風景了!英國著名詩人拜倫寫過一首詩,贈給《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的詞作者托馬斯·摩爾,詩里面說:“愛我者,我報之以嘆息;恨我者,我哂之以微笑;無論頭上的蒼穹如何不測,我對任何一種命運都不在意!”“即令我掙扎在生命的懸崖,泉水決不會枯無一滴;在我衰微的靈魂離開之前,為了你,我將啜飲不已……”雖是兩個大男人之間的贈詩,卻愣是讓人讀出情詩的感覺。也罷,“夏蟲不可以語于冰”,不配被“語”的,或者,就是我們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