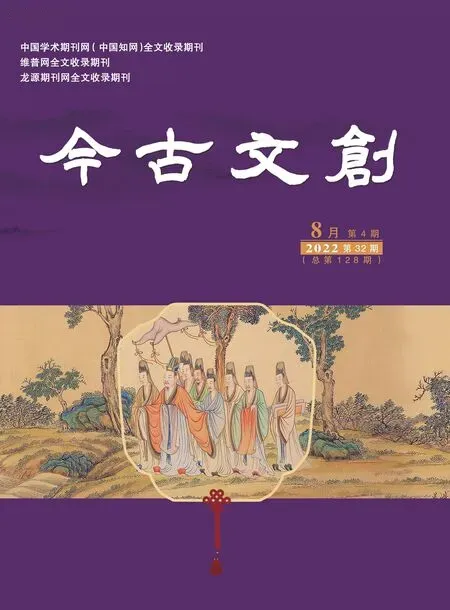《曼哈頓中轉站》中主體性的消亡
◎霍蕊麗
(西安外國語大學英文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05)
一、引言
約翰·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頓中轉站》出版于1925年,在這一歷史時期,美國確立了壟斷資本主義的統治地位,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完成促使社會生產力大幅提高。生產方式的變革帶來了富足的物質生活,也帶來了這個時代特有的精神困境。人們對“物”的崇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物化結構越來越深入地、注定地、決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識里”(盧卡奇,156)。現代物質社會富足激發了人們對財富和地位非同尋常的渴望,但物質社會所具有的單一同質性、生存被動性與合理化過程同時也在磨滅著人的主體性,誘惑人們心甘情愿地陷入精神困境。帕索斯敏銳地觀察到了他所處時代的異化,將其匯聚成文,寫出了他自己獨特的思想。《曼哈頓中轉站》聚焦于美國的城市生活,講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紐約曼哈頓各行各業人們的日常生活,小說中人物為獲得成功而努力向上攀爬,其結局卻多以失敗告終。物質社會充斥著機械、僵硬和破碎的氣息,人的主體意識在資本主義物化結構的影響下漸漸消亡。
當前,國內外學界關于《曼哈頓中轉站》的研究都大多集中于探討帕索斯高超的空間化敘事技巧和城市主題。“不以情節構思和人物設計取勝,其魅力更多地來自敘事的空間化,尤其是以‘攝像機眼’的時空并置方式展現紐約的都市風貌,通過嵌套、圓圈、拼圖等手法實現小說中共時性空間最大化”(劉英 2017)。誠然,探討帕索斯創新性的寫作技巧固然重要,卻也不能因此忽視對其創作意圖的研究。作為一名曾經的左翼作家,帕索斯的前期創作更傾向“在人們認為金錢萬能的世俗世界里,關心的卻是群體以及個人的命運”(伯科維奇)。這部小說里有巧舌如簧的律師、愛慕虛榮的女演員、虛度光陰的豪門青年,更有食不果腹的底層工人。上層社會的精神“荒原”和底層社會的窮困潦倒無一例外地證明了物化意識已經深入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盧卡奇在其著作《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強烈地批判了資本主義這一特質,揭示了物化對人身體和心靈的雙重打擊;帕索斯也在《曼哈頓中轉站》中以大多數人物的失敗與絕望警示人們資本主義物質社會絕不是人類獲得幸福的理想國。因此,本文從單一同質性、生存被動性與合理化過程等三個維度批判了物質社會對現代人主體意識的消亡作用。只有遠離“物”的重重包圍,拒絕成為“物”的奴隸,人才能真正覺醒自我主體意識,在現代生活中更好地生存下去。
二、物質社會的單一同質性
物質社會的單一同質性體現在人們的夢想趨于一種異化的一致。現代社會碎片化的生活與異化的物質需求將人生存的單一目標固定在對金錢的追求中,因此人們會陷入一種無意識的自我異化,從而逐步喪失在社會中的主體性地位。“現代‘順從的人’會感到他的生活毫無意義,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厭煩,卻沒有自由于自己認為是合適的工作,思考自己所能思考的事情。”(弗洛姆,127)在小說中,吉米·赫夫出身豪門,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但他卻“順從地”接受了資產階級“虛假”的主體意識,將人的終極追求囿于物質生活。在異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他的夢想被迫同質化,也迷失了最本真的自我。
吉米童年時期才被帶到美國生活,這片別人眼中自由的國土在他幼小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愛國情懷讓他一度忍不住想要“親吻這片土地”。成年后的吉米才明白,真實的美國社會與自由相去甚遠,反倒更像是物欲橫流的金錢帝國。與此同時,他自己也喪失了追求夢想的自由,被迫淪落為被金錢操控的提線木偶。在母親去世后,他一直接受著法律監護人杰夫姨父“無微不至”的關照。這位“好心人”以勸導的方式強行控制了吉米的職業選擇,還向他輸入自己所認同的拜金主義價值觀,即金錢是衡量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在這座異化的城市中,“人的意識發展以及人與人的關系都被不連貫的商品法則所決定和支配”(165)。吉米本想成為一名記者,但彼時涉世未深的他只有沉默和服從,最終機械地走進了別人為他規劃好的未來,“我一被解雇,杰夫姨父就幫我找到新工作”(146)。于是,吉米在機械化的安排下逐漸喪失自我意志,“我不能確定我想要什么,所以我只是原地轉圈,又無助又沮喪。”(146)更為沮喪的是,當吉米終于擺脫杰夫姨父對他的影響,成為一名報社記者后,他卻發現新聞業也不過是被金錢控制的工具,正直、自由無處可尋。
一段時間后,吉米深感新聞業的膚淺勢利,最終只能辭去報紙職務,他感覺自己成了一只“趴在一座亂七八糟城市頂上的蒼蠅。”二十世紀繁華的大都市總是以金錢為誘餌,營造出“遍地都是金子”的假象,借此消滅人們心中的個體夢想,將所有人的夢想同質化為對金錢和物質的追求。最終,吉米察覺到了真相:紐約這座由大量的香檳和美元所筑就的城市是絕非人們心中的理想之城和王道樂土。在沒有工作的日子里,吉米在街頭四處晃蕩、酗酒,這段醉醺醺的生活反而給了他逃離紐約的勇氣。在小說的結尾,他選擇搭上了一輛順風車離開這座異化的城市,但是當被問及他想去哪的時候,他也只是模糊的回答“不知道,也許相當遠。”(330)
吉米就是一種盧卡奇所說的“幻滅的浪漫主義抒情英雄:主觀性的自我滿足是其最絕望的正當防衛,更是對在外部世界為實現心靈的任何斗爭——已經先天地被看作。無望的目的且只是被貶低的斗爭的放棄”(166)。在以金錢衡量一切的現代社會中,吉米徹底失去了對自己生活的認知、向往和追求,他最終長成了與夢想中完全不同的樣子:從豪門青年變成了一個面對殘酷的社會現實無力改變反而屈服、逃離的底層青年。帕索斯利用吉米這一人物形象,揭示了當時的美國青年在世紀之初的美國社會所感到的孤獨和絕望:人們在物質社會中的主體性和選擇權會普遍地被異化的城市抹殺掉。
三、物質社會的生存被動性
在社會分工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人們迷失在富足的物質生活之中,不由自主地踏進了“消費主義”陷阱。比如,人的行為舉止和心理變化等都受到物的影響和操縱,其欲望也在無形之中漸漸膨脹。最終,人失去了自己的主體性,只能依靠物來表達自己、標識自己;物也失去了往日的使用價值,更多的呈現一種符號價值,成了地位、身份、名望等等具有人性表征的存在。人的欲望從天然的需求逐步被圈定在資本主義拜物教的框架之中。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提道:“商品拜物教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即現代資本主義一個特有的問題。”(144)在這個時代,人們普遍陷入了精神困境,小說中艾倫·薩切爾的結局就是如此。
二十世紀的紐約大都市繁華絢爛,但毫無特色。麻木的人和機械的城市相互影響,人們被動地被物質裹挾著前進。紐約時代廣場是人們心中的造夢工廠,上千塊耀眼奪目的電子廣告牌不斷吸引著各地的人們來這里尋找“金子”。艾倫也是其中一員,她被觀眾的鮮花、掌聲和舞臺耀眼的燈光深深吸引,每當她注視著光彩奪目的百老匯時,她的內心總有一種不可言說的滿足感和幸福感。艾倫看著自己所崇拜的身著綠衣騎著白馬的“當德琳”女神,幻想著自己也能成為萬人矚目的明星,殊不知“當德琳”只是一個被廣告和市場打造出來的符號。
列斐伏爾在《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指出,消費者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符號物品上,自我認同成了符號認同,最終形成了消費意識形態的認同。也就是說,艾倫自以為她所期盼的是美好的夢想,但實際上,她是將自己的夢想投射在了一個虛幻的符號上,她拼命向上攀爬只是為了成為同樣虛幻的符號。為實現這一“虛幻”的目標,艾倫貪婪地追求她心目中的成功,將婚姻當作一件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她的第一任丈夫約翰·奧格勒索普是她走向成功的第一個跳板。在其他人眼里,這樣的婚姻只能用“美女與野獸”(112)來評價,但是脾氣暴躁的“野獸”奧格勒索普能夠將艾倫從默默無聞的合唱團推上有著萬千觀眾的舞臺。她的成功比嘉莉妹妹來得更加迅速,“只要對她有利,那女孩甚至能嫁給電車”(129),艾倫在追求夢想的路上將自己變成了一個毫無感情的商品,婚姻僅僅具有她所需要的交換價值。她想:“婚姻就那么回事,對嗎。”(168)在隨后的利益交換中,艾倫變得越來越機械麻木。和奧格勒索普關系破裂后,她和有錢的花花公子斯坦恩·埃默利暗中來往,和精英律師喬治·鮑德溫調情,但又不想被任何人占有。從小說中艾倫的幾段感情經歷來看,看似是她在操控著這些執著的追求者,但實際上,是利益和欲望在操控著艾倫在應對追求者時進行機械的表演。在這種被動的生存中,艾倫的行為活動“同其人格相對立的客體化變成持續的和難以克服的日常現實。”(盧卡奇,152)在這種日常現實的影響下,艾倫最終完全喪失了其自身的主體性,僵硬被動地在異化的城市中生存。
在小說結尾處與律師喬治·鮑德溫的交往是艾倫的最后一段感情經歷,為了財富、名聲、地位,她必須和這個男人繼續周旋。但她已經不像初來乍到時那樣既活潑又自由,艾倫像發條娃娃一樣精心扮演著別人需要的角色,時時刻刻都像機械一樣呆板而僵硬:“她腳踝交叉,衣服下面的身體僵硬的像尊瓷像,周圍的所有東西似乎都變得越來越硬,并被涂上釉彩,漂浮著藍色煙霧的空氣正在變成玻璃。”(308)艾倫的結局同樣沒有逃過物質社會帶給她的命運,作為一個孤立的個體,她不得不需要這種扭曲異化的人際關系來維持體面的生活。但是在體面的背后,存在著宛如黑洞一般的精神困境,吞噬著這個年輕女孩的感情與活力。向欲望妥協的艾倫不能像吉米一樣逃離這座異化的城市,只能徹底地與之相融,她注定要在這里被動地生存下去。
四、物質社會的合理化過程
合理化過程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獨有特點,也是現代企業發展的首要基礎,勞動者和勞動組織更是要遵循合理技術的前提下進行“物”的生產。在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影響下,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也隨之改變。埃里希·弗洛姆認為,合理化是造成社會無意識的一個機制,正是因為合理化,人們會認為每個人都是受理性和道德的力量驅使的,由此掩蓋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本來產生行為的真實動機與合理化的思想是相反的。人在錯誤的行動,卻意識不到他在以不合理不道德的方式行動。在小說中,律師喬治·鮑德溫一步步從默默無聞的小律師變成了名利雙收的政界高層人物。在此過程中,他靠著非凡的頭腦和不顧一切的手段,為自己一切不道德的行為尋找合理化的借口。在真實意圖與合理化思想長期分裂的生活中,鮑德溫最終陷入了精神困境。
小說中的鮑德溫生活在繁華的紐約大都市,他從法律學校畢業后開了一家小小的律師事務所,但是三個月沒有生意上門。這時,鮑德溫在報紙上看到送奶工戈斯·麥克尼爾在工作時被火車撞成重傷,他立刻想到如果能成功辦成這件索取賠償金的案子,就能迎來名氣和人脈的雙豐收。為了將這筆生意徹底搶到自己手中,他引誘了戈斯的太太,奈莉。然而,鮑德溫并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錯誤的行動,他反而為這種不道德的行為找了合理化的借口。從主動上門的那一刻起,鮑德溫就在掩蓋自己真實的動機:“這里面涉及幾則法律條款,我覺得有責任告知您。”(42)當看到奈莉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后,鮑德溫腦海里逐漸升起一個不道德的念頭,但他卻冠冕堂皇地問奈莉:“我可以定期來這里報告案情的進展嗎?”(43)于是,單純的麥克尼爾太太完全陷入鮑德溫充滿甜言蜜語的圈套中,相信了從鮑德溫口中說出的愛意,也相信只有他能辦成這個案子。
當這場官司成功結束后,麥克尼爾一家人獲得了一筆巨額賠償,鮑德溫也開始小有名氣,認識了好幾個“有價值的大人物。”(75)然而,目的達成后,鮑德溫決絕地撇開了這段不光彩的過去,毫不留情的與奈莉斷絕了關系。做出這種決定的鮑德溫,實際上也是在和具有自我主體意識的人格分裂開來。正如弗洛姆所說,“某一種愛好(比如權力、金錢、對女人的愛好等)漸漸地控制脫離這個人的全部個性,從而成為他的統治者,也成了他所服從的偶像,盡管這個人能合理地說明偶像的本質,并賦予他許多不同的、通常是悅耳的名稱。他卻成了自身一部分欲望的奴隸。”(59)同樣的把戲在幾年后又重復上演,鮑德溫和家世顯赫的西西莉結婚,得到了他夢寐以求的社會地位,與此同時,他卻在結婚后與其他女孩緋聞不斷。種種事實被西西莉發現后,鮑德溫仍然不愿承認他們的婚姻也是他獲取事業成功的一種手段,而是絞盡腦汁地為出軌尋找合理的借口:“一個像你這樣的女人是沒辦法了解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的生理需求的。”(153)無論是和西西莉的婚姻,還是和奈莉那段不光彩的婚外情,都是鮑德溫人為給自己制造的一種幻想。他對自己的思考和選擇的自由感到如此的驕傲,認為他是在按照自己的自由意識行動。事實上,鮑德溫也只是一個被操控的提線木偶。因此,鮑德溫虛構了種種合理的說法,迫使自己相信他們之間有著濃烈的愛意,即使是出軌,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以此證明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出于合理的道德理性。
資本主義的合理化過程深深地影響了現代人的思維方式與生活習慣,“而這種普遍的生活習慣則形成了人的本身。”(弗洛姆,42)當真實意圖與合理化思想的對立成為普遍之時,人的主體性也隨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被合理化的客體。也就是說,欲望被冠以合理之名,支配了人的行為活動,人最終會陷入精神困境。鮑德溫在物質社會中不顧一切地追求著地位、名聲、權力,但是也失去了忠誠和愛的能力,在追名逐利的路上慢慢成為一個“空心的鐵皮玩具兵”(330)。這樣的結局也正如盧卡奇所說“他的心理特性同他整個人格相分離,同這種人格相對立地被客體化。”(149)因此,在異化的城市中以物質為導向而不斷向上攀爬的野心家們注定會喪失主體意識,走上一條與自由和解放完全相反的道路。
五、結語
帕索斯對自己所處時代全面異化的美國社會進行了全方位的觀察與剖析,強烈地批判了20世紀二十年代資本主義腐朽墮落的生活方式對全體美國人民帶來的不良影響。帕索斯十分關切個人命運在物質社會中的發展,他敏銳地察覺到物質社會的生存被動性、單一同質性和可計算性以及這些異化對人們生活的全方位操控。因此,《曼哈頓中轉站》這部小說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僅在于帕索斯高超的寫作技巧,還有他對整個美國社會的批判與反思和對個人命運的深切關心。所以,每個人都應具有從物質社會的漩渦中抽身并覺醒自我意識的能力,使自己能夠作為一個擁有完整人格的獨立個體在現代生活中更好地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