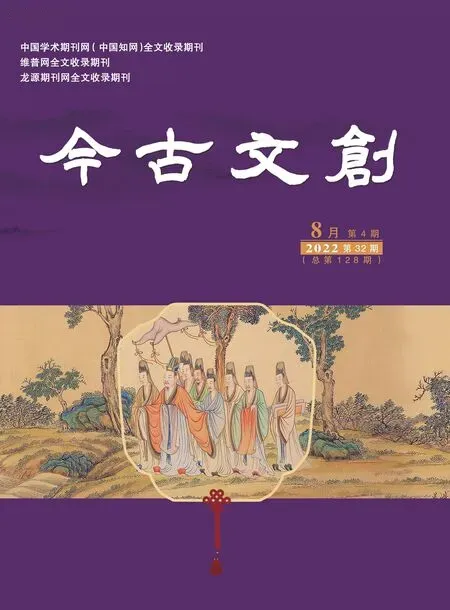“ 中庸 ” 思想
——孔子與亞里士多德政治倫理之比較
◎黃彥墁
(華中科技大學 湖北 武漢 430074)
一、兩種“中庸”思想的內容
孔子和亞里士多德很巧的都是同一個時代不同地方的兩位偉大的先哲,同時也是中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作為人類倫理思想史上的璀璨結晶,“中庸”思想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并且極大地受到了古代中國先秦和古希臘思想家的推崇。
(一)孔子的“中庸”之道
《論語》中,最早有了“中庸”兩個字——“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所說的“中庸”就是“執兩用中”,主要指的是做什么事都要掌握好適當的度,恰得其中,結果才會達到最佳。“兩”的意思是指“兩端”,而“中”向來是孔子慣用的思想方法,即在兩端之間,準確地把握其有利于事物正常運動的最佳結合點。在《論語》中,孔子把“中庸”與“過猶不及”聯系在一起,“不及”亦即離“中”還差一點,原因是太過于死板不知變通;“過”則是比“中”還要過一點,追根到底是太過于圓滑且自行其是,二者都沒有達到適度的中間狀態。而“中庸”恰恰防止了“過”與“不及”,達到恰到好處的境界,既不過火、也無不及。在孔子這里,“中庸”和其他德目如“仁”“禮”等一樣,是儒家中最重要的道德范疇,“用中”相當于“仁”、用“禮”。
在政治統治上,孔子提倡“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將“仁”視為德的核心,將賢能與政治實踐聯系起來。孔子認為最適合做統治者的圣賢——擁有中庸品質的君子。《中庸章句》中提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所以被稱為君子,無非是因為他把中庸作為自己的道德標準,并用來規范指導自己的一言一行,讓其既不過分也沒不足。孔子把君子看作“中立而不偏不倚”之人,“君子貞而不諒、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孔子非常強調“仁”,“仁”使人成之為人,一個“仁”者,是一個標榜了中庸并代表了人的生活應該是怎樣的人。所以其倫理目的和政治目的便是“天下歸仁”的最終境界。所以他認為,只要執政者都夠自身做到仁義,那么天下之民都將自覺、自愿地追隨這樣的君主,國家就能夠治理得很好。例如魯哀公曾經向孔子問什么樣的才是“政”,孔子就說:“正人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不為,百姓何從?”還有《中庸》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句話說的是人們在個人修養與治理天下的時候,得實行中庸之道,畢竟這是天下的“大本”,是最大的根本。為了鞏固統治,以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孔子竭力提倡他的中庸之道,試圖用這個來實現治國理政。
(二)亞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在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被提到,他聯系所處的社會環境,立足于中產階級,提出了中庸思想。他所提及的“中道”即是“中庸”,有“適中”“適度”之意,恰好“既無過亦無不及”。“過度與不及是惡的特點,而適度則是德性的特點”,“所以,有三種品質:兩種惡——其中一種是過度,一種是不及——和一種作為他們中間的適度的德性。”例如,在魯莽和膽怯兩種惡之間,勇敢是作為他們之間一種適度的善的德性;在揮霍和吝嗇兩種惡之間,慷慨是作為二者中間一種適度的善的德性。所以在他看來,中道是一種恰到好處的、最好的美德,也可以說是“至善”“至德”。
亞氏提倡“為政應取中道”,主張“使事物合乎正義(公平)”。城邦需由中產階級支配政權。在其著作《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覺得政治社會(城邦)最善的形態是由處于中產階級的公民組成并掌握權力,在政體與政治思想中選擇中道。古希臘的城邦公民被亞里士多德區別成三個階層——窮人、富人以及在他們中間的中產階級。窮人階級是平民勢力,他們卑微狡詐,沒有能力統治城邦,只能做被統治的那一方;富人階級是寡頭勢力,他們暴戾豪橫,不能好好地統治城邦,對城邦是有害的。這兩個階級是兩個不一樣的極端,彼此壓制、彼此對立,致使城邦傾向極度的不平衡。而中產階級為民主勢力,他們支持共和政體、統籌貧富兩個階級的利益,是過度與不及的評判者,是適度、適中的象征。中產階級既不會胡亂作威作福,也不會隨便貪圖他人財物,他們遵循中道,是貧富二者的調和者。正如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說:“由中產階層構成的城邦必定能得到最出色的治理,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如前所述,富人階級和窮人階級是亞氏所認為的兩種惡,而中產階級是處于二者之間的適度的善。所以為了避免政體趨于任何一個極端,必須由中產階級支配政權的力量,唯有如此每個公民的財物與權利才能達到一種均衡的狀態,那城邦的社會治理就會很井然有序、和諧穩定。所以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最優的政體應該是由中產階級為主要部分的政體,最善的城邦應該是由中產階級組成并由其統治的城邦。
二、兩種“中庸”思想的比較分析
(一)孔子與亞里士多德之“中庸”思想的共同之處
孔子和亞里士多德都是偉大的思想家,并且是各自思想流派的集大成者。文化是由經濟政治決定的,所以不可避免的,他們的倫理思想會為政治統治服務,而政治階級也會決定著其思想走向。
1.從時代背景的視角來看
在秦代以前,社會極其不穩定,因為是處于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過渡階段,所以時局混亂動蕩、爭霸戰爭不斷,秩序全面失控。為此,諸子百家紛紛出謀劃策,以尋求政局穩定、天下太平。在這百家爭鳴之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運籌帷幄,用儒家思想干預政治以求得統治,所以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思想,以便解決犯上作亂的大逆不道、使所有人的行為合理,然后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穩定秩序。亞里士多德所處的時代背景類似于同時期的先秦時期,當時希臘諸城邦相互對立,各城邦、各奴隸主、奴隸主和奴隸之間都有著激烈的斗爭,矛盾尖銳、政治混亂。在這樣的情況下,亞氏提出了中庸倫理,希望通過它來穩定政局,以實現“人人用中執中,以立有序”的政治統治。在他的觀點中,中庸是至善、是美德,所以亞氏特別主張中庸論,并且有理性的人都在追求“中庸”這個目標。他的看法是每個人如果遵循中庸之道,就會成為理想的道德之人,由這些人來統治城邦,就能很好地建立起一種穩定的統治秩序。人人以中道為善行德,就會是一個有序安定的政治統治,就會是一個和諧有序的社會。
2.從階級立場的視角來看
在孔子看來,“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從這里可以知道,孔子認為君子是仁愛的、無私的,能隨時隨地對所有人都可以做到適中;而小人對立于君子,拉幫結派搞小團體肆無忌憚地作亂,背離了中庸之道。作為古代中國傳統的儒家主流文化,其代表人物孔子的中庸之道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他認為只有少數人能擁有中庸之道,絕大多數人是無緣于此的。這樣看來,小生產者、奴隸等社會底層階級就是所謂的小人,他們實質就是被統治者,沒有具備中庸美德,而在統治者這里,中庸之道是其統治武器。照這看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便很明顯地體現中庸在君子和小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那是非常不一樣的,甚至是對立的。與孔子一樣,亞氏中庸觀也是為其政治觀服務的,中產階級政治論便是證據。他在其著作《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提到,每個公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追求某種“善”,例如鍛煉身體是為了追求健康、做生意及工作是為了追求財富、參與政治是為了得到權力、做好人好事是為了得到榮譽等等,這些健康、財富、權力和榮譽都是“善”的東西,會使得生活狀況整個的美滿如意,也就是所謂的“幸福”,“善”即是“幸福”。而每一個公民的幸福構成城邦的“善”,這是最高的善,有了城邦之善才有個人之善。在亞氏看來,由中產階級掌握權力的城邦是最好的善,因為中產階級擁有中庸這一美德,原因前面已經提到過,簡單來說就是他們擁有適度的財產,不會像富人那樣狂妄暴戾、也不會像窮人那樣貪婪無知,而是會利用理性去解決問題,在行為優良且合乎德性的活動中表現中庸,最終使城邦變得善的。
(二)孔子與的亞里士多德之“中庸”思想的不同之處
兩位先哲處在同一時代不同的東西方,自古以來就存在著很多的差異,無論是社會背景還是政治經濟背景等,都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各自的思想文化,毫無疑問,孔子和亞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也會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異。
1.從終極目標的視角來看
“天人合一”“致中和”,是孔子的中庸所追求的終極目標。禮崩樂壞、社會混亂動蕩,是他那個時代的明顯特征,為探索一個平衡點,實現社會穩定、達到天下太平,孔子的“中庸”的思想是一個最好不過的選擇。因其是為了統治者服務的,所以使得儒家思想頑強存在、屹立不倒,并且在很長一段歷史中居于正統地位。如前所述,亞里士多德認為每個公民的善(幸福)是中庸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在他看來,人是最重要的,做中庸等諸如此類的道德行為只是追求幸福的手段。這樣一來,雖喚醒了人們追求幸福、自由、民主生活的意識,但把個人凌駕于社會之上,那最終必然導致更激烈的社會矛盾。因此,亞里士多德的中庸觀存在某些空想意味。
2.從政治統治的方式來看
孔子不僅把中庸看作是倫理之“禮”,還把中庸看作道德之“仁”,因而在政治統治方式上提倡的是德(禮)治。根據上述我們知道,“用中”相當于“仁”、用“禮”,所以中庸的內容即是“仁”,“仁者愛人”,表現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高尚品德。由此看來,孔子的中庸所強調人的中庸行為不是法律上的,而是道德上的利他行為。區別于孔子的德治思想,亞里士多德反而更注重的是法治思想。他的中庸倫理觀與民主政體有很深的聯系,并且把中庸德行與法律接洽在一起是它的一個主要特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古希臘時期雅典城邦的民主政體淵源。根據亞氏的看法,法律在中庸的標準乃至人們對中庸的廣泛關注與接受中皆是必要的環節。在他看來,法律是城邦政治公正的基礎,公正要以法律為準繩,又因為“公正是中道”,因而法律是中庸的標準、體現著德性,同時也是德性。
三、兩種“中庸”思想在政治倫理上的啟示
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存在著一種互補性,二者之間相互有借鑒、取長補短的地方。首先,孔子的“中庸”在政治倫理上的實現路徑是從個人到家庭到國家到天下,一個擁有“仁”的人才是君子,君子遵循中庸之道才能成為圣賢,才能管好一個國家,才會促進天下大同。亞里士多德的“中庸”在政治倫理上的實現路徑是從國家(城邦)之善到市民個人的善,認為只有城邦管理好了,底下的公民才會好。總的來說,孔子的“中庸”最后所要追求的終極目標是集體人的穩定、天下人的太平,而亞里士多德的“中庸”最后所要追求的終極目標是個體的幸福、個體的自由自主。所以,亞里士多德的“中庸”可以從孔子那得到的補充是多關注集體,關注整個集體社會的幸福,而不是把個人的利益和幸福凌駕在集體之上,因為這樣容易產生沖突、加劇社會矛盾。
其次,孔子重“德”,以“仁”和“禮”為標準,所以圣賢在統治臣民的時候要重視“以德治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比較了道德與法律這兩種方式之優劣后,孔子更注重于道德,認為道德教育比刑罰的手段更適合穩定社會的秩序,更符合封建社會宗法血緣關系上的政治倫理秩序,有著比刑法更為優越更為持久的生命力。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中庸是美德的特性”,因為美德是“以居中者為目的的”,而法律是中庸的衡平。他強調“法”,強調法制教育,用法律的公正、正當精神促進公民成為一個至善至德的人,因為他認為整體是由部分構成的,所以實現了個體的善,進而也就實現了城邦整體的善。因此中產階級在治理城邦的時候要公平、適度,“以法治國”。這樣看來,作為孔子和亞氏不同的政治倫理追求,“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各自在內容和形式的體現上表現出顯著的差異,然而實際上都是為了實現人類社會的和諧,達到至善至德。顯然二者之間是非常可以互補的,一個可以加強關注法治,一個可以多多關注德治,從而形成“德法結合”的模式,發揮孔子和亞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在政治倫理維護社會和諧上的作用,在道德與法律之間找到一個合適的度,為執政者提供更合適的統治國家的思想,實現社會穩定、有序發展的最終目的。
總的來說,孔子和亞里士多德這兩個分別是東西方先哲,在同一時代并且都提出了類似的“中庸”思想,這很神奇也很有意思。兩種思想在政治倫理上存在著相同點和不同點,通過分析這些,找出他們的互補之處,這對于兩者、對于政治倫理都是有著一定的思考性和意義的。特別是在當今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利益關系越來越復雜,在兩種治理方式德治和法治中應該選擇怎么樣的一種方式,就可以從孔子和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倫理上的“中庸”思想得到很多有益的啟示。
①王林森:《統戰工作的智慧——執兩用中》,《中國統一戰線》2013年第6期,第77-78頁。
②《論語·堯曰第二十》。
③《禮記·哀公問》。
④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49頁、第56頁。
⑤呂振:《論亞里士多德中道觀與先秦儒家中庸思想異同》,《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第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