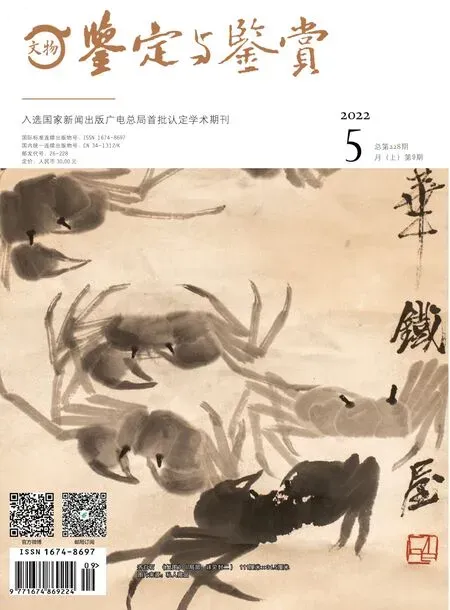從曾侯乙墓編鐘看東周時期禮樂文化
張銘浩 郝旺
(1.山東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2.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2)
1978年,曾侯乙編鐘在湖北隨州出土,包括一件不能演奏的樂器——镈,共65件。曾侯乙編鐘的出土可謂“震驚世界的地下音樂寶庫”,整套編鐘數目之大,保存之完好,真實地為世人展現出當時作為國君的曾侯乙享用器物的組合情況。曾侯乙編鐘作為先秦時期編鐘發展至高峰時期的代表,其完整性為研究東周時期的物化禮樂和政治典制提供了豐富資料,同時也為研究這一時期禮樂文化的演變軌跡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證據。
1 禮的內涵和由來
禮是古代社會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制度性規范,是中華民族精神形成的引導性因素,同時也是中國文化區別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根本性特征。禮在中國古代以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出現,“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對于禮的形成和發展,現代學者產生了幾種不同的看法:①郭沫若的祭祀起源說;②楊寬的禮儀起源說——原始社會中的禮儀被用作維護社會秩序、鞏固社會組織和加強部落之間聯系,后來逐漸作為鞏固統治階級內部組織和統治人民的一種手段,“周禮”就是屬于這樣一種性質;③楊向奎的交易起源說——宗周時期貨物的交易行為帶有濃厚的禮儀性質,后來周禮中逐漸減少了禮儀中的商業性質;④陳戍國的多元起源說——禮制是層疊地構成的,也就是說禮制的所有部分不是在同一個時間產生的,而是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起源,然后逐步走向完善。正如吳十洲所說的那樣,“中國禮制的產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產生于形成的最初階段是與宗教聯系在一起的,后來禮作為政治權利分配的確定因素,用來調整君與神、君與臣、官與民、夏與夷以及貴族之間的政治關系”。
關于禮的起源,有學者也進行過相關考古學研究:人類早在舊石器時代就有意識地規劃出用來埋葬死者的墓地;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墓地與居住地往往相隔不遠,也沒有嚴格的喪葬制度;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后,出現公共墓地,與此同時各地區的禮儀風俗也表現出了不同層次的差異性,逐漸出現對祖先的崇拜祭祀和以“薩滿”或“巫”為特點的一系列宗教祭祀活動;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規模不斷擴大,部分墓葬甚至出現了殉葬現象,不同文化類型的內部族群之間的社會等級得到更為清晰的展示,隨葬品的數量和質量也出現明顯不同,而喪葬禮儀中的隨葬品的數量和獻祭儀式標志著對祖先的崇拜已經同社會等級秩序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進而成為社會制度的一部分,并最終伴隨著國家形成而完成。
關于禮字,最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學者發現與其內涵相近的“豐”,王國維在《觀堂集林·釋豐》中對這個字進行過相關釋義:“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謂之豐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豐。”郭沫若對這個字也進行過同樣釋義:“從字的結構上來說,是在一個器皿里盛兩串玉具以奉事于神。《盤庚篇》里面所說的‘具乃貝玉’,就是這個意思。大概禮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來從示,其后擴展而為對人,更其后擴展而為吉、兇、軍、賓、嘉各種儀制。”《說文解字》中也記載:“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商周時期開始,原先帶有宗教色彩的禮儀活動的內涵發生變化,逐漸朝著倫理化與政治化的方向發展,最終伴隨國家形態的形成而最終完成。
2 禮樂制度的形成和特點
周禮是在殷代乃至更久遠之前的禮節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論語》中就有“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形成了一整套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禮儀為表象的宗法制和分封制。統治者將神權、祖權、政權三者結合,從而得以構成一個獨特的禮制性社會。這樣一來,從國家政治的角度來看,是周天子對“天命”的絕對獨占性和權威性的體現;從血緣宗族的結構來看,是宗法分封制正常維系運行的一種重要表現。
關于周禮的形成,最早見于《左傳·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禮。”《尚書大傳》言:“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衛侯,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禮記·明堂位》記載:“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楊華認為兩周時期的禮樂制度的形成經過了成、康、昭、穆等諸王近百年的發展完善,真正的禮樂文化從周穆王時期到公元前500年左右。在這一時期,禮樂制度在事實上已趨于完備,并將整個社會的制度和文化結構包含其中。就周禮的實質而言,已經不單單是一種儀式,而轉變為一種兼備國家管理與協調社會等級關系的一種政治制度。
禮樂制度,是禮制與樂制的結合,“不知音者不可與之言樂,知樂則幾于禮矣”。《禮記》中對此有頗多描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圣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禮是體現行為舉止的規范和原則,而樂是為了禮的順利實施而做的補充,“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禮樂制度在形成后對各級貴族的生活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各級貴族的行為上至國家祭祀,下至步履行動都被賦予了大小不同的政治意義,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也正如楊華在《先秦禮樂文明》中所敘述的那樣:“禮和樂相輔為用,都具有為統治者的政治服務的特點。禮是從外在的客觀的強制的方面來規定臣民的等級名分,使統治得以穩固;而樂則是從內在的主觀的自然的方面來使臣民服從于宗法制的等級規范。”
禮樂制度最為直觀的表現形式是相關禮器的使用,禮器是專門與禮行相關的特殊器具。禮器,從縱向關系看產生于自發的祭祀用器與權力象征物,慢慢發展為表示不同等級的禮用之品;從橫向關系來看是表示政治權利的媒介之物,主要體現在國家和貴族的各種禮儀中。禮器制度是這一時期王權與分封制度的產物,主要體現在不同等級的貴族對禮器的管理與分配。君王將不同品級的禮器賞賜或分配給不同等級的貴族,以維持統治集團內部的穩定秩序,這是禮器制度最重要的政治功能。在持有禮器的社會群體中已構成了明顯的尊卑、貴賤及上下之關系,而嚴密的典章制度成為其社會集團安定的重要保證之一。禮器的使用一旦超過原有的限度,就被認為是“非禮也”,而區分的主要標準就以禮器的組合標準、數量關系來確定并標志貴族的等級關系。
伴隨著周王室衰微,原有的關系與秩序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壞,并直接導致以周王為中心的等級制度逐漸失去根基。但與周王室地位下降相比,禮器的使用混亂具有更加明顯的表象,以周王為主的禮器授受形式基本不復存在,相比之下的是諸侯國內部、諸侯間的授受逐漸豐厚起來。此外,雖然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紛爭直接導致舊貴族等級制度的瓦解,但地方諸侯國內部勢力的增強迫使禮器制度朝著新的方向發展,被稱為“僭越”的現象發展得日益明顯且頻繁,諸侯內部分封形式也逐漸普遍起來。
3 曾侯乙編鐘與樂懸制度
中國是最早制造和使用樂鐘的國家,樂鐘主要有甬鐘、紐鐘、镈鐘等類,并按相應次序進行組合,稱為編鐘。無論是《詩經》《周禮》等傳世文獻資料,還是目前已知的考古資料都證明,在宗周時期實行的禮樂制度,鐘、磬等金石器共同構成了王宮雅樂的基本體系,而這些金石器也成為這一時期宗法等級制度的物質載體,鐘樂也只為高等級貴族服務,“諸侯之大夫,未蒙君賜,在私家不得有鐘磬與镈之樂,其有之者,蓋出于特典”。這樣一來,由這些金石器發出的“金石之聲”與周禮規定出的社會制度規范互為表里,“揖讓而治天下”共同維系宗周政治體系的穩定。
編鐘是研究周代物化禮樂制度最具代表性的器具之一。西周中晚期編鐘體制的建立,標志著西周禮器由早期的重酒器與重食器體制到中期的重食器與重樂器體制,尤其是樂器體制的出現并逐漸走向成熟。在以編鐘為主的青銅樂器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是被作為主要的隨葬器陪葬于天子、諸侯等一些高等級貴族墓葬中。依照《周禮·春官》中“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的記載,一些高等級貴族將編鐘等金石器作為陪葬器,是一種傳統禮制身份的傳承。“禮者,謹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雖然編鐘作為隨葬器已經失去了樂用功能,但作為一種禮器,仍然是墓主身份等級證明的重要標志,并且可以將其作為分析和解釋社會組織的主要研究對象,來說明人類社會在發展中實現的層級分化、族群分化、區域互動等問題。兩周時期的喪禮通過舉哀、隨葬、祭祀等制度,與用鼎、用鐘等器物使用制度相結合,加之所蘊含的等級名分之要義,將社會信仰與社會統治相結合,進而反映出當時整個社會所信奉的一種思想價值觀。
而樂懸是指通過有差別地排列起編鐘、磬等單獨或組合樂器而形成的一種編懸結構,并且以天子“宮懸”為主要標志,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是指懸掛起來的鐘磬類大型編懸樂器;廣義是指各類金石器組成的大型堂上樂、堂下樂等,主要應用在吉禮、賓禮、嘉禮中。樂懸制度不僅是樂制的核心,同時也是體現鐘磬音響和貴族身份的專門方式。所謂“大夫無故不徹縣(懸),士無故不徹琴瑟”,就是這個道理。
出土于湖北隨州的曾侯乙鐘是先秦時期編鐘發展至高峰時期的代表。鑒于曾侯乙在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通過墓室內物品的碳十四鑒定、中室內镈鐘上的銘文和棺槨內的骨架鑒定,并結合同時期東周墓葬內的一些典型器物進行對比,綜合推斷,認為曾侯乙墓屬于戰國早期的墓葬。
墓內中室的樂器有:編鐘1架,有鐘65件,分三層懸掛在鐘架上;編磬1架,有磬32件;鼓3件;瑟7件;笙4件;排簫2件;篪2件。出土時,基本保持下葬時的陳放位置。編鐘靠南壁和西壁立架放置,鐘體還多懸掛在鐘架上;編磬靠北壁立架放置;建鼓靠東南壁,靠近編鐘;瑟、笙、簫等列于鐘、磐、建鼓所構成的長方形空間內。其中以編鐘、編磬、建鼓為主的“鐘磬之樂”與以鼎為主禮器構成的“金石之樂”共同呈現出諸侯鐘鳴鼎食的禮樂場景,與東室以琴、瑟、笙等竹木樂器構成的“絲竹之樂”形成了鮮明對比。
《周禮·春官》記載的樂懸制度:“正樂縣(懸)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玄注:“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四面象官室,四面有墻,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表面看曾侯乙所能受用的“軒懸”之制似乎與周禮典制吻合,但加以分析后發現,曾侯乙墓編鐘仍需依靠北面的編磬才能構成三面“軒懸”之制。并且需要注意到的是,曾侯乙編鐘在懸掛擺放制度上的差異不能在其他地區同等級的貴族墓葬隨葬樂器考古發掘資料中得到印證,也就是說我們無法直接證明曾侯乙墓編鐘是依據標準的禮制進行擺放的。
張聞捷在《葬鐘陳列與周代樂懸制度》一文中,將曾侯乙墓與同時期的同等級貴族墓葬中鐘磬組合所形成的樂懸形制相比較,得出結論:樂懸制度在東周時期普遍流行,但貴族群體只是在表面形式模仿《禮經》中所記載的多面樂懸制度,并依據具體需要對隨葬鐘磬進行調整,從而體現一種“事死如事生”的觀念,但這并不能反映出如西周時期禮樂一樣的等級秩序,更主要的是貴族間凸顯自己身份地位的一種象征手段。因此這一時期的墓葬中所展現出的折曲鐘磬應是一種形式化的樂懸,其蘊含的祭祀禮法意義與宗法政治意義正逐漸消退,向世俗化的方向轉變。
因此,這一時期社會的變革帶來的是文化的轉型,禮樂文化最直接的轉變就是從敬祖、敬神轉變為娛人,已逐漸喪失最初配合政治宗法體制所起到的教化輔助功能,只剩供人享樂的軀殼。與此同時,被形容為“靡靡之音”的民間絲弦樂盛行,甚至在戰國中期幾乎取代了“金石之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但不管怎樣,曾侯乙編鐘的擺放、“一鐘雙音”的特質、音域跨度之廣、“合瓦式”的樣貌、各國律名的排列等都體現出它是周代禮樂活動的重要禮樂之器。
4 結語
西周中晚期,特別是“昭王南征而不復”后,王朝的中央權力不斷弱化,一直以來奉行的宗法分封制等一些重要的制度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各諸侯之間也從原來的宗法關系轉變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個體,禮樂制度從傳統的天子禮法變為諸侯禮法,成為諸侯間的一種秩序規范。禮樂制度一方面繼承了春秋以來的發展和完善,另一方面為了滿足諸侯間交往日益頻繁的需要在形式上不斷發生變化,這一時期的禮,愈來愈多地表達一種現實理性的原則,而不是傳統的宗法親親原則,并且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禮樂越來越流于表面而不再注重于內在等級秩序,在春秋中期到春秋晚期將近兩百余年的時間里成為體制。曾侯乙墓內編鐘和大量絲弦樂器的出土說明原有的禮樂制度逐漸被僭越,這一時期的貴族們追求自我享樂,因此原先以宗法等級功能為主體的雅樂也逐漸被陶冶性情供人娛樂的絲弦樂所替代。而樂的崩壞表明,這時的禮樂制度已經不能夠繼續被某個諸侯個體乃至與整個社會所需要和接受,樂從禮的附屬中擺脫出來獲得新的發展。隨著新興的地主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禮樂制度也變得黯然失色,最終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①陳戍國,陳雄.從“周因殷禮”到“周文郁郁”——西周宗法禮樂制度的建構[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114.
②楊寬.古史新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38.
③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56.
④陳戍國.中國禮制史:先秦卷[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10.
⑤吳十洲.兩周禮器制度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13.
⑥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220.
⑦王國維.觀堂集林[M].北京:中華書局,1956:290.
⑧郭沫若.十批判書:孔墨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82-83.
⑨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7.
⑩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21-2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1:633.
?孫希旦.禮記集解[M].王星賢,沈嘯寰,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842.
?楊華.先秦禮樂文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2.
?孫希旦.禮記集解[M].王星賢,沈嘯寰,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990.
?孫希旦.禮記集解[M].王星賢,沈嘯寰,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992.
?孫希旦.禮記集解[M].王星賢,沈嘯寰,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982-983.
?楊華.先秦禮樂文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73.
?吳十洲.兩周禮器制度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24.
?胡培翚.儀禮正義[M].段熙仲,點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459.
?連秀麗.青銅禮器與禮樂制度的歷史沿革[J].北方論叢,2005(6):2.
?孫詒讓.周禮正義[M].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1899.
?楊英.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先秦禮學與禮制研究[J].古代文明,2019(3):4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曾侯乙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461-463.
?孫詒讓.周禮正義[M].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1823.
?張聞捷.葬鐘陳列與周代樂懸制度[J].音樂藝術,2020(1):1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