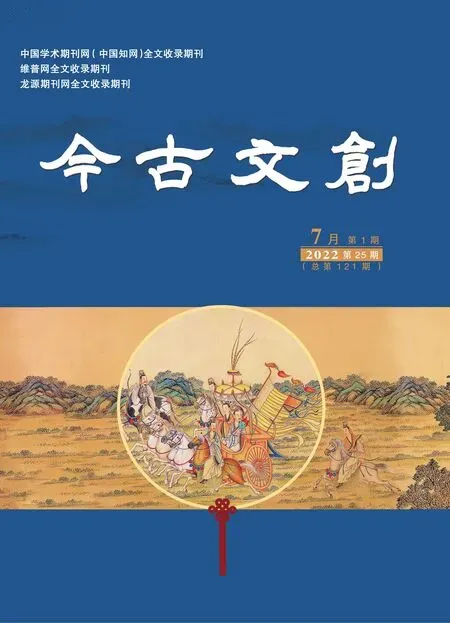從《政治學》第一卷看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隸說
◎余 游
(重慶交通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重慶 400074)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第一卷提出了自然奴隸說,此理論漏洞百出,常被后世所詬病。但是,批判容易,而要回答亞氏這樣的大哲學家為何竟會犯如此低級的錯誤,批判者們卻回答不上來。盡管有些人認為,這明擺著出于政治需求。可實際上在認真研讀原著后發現,亞氏的真正動機遠不是出于政治需求,而是完完全全地為了其形而上學理想。
一、亞氏提出自然奴隸說的動機
很多人會因為亞氏生于遠古而輕易地體諒他犯錯的原因。可是,憑什么一個頂尖形而上學家會為了世俗的政治利益而輕易地犧牲對真理的追求?經研究發現,亞氏自然奴隸說其實更多的是與形而上學耦合,因為二者都具有其關鍵特征:對范疇普遍性的追求。
古希臘史學家保羅·卡特里基認為,當時在希臘奴隸主群體中,自然奴隸說其實已經是非常流行的觀點了。在公元前4世紀的下半葉,在希臘世界數以萬計的奴隸中,非希臘人出身者占了多數。由于希臘人戰勝了波斯人,就產生了一種非希臘人自然低劣的看法,亞氏不僅接受了流行的看法,并且有意強化它。
卡特里基并沒有明確指出亞氏的動機,但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亞氏的這個理論不過是已經非常盛行的觀點。但這個說法最大的問題在于,既然亞氏只是把民間奴隸主的奴隸觀搬到臺面上來講而已,可為何又要絞盡腦汁地通過復雜的形而上學邏輯來“添油加醋”呢?萬一被某個聰明人看出其邏輯漏洞豈不是丟盡了大哲學家的臉面?
此外,更主流的說法則將其與亞氏的政治理想聯系起來。希斯認為“我們總是可以將其解釋為意識形態偏見的產物”。毛利云也認為,城邦中的自然奴隸是公民所做政治決斷的產物,是為使城邦中一部分人能夠實現人性所期許的卓越而不得不做出的犧牲。
以上觀點看似非常合理,但這仍然解決不了一個疑惑:如果非要通過邏輯來論證自然奴隸說的合法性,又何必漏洞百出呢?還擺出一副嚴謹的形而上學架子?因此,想要知道亞氏的真正動機,就必須重新解讀他的論證過程,嘗試體會亞氏所舉的每一個例子,回到那個時代與亞氏本人對話,才能得到答案。
二、形而上學與自然奴隸說的耦合點
(一)減少個體性,增加普遍性
那么,形而上學是如何淋漓盡致地體現在亞氏的自然奴隸說中的呢?首先,就是要搞清楚亞氏一直所堅持的整體自然主義。
整體自然主義是亞里士多德奴隸觀最大的特點,它有一句名言:“人類天生是合群的動物,必須過共同生活。”其實現在仔細一看,才發現“天生”與“必須”這兩個詞用的是如此篤定,難道不顯得蹊蹺?任何一個政治家在論證自己的政治觀點往往是基于科學的邏輯論證,結果亞氏竟自以為是地以自己的名義來為這兩個大前提命題背書,想必也肯定不是為了其政治理想,否則豈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實際上,亞氏一直有著一個形而上學夢,形而上學的本質就是對普遍性的終極追求,最終達到一種類似于“奇點”一樣的第一范疇才是亞氏的目標。然而亞氏發現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人作為個體分散開來就必然意味著普遍性的喪失,這種“熵增”現象使得亞氏百思不得其解,個體性越突出,就意味著越難以歸納出普遍性。所以,亞氏才要千方百計地試圖重新建立起政治生活中每個混亂個體間的穩固聯系,這也是為了將人類社會完美地嵌入到自己龐大的形而上學體系中。
他充分意識到了個體的貪婪與邪惡,脫離了城邦法律的約束,必然越來越混亂。所以,亞氏不得不將人作為“天生的政治動物”,并將其作為一種自然法納入城邦的法制當中,以此來規制個人的欲望,從而使得原本混亂無序的人類個體通過城邦法制這個強行塑造出普遍性的制度工具,變得越來越具有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其實就是亞氏一直所追求的“善”。
在亞氏眼中,人類個體組成社會從來就不是為了獲取和交換物質生活資料。只要能夠減少個體性、增加普遍性,能夠想方設法地構成一個有序運行的城邦共同體,具體用什么邏輯解釋也不重要了,不管嚴謹或粗糙,只要是稍微像樣點兒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都可以塞進自己的論證過程之中,畢竟這都只是一個論證工具而已,只要最終能夠證明自己的論點即可。
因此,亞氏就喜歡這種具有普遍性的東西,哪怕是強行捏造出來的論據,用形而上的“善”來獨斷地說明形成共同體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也要證明自己的理論。
明白了這個思想特點,也就明白了亞里士多德的奴隸觀了。簡而言之,亞氏的奴隸觀就是整體自然主義在家庭組織層面中的反映。前面提到的整體自然主義的核心內涵就是在于減少無序性,增加普遍性,從而服務于他的形而上學體系。所以,在城邦社會的組織層面,在整體自然主義的意義訴求下,個體就應為城邦服務。
(二)自然奴隸是增加普遍性的有效工具
同理,在家庭組織層面,奴隸就應該為整個家庭的正常運轉服務,而整個家庭的權力集中在奴隸主身上,所以亞氏就必然要為主奴關系存在的正當性做必要的辯護。盡管這種辯護與城邦組織層面的論證一樣牽強附會,但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白為什么亞里士多德認為將奴隸視為天生的自然的就能使家庭、奴隸和主人提高普遍性。
首先,城邦由家庭構成,所以,一個個穩固的家庭是穩定的城邦的基礎。其次,奴隸作為社會中的少理智者,恰恰是最容易侵犯法律的群體,所以,通過主人對奴隸的規訓,可以增加奴隸的普遍性,因為理智本身意味著有序,所以少理智甚至無理智者的存在是亞里士多德大為反對的。
最后,主人也通過奴隸在經濟上為主人輸送的有序而變得有序。但要說明的是,奴隸向主人輸送的有序是身體勞作機能的有序,身體勞作機能的有序是為主人和奴隸所共有的,但多理智者通過吸收奴隸的有序,從而節約自己身體勞作機能上的有序,間接增加自身理智思維機能上的有序,最終使得自己作為主人個體以及整個家庭的總的有序性和普遍性增加。在這里,身體勞作機能與理智思維機能實際上就對應著馬克思所說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
亞氏無法拒絕這樣一種大大增加普遍性的途徑,這就是亞氏奴隸觀的根本出發點和動機。亞氏的家政學實際上也是此理論的延伸發展,也反證了此理論的正確性。亞氏花了很少的篇幅來論證自然奴隸的合法性,隨后便主要地探討家庭管理的技術,這就充分說明了亞氏論證奴隸的最終目的是落腳于家庭,而不是單獨地重視奴隸本身,關鍵還是要致力于找到整個家庭、整體城邦繁榮穩定的組織方法,奴隸的死活與地位不重要,就是要犧牲他們的個體性才對。
三、具體的論證過程
(一)對自然法前半部分的論證
以上為結論,后文將展開具體的論證。對于善于利用三段式的亞里士多德來說,要想論證一個命題的合法性,首先就是要找到它的上一級范疇。通過論證上一級范疇的合法性,從而證明此命題范疇的合法性。所以,要證明奴隸天生就存在的合法性,亞里士多德就要首先找到一個更高一級的“法”,然后將奴隸納入這個更高一級的法的約束對象中,即可證明奴隸的存在是合法的。不過,這個法應該是自然法而不是人為法,否則就失去了普遍必然性。因此,亞氏找到的這個自然法便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且這種關系不僅是必需,而且是有益的。
不過,這個自然法首先得要經過論證才行,畢竟這個自然法還不至于像“人都是動物”這樣的命題一樣輕易地令人信服。而作為大前提,則必然只能用歸納法來論證。他首先證明的是前半部分,即要證明“在一切形成組合體的事物和一切由部分構成的事物中,無論它們是連續的或分離的,其間顯然都存在著統治元素和被統治元素的區別。”
他首先舉了一個非生命的例子,比如在一首歌曲中,一定存在著主旋律,其次才是和弦與和聲。他又舉了一個有生命的例子,比如動物是由靈魂和肉體構成的,靈魂居于統治地位,肉體被靈魂所統治。這兩個例子盡管看起來全面,既涉及了生命,也涉及了非生命。不過,亞氏還是明顯地感覺到這兩個個例還是缺少普遍性,于是緊接著又補充強調了“我們應該來考察在那些本性得以保持的事物中,而不是在被敗壞的事物中,其本性目的是什么,所以我們必須了解在最完善狀態下既具有肉體又具有靈魂的人,因為在他身上我們才能看到這兩者的真正關系。”
“雖然在壞的或在腐敗了的狀況下,肉體似乎經常支配著靈魂,因在壞時它們就處于邪惡和背離自然的狀態。”也就是說,亞氏也意識到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地位是可能轉變的。例如一首樂曲中原本的和弦和聲也可能在某個時間段“喧賓奪主”。
這樣的“補充”盡管完善了亞里士多德的歸納,卻又同時破壞了自身的演繹。對于那些無法解釋的反例,亞氏索性冠以“敗壞”的名頭,同時又沒有對事物為什么會發生“敗壞”做出任何的解釋,這樣的推理明顯牽強附會。
(二)對自然法后半部分的論證
在對“法”的前半部分做了粗劣的論證后,亞里士多德緊接著便開始了后半句的論證,即要說明這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是“有益”的,論證方式同樣是歸納法。
他首先將靈魂和肉體進行了二元對立。他說,靈魂統治肉體就是自然而且相互有益的。相反,二者平起平坐或者低劣者居上則總是有害的。接著,他開始舉例論證:被人類馴養的動物就比野生動物更馴良,正是因為他們相對野生動物具備了更多的理智,也因此它們的生活比野生動物更為安逸。
正好由于當時的女性地位極其低下,亞里士多德便大膽地將男女關系也遷移到了此論證之中。他說,雄性更高貴,而雌性則低賤一些,一者統治,一者被統治,這一原則可以適用于所有人類。所以,那些只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了自己的肉體而沒有用到理性的人來說,如果沒有外界的約束即主人的管教,僅憑他們自己是不可能做出任何好事情,只會給自己、給其他人、給整個城邦帶來無序性。但是,大自然卻通過賦予奴隸適合勞作的強壯身體,使其與主人適合理智思考與政治生活的優勢互補,從而使雙方都能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四、對邏輯漏洞的整理與解釋
(一)前半部分的邏輯漏洞
至此,亞氏便完成了對后半部分的論證。而且在論證末尾也順便把兩個范疇的定義收納工作完成了,最終得出“主奴關系作為一對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是天生的、自然的且相互有益的結論”。
回顧他所篩選的例證,可以看出,這些例子都具有明顯的刻意選擇性,其余很多反例都被主動排除掉了。而且,他如果不解釋這些反例的存在,說不定會更有說服力,但卻在前半部分的論證中強行地將這些反例冠以“腐敗”的名頭,可以說是赤裸裸地“賊喊捉賊”了。
那么,怎樣的例子完美地達到了亞氏的篩選標準呢?首先就是要既符合“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又符合“必需且有益”。其次,最好與人類有類似的性質,這樣就可以更好地將此理論運用到主奴關系中。經過他的精心篩選,動物的“靈魂與肉體”便成了他的理想例證。
不過,這個選擇的邏輯漏洞仍然非常明顯。首先,如果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存在著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種元素,那么明顯與他的實體學說產生沖突了。因為亞里士多德對實體下了一個基本的定義:“實體,在最嚴格、最原始、最根本的意義上說,是既不述說一個主體,也不依存于一個主體的東西。”實體是“不用述說他物的終極載體。”是若按此定義來看,若某事物統治另一事物,則必定可以述說被統治事物,而被統治事物也必然依存于統治者。這兩個理論明顯自相矛盾了。
(二)后半部分的邏輯漏洞
此外,亞氏關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是必需且有益的關系也明顯存在著主觀臆斷的問題。因為必須與有益本身屬于一種價值判斷,而價值的基本定義就是指客體能夠滿足主體需要的關系。所以,對客體的屬性和功能的價值判斷必須基于確定的主體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另外,即使對于同一主體和客體,也有可能在不同的時間、階段產生不同的價值效應。而亞里士多德不僅直接默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為主客體關系,還錯誤地獨斷了他們的價值判定都是正向的、積極的。
然而,在實際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這兩個元素構成的系統中存在著三個可以被判定價值的對象:一是統治者;二是被統治者;三是整個系統。亞里士多德本應從三者的角度分別考察,但他卻簡單地從統治者的利益需求出發,忽視了后兩者作為主體的價值判定或者說錯誤地對其進行了判定。
例如,在他舉的第一個例子中,被馴養動物的“馴良”僅僅是從人類的利益需求角度來看的。因為“馴良”是相對于野生動物的“野蠻”而言的,而這種“野蠻”與“馴良”卻是由人類捕獵動物時的難易程度來定義的。當人類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將動物捕獵變成食物時,姑且就稱之為“馴良”。當人類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去捕獵時,就稱之為“野蠻”。
而如果將主體轉換為客體,即被馴養的動物身上,表面上看起來因為有人類的飼養,所以生活看起來似乎要比野生動物更加“安逸”,這也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對“安逸”的定義仍然是人類的獨斷定義,也許對于動物而言,被飼養而不用親自覓食并不是它們想要的安逸。相對于這種被圈養的生活而言,親自覓食本身就是一種有趣的生活方式,又或者他們根本不想為了獲得所謂的“安逸”而犧牲掉“自由”。
當然,以上從動物角度出發的價值判斷仍然只是主觀臆斷罷了。這個問題是哲學問題,不能簡單地用生物科學來解答,畢竟“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