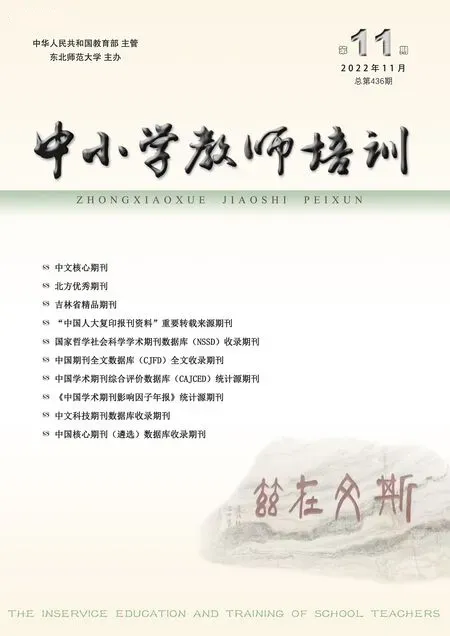從靜態文本到動態過程:具身認知視角下寓言教學路徑研究
陳 文, 董文婧
(1.成都市龍王廟正街小學, 四川 成都 610000;2.成都市錦江區教育科學研究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中繼續強調語言文字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信息載體[1]。其中,語文課程面向全體學生,圍繞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充分發揮其獨特的育人功能和奠基作用。在具象認知視角下,身體是語文發生的本體,因為語文的發生或發聲無不源于身體[2]。由此可見,語文的學習一定是具身的,而非離身,身體參與于語文學習的方方方面面。寓言作家拉·封丹說:“一個寓言可分為身體與靈魂兩部分:所述的故事好比是身體,所給予人類的教訓好比是靈魂。”[3]由此可見,寓言的學習也離不開身體意識的覺醒,離不開身體認知的范圍。特別是在“雙減”背景下,語文學習的目標、內容、空間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轉變,而寓言的目標、知識、空間也必須做出一定的改變。此種背景下,具身認知理論為學生寓言的學習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為寓言教學的更新和發展提供了新的實踐方式。
一、新課標實施推動寓言教學觀念轉向
新課標中提出以語文實踐活動為主線,以學習主題為引領,以學習任務為載體,整合學習內容、情境、方法和資源等要素,設計語文學習任務群。學習任務群的安排注重整體規劃,根據學段特征,突出不同學段學生核心素養發展的需求,體現連貫性和適應性。在此種背景下,教育必然做出新的改變,而教學也同樣面臨著新的挑戰。寓言教學作為語文教學的下位分支,在“雙減”背景中,其目標、知識和時空等都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
(一)寓言目標:知識技能轉向核心素養
“雙減”表面直指作業的變革,作業作為教學中不可缺少的環節,作業的變革實際是教學的變革,實際是教學目標的變革。寓言用一個短小的故事表達深刻的道理,在日常的教學中,寓意的教學是整個寓言教學中重中之重,有很多教師會讓學生背誦寓言的寓意,抄寫寓言的寓意;而忽略了教學過程中,學生對寓意的理解,特別是一些寓意離學生的生活比較遙遠,學生就知識死記硬背地將寓意記住而已。減少這種生硬的背記作業,必然促進寓言教學要往更深化的方向發展,即轉向語文核心素養的實踐,轉向語言的建構、思維的發展、審美的鑒賞、文化的傳承。同時2022年版義務教育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創造性地提出“課程核心素養”概念,對語文教學提出的新的要求,也更突出了語文核心素養實踐與落實的現實需要。
(二)寓言知識:教學符號轉向教學情境
科學主義認為普遍、永恒和客觀的知識是我們永恒的追求,因此知識更多是一種規律,一種抽象化的存在。“雙減”強調人的主體作用,人的身體機能,高濃度、高抽象、高速度的知識傳授遠遠超越了學生的身體負荷,學生的近視率直線上升,學生的身體素質急速下降。大量符號知識堆積充斥了學生的大部分時間,寓言學習中,學生可能體會不到《亡羊補牢》的懊悔,感受不到《掩耳盜鈴》的可笑,寓言的知識性學習占據了文本本身的趣味性。因此,在“雙減”的背景中,在身體回歸的呼吁下,教學符號必然需要向教學情境轉變。
(三)寓言時空:課外轉向課內
“雙減”對校外機構的規范,促進學生的學習必須轉向課內,這倒逼課堂質量必須提升,課堂必須做到全員覆蓋,做到身與心的全面參與。這對于寓言教學來說,提升課堂教學的趣味性、參與性成了重點,寓言教學不能再僅僅以考試為目標的背誦寓言,而是要真正促使學生在課堂中感知故事人物形象,對文本進行重構和結構,與人物一起同呼吸、共命運,讓故事成為身體的一部分。這樣,才能抓住學生涌入課堂的時機,抓住學生的身與心。
二、具身認知理論與寓言教學的耦合
具身認知源起于現象學和生物學,胡塞爾強調意識體驗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梅洛-龐蒂提出人類實際上是借助身體與外界進行交互的,應該重視身體的體驗。而后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等人從生物學的視角出發,認為認讀認知來源于多感官身體所產生的不同經驗,并且身體的感知功能會天然融入一個更寬廣的物質、文化、心理等的具體情境中[4]。實際上,具身認知是指在認知加工過程中,人的身體發揮著關鍵作用,認知主要是通過身體各種感官在環境中的交互體驗及其活動形式而形成的[5]。由此,可以看出,具身認知強調人身體的參與,強調與環境之間的交互,強調實踐過程中身體的體驗。那么,進一步而言,具身認知正好為寓言教學提供了有效的啟發,寓言的故事性和寓意的實踐性正是寓言教學所重點強調的。在教學場域中,寓言與具身認知理論的相遇,必然產生耦合反應。
(一)寓言故事中的真情境
好的寓言閱讀教學,首先是引導學生探尋“有靈魂的身體”。寓言是短小精悍的故事,故事有人物、有情境、有曲折、有沖突,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去尋找身體的美。這樣的身體美是由情境所烘托和渲染的,寓言的故事性必須在真實的情境性中,讓認知發生,此時的認知是和身體同在的,是文化符號所賦予的真實,它來源于文化同時又是文化基礎上的一種再生。在真實的情境中,寓言的故事性得到最大的擴張,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人物的心理、語言、動作、表情都得以活靈活現。在寓言教學中創造真實的情境,其實在日常教學中我們經常會發現有很多教師會讓學生來演繹,例如《守株待兔》中演示農夫、演示其他的宋國人等。此時,情境雖然創造出來了,但是并非真實的情境,只是一種形式上,或者物理環境上的情境,并沒有讓學生真正走進去。具身認知理論認為,認知活動不是脫離情境、孤立于大腦的抽象符號運算,而是發生于一定文化環境中,受到情境因素的制約[6]。由于寓言的文化環境不同,我們在創造情境時是根據文化背景而來,同時也要為學生鋪墊一定的文化背景。在分析文化背景的同時,也要對文本進行細致的解讀,如進行閱讀、思考、理解、想象、揣摩、欣賞、表達。只有在文化情境和文本分析到位后,真實的情境體驗才可能發生,才能真正理解人物,理解故事,為提取故事的寓意奠定基礎。
(二)寓意訴求實踐與反思
寓意是整個寓言故事的中心,是語言故事傳遞給世人的道理。經常在教學過程中,在得出寓意后,我們會讓學生聯系自己的實踐生活,舉例說一說自己身邊是否有這樣的人或者事,但此時學生可能覺得寓言中的人和事都離自己太遠了,很難舉出比較貼切的事情。具身認知理論認為,認識不是一種表征和計算,而是一種以適應環境為目的的實踐活動。在這種實踐活動中,我們主要是通過身體的經驗來形成認知,思維、判斷、意象、隱喻、情緒和想象等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我們的身體構成、身體組織和感知—運動圖式相關聯。人的認知是身體、環境、活動三者協同作用的結果,它總是發生于社會實踐過程中[7]。基于此,如果對寓意理解得不夠充分,我們是沒有辦法做到精確聯系到自己的實踐生活的,也很難通過得出的寓意對自己的認知、思維、想象進行反思。此時,教師必須使用大量社會生活實踐中的例子,引導學生明確寓意的精準使用,再聯系到生活中的自己,再聯系到自己的生活,才能將自己的身體、活動、認知、環境融為一體,真正接納、理解、反思寓言的寓意。寓意的理解與具身認知的實踐與反思才真正在認知場域相遇并發生意義。
三、具身認知視角下的寓言教學原則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指向學生的核心素養發展,具有情景性、實踐性和綜合性,結合具身認知理論的啟示,因此,寓言教學過程中需要注意情境性、實踐性、動態性、反思性等原則。
(一)情境性
具身認知理論不再強調抽象符號的形式操作,強調認知必須從“離身性”與“去情境化”轉向“具身性”與“情境化”。那么在寓言教學過程中,就需要盡量做到為故事創造出真實的情境,或用朗讀、或用劇本、或感悟修辭、或用文化鋪墊等,不同的寓意有不同的故事情境,不論運用什么樣的手段,將情境營造得越逼真、越有氛圍,那么就和故事人物貼得更近,就更能從身體上感知故事的溫度,更能通過身體形成思維認知的發展。
(二)實踐性
具身認知理論認為,身體是認知發展的第一接收器,那么在寓言寓意的辨析中,不可或缺實踐性的原則。寓意的實踐實際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己的親身體驗,另一種是替代性社會體驗。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身體的反映,獲得認知。如《掩耳盜鈴》中,雖然每個人都知道,捂住耳朵僅僅是自己聽不見了,別人能聽見,但是如果真的將自己想象成那個偷盜鈴鐺的人,捂住自己的耳朵,將身體參與其中,將故事情節進行實踐,就能更加深刻地體會到這個人物的諷刺意味。寓意必須聯系生活,如果自己真的沒有經驗和認知,那么此時引導學生思考身邊人的替代性的經驗,再將自己代入其中,也是一種良好的實踐。
(三)動態性
具身認知強調靜態的表征必須轉向認知的動態發展,知識結構不是給定的、靜止的,具身認知認為認知結構具有時間屬性,即結構有其發展過程,隨時間的展開而變化。也就是說認知的過程并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發展的,是經歷和體驗發展的過程。這種動態性要求在寓言教學過程中,對學生的學習要求并非是固定的,是隨著學生年齡和學段的發展,不斷螺旋上升的過程。不同學段中,寓言教學的具身要求不同,如低段是聲音的反映,中段是動作的反映,高段是認知思維的再創作。
四、文本到實踐:具身認知視角下寓言教學路徑
具身認知理論讓人通過身體的視、聽、觸等多種感官真實地感知世界,這些觀點和理念為寓言教學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過程、教學評價等多方面都帶來了不同的思考。
(一)教學目標的時間性
人的認知發展會隨著時間的不同,而產生動態的變化。在具身認知理論下,寓言的教學目標也不應該是一成不變的,因此,基于具身認知理論,不同學段的學生用身體認知寓言的形式應該是不同的。在梳理部編本教材的寓言故事中發現,寓言故事主要集中在中低段,高段的學習相對較少,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部編本教材的寓言故事
對于低段的學生來說,寓言教學的目標主要定在朗讀上,學生通過朗讀感知寓言故事的有趣和寓言形象的可笑,學生在讀中感悟故事的情境性,認知寓言故事與其他體裁的不同。對于中段的學生來說,主要是講好寓言和演好寓言,通過對寓言角色的分析,講出故事的可笑、滑稽或諷刺,同時可以通過編寫劇本、演繹劇本等方式,將身體投入到寓言故事的感知與創作中,感知人物的語言、表情、動作、心理。對于高段的學生來說,主要是對寓言進行實踐,實踐自己根據寓意創編寓言,在實踐過程中鑒賞、反思、比較寓言的不同,反思生活情境,在實踐中促進語言表達的發展。
(二)教學內容的情境化
寓言具有極強的故事性,這和具身認知所強調的情境性是不謀而合的。在寓言教學中,需要為學生營造真實的情境,這種真實的情境的方式較多,可以通過朗讀,用不同的語音語調或者人物的對話,創造情境;可以通過補白的方式進行,故事中的人物可能會想什么、說什么、做什么動作……,在不斷補白的二次創作中,促進學生進入情境之中;還可以運用劇本演繹創作的方式,讓學生將寓言改變成一個劇本,將所有人物賦予其更突出的戲劇色彩,然后通過身體的演繹,感知故事的變化與沖突,從而更深刻地理解寓意。寓言創編中需要給予寓言創作導學單進行支架的搭建,經過“明確主題道德/寓意—鋪設可笑的行為—寓言人物設定—故事內容—寓言名字—表達手法—插圖設計”等七個步驟來推進,豐富教學內容的情景性。
(三)教學過程的實踐性
寓言教學的過程需要注重實踐性,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親身體驗、感悟、認知寓言故事的情節,對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有自己的感悟和體驗,最重要的是讓學生在實踐過程中,將自己的身體動用起來。例如三年級專門的寓言單元,《陶罐和鐵罐》中陶罐的材料和鐵罐的材料,在課前讓學生觸摸這兩種材料,感知它們各自的優缺點,然后再來看兩人之間的對話,就不會有陌生感和距離感。這是課前的實踐,對于課后的實踐,學生在理解寓意的基礎上,可以進行書簽、小報等的制作。例如L校三年級的學生,在學習寓言單元后,在快樂讀書吧推薦的《中國古代寓言》《克雷洛夫寓言》和《伊索寓言》等書籍后,根據自己對故事的理解,將自己覺得很有啟發的小故事寫在書簽的頂端,然后通過繪畫展示寓言的重點情節,最后在書簽的背面寫上寓言故事的寓意或者自己的感想。不論是親自感受材料的不同,還是動手制作寓言書簽,學生都在親身的實踐過程中,進一步內化寓言所想要傳達給世人的道理。
(四)教學評價的表現性
寓言教學的評價主要是采用表現性評價,在“雙減”背景下,對學生的考核主要通過實踐性作業,那么具身認知理論的指導下,主要對學生的表現性、參與性進行評價。寓言的學習并非是靜止的,是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整個學段的學習,在此學習過程中,由于每個年段的目標不同,那么每個年段的評價目標也是不同的。從橫向來劃分,可以將寓言學習的評價放入每一課的課后、每一學段的期末。從縱向來劃分,可以將寓言學習的評價利用檔案袋的方式,裝入寓言評價袋中,如一、二年級學生錄的故事音頻可以放入袋中,三、四年級,學生做的寓意小報、寓言讀書筆記、寓意書簽、寓言劇本、寓言演出視頻,五、六年級,寓言實踐的再創作或者直接創作,寓言的鑒賞與反思。六年下來,每個學生的寓言檔案袋記錄了學生對寓言的認知,對寓言動態變化的理解、對寓言的全面參與情況。
總之,新課標的到來,寓言教學的改進,其運作過程必然從靜態的文本解析走向動態的過程實踐,只有重視學生的主體性、主動性、生命性,才能將寓言的道理與學生的認知匹配起來,具身認知理論為寓言教學的進一步發展和研究,帶來了新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