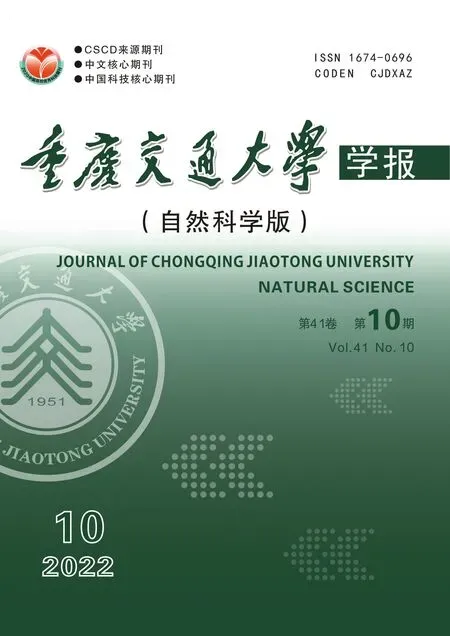高速列車車輪與高速道岔可動心軌接觸分析
張 軍,田志鵬,牛 巖,馬 賀,鄒小春
(北京建筑大學 城市軌道交通車輛服役性能保障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44)
0 引 言
道岔是列車實現軌道轉換重要的線路設備,對列車的運行速度和安全有重要影響[1]。列車在通過道岔區段時,輪軌垂直方向的動力不平順比水平方向高出很多。因此,與普通線路相比,道岔區的養護工作更大,使用壽命更短[2-4]。車輪與道岔型面的合理匹配,對提高列車行駛穩定性、改善列車通過曲線的能力、降低輪岔接觸力和磨損、提高輪岔使用壽命及保證列車運行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在道岔區動力學方面,大量學者通過建立動力學模型,對列車通過道岔區的安全性、平穩性及動力學響應進行了分析[5-7];還有學者通過動態仿真模型,對道岔區心軌的關鍵型面進行優化[8-10]。
在道岔區靜力學方面,有學者對高速道岔轉轍器區段的輪軌接觸力學行為進行了研究[11];王大奎等[12]通過實際測量可動心軌及車輪型面,計算了不同車輪在心軌不同位置處的接觸狀態;溫澤峰等[13]采用數值分析法,對2種不同型面的輪對與鋼軌滾動接觸時的接觸幾何、蠕變率和摩擦功進行了分析;M.WIEST等[14]通過建立4種不同的輪岔接觸模型,為研究輪軌接觸區的彈塑性結構和蠕滑提供了理論依據。
以上成果對研究道岔區輪軌動態相互作用及輪軌接觸行為具有重要意義,但以往研究大多對固定轍叉進行分析,對因列車長期運行導致車輪型面改變,進而引起高速道岔可動心軌區段輪軌接觸狀態變化的分析較少。對此,筆者以60 kg/m鋼軌18號可動心軌道岔心軌部分為研究對象(圖1),對CRH5型動車車輪與可動心軌的幾何形狀進行實地測量并建立三維有限元模型,研究不同車輪與可動心軌的接觸狀態,為進一步優化可動心軌型面提供參考。

圖1 60 kg/m鋼軌18號可動心軌道岔
1 車輪與可動心軌計算模型建立
為分析車輪由長心軌運動到短心軌的接觸過程,分別建立了標準及磨耗后車輪與磨耗后心軌的三維有限元接觸模型。通過采集大量CRH5型動車車輪型面并進行篩選,選出磨耗量最大的型面,記為磨耗后車輪型面,如圖2。相較于標準車輪,磨耗后車輪的輪緣及踏面均產生磨耗,磨耗量分別為5.96、0.70 mm。

圖2 標準與磨耗后車輪型面比較
利用鋼軌型面測量儀,對可動心軌軌頂型面進行測量。由于可動心軌為變截面結構,因此選取心軌關鍵截面進行測量。以可動心軌尖端為基準,取距可動心軌尖端220~300 cm的區段,每隔20 cm對鋼軌型面進行一次測量,所測得的可動心軌型面如圖3。

圖3 可動心軌型面
將測得的可動心軌型面和不同車輪進行匹配,建立距離心軌尖端230、240、250、260、270、280、290 cm的輪岔接觸有限元模型。圖4為車輪-可動心軌接觸有限元模型,列車車輪直徑為915 mm。由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接觸區應力遠大于非接觸區應力,為獲得較為清晰的結果,同時節省計算時間,在網格劃分時,接觸區網格密度較小,非接觸區密度逐漸變大,接觸區單元網格的最小邊長為1 mm。車輪有限元模型共62 693個節點,58 062個單元;可動心軌有限元模型共28 539個節點,25 137個單元。

圖4 輪軌接觸三維有限元模型
建模時車輪材料彈性模量取200 GPa,泊松比0.3,屈服極限600 MPa;可動心軌材料彈性模量取210 GPa,泊松比0.3,屈服極限490 MPa,車輪與可動心軌材料本構模型采用應力-應變雙線性模型,如圖5。輪軌間摩擦系數為0.3。

圖5 車輪與可動心軌材料本構模型
可動心軌及標準軌底部采用固定約束,長心軌與短心軌間施加綁定約束,約束車輪兩端橫向、縱向位移,并對車輪的轉動進行約束,在車軸軸箱處施加垂向的集中載荷8.5 t(動車滿載軸重17 t)。
2 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分析
2.1 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斑分析
圖6為距可動心軌尖端240、250、260 cm處輪岔接觸斑。距可動心軌尖端240 cm處,車輪僅與長心軌接觸;在距可動心軌尖端250 cm附近,車輪與長心軌和短心軌共同接觸;在260 cm處,車輪只與短心軌接觸,此時車輪已完全從長心軌過渡到短心軌。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匹配時,接觸斑呈橢圓狀,形狀狹長。

圖6 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斑
表1為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斑的面積及縱、橫向長度,可知接觸斑面積最大為111.40 mm2在距可動心軌尖端250 cm處。在車輪完成從長心軌向短心軌過渡后,接觸斑面積逐漸增大,這是因為隨著短心軌軌頂不斷變寬,車輪與短心軌接觸更加充分。

表1 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斑情況
2.2 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等效應力分析
圖7為距可動心軌尖端240、250、260 cm處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等效應力分布。距可動心軌尖端240 cm處,最大等效應力主要分布在長心軌上,其值為629.4 MPa;距可動心軌尖端250 cm處,車輪同時與長短心軌接觸,長心軌與短心軌都有等效應力分布,但最大等效應力由長心軌轉移到短心軌上,其值為556.8 MPa;距可動心軌尖端260 cm處,短心軌上的最大等效應力繼續增大,其值為595.5 MPa。
在距可動心軌尖端240、250、260 cm處,最大等效應力從長心軌向短心軌轉移,短心軌上的最大等效應力值不斷增大。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隨著距可動心軌尖端的距離增加,短心軌軌頂不斷增寬加高,使短心軌逐漸承受軸重。
表2為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在不同位置處接觸時最大等效應力。接觸斑面積在距離可動心軌尖端250 cm處最大,等效應力值最小,為556.8 MPa;接觸斑面積在距離可動心軌尖端290 cm處相對較小,且接觸斑形狀狹長,車輪載荷施加在小面積鋼軌上,因此等效應力在此處最大,為662.7 MPa。

表2 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最大等效應力
在距可動心軌尖端230至290 cm區段關鍵位置處,可動心軌材料的屈服極限值均低于輪軌接觸產生的最大等效應力值,列車在反復通過可動心軌區段時,車輪頻繁與可動心軌進行接觸,可動心軌會產生磨耗,嚴重甚至會造成剝離等破壞。
2.3 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等效塑性應變分析
表3為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最大等效塑性應變值。距可動心軌尖端240 cm處等效塑性應變值最大,為1.205×10-2,距可動心軌尖端250 cm處等效塑性應變值最小,為8.063×10-3。在距可動心軌尖端230至290 cm區段關鍵位置處,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均產生等效塑性應變,可動心軌會產生磨耗。

表3 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最大等效塑性應變
3 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分析
3.1 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斑分析
圖8為距可動心軌尖端240、250、260、270 cm處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斑。較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相比,磨耗后車輪從長心軌向短心軌過渡區段相對延長。在距可動心軌尖端240 cm處,車輪只與長心軌接觸;與可動心軌尖端相距250至260 cm區段,車輪與長、短心軌共同接觸;與可動心軌尖端相距270 cm處,車輪只與短心軌接觸,且接觸斑逐漸向短心軌外側移動,此時車輪完成了從長心軌向短心軌的過渡。

圖8 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斑
表4為磨耗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斑的面積及縱、橫向長度。接觸斑面積在與可動心軌尖端相距230 cm處最大,為119.36 mm2。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斑沿縱向的半軸長度較沿橫向的半軸長度大,但相差數值相對較小。因此,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的型面匹配相較標準車輪更加良好。

表4 磨耗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斑情況
圖9為距可動心軌尖端290 cm處接觸斑。此處短心軌頂面上的接觸斑出現了不連續現象,接觸斑分成了兩部分,車輪與短心軌間產生了兩點接觸,這是輪軌接觸中的一種常見狀態。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磨耗后的車輪與這段鋼軌的接觸區內存在縱向“凹陷”,“凹陷”內所對應的區域與車輪并不產生接觸,因此形成了條形間斷接觸斑。

圖9 距可動心軌尖端290 cm處接觸斑
3.2 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等效應力分析
圖10為距可動心軌尖端240、250、260、270 cm處可動心軌等效應力分布。距可動心軌尖端240 cm處,最大等效應力分布在長心軌上,其值為569.0 MPa;與可動心軌尖端相距250、260 cm處,車輪與長、短心軌共同接觸,但均在短心軌上產生最大等效應力,在260 cm處短心軌上最大等效應力相對250 cm處較小;距可動心軌尖端270 cm處,車輪已完成過渡,等效應力完全轉移到短心軌上,此時最大等效應力為605.1 MPa。

圖10 不同接觸位置的心軌等效應力圖
表5為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在不同位置接觸的最大等效應力。距可動心軌尖端270 cm處最大等效應力值最大,為605.1 MPa;在距可動心軌尖端230 cm處,接觸斑面積相對最大,此處最大等效應力值最小,為501.4 MPa。

表5 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的最大等效應力
3.3 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等效塑性應變分析
表6為磨耗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最大等效塑性應變值。距可動心軌尖端270 cm處,輪軌接觸最大等效塑性應變值最大,為9.759×10-3(最大值位于270 cm處短心軌,250 cm處數值并非長短心軌相加,兩者是獨立的);距可動心軌尖端230 cm處,最大等效塑性應變值最小,為5.326×10-3;距可動心軌尖端250 cm處,長短心軌同時產生塑性應變,這是由于此處為車輪過渡區段,車輪與長短心軌共同接觸,使長短心軌同時產生磨耗。

表6 磨耗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最大等效塑性應變
4 標準和磨耗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對比
4.1 接觸斑對比分析
圖11為標準和磨耗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斑面積變化曲線。通過對比標準和磨耗后的車輪在相同截面位置的接觸斑總面積可以發現,與標準車輪相比,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的接觸斑面積更大。這是由于經列車運行,車輪踏面發生磨耗,磨耗后車輪踏面形狀和可動心軌匹配更好,因此接觸斑面積有所增大。

圖11 接觸斑面積變化曲線
4.2 等效應力對比分析
圖12為標準車輪與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最大等效應力變化曲線。在車輪同時與長短心軌發生接觸前,最大等效應力值均呈先增大后減小的趨勢,同時接觸后,鋼軌等效應力均成先增大再減小,后再增大的趨勢。此處以車輪與長短心軌同時接觸為分界,標準車輪在250 cm處同時接觸,260 cm處結束;磨耗車輪在250 cm處同時接觸,在270 cm處結束,后同。除距可動心軌尖端250 cm和270 cm處外,與標準車輪相比,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的最大等效應力值更小。這是由于相對標準車輪,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斑面積較大,等效應力值相對較小。相比于標準車輪,磨耗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狀態更加良好,但兩種接觸情況的最大等效應力值仍大于可動心軌材料的屈服極限,在車輪與鋼軌的反復接觸過程中,同樣會造成鋼軌磨耗。

圖12 最大等效應力變化曲線
4.3 等效塑性應變對比分析
圖13為標準車輪與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最大等效塑性應變曲線。在車輪同時與長短心軌發生接觸前,最大等效應變值均呈先增大后減小的趨勢,同時接觸后,等效應變值均成先增大再減小,后再增大的趨勢(同4.2節),其變化趨勢與輪軌接觸最大等效應力變化趨勢相同。除距可動心軌尖端270 cm處外,與標準車輪相比,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的最大等效塑性應變值更小。這是因為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等效應力值較小,相比于標準車輪,磨耗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狀態更加良好。但兩種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均產生塑性應變,鋼軌均會產生磨損變形。

圖13 最大等效塑性應變曲線
5 結 論
筆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建立標準XP55車輪和磨耗后車輪與60 kg/m鋼軌18號高速道岔可動心軌的接觸模型,利用有限元分析方法求解計算,得出接觸斑形狀及面積、等效應力的大小及變化規律。根據計算結果得出以下結論:
1)列車通過可動心軌區段時,均由長心軌向短心軌過渡,且相較于標準車輪,磨耗后車輪的過渡區段相對延長。
2)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的接觸斑面積均小于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的接觸斑面積。標準車輪與可動心軌匹配更易發生應力集中以致加劇輪軌磨損。
3)標準車輪和磨耗后車輪與可動心軌接觸時,在可動心軌表面均產生應力集中,且最大等效應力值均大于鋼軌材料的屈服極限,可動心軌出現塑性形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