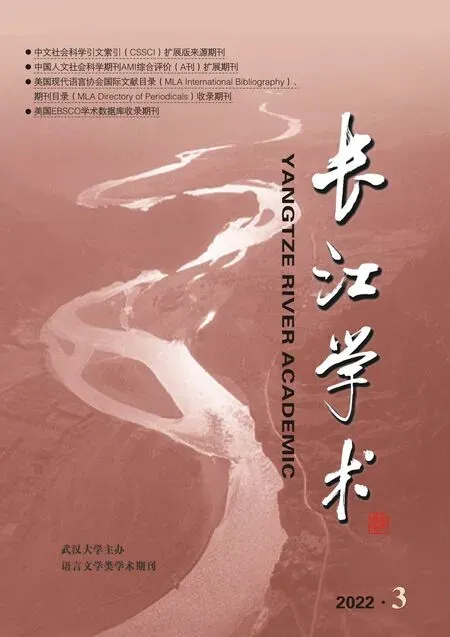車中被背叛的女人:張愛玲《封鎖》對莫泊桑《羊脂球》的多重反轉
〔日〕藤井省三
(東京大學 文學部,日本 東京113-8654)
一、《封鎖》——發生于反轉之城上海的反轉愛情
1937 年7 月中日戰爭爆發,中國雖在首戰中浴血奮戰卻仍不敵日軍攻勢。11 月上海、12 月南京,1938 年10 月武漢、廣州等從沿海到內陸的主要城市均已被日軍占領。美英法所有主權的上海租界區相對于廣大的淪陷區來說儼然成為一座孤島,但隨著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戰爭的全面爆發,上海租界也最終被日軍接管。從1941 年底到1942年初,日軍借口發生恐怖襲擊事件,連續在南京路、浙江路等鬧市區和閘北、楊樹浦等居民稠密地區實行封鎖,嚴禁市民出入。劉惠吾所編《上海近代史》中有如下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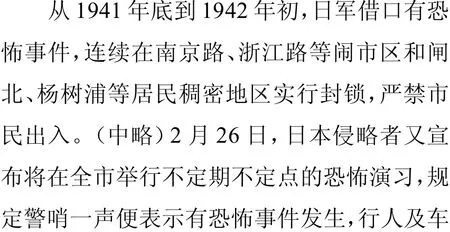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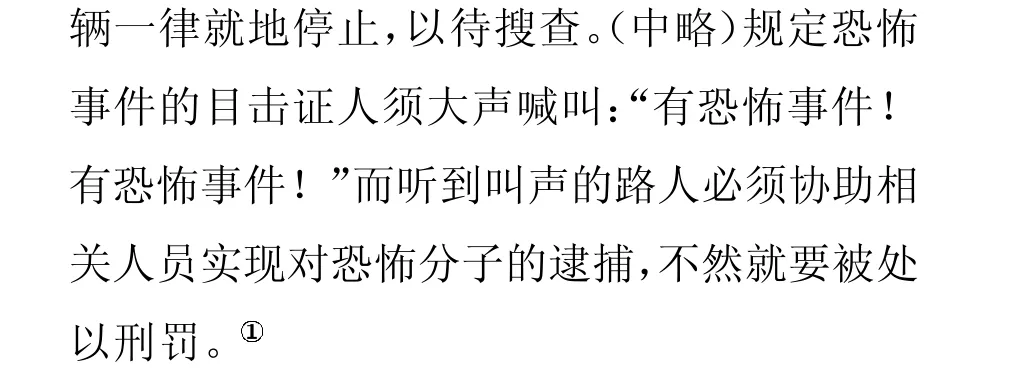
1943 年11 月,張愛玲(Eileen Chang,1920—1995)以日軍占領下的上海為背景,在《天地》月刊上發表了短篇小說《封鎖》。故事發生在因日軍突如其來的封鎖措施而長時間滯留原地的電車里,講述了一等車廂中銀行高級會計呂宗楨向大學英語助教吳翠遠搭話而生出情愫,由此二人墜入情網,然而隨著封鎖的解除,呂宗楨卻棄吳翠遠而去。
滯留原地的電車內,兩人之間的感情急速升溫。呂宗楨拋出一句“我打算重新結婚”,其后又改變主意,說:“我不能夠離婚。我得顧全孩子們的幸福。我大女兒今年十三歲了,才考進了中學,成績很不錯。”不由嘆道:“我年紀也太大了。我已經三十五了。”對此,吳翠遠回應道:“其實,照現在的眼光看來,那倒也不算大。”當呂問她“你……幾歲?”時,她低下頭去,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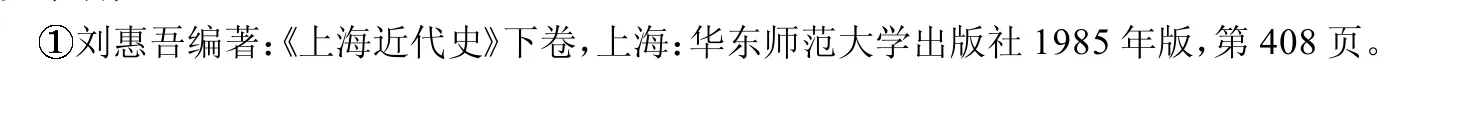



二、《羊脂球》中反轉的報紙瑣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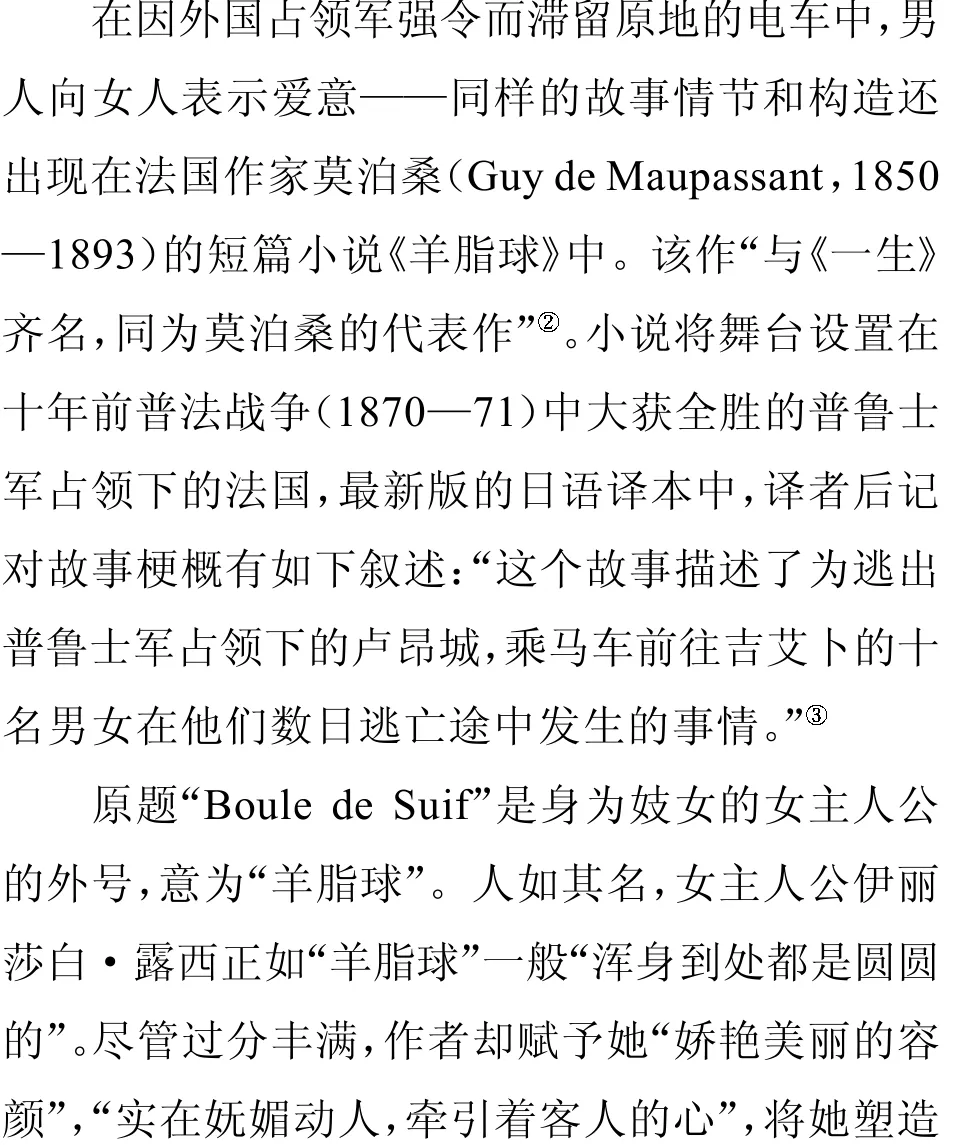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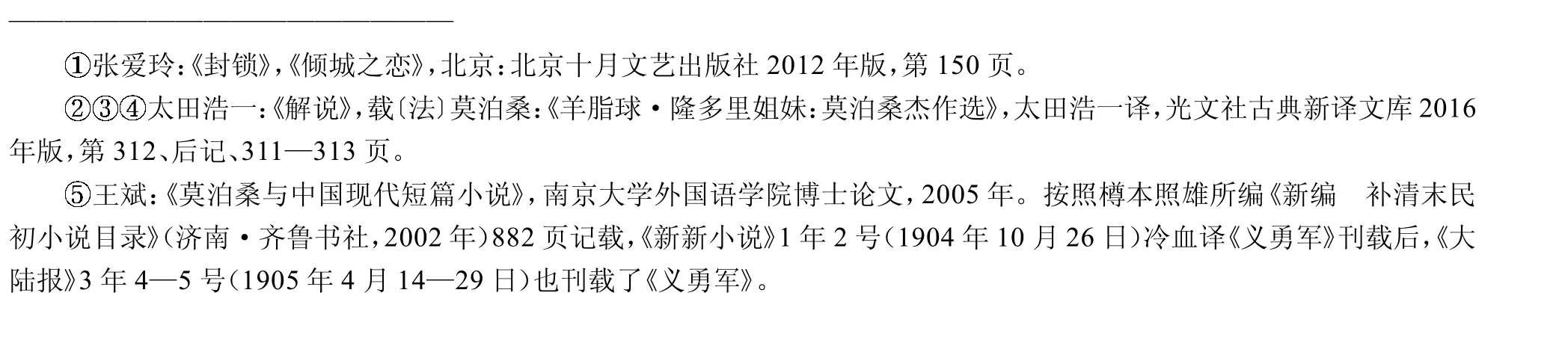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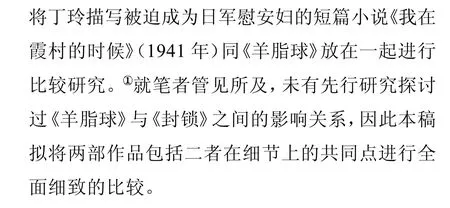
如前所述,《羊脂球》和《封鎖》的情節框架相同,都講述了在因外國占領軍而長時間滯留原地的車中,男性覬覦車中女性的故事。《羊脂球》中,以妓女羊脂球為首的所有人物都表露出了對普魯士軍的憎惡。而向妓女投射的感情,不僅包括占領軍軍官的欲情,更包含了為求再次啟程而希望妓女獻身的馬車上同乘者們的丑惡又滑稽的利己心。
與此相對,許是因為《封鎖》執筆和發表于日軍占領上海時期,作品中并沒有涉及人物對日本軍的憎恨。但是,對女主人公吳翠遠產生想法的男性不是日本軍官,而是和吳相同的上海人,以及呂宗楨在封鎖解除后馬上忘卻自己先前愛的告白,這兩點都體現出該作與《羊脂球》的決定性差異。《羊脂球》中的貴族和資本家在妓女犧牲自己而滿足占領軍官的淫欲之后,非但沒有忘卻此事,反而對她的妓女身份產生了更加強烈的厭惡。如此看來,《封鎖》中存在著對《羊脂球》兩重、甚至三重的反轉。不僅如此,給予張愛玲這一反轉構想的正是《羊脂球》里馬車再次啟程后緊接著的那一節。
小說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因妓女的獻身而得以再次啟程的一行人,在馬車中完全無視她的存在,一邊暗暗地背地里議論、一邊吃著自備的食物。而四五天前,逃出普魯士軍占領下的盧昂城的第一天,因路面積雪、車輪損壞致使他們深夜才到達多特的旅館。一路上,妓女分明拿出自己儲備的三天量的口糧和葡萄酒與同伴們分享,讓他們免于饑餓。但是到了重新出發的那天,沒有一個人分東西給她吃。悲哀的妓女羊脂球因屈辱寂寞和饑餓而抽泣……
熟悉《封鎖》的讀者,從這個充滿欺騙卑劣的車內餐會描寫中,想必會注意到以下一節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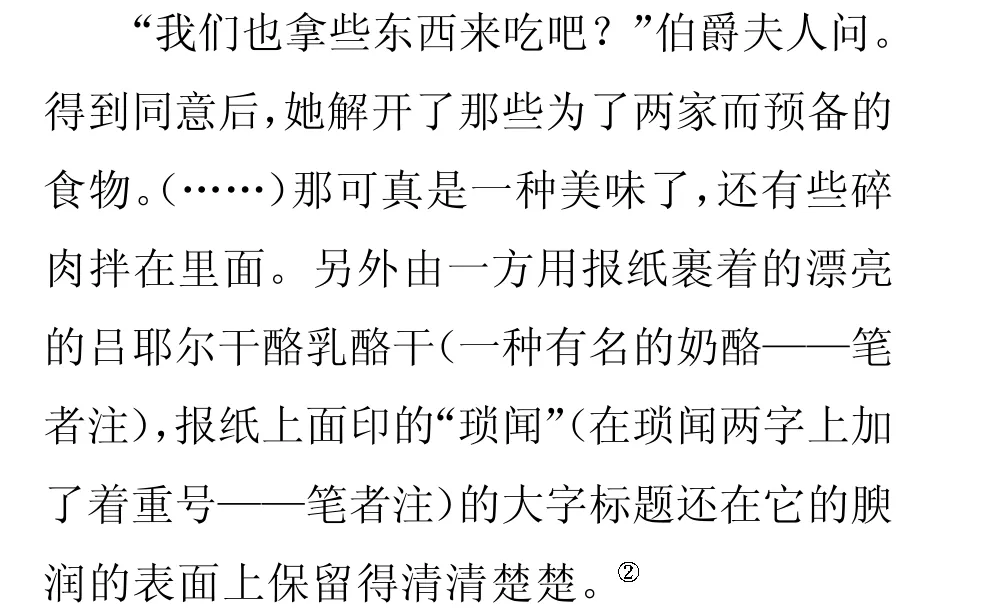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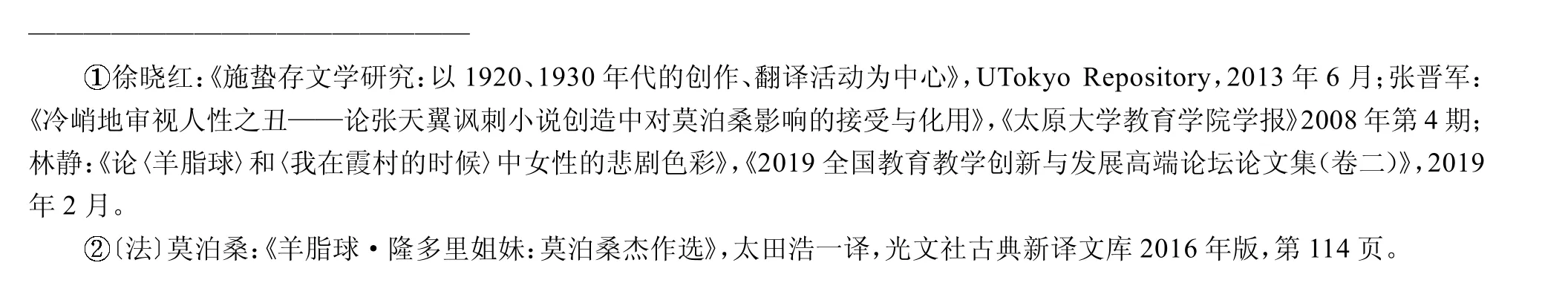
奶酪上顛倒印著的“瑣聞”究竟是什么?對于筆者的疑問,法國文學研究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廣播大學教授野崎歡作出了解釋:
小說此處提到的“瑣聞”,應是報紙的“欄”的標題(即用來表示新聞報道的類型標題)。實際是在報道“社會新聞”,用“瑣聞”(faits divers)作為標題。將記錄市井雜聞的多篇報道刊登在一起,是當時新聞報紙的風格。
因此,包裹乳酪干的是新聞中最粗俗的“社會新聞”,而不是什么特別的新聞。從這一點可以體會到作者的諷刺,即《羊脂球》故事本身刊登在“瑣聞欄”(或許連“瑣聞欄”都登不上),不過是不值一提的人生片斷罷了。
初讀太田先生的新譯,雖認為是一部精心譯就的好譯本,但是否真的有必要在“瑣聞”兩字上加著重號(原文并未采用斜體而是加了括號)呢?依我拙見,譯文中“瑣聞”二字是否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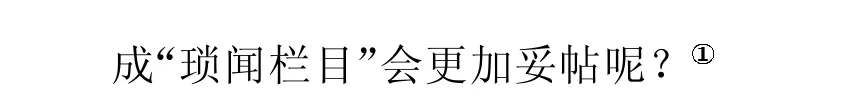

三、《封鎖》對《羊脂球》的三重反轉
莫泊桑的《羊脂球》中設置了這樣一個反轉——面對占領軍仍有強烈的自尊及愛國之心、富有同胞之愛的妓女遭到貴族及資本家們的背叛而陷于凄涼境地。反印在瑞士奶酪上的報紙瑣聞欄目,正是對妓女反轉的悲慘境地的隱喻。
張愛玲構思《封鎖》時,不僅從《羊脂球》中有關奶酪上反印著報紙瑣記的情節中獲得靈感,還對其情節構造進行了多次反轉。第一次反轉恐怕是為了逃避日軍檢閱,防止小說被禁發,作者在小說中隱去了封鎖的主謀者日本占領軍的身影。全文談及日軍的只有“街上一陣亂,轟隆轟隆來了兩輛卡車,載滿了兵”這一句。這一句描述帶同一起回頭看向卡車的男女主人公的臉“異常接近”,起到了“像銀幕上特寫鏡頭一般的”效果,發揮了讓“他們戀愛著了”的作用。敘述者利用日軍短時間的登場,將其轉化為戀愛劇情里的大型催化工具。作者借此向讀者明示了小說《封鎖》和《羊脂球》一樣以外國軍占領下的城市為舞臺,暗示了兩篇作品間的影響關系,并用敘述技巧躲開了占領軍的檢閱。
第二重反轉是上文所提到的“老實人”呂宗楨突如其來的人格變化,并且該反轉循環往復著進行——呂宗楨由于十分厭惡妻子的外甥而做出車中調情的輕浮舉止,雖然在外甥離開后立馬變回“老實人”,但他還是在和吳翠遠的對話中陷入愛河,只是封鎖解除的同時就將此前情話拋諸腦后。這一系列不斷重復的反轉和《羊脂球》中貴族、資本家一以貫之的狡猾與歧視心理形成了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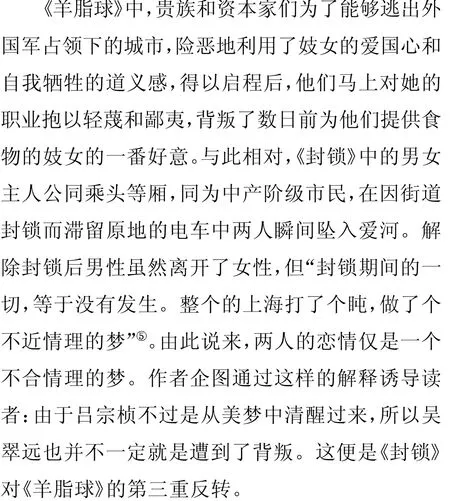

張愛玲受《羊脂球》啟發的同時,在《封鎖》中實現了對該作的三次反轉。憑借這三次反轉,作者描繪了不合情理的封鎖背景下一段短暫而耀眼的戀愛美夢,也向熟悉莫泊桑的讀者控訴了日本侵略軍的不正當行為。講述了男女主人公發生的一場不合情理的美夢,《封鎖》不單是一部戀愛小說,還潛藏著反戰和愛國的主題。就其表現的多樣性和情節的多屬性而言,《封鎖》稱得上是張愛玲文學的代表作。
《封鎖》從頭至尾將舞臺設置在電車中,小說始于對電車司機的描寫,并在他的怒罵聲中走向結束。《羊脂球》將舞臺設置在主人公們同乘的馬車和同住的旅館兩個空間里,小說中也寫有一個馬車夫。兩相對比,前者中電車司機的存在感要強烈得多。以下是《封鎖》的開頭和結尾:
(開頭)開電車的人開電車。在大太陽底下,電車軌道像兩條光瑩瑩的,水里鉆出來的曲蟮,抽長了,又縮短了;抽長了,又縮短了,就這么樣往前移……柔滑的,老長老長的曲蟮,沒有完,沒有完……開電車的人眼睛盯住了這兩條蠕蠕的車軌,然而他不發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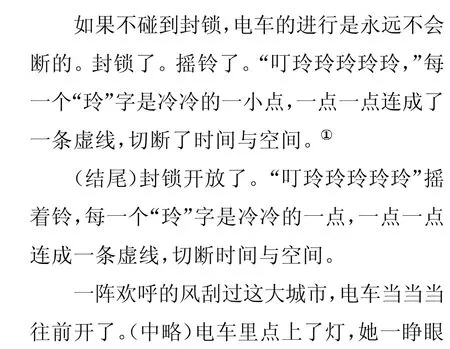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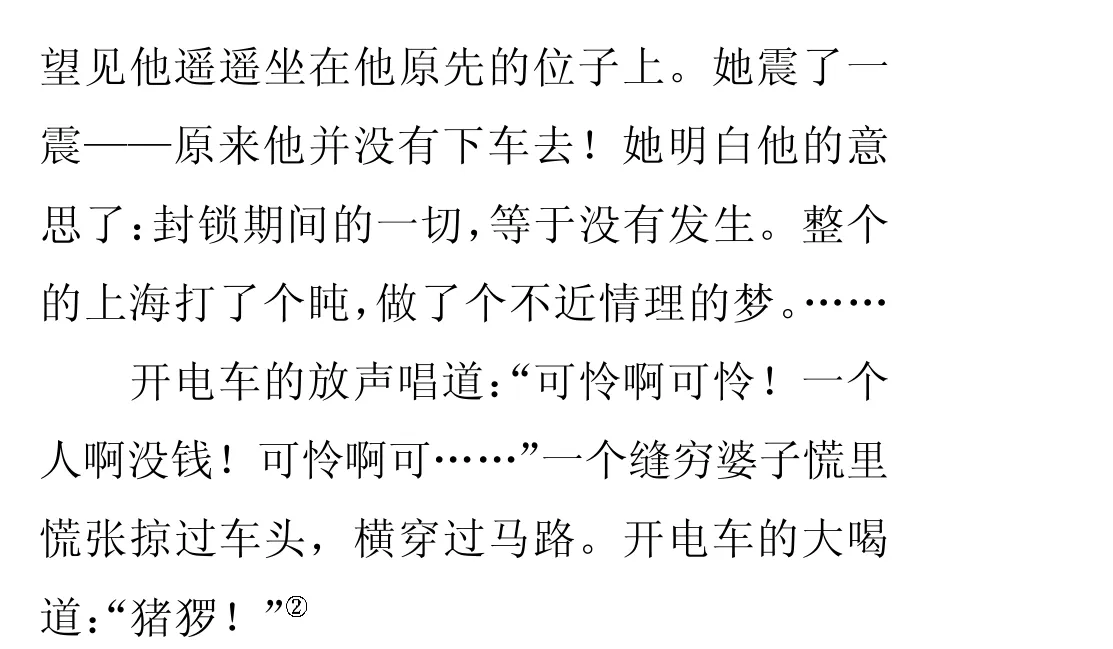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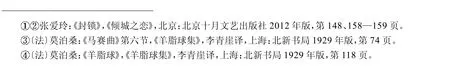
四、電車前橫穿馬路的老婆子——魯迅《一件小事》的影子
張愛玲為何不將《封鎖》的故事結束于“可憐啊可憐!”的歌聲中,而是新加了一位“縫窮婆子”作為第四重的反轉呢?看到這位在有軌電車前橫穿馬路的老婆子,應該會有不少讀者聯想到魯迅的短篇小說《一件小事》(1912 年12 月發表)。在“大北風刮得正猛”的北京,“我”搭乘人力車去上班,車子撞到了一位突然在車前橫穿馬路的“衣服都很破爛”的老婆子。“我”甚至懷疑這是老婆子精心設計的騙局,而滿身灰塵的車夫卻對老婆子溫柔以待。“我”被其堅定的善意所打動,反省了自身對他人的不信任,發出了如下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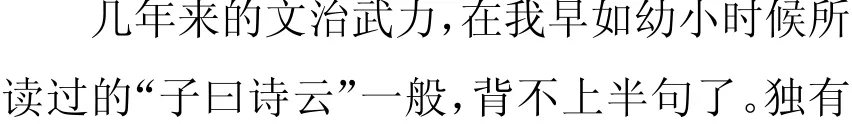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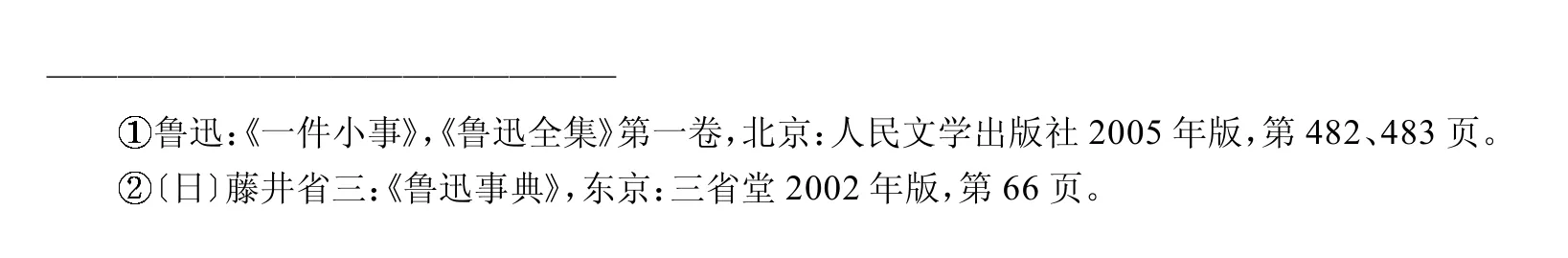
關于《一件小事》,筆者認為“以這些世間常有的事為題材創作的小說中,魯迅想表達的是,自以雜志《新生》(日本留學期間創辦的文藝雜志)為陣地發起的文學運動開始以來,始終流淌在他內心深處的那份對世間萬物不滅的希望。”不過,許是張愛玲對該作抱有別樣的看法,例如,不管是在“大北風刮得正猛”的北京,還是在“太陽滾熱地曬在背脊上”的上海,老婆子都像是目睹了一場“不合情理的夢”。她也由此產生了上述諸如此類的悠遠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