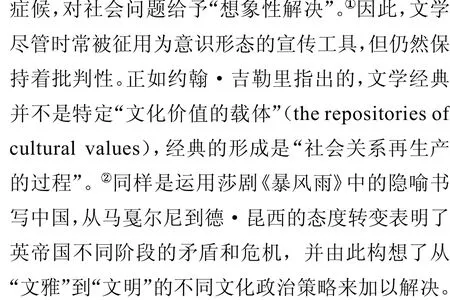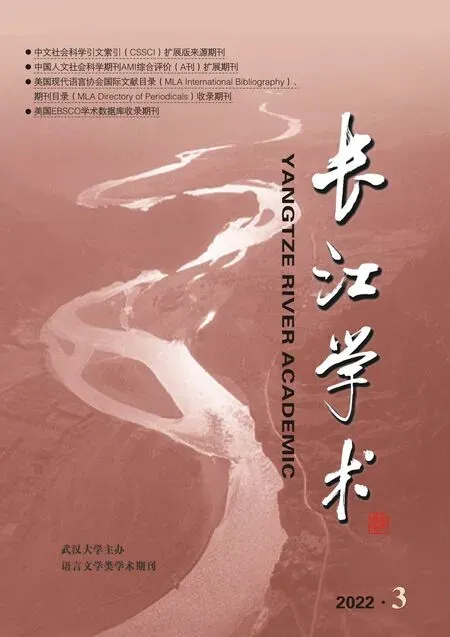“中國卡列班”:《暴風雨》、中國想象與英帝國的文學經典重塑
王冬青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英語語言文化學院,廣東 廣州 510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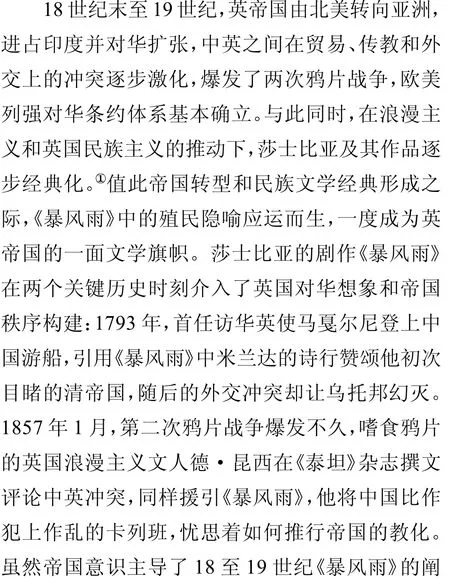


一、英國米蘭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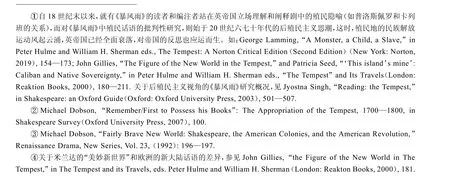



“美妙新世界”的假象:[清朝]朝廷的性格是一種獨特的組合:外表好客,內心多疑……(223)。
與神通廣大,主宰眾生命運的普洛斯佩羅不同,在中國,馬戛爾尼代表的英帝國扮演了米蘭達的角色,生活在普世主義的幻想中,是女性化、孩子氣的,遠非日后那個父權式的帝國形象。馬戛爾尼的“美妙新世界”,與其訪華之行一道,見證的是帝國夢的挫折和啟蒙價值觀的危機,也標志著包容性的“文雅社會”逐漸走向排他性的“文明—野蠻”的認識論。
二、中國卡列班
在馬戛爾尼所處的18 世紀末,清代中國在亞歐貿易中仍處于主導地位,英屬東印度公司正竭力爭取對華外交地位和貿易特權,因此馬戛爾尼總體認可中國的穩定社會秩序、繁榮的商業和文雅的生活方式。然而,馬戛爾尼使團和隨后1816 年阿美士德使團在訪華交涉中遭遇的挫折和沖突,深刻影響和改變了19 世紀的中英乃至中西關系,為鴉片戰爭的爆發埋下了伏筆。與此同時,“美妙新世界”的烏托邦光環褪去,英帝國的征服和教化的沖動開始主導對文化他者的認知。維多利亞時代英帝國海外殖民和貿易的迅速擴張,逐漸召喚出莎士比亞作品中的殖民隱喻:如果說《暴風雨》是一部帝國的傳奇,那么如今馬戛爾尼的米蘭達退場,托馬斯·德·昆西筆下的普洛斯佩羅和卡列班登上了歷史舞臺。威在文化領域的投射,經典化的莎翁作品由此成為帝國文化資本的代表。其中,《暴風雨》在形式上(宗主國的文學作品升華為世界文學經典)和內容上(海外殖民隱喻)都契合這樣一種“文化帝國主義”。在這股風潮下,《暴風雨》闡釋的焦點也從普洛斯佩羅-米蘭達的婚戀教誨轉移到普洛斯佩羅-卡列班的帝國統治,從中產階級家庭走向了海外殖民地,盡管二者都隱含了父權制的結構。就在維多利亞女王就任“印度女皇”的同年,菲爾伯茨編注的新版《暴風雨》出版了,并成為“拉格比公學版”莎士比亞選集叢書系列之一(the Rugby edition)。他在編者序中主張,在文藝復興時期英格蘭海外擴張的語境下,普洛斯佩羅扮演著殖民者角色,肩負著“教化野人”的“文明使命”:

這個角色可能和那個時代的重大命題有著特殊關系,當時我們正發現新國度,馴服未知的野人,建立全新的殖民地。如果普洛斯佩羅可以剝奪(dispossess)卡列班,英格蘭也可以剝奪殖民地土著。即使起初接觸文明社會會給野蠻種族帶來特別的危險,但我們可以證明,由精神和道德上的強者奪取權力是合理的,只要奪權是為了教化野人,使之通人性。這套拉格比版《莎士比亞劇作選》為小八開本印制,是利文斯頓出版社面向中學生推出的平價文學讀本。除《暴風雨》外,還包括《皆大歡喜》《麥克白》《哈姆萊特》《科利奧蘭納斯》等,大部分作品的編者為拉格比公校的教師(Assistant Master),而菲爾伯茨亦曾在拉格比公校任教12 年之久,1875年接任貝德福德校長。作為英國歷史上最早和最有名望的公學之一,拉格比是文化權勢的象征,這些讀著莎士比亞長大的貴族學生,日后將肩負帝國的重任。正如霍華德·菲佩林指出的,進入維多利亞時代貴族教育體制的莎士比亞作品肩負著兩大使命:英帝國的鞏固和英國民族文學經典的形成,《暴風雨》中,如果借用馬克斯·韋伯對政治合法性的論述,普洛斯佩羅是魅力型領袖和僭主的結合:一方面,科學和魔法知識奠定了他的政治權威,得以“解放”愛麗兒,“啟蒙”卡列班;另一方面,知識和真理又轉化為暴力,以“暴風雨”之勢驅使愛麗兒,奴役卡列班和懲罰篡位者。


然而,我們往往不甚留意的是,德·昆西的焦慮也暴露了權力話語的危機:和魯濱遜招撫“星期五”不同,《暴風雨》中殖民者的教化并未成功,普洛斯佩羅教授卡列班語言,卻被卡列班用來詛咒,密謀反抗,并要“燒了他的書”,將帝國統治連同與其共謀的知識體系連根拔起,一同摧毀。這表明,歷史并未遵循奈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的“帝國必勝”式線性敘事,即使在19 世紀英帝國走向巔峰之際,其文化領導權仍在經受挑戰。德·昆西的中國論述在中英關系的歷史糾葛和現實沖突中穿梭,時而捍衛英國的文明和尊嚴,時而譴責英商見利忘義地對華妥協,時而咒罵中國是“最惡毒和最愚蠢的國家”,擺出“非人的傲慢”。在這樣近乎歇斯底里的仇恨和侮辱看似咄咄逼人,卻掩藏著深刻的文化身份焦慮。無論是叛逆的卡列班,還是“傲慢”的中國,都指向了德·昆西焦慮的核心:英帝國雖然憑借暴力建立了半殖民統治,但卻尚未建立文化領導權。帝國代表的“真理”尚未確立和傳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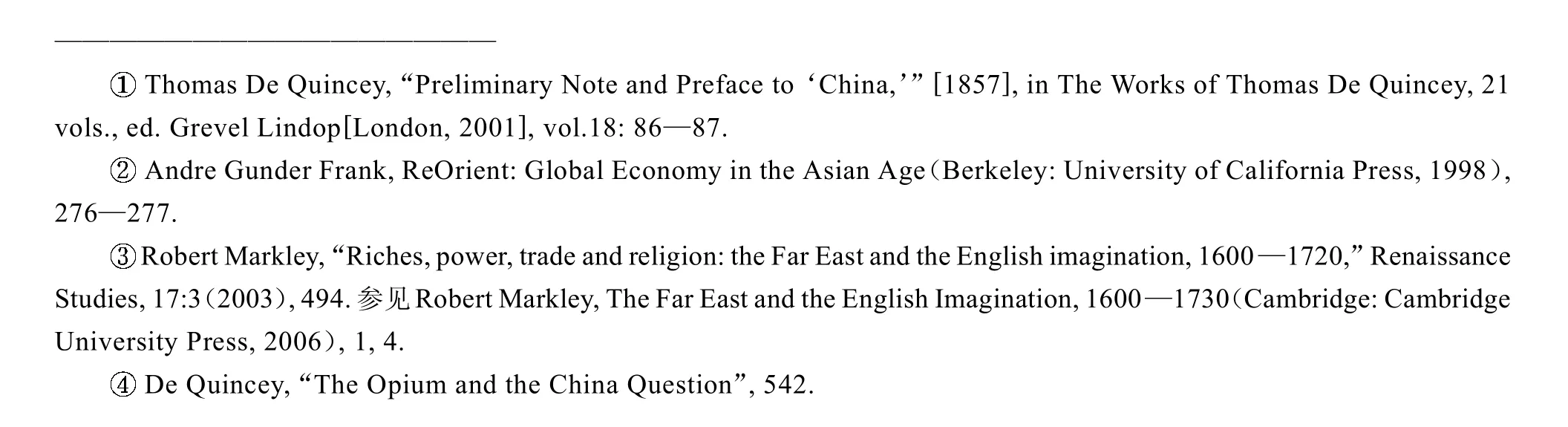
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從小人國眼中的巨人格列佛變為了普洛斯佩羅眼中的野人卡列班,地位一落千丈,但德·昆西的文化焦慮卻依然強烈。帝國雖然“制服”了格列佛,卻尚未“馴服”卡列班,因此以“書”代“箭”,從暴力征服走向意識形態的教化。在德·昆西看來,英帝國貿易、傳教和外交的受挫有著根本原因,那就是“接種”文明的失敗,帝國“教化”的失敗。運用有機體“免疫”的隱喻,德·昆西稱“接種”對中國這個社會有機體是無效的,因為沒有古希臘知識傳統中對真理的“愛”,中國不具備生產思想的能力。這種無知表現在中國并未認識到不列顛文明的“重大優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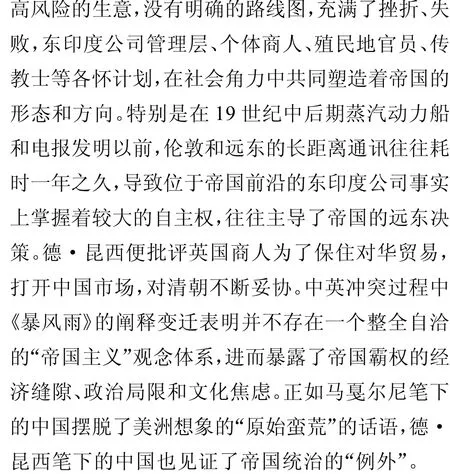

結語
如前文所述,許多后殖民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研究已經分析了莎士比亞作品中關于非西方“他者”的權力話語,如《奧賽羅》中的種族問題和《威尼斯商人》中的猶太人形象等,揭示了“文本的歷史性”。由此,本文進而強調的是,對“帝國”和“殖民”的指涉并不完全是莎士比亞文本的固有“屬性”或“內涵”,而是體現在批評家、文人和公眾對作品的闡釋、編注和傳播過程中建構出來的文學形象、審美效果和社會功能。18 和19 世紀莎士比亞的經典化,代表了英國“民族文學”觀念和英國文學學科建制化的形成,也作為一種文化運動參與了英帝國迅速擴張并稱霸全球的歷史過程。以《暴風雨》為例,故事雖然取材于英格蘭早期海外擴張,并隱含了帝國的想象,但尚未形成清晰自覺的帝國意識。馬戛爾尼和德·昆西在中英交往與沖突中對《暴風雨》的挪用和重釋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暴風雨》的殖民話語不僅“反映”了大航海時代海外貿易和殖民的歷史現實,同時也是18 和19 世紀英帝國事后建構的產物。可以說,自文藝復興至維多利亞時代,一部《暴風雨》的改編、評注和闡釋史,也是英帝國危機和發展的“癥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