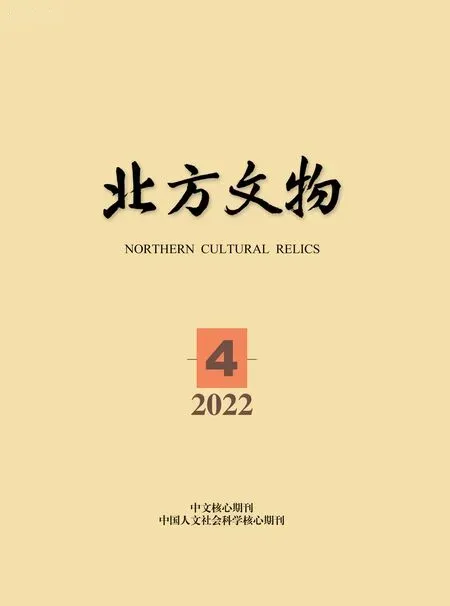蘇秉琦與西北史前考古
任瑞波
(吉林大學(xué)考古學(xué)院)
〔內(nèi)容提要〕 中國(guó)西北地區(qū)史前考古工作距今已有百年的歷程,但取得突破則是在“區(qū)系類型理論”的指導(dǎo)下完成的。蘇秉琦《關(guān)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wèn)題》和《關(guān)于考古學(xué)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問(wèn)題》都談及西北史前考古的要點(diǎn)和難點(diǎn)。從1986年起,蘇秉琦在蘭州召開(kāi)的“大地灣考古座談會(huì)”以及一系列的相關(guān)會(huì)議上,持續(xù)不斷為西北史前考古工作進(jìn)行了大量的細(xì)致規(guī)劃,為西北地區(qū)史前考古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
蘇秉琦是中國(guó)考古學(xué)的奠基人和開(kāi)拓者①,為中國(guó)考古學(xué)的正確發(fā)展夯實(shí)了理論基礎(chǔ),指明了前行方向。雖然沒(méi)有對(duì)中國(guó)西北地區(qū)的某一支史前文化進(jìn)行專文研究,但是,蘇秉琦部分經(jīng)典之作和重要思考——以“兩問(wèn)”和“一會(huì)”為代表,清晰展現(xiàn)了他對(duì)西北地區(qū)史前考古的探索。這些思考對(duì)中國(guó)西北地區(qū)特別是甘(肅)、青(海)、寧(夏)史前考古學(xué)的研究,不論在當(dāng)時(shí),還是現(xiàn)在,都具有重要且深遠(yuǎn)的指導(dǎo)意義。
一、“兩問(wèn)”關(guān)于西北史前文化的認(rèn)識(shí)
所謂“兩問(wèn)”,其實(shí)就是蘇秉琦發(fā)表的兩篇重要學(xué)術(shù)文章,一篇是《關(guān)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wèn)題》,另外一篇是《關(guān)于考古學(xué)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問(wèn)題》。
1965年,蘇秉琦發(fā)表了《關(guān)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wèn)題》②,針對(duì)甘肅地區(qū)的仰韶文化和相關(guān)問(wèn)題,他提出自己的觀點(diǎn)。
第一,關(guān)于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圍。甘肅東部的平?jīng)觥焖媳豹M長(zhǎng)地帶,經(jīng)歷了仰韶文化從早至晚的各個(gè)階段,屬于仰韶文化的中心分布區(qū)之一。洮河流域的臨洮一帶、青海東部邊緣的民和一帶屬于仰韶文化的外圍分布區(qū)。
第二,關(guān)于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由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重疊堆積的層位關(guān)系,可知馬家窯文化晚于仰韶文化。
第三,關(guān)于馬家窯文化諸類型遺存內(nèi)部之間的關(guān)系。1.從分布范圍上看,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和馬廠類型在甘青地區(qū)自東向西分布交錯(cuò);2.從時(shí)間上看,馬家窯類型最早,半山類型次之,馬廠類型最晚,三者既有先后,亦有重合;3.從文化關(guān)系上講,半山類型是馬家窯類型和馬廠類型的中介。
第四,關(guān)于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發(fā)展方向。在甘肅地區(qū),早至仰韶文化,晚至半山文化,它們的移動(dòng)方向自始至終都是自東向西:從甘肅東部延伸至甘肅中部再到甘肅西部,最后一直伸入河西走廊西端。
以上四點(diǎn),就是截至1965年蘇秉琦對(duì)甘肅史前文化的基本看法。
隨著考古資料的不斷積累,10年之后,蘇秉琦在提出對(duì)全國(guó)考古工作具有指導(dǎo)意義的“區(qū)系類型理論”的同時(shí),也深化了對(duì)西北地區(qū)史前考古的新認(rèn)識(shí)。
1975年8月,蘇秉琦在北京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為吉林大學(xué)考古專業(yè)師生做學(xué)術(shù)報(bào)告,首次正式提出了考古學(xué)文化區(qū)系類型理論③。1981年,《關(guān)于考古學(xué)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問(wèn)題》④一文發(fā)表。在這篇文章中,蘇秉琦將全國(guó)的考古學(xué)文化分為六大區(qū),其中第六區(qū)為“以長(zhǎng)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qū)”,這一大區(qū)又可分為三小區(qū):第一小區(qū),以昭盟為中心的地區(qū);第二小區(qū),河套地區(qū);第三小區(qū),以隴東為中心的甘青寧地區(qū)。針對(duì)甘青寧地區(qū)的史前文化,蘇秉琦主要談及以下六點(diǎn)認(rèn)識(shí)。
第一,隴山(六盤(pán)山)東側(cè)經(jīng)歷了從前仰韶文化到仰韶文化發(fā)展的各個(gè)階段,與隴山西側(cè)的文化發(fā)展進(jìn)程相一致。
第二,秦安大地灣遺址相關(guān)遺存的發(fā)現(xiàn)為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銜接提供了可靠的線索。
第三,仰韶文化之后,隴山東西兩側(cè)的文化走上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
第四,甘青寧地區(qū)青銅時(shí)代的文化相當(dāng)復(fù)雜,但該地區(qū)進(jìn)入青銅時(shí)代的時(shí)間不晚于商代,是我國(guó)較早發(fā)明青銅器的一個(gè)地區(qū)。
第五,河西走廊到新疆東部一帶的細(xì)石器和彩陶,是甘青地區(qū)古文化的延伸。
第六,隴東地區(qū)因與其東向、西北向和西南向這三面文化都有關(guān)系,屬于文化意義上的“三岔路口”。
以上六點(diǎn),就是蘇秉琦在正式提出區(qū)系類型理論的同時(shí),對(duì)西北地區(qū)史前文化的新思考和新認(rèn)識(shí),較10年前有明顯的區(qū)別:時(shí)間上,早至前仰韶,晚至青銅時(shí)代;地域上,東至甘肅東部,西至新疆東部;內(nèi)容上,既有對(duì)具體遺存的性質(zhì)判別,也有對(duì)某一區(qū)域文化發(fā)展模式的思考,還有以前兩者為基礎(chǔ)的理論構(gòu)建。
二、“一會(huì)”引發(fā)的對(duì)西北史前文化的思考
所謂“一會(huì)”,從狹義上講,專指1986年在蘭州召開(kāi)的“大地灣考古座談會(huì)”(即蘇秉琦常提的“蘭州會(huì)”)。從廣義上講,是指以“蘭州會(huì)”為中心的一系列會(huì)議,包括“呼市會(huì)”(1984年8月)、“蘭州會(huì)”(1986年8月)、“包頭會(huì)”(1986年8月)、“廣漢會(huì)”(1987年5月)、“第二次渤海會(huì)”(1988年5月)等。雖然這些會(huì)議舉辦的地點(diǎn)不同,會(huì)議主題也各異,但在這些會(huì)議上,蘇秉琦都不斷深化他在“蘭州會(huì)”上闡述的觀點(diǎn)和設(shè)想。

1986年8月在蘭州召開(kāi)的“大地灣考古座談會(huì)”全體代表合影(前排左起第六為蘇秉琦)(圖片摘自《考古學(xué)研究(十)——慶祝李仰松先生八十壽辰論文集》,科學(xué)出版社2012年。)
1984年8月,蘇秉琦在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市舉辦的“內(nèi)蒙古西部地區(qū)原始文化座談會(huì)”上做了題為《燕山南北·長(zhǎng)城地帶考古工作的新進(jìn)展》的匯報(bào),報(bào)告的部分內(nèi)容是對(duì)區(qū)系類型理論進(jìn)行的深入闡釋。針對(duì)中原地區(qū)的文化,他提出了“五個(gè)縱剖面”“三個(gè)橫剖面”“兩個(gè)界標(biāo)”和“三個(gè)層次”,其中部分內(nèi)容涉及甘肅東部:秦安大地灣遺址是第五個(gè)縱剖面,秦安大地灣下層屬于第一個(gè)橫剖面的西端,天水、寶雞間的隴山東西屬于兩個(gè)界標(biāo)之一,隴山西屬于“燕山南北·長(zhǎng)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qū)”,隴山東屬于中原地區(qū)。
1986年8月4日,蘇秉琦在蘭州召開(kāi)的“大地灣考古座談會(huì)”上明確指出,甘肅東部涇渭流域自成體系,以蘭州為中心的洮河流域?qū)儆诹硪粎^(qū)系,但是,它們都屬于“中國(guó)北方考古”這一大的范疇,是“大北方”的西部。不僅如此,他還提出了“大北方地區(qū)考古”的設(shè)想。在蘇先生眼中,大北方不僅包括了半個(gè)中國(guó),而且連接亞歐大陸,因此,他呼吁,“大北方考古”應(yīng)該引起足夠的重視⑤。
1986年8月,在內(nèi)蒙古包頭市,蘇先生發(fā)表“從蘭州到包頭”講話。他強(qiáng)調(diào),1984年“呼市會(huì)”和1986年“蘭州會(huì)”是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并再次明確指出隴東地區(qū)(甘肅東部、隴山東西、涇渭流域上游)和陜西關(guān)中西部既有密切聯(lián)系,又有不同的發(fā)展道路,隴東地區(qū)的古文化大約在五六千年間“分道揚(yáng)鑣”,隴山以東與關(guān)中西部的同時(shí)期相近,而隴山以西則與馬家窯文化有淵源和相互影響關(guān)系。不僅如此,甘肅蘭州本身還自成“小區(qū)系”⑥。
1987年5月,在四川省廣漢市,蘇秉琦再次談到蘭州。他說(shuō):“區(qū)系是從生物學(xué)(生態(tài)學(xué))借來(lái)的名詞,即條條塊塊……現(xiàn)在劃六大區(qū),或劃個(gè)十字,分東北、西北、東南和西南四大塊也可以。北方座談會(huì),范圍東起遼東,西到蘭州,就是我們所謂的北方。”在“廣漢會(huì)”上,蘇先生闡釋了區(qū)系的基本理念和劃分思路,而且指出“北方”的西界就是蘭州。對(duì)于中原和西部的界限問(wèn)題,他進(jìn)行了更為明確的總結(jié):“渭水上游到大地灣就是分界線,中原到此為止,到洮河流域就是馬家窯文化,是另外一回事了,再往西是中亞。從隴東到隴西,就是中間模糊地帶,它既是東西兩半塊的界限,本身又有突出特征。”⑦
1988年5月,在第二次環(huán)渤海專題系列座談會(huì)⑧上,蘇先生又一次提到“蘭州會(huì)”,并且詳談了“蘭州會(huì)”的會(huì)后工作思路,即準(zhǔn)備在1989年在蘭州再次舉辦會(huì)議,內(nèi)容是“向西、向大西北,面向中亞和西亞。要以洮河流域的古文化為中心,闡明亞洲東——中兩大部分之間的結(jié)合點(diǎn),文化特征和發(fā)展機(jī)制”⑨,并且明確總結(jié)了蘭州會(huì)的四個(gè)會(huì)議共識(shí)。
( 一)大地灣是一處大遺址,區(qū)別于隴東同時(shí)期的諸遺址,需要長(zhǎng)期堅(jiān)持下去。
( 二)隴山東西、涇渭流域的古文化遺存不宜混為一談,要區(qū)別開(kāi)。
( 三)從大地灣下層到馬家窯文化諸遺存之間的關(guān)系是一個(gè)大課題,據(jù)現(xiàn)有的材料進(jìn)行論證是管窺蠡測(cè)。
( 四)為了向更高層次開(kāi)展研究,進(jìn)行工作,有必要暫把“長(zhǎng)城地帶”這個(gè)區(qū)系考古專題系列座談的范圍到劃此為止。
此外,蘇先生再次提到開(kāi)展下一次“大西北地區(qū)”的專題會(huì),這也是從1986年的“蘭州會(huì)”開(kāi)始,他連續(xù)四次倡導(dǎo)的這一會(huì)議的召開(kāi),可惜最后無(wú)果而終。
1992年,在第四次環(huán)渤海考古座談會(huì)上,蘇先生又一次提到1986年召開(kāi)的“大地灣專題座談會(huì)”,并特別說(shuō)明所謂的“環(huán)渤海考古”就是在1986年“蘭州會(huì)”之后,“由一部分同志商定而提出的”⑩。
1993年,蘇秉琦發(fā)表《迎接中國(guó)考古學(xué)的新世紀(jì)》一文,他在“關(guān)于北方地區(qū)的考古再實(shí)踐”一章中,把以蘭州為代表的西北地區(qū)放在第五部分進(jìn)行討論,并再次提到1986年召開(kāi)的“蘭州會(huì)”。他明言:“大地灣的文化仍可往東靠,它的主人屬于仰韶文化系統(tǒng),而不屬于馬家窯文化系統(tǒng)。馬家窯文化雖然有很發(fā)達(dá)的彩陶,但所反映的思維方式與‘仰韶人’不一樣,這一點(diǎn)很明確。”此外,他還指出,大地灣仰韶晚期的大房子具有“宮殿”的性質(zhì)和作用。
通過(guò)上述蘇秉琦圍繞“蘭州會(huì)”及其前后相關(guān)會(huì)議發(fā)表的看法,不難發(fā)現(xiàn),在區(qū)系類型的理論指導(dǎo)下,他對(duì)隴山東西兩側(cè)的文化遺存性質(zhì)和文化演進(jìn)模式都有著漸進(jìn)式的深入思考。同時(shí)以“蘭州會(huì)”為出發(fā)點(diǎn),他對(duì)西北史前文化的縱、橫兩個(gè)方面,在微觀和宏觀層面都進(jìn)行了精煉的闡釋。
三、從“兩問(wèn)”“一會(huì)”看蘇秉琦學(xué)術(shù)風(fēng)范
從1965年蘇秉琦的“第一問(wèn)”提出至今,西北地區(qū)經(jīng)科學(xué)發(fā)掘所獲的考古材料層出不窮,新的研究認(rèn)識(shí)和結(jié)論也日漸增多,但蘇秉琦針對(duì)西北地區(qū)史前文化所提出的觀點(diǎn),或是被新的考古材料不斷證實(shí),或是被后續(xù)的研究者繼續(xù)深化,還有一些他提出的問(wèn)題至今依然是當(dāng)前西北地區(qū)史前考古研究的重點(diǎn)、熱點(diǎn)和難點(diǎn)。
例如,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之間的銜接問(wèn)題、隴山東西兩側(cè)考古學(xué)文化走向不同發(fā)展道路的問(wèn)題、甘青寧青銅時(shí)代早期青銅器的問(wèn)題、從大地灣下層到馬家窯文化諸遺存之間的關(guān)系問(wèn)題,它們雖然都是1981年蘇先生看似輕描淡寫(xiě)簡(jiǎn)要提出的,但至今多數(shù)仍懸而未決,依然具有很強(qiáng)的學(xué)術(shù)生命力和廣闊的學(xué)術(shù)前景,我們不難從中窺見(jiàn)蘇先生的學(xué)術(shù)風(fēng)范和深遠(yuǎn)影響。
1.學(xué)術(shù)思考循序漸進(jìn)
從1965年的第“一問(wèn)”,到1981年的第“二問(wèn)”;從1986年的“蘭州會(huì)”,到1987年的“廣漢會(huì)”,再到 1992年的“第四次環(huán)渤海考古座談會(huì)”;從1975年區(qū)系類型的提出,再到1997年《中國(guó)文明起源新探》出版,蘇秉琦對(duì)西北地區(qū)史前文化的認(rèn)識(shí),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循序漸進(jìn)。在每個(gè)階段,他都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當(dāng)時(shí)公布的材料,謹(jǐn)慎得出結(jié)論,隨著考古資料的增加,再對(duì)自己的認(rèn)識(shí)進(jìn)行深化或調(diào)整。
例如,對(duì)于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關(guān)系,1965年,他認(rèn)為,馬家窯文化晚于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因?yàn)橛卸叩亩逊e疊壓關(guān)系。1981年,他提出二者之間還有銜接,這是因?yàn)榇蟮貫尺z址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再如,1965年談及西北地區(qū)史前文化時(shí),蘇先生多將視野放在甘肅省,而1981年再次談同一問(wèn)題時(shí),他將地理范圍擴(kuò)展至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東部。再如,在“蘭州會(huì)”上,蘇秉琦提出甘肅東部涇渭流域和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各自成一系統(tǒng),在其后的“呼市會(huì)”“廣漢會(huì)”,乃至第二次環(huán)渤海專題系列座談會(huì)上,他依然不斷對(duì)“蘭州會(huì)”上提出的這一認(rèn)識(shí)進(jìn)行深化,明確甘肅東部和關(guān)中西部關(guān)系密切,隴東到隴西屬于“模糊地帶”,洮河流域?qū)儆隈R家窯文化。再如,1981年,蘇先生將甘青地區(qū)視為長(zhǎng)城地帶這一大區(qū)中的一個(gè)小區(qū),該小區(qū)自身的特點(diǎn)早在1965年蘇先生在討論仰韶文化和相關(guān)問(wèn)題時(shí)已經(jīng)初見(jiàn)雛形。另外,隨著甘青地區(qū)材料的不斷增加,他又將蘭州地區(qū)、洮河流域、隴山西側(cè)的渭水上游各自視為一個(gè)“小區(qū)系”,這是以西北地區(qū)為“試驗(yàn)田”,他對(duì)區(qū)系類型理論中的“區(qū)中區(qū)”和“系中系”進(jìn)行的最典型闡釋。
當(dāng)然,隨著材料的增加和思考的深入,蘇秉琦也會(huì)及時(shí)調(diào)整自己的一些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例如,在20世紀(jì)80年代,蘇秉琦認(rèn)為,大地灣與隴東地區(qū)的同時(shí)期遺址應(yīng)區(qū)別對(duì)待,而進(jìn)入90年代,他則認(rèn)為,大地灣完全可以放在仰韶文化系統(tǒng)中去。
2.學(xué)術(shù)思想薪火相傳
早年,蘇秉琦關(guān)于西北地區(qū)史前考古提出的很多認(rèn)識(shí)、發(fā)表的很多觀點(diǎn),都是在當(dāng)時(shí)考古資料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得出的。不過(guò),隨著考古資料的增加,一些認(rèn)識(shí)和觀點(diǎn)依然引導(dǎo)他的學(xué)生乃至學(xué)生的學(xué)生繼續(xù)深思和闡釋,使得相關(guān)問(wèn)題的研究得到不斷的充實(shí)和深化。
例如,1965年,蘇秉琦指出,西北地區(qū)從仰韶文化至半山文化是不斷西進(jìn)的。1978年,他的學(xué)生嚴(yán)文明發(fā)表《甘肅彩陶的源流》,將甘肅全省、青海東部和寧夏南部發(fā)達(dá)的彩陶文化進(jìn)行了系統(tǒng)梳理,闡明了這些彩陶文化從半坡期、廟底溝期、馬家窯期、小坪子期、半山期、馬廠期一直到四壩文化是不斷向西開(kāi)拓的過(guò)程,首次用考古實(shí)物資料駁斥了“彩陶文化西來(lái)說(shuō)”。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在“區(qū)系類型理論”指導(dǎo)下,甘青地區(qū)史前研究出現(xiàn)一個(gè)學(xué)術(shù)高潮,一些區(qū)域性考古學(xué)文化的研究堪稱經(jīng)典:例如,在嚴(yán)文明指導(dǎo)下,李水城完成博士論文《半山與馬廠彩陶研究》,張弛完成碩士論文《半山式文化遺存分析》;在張忠培指導(dǎo)下,李伊萍完成碩士論文《半山、馬廠文化研究》,許永杰完成碩士論文《河湟青銅文化的譜系》。2007年,在嚴(yán)文明的鼓勵(lì)下,其學(xué)生韓建業(yè)《新疆的青銅時(shí)代和早期鐵器時(shí)代文化》出版,這本書(shū)是首次在“區(qū)系類型理論”的指導(dǎo)下,對(duì)新疆史前遺存進(jìn)行的科學(xué)的考古學(xué)基礎(chǔ)研究。2013年,韓建業(yè)發(fā)表《“彩陶之路”與中西文化交流》,清晰勾勒出約公元前3500 年、公元前3000 年、公元前2200 年和公元前1300 年四波彩陶文化在中國(guó)西北地區(qū)的西漸。這些研究,雖然時(shí)間有早晚,形式不同,主旨各異,但無(wú)一不是對(duì)蘇秉琦西北地區(qū)史前文化研究的學(xué)術(shù)深化和延伸。
再如,1975年,蘇秉琦指出,仰韶文化之后,隴山東西兩側(cè)的文化走上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2013年,他的學(xué)生張忠培在“中國(guó)考古學(xué)會(huì)第十六次學(xué)術(shù)年會(huì)暨第六屆會(huì)員代表大會(huì)”上進(jìn)行匯報(bào),將渭水流域史前文化的分化、發(fā)展和遷徙動(dòng)態(tài)給予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無(wú)疑是對(duì)蘇先生40年前認(rèn)識(shí)的深化和充實(shí)。
3.學(xué)術(shù)視野高瞻遠(yuǎn)矚
蘇秉琦對(duì)西北地區(qū)史前考古的成功引領(lǐng)和指導(dǎo),得益于他高瞻遠(yuǎn)矚的學(xué)術(shù)視野。例如,1981年,他明確指出隴東地區(qū)屬于“三岔路口”。“三岔路口”看似是一個(gè)非常普通的名詞,但其中的理論意味妙不可言。這一名詞的出現(xiàn),其實(shí)就是對(duì)考古材料和考古現(xiàn)象進(jìn)行的高度理論提升和概括。從1981年至今,相關(guān)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考古新材料完全能夠?qū)㈦]東地區(qū)的“三岔路口”作用清晰呈現(xiàn):以天水地區(qū)為中心,向西到渭水上游乃至河湟谷地,向東到關(guān)中西部,向南到甘南和川西北,這些地區(qū)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馬家窯文化時(shí)期呈現(xiàn)出的種種相似或類似的文化現(xiàn)象,都足以證實(shí)隴東地區(qū)“三岔路口”的真實(shí)歷史地位。再如,1986年的“蘭州會(huì)”,雖然會(huì)議的出發(fā)點(diǎn)和切入點(diǎn)都是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但在“蘭州會(huì)”及其此后的一系列相關(guān)會(huì)議中,蘇先生的思考不限于大地灣遺址,也不拘泥于甘青寧地區(qū),而是面向北方長(zhǎng)城地帶,面向整個(gè)中國(guó)大北方,面向中亞和西亞。更為難得的是,即便專門(mén)談及甘青寧地區(qū),蘇先生也從未將這一區(qū)域單獨(dú)看待,而是將其視為“北方長(zhǎng)城地帶”大區(qū)中的一個(gè)小區(qū),并不斷提醒我們要將這一地區(qū)的文化發(fā)展放在“中國(guó)北方考古”乃至連接歐亞大陸的“大北方考古”中去考量。
通過(guò)上述簡(jiǎn)要回顧,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蘇秉琦所涉及的西北地區(qū)史前考古工作和研究具體內(nèi)容雖各不相同,但無(wú)不彰顯其學(xué)術(shù)理論深耕于田野實(shí)踐并指導(dǎo)田野工作。當(dāng)今的西北史前考古,多數(shù)地區(qū)考古學(xué)文化時(shí)空框架的構(gòu)建已經(jīng)大體完成,譜系關(guān)系的梳理也日漸完善,各類專題研究正在如火如荼開(kāi)展,理論探索也若隱若現(xiàn),但我們不應(yīng)忽視西北史前考古工作在“區(qū)系類型理論”指導(dǎo)下取得的重要學(xué)術(shù)成果,也不能忘記蘇秉琦在西北地區(qū)史前考古的學(xué)術(shù)研究和工作規(guī)劃中做出的重要貢獻(xiàn)。
注 釋:
① 張忠培:《中國(guó)考古學(xué)的奠基人與開(kāi)拓者——沉痛悼念蘇秉琦教授》,《遼海文物學(xué)刊》1997年第2期。
② 蘇秉琦:《關(guān)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wèn)題》,《考古學(xué)報(bào)》1965年第1期。
③ 吳汝祚、汪遵國(guó)、郭大順:《蘇秉琦大事年譜》,《東南文物》1995年第4期。
④ 蘇秉琦、殷偉璋:《關(guān)于考古學(xué)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問(wèn)題》,《文物》1981年第5期。
⑤ 蘇秉琦:《“大地灣會(huì)”講話》(提要),《華人·龍的傳人·中國(guó)人——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下同,第31、32頁(yè)。
⑥ 蘇秉琦:《從蘭州到包頭——在“包頭市文官處座談會(huì)”上的發(fā)言》(提要),《華人·龍的傳人·中國(guó)人——考古尋根記》,第15、16頁(yè)。
⑦ 蘇秉琦:《西南地區(qū)考古——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考古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華人·龍的傳人·中國(guó)人——考古尋根記》,第15、16頁(yè)。
⑧ 蘇秉琦:《環(huán)渤海考古與青州考古》,《考古》1989年第1期。
⑨ 蘇秉琦:《環(huán)渤海考古的理論與實(shí)踐》,《華人·龍的傳人·中國(guó)人——考古尋根記》,第61—63頁(yè)。
⑩ 蘇秉琦:《在“第四次環(huán)渤海考古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摘要),《華人·龍的傳人·中國(guó)人——考古尋根記》,第141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