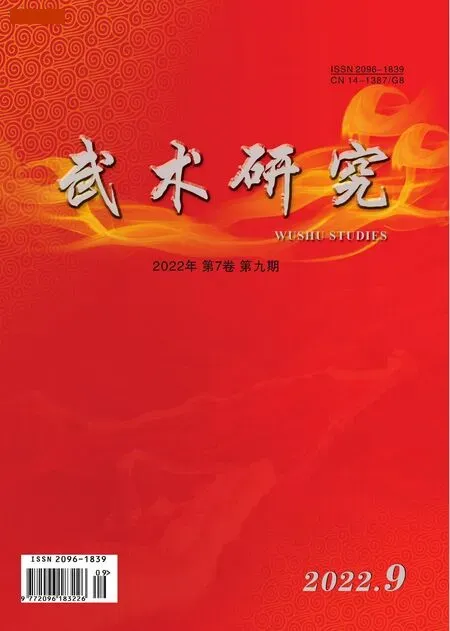文化學視野下的武術本體論探討
李坷軒 王太林
中北大學體育學院,山西 太原 030051
1 前言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時代背景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發展蒸蒸日上。如今,學界對于“武術”的探討不絕于耳,各類學術期刊上刊載諸多該類研究。其中,有使用文化學理論將武術本身作為文化本體進行研究的,這就明晰了“武術是不是僅僅作為一項體育運動而存在”,“武術課的體操化是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這些爭論已久的問題。這也從更高維度去解讀武術本身,能夠更為宏觀的去理解武術。
當然,也有一些研究突出了武術的“文化”屬性,以此來區別于普通體育項目,甚至是抨擊“體育視角下的武術”這一現實狀況。而本文認為,無論如何解讀武術,目前已知的現實存在都可看作是武術功能的具體指向,只有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才能將武術的眾多功能與價值全方位、多維度的釋放出來,共同推進武術在當前社會的快速發展。
想要明確“武術”這一概念的內核,就不得不對“武術文化”進行探討與解讀。就“武術文化”研究本身而言,已有成果大多流于表面,無法切實指導實踐。由此,對于“武術文化”如何能夠進行鞭辟入里的探討就成為“武術”這一本體研究領域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如果“武術文化”“武術文化發展的主要抓手”這些問題模棱兩可,那么所謂的武術傳承與發展注定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因此,本文在“武術”及“武術文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整理歸納,試圖厘清“武術”與“武術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尋找推進武術發展的有力抓手,以期為武術的發展與弘揚提供切實可行的實踐路徑。
2 “武術”與“武術文化”的邏輯探討
隨著改革開放對于社會經濟的全面促進,物質的豐富,思維的拓展勢必促進文化的全面發展。武術界也不例外,眾多學者嘗試從文化學的視角來重新審視武術、剖析武術。1988年,時任國家體委副主任、中國武術協會主席的徐才先生在《武術科學探秘》一書中提出了中國武術未來的兩個走向,“一個是從中國走向世界,一個是從小武術走向大武術”。所謂小武術即指代拳術或技術動作,而大武術是除拳術外,還涉及武術哲學、武術倫理、武術文學、武術醫學、武術經濟等獨特的文化品種。不難看出,“大武術”和“小武術”從傳統文化視角來看就是“道”與“術”的關系,具體而言,即為武術文化、思想和武術技術之間的聯系。徐才先生指出,武術的發展應是由“術”入“道”,由技術而逐漸沉淀出文化。“大、小武術”的觀點強調不應把武術只當作一項體育運動或運動技術來看,更應重視其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影響。這一觀點對于武術界的影響極為深遠,甚至成為我國“武術”發展的指南針。
近年來,針對“武術”的研究發展還受到另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的影響。在08年北京奧運會上,武術比賽成為特設項目出現在奧運舞臺。此次武術比賽共計產生15枚金牌。可惜的是,這些金牌并沒有記入奧運會的獎牌數中。這一次,武術只是“走近了奧運”,但卻沒有真正的“走進奧運”。直至2020年1月8日,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會議通過“將武術列入2022年‘第四屆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比賽項目”,這是武術首次成為奧林匹克系列運動會正式比賽項目。此次武術進入青奧會,實現了我國《體育強國建設綱要》中提出的“力爭武術項目早日進入奧運會”的戰略部署,使我國向體育強國建設目標邁出了堅實有力的步伐,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武術成為奧運項目不僅提升了中國體育的國際影響力,更是推動了東、西方文明交流與互動,拓寬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傳播渠道,對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此,眾多學者開始思索武術在“成為”競技體育項目的過程中所體現出的文化屬性和獨有的文化特色這一歷史存在。在此語境下,“武術應如何更好得繼承中華傳統文化”“如何更好的代表中華傳統文化”“如何更好的發揚中華傳統文化”這些問題就更加值得我們進行深入思考。基于這樣的認知背景,對于武術本體的重新審視,將武術重新作為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已成為主流認知,武術文化也從傳統文化中的文化符號逐漸轉變成為擁有獨立屬性的歷史存在。
3 文化作為武術的本體存在
何為“武術”?何為“文化”?“武術文化”又該如何理解?在不同學者的視角下自然存在諸多觀點。簡單來說,文化是社會行為的聚合體,而社會行為的載體是人本身。古語有云“人無完人”,任何人都是優點與缺點的集合體,文化也不例外。如果不對事物本身的具體指向進行切實的定義,那么文化的傳承就無從提起。許多人在對“武術”進行描述時經常出現“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等泛泛空談,更有甚者,將“武術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劃上了等號,這不僅不利于對于“武術”進行深刻理解,也無法促進武術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由此,文章針對目前已有的代表性觀點進行羅列與分析,從而幫助進一步厘清概念。
目前,較為常見的范式為用文化的概念來界定武術文化,由于有武術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理論預設,那么大多數學者在對于武術文化進行詮釋時習慣使用武術文化的上位概念——文化來進行解釋。溫力在《武術與武術文化》一書中提到:“武術文化是以技擊技術為核心,以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為基礎,包括與武技密切相關的器物、傳承形式和民俗,以及由它們所蘊涵的民族精神共同組成的中國傳統文化。”郭玉成則認為:“從廣義上的角度來看,武術文化可以定義為:與武術相關的各種文化的總和,包括文化遺產中的武術、體育領域中的武術、影視中的武術、文學中的武術、學校教育中的武術等等;從狹義的角度來看,武術文化專指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風格獨特、自成體系的傳統武術拳種流派,其中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內涵,以及武德要求、傳承制度等”。以上運用“文化”來界定“武術文化”,雖然在表述存在一些區別,但可以看出概念包含的范圍非常之廣,而實踐過程中則僅是指代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也有學者從武術所包含的獨特技術屬性來理解武術文化。栗勝夫指出:“武術文化是以研究技擊為核心,以精神和物質為主要內容的動態的綜合系統,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葛國政認為:“武術套路和技法是武術文化的‘活化石’,通過對套路技術的結構和技法運用的學習和繼承,為我們在現代與古代之間建立了一種活動平臺。”以上觀點較為強調“武術文化”的技術屬性,很容易在實踐過程中將“武術文化”與“武術技術”相混淆,使“武術文化”概念本身失去了存在價值。
眾所周知,“武術文化”是對“武術”這一概念的延伸,但許多研究中并未對“武術”與“武術文化”進行清晰的劃分,甚至將二者視為同一事物,這也使得“武術文化”成為“武術”在不同語境下的另一表述而已。一些以“武術文化”為題的研究,實際上還是對“武術”這一概念進行解讀與拓展而已。事物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物質決定意識,那么我們便可以清楚的知曉,一定是先有武術才有可能出現武術文化,武術文化更像是武術本身的衍生物,因為武術概念本身就包含技術及思想文化方面的內容。但在實踐過程中可以發現,二者似乎又呈現出一種微妙的并列關系:“武術”更為偏向技術層面,而“武術文化”則更偏重思想層面。
由此,我們在探討“武術”時不妨加上“技術”二字。這樣,“武術”與“武術文化”的關系實質上就是“武術技術”與“武術文化”之間的關系,二者指代了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就像硬幣的兩面一般不曾分開,但又彼此存在于自己的場域之中。另外,當“武術技術”與“武術文化”相對應時,那么“武術文化”真實所指代的就應該是武術中“非技擊技術”層面的內容,主要是思想內涵,功能價值等精神層面的指代。
4 技擊技法作為武術文化的核心存在
在探討“武術文化”核心之前,我們應明確的知道,武術文化不能等同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只有建立了文化自信,才能成就“文化強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自然而然的要求著“武術文化”與國家的“文化”政策相對接,這都會促進“武術文化”在新形勢下得到快速的發展。但我們也要知道,想要發展“武術文化”必須清楚的知曉其所指代的意義與所包含的內容,這樣我們的工作才不是水中撈月,竹籃打水。
將武術視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可靠載體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因為武術文化本就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把二者劃等號,僅僅強調二者的淵源但不解釋二者的區別,那將使得任何在華夏土地上出現過的藝術形式成為一種虛無,類似于“武術文化”這樣的具有獨立特種的文化子系統將不復存在。
“武術文化”和武術的“文化屬性”是有本質不同的,前者說明武術本身是一種有著自身理論體系的文化架構,而后者則表示武術僅僅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載體之一。以往我們總是將后者看作為前者,混淆使用。就已有研究來看,武術更多是作為一種豐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子文化存在,一種對于母體文化中有關于身體技擊技術的補充。就“武術文化”中經常提到的“八卦”“陰陽”“太極”“克己復禮”“天人合一”“仁義禮智信”等等基本上都是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化用,并未發展出特有的、成體系的理論架構。另外,“武術文化”區別于其他一般文化的特殊性,這樣才能使其具有存在價值。就“武德”而言,也是建立在中華民族傳統道德基礎上的使用“武力”的“道德”而已,它仍是建立在中華民族傳統道德上,同師德、藝德有著同樣的意味。如今,我們再談到“武術文化”時,一定要強調其所具有的時代性及先進性,“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文化領域也同樣適用,只有它的內核與外延都能符合現今社會發展過程中倡導的價值觀時,才能繼續蓬勃發展,反之,勢必被歷史的洪流所吞沒。
既然“武術文化”并不等同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武術文化”與武術的“文化屬性”也不是同一事物,那么“武術文化”到底指代什么?我們可以把它視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存在,更多的作為身體技擊技法,從攻防轉換思想層面豐富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所謂“技擊技法”,應與“武術”中的“技術”相區別,“技擊技法”是思路、是一種思維方式,而“技術”是具體形式、形態。思維方式是文化體系的實質,是文化體系結構中的內核,它從宏觀上規定了文化體系的發展方向及發展程度,成為體系是否完整的關鍵所在,這些思維方式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浸潤良久,才會衍生出所謂“亢龍有悔,盈不可久”“陰陽調和”“剛柔并濟”“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等等“技擊技法”。
總之,武術中圍繞攻防中所使用的技擊思路就是武術的“技擊技法”,也就是武術文化體系中的核心構成。這些“技擊技法”來源于實踐并經過文化母體的熏陶再次通過整合后重新建構出可以指導實踐的理論體系,這些才是“武術”真正區別于其他同類體育項目的根本原因。“技擊技法”的重要性還體現在,所有的身體動作并不是隨意為之,且仍有向上的拓展的空間,“技擊技法”從哲學層面解釋了身體動作各種安排的合理性,這也為“武術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一定思路,在武術文化的傳播過程中,這些思維方式的沿襲勢必為武術的發展提供了切實可用的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