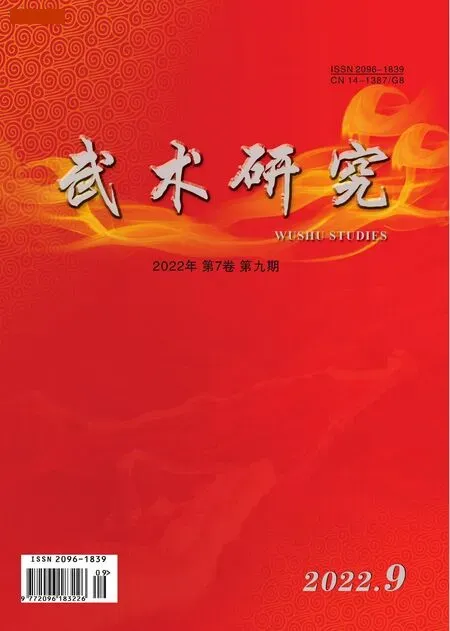村落武術傳承人社會行動研究
鄧曉香 辛 欣
吉首大學體育科學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0
傳統(tǒng)武術在現(xiàn)代社會中發(fā)展式微,而村落武術傳承人肩負著武術門戶發(fā)展的使命。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一些村落武術傳承人仍選擇堅持傳承武術,對促進武術的長遠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在市場化、標準化的理性支配下,傳統(tǒng)武術不斷轉型。然而,在經(jīng)濟、政治和日常生活中仍存在著社會非理性化的現(xiàn)象,中國是一個“人情化”的社會,體現(xiàn)在村落武術傳承人的社會行動之中。本文通過研究村落武術傳承人傳承的社會行動,探究村落武術傳承人社會行動的策略,為武術適應現(xiàn)代化發(fā)展提供依據(jù)。
1 村落武術的再發(fā)現(xiàn)
在社會總體化的運作模式下,社會行動理論關注的視角是人在社會中與成員之間的互動,以及根據(jù)自身的行動,分析個體在適應社會中的行動。本文以村落武術傳承人對鄉(xiāng)土社會的闡釋為基礎,關注村落武術傳承人的人情與面子的關系。以微觀的社會行動為研究,立足村落武術傳承人傳承的社會事實和情境,促進村落武術傳承的認知。在現(xiàn)代化發(fā)展時期,村落具備開放性和傳統(tǒng)性的雙重概念。在城鄉(xiāng)融合的社會時期,村落武術傳承人往返于城鄉(xiāng)之間生存。村落武術是出身于村落的武術傳承人,以某拳種為主要載體。在村落發(fā)展的狀態(tài)下,村落武術的傳承人都是以地方武術拳種為傳承載體,在村落社會進行的武術傳承活動。傳承人的社會行動扎根在當?shù)氐奈湫g拳種,是村落武術傳承人獨特的生活方式。因村落武術傳承人的鄉(xiāng)土出身,以及在現(xiàn)實生活城鄉(xiāng)融合的性質,傳承人面臨著“陌生社會”的人情關系和“熟人社會”的鄉(xiāng)土倫理。根據(jù)調查,村落武術傳承人有的兼任武協(xié)職務,但無實質性的身份權力。
2 村落武術傳承人的社會行動策略
2.1 遵守村落法則,贏得當?shù)厝说闹С?/h3>
傳承人在熟人社會,主動退讓利益。今天的村落仍然帶有明顯的“非正式制度社會”的色彩。在村落法則的規(guī)范下,師父收徒開館,面臨著生計問題,武館的經(jīng)營呈現(xiàn)出與契約社會的差異性。在收徒時,本村的徒弟比外村的徒弟收取費用低,享受村落人情的特殊優(yōu)惠。隨著徒弟學武的年限增加,學費逐年遞減,甚至到三、五年不收學費,一是師徒之間日久情深,礙于情面;二是徒弟通過學拳的成效和口碑,為武館創(chuàng)造了免費的宣傳。大多數(shù)的傳承人是直接在自己家里建“學武堂”,一方面是因為城市的孩子對現(xiàn)代體育項目的喜愛和熱情大于傳統(tǒng)武術,愿意學習武術的人較少;另一方面村落學武的歷史悠久,本村的孩子放學后直接去學習武術,家長既放心也能鍛煉孩子身體。而這種親密的社會關系在商業(yè)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不是說不會發(fā)生交易,而是他們更多的是用“人情”來維持交易,主要的方式是相互饋贈,村落武術傳承人少收費,甚至免收學費,因為傳承人認為只有這樣才是遵守村落的法則,才能在村落中得到當?shù)厝说闹С郑拍苁盏礁嗟耐降埽@是村落武術因現(xiàn)代化發(fā)展困境而回歸傳統(tǒng)“鄉(xiāng)土交易”的策略。傳統(tǒng)武術展演,豐富了村落生活。在傳統(tǒng)的農(nóng)耕社會,中國社會本質上是尋常百姓日常生活的世界。傳統(tǒng)社會武術的價值在于用來防身、戰(zhàn)爭或是游藝,亦或是農(nóng)閑時的娛樂手段,無論如何,都與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改革開放以后,加劇了農(nóng)村人口單向度的向城市流動,原本以教武為生的傳承人也到城市生存,沒有領頭人,村落的傳統(tǒng)節(jié)慶變得冷淡,成為了老一輩人心中的記憶。在國家鄉(xiāng)村戰(zhàn)略的實施下,城市與農(nóng)村趨于同質化,人口回流的現(xiàn)象愈加明顯,在城市生存的人也開始回歸故里,村落的祭祖儀式、續(xù)寫家譜等地方性節(jié)慶形式重回鄉(xiāng)土。地方政府和社會團體提倡武術與精準扶貧、文化、旅游相結合,通過地方拳種的展演,促進文化、經(jīng)濟的發(fā)展,武術成為當?shù)厝巳粘I钪械奈幕嬖冢藗儗τ卩l(xiāng)土的依戀才是武術重歸鄉(xiāng)土的紐帶。加強鄉(xiāng)村建設,促進地方發(fā)展。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實施提出了深挖農(nóng)耕文化所蘊含的優(yōu)秀道德規(guī)范、人文精神和思想觀念,發(fā)揮其淳化民風、教化群眾和凝聚人心的作用。村委會干部是基層權力的代理人,是村落的一份子,在村落的人際關系中發(fā)揮著重要的調節(jié)作用,武術回歸鄉(xiāng)土,首先要做到為村里做貢獻,可以得到村委會的支持,才能得到村民的認可。在節(jié)日中,進行武術展演可以促進當?shù)卣c村落的聯(lián)結,同時,村落子女習武也會受到政府的贊揚,武術傳承人在鄉(xiāng)土中生存,融入鄉(xiāng)村建設是必不可缺。
2.2 調試人際關系,贏得社會的支持
村落武術傳承人對城鄉(xiāng)社會秩序的“文野之別”不甚通識,在武術傳承的外部條件上,傳承人更多的是采取變通之道。村落武術競賽是其中一種,當?shù)氐捏w育部門主辦,地方武術協(xié)會承辦,協(xié)會的操辦者就是當?shù)氐娜N掌門人。傳承人在借助當?shù)卣臋嗔ο拢ㄟ^組織競賽促進各村落武術組織的聯(lián)合,競賽作為當代武術的“禮物”在各門派、拳種之間流動,維護和拓展了村落武術的社會關系。承辦方在競賽中不僅收取了一定的費用,還進行了大范圍的宣傳,有利于為本門派收徒;政府落實了“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體育文化”的工作;參賽者則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認可。競賽“禮物化”的形式顯示出傳統(tǒng)武術人的武德,在不能與現(xiàn)代競技武術同臺比試的情形下,傳統(tǒng)武術的“禮”,拓展了其生存和發(fā)展空間。“政治化”敘事符合國家對武術的要求。與拳譜拳經(jīng)的秘傳相比,村落武術傳承人更加重視書寫與傳播武術,如縣志中武術傳承人擊殺日本兵、勇除漢奸等,此壯舉吸引了一群想要學武的群眾。如地弓拳、梅花拳的資料記載,傳承人以參加反帝反封建的義和團運動為宣傳,體現(xiàn)了為國爭光的武術敘事“政治化”。中國武術代表團曾赴美交流,被領事館贊譽,這一事件在當?shù)孛襟w、朋友圈、網(wǎng)絡等廣泛傳播,實現(xiàn)了民間武術外交。村落武術傳承人的武術敘事政治化不是完全的指向消費者,更多的是在展示文化認同,傳承人傳承的政治正確是首要前提。“網(wǎng)絡化”門戶為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創(chuàng)造新的機遇。村落武術傳承人傳承空間更加廣闊,如傳承人在學校的徒弟以社團的形式傳播武術;成立體育文化公司,推廣武術,促進武術對社會的影響。在城里收徒,村落的鄉(xiāng)土化弱化,收徒的地緣、年齡等分布廣泛,不再局限于本村落和周邊的村落。同時,傳承人還鼓勵徒弟學習不同的武術拳種,拓寬師徒的關系網(wǎng)絡,在傳統(tǒng)的禮俗秩序中,建立的師徒關系發(fā)展到同事、同鄉(xiāng),打開更多的網(wǎng)絡化門戶,嘗試傳統(tǒng)武術回歸民間。
2.3 傳承人對武術文化傳承的情懷
堅守武術的信仰。村落武術傳承人講練功要能“沉得住氣”,短時間內追求成果是不能得到武術傳承人的認可,往往練武的儀式意義是傳承人更注重的。在師父眼中,學習武術不僅是對意志的鍛煉,也是在日常生活中融入習武理論,堅持武術的信仰。傳承人認為武術是人與自然和諧的載體,有利于延續(xù)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根脈,流傳在民間的武術才是原生態(tài)的武術,是不可或缺的本土體育。堅持傳承的本色。村落武術傳承人對社會適應有自己的底線,以本門的武術傳承為主,不會因利益而更改,這是傳承人進城開館授徒,站在市場化運行中的變通。傳承人在理性、道德、風俗、法律和習慣中做出合理的傳承,他們不善于商業(yè)運作,不愿改變傳統(tǒng)的生活現(xiàn)狀,不愿迎合市場的需求,弱化本門武術的傳承,愿意追求自己傳承的本心,守住傳承的本色。堅定武術傳承。民間的武術傳承人都將本門的拳法傳承作為一種嚴肅事業(yè),不以營利為主要目標。傳承人在社會取向中反映出對師門的忠誠,他們在收入上一直在做賠本買賣,但在傳承過程中,充滿了對武術傳承的執(zhí)著和熱愛,在村里建武館,成立武術隊,在學校推廣本門武術,這種以武為樂的情懷是使傳承得以延續(xù)的根本。
3 村落武術傳承人的“文化人”趨向
圍繞村落武術傳承人經(jīng)營武館、競賽等社會行動,發(fā)現(xiàn)傳承人將自身融入到社會結構,以“文化人”的角色,在現(xiàn)代化轉型中展現(xiàn)自身的生存能力。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城鄉(xiāng)融合下,層級權力、市場壓力、認親關系等對傳承人的社會行動造成了制約,面對這種情況,傳統(tǒng)的江湖、師徒、鄉(xiāng)土等為傳承人提供了重要的傳承理念。傳承人社會行動在于將本門武術傳承給下一代,培養(yǎng)武術文化的傳播者和傳承者,體現(xiàn)出“文化人”的趨向。傳承人的文化水平和經(jīng)濟水平普遍較低,生存資本薄弱,在獲取外界支持時不占優(yōu)勢,以鄉(xiāng)土色彩和自身有限的資源用于傳承事業(yè),為促進村落武術傳承,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傳承人“文化人”的邊界,在重建武術文化生態(tài)中要正確衡量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城鄉(xiāng)和利益的矛盾,面對外界有知識、有眼界的人,傳承人該如何守住本心?在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中,傳承人的社會行動既要適應社會結構的變動性和復雜性,也要符合傳承的傳統(tǒng),傳承人傳承武術任重道遠。
4 結語
村落武術傳承人在鄉(xiāng)情、人情和武術情的社會行動策略上進行傳承,在適應變動的、復雜的社會結構中謀求發(fā)展,大多數(shù)傳承人采用“以商養(yǎng)武”的形式進行傳承和生存,但無論他們是以“傳承人”的身份,還是“文化人”的身份,都依然堅守著傳承本門武術的使命,以武為業(yè)的執(zhí)著是村落武術傳承人傳承的精神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