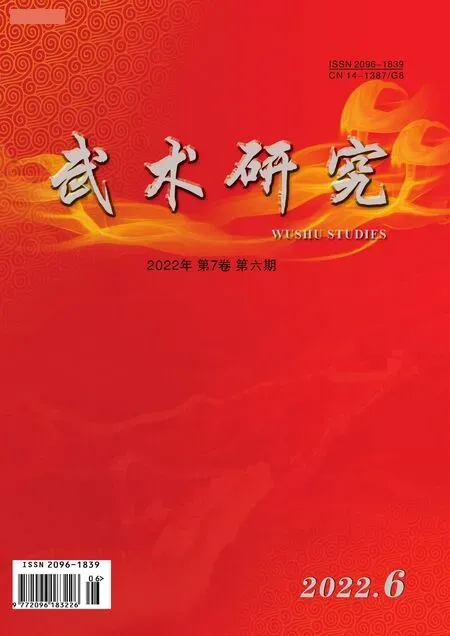推進社會武術規范化發展研究
張路平
國家體育總局武術運動管理中心,北京 030021
1 前言
在國家相關政策文件的支持下,社會武術作為全民健身活動的主力軍,激發了巨大的活力,短短幾年內,武術賽事、培訓以及交流活動蓬勃發展,形式多種多樣,規模日趨擴大,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的精品賽事與培訓活動,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對社會武術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帶動作用,也進一步勾勒與拓展出社會武術的未來發展趨向。然而,部分社會武術賽事、活動的組織者或社會武術個體對經濟利益的過分追求,使得社會武術無序雜亂的“野蠻生長”,對社會武術的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因此,亟需采取措施,規范管理,使社會武術的發展在回歸理性的基礎上,合法合規的健康成長。本研究通過分析當下我國社會武術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從社會和文化兩個層面深入探索影響社會武術規范化發展的成因,通過建構新時代社會武術的發展模式,全面提升社會武術的治理能力,為我國社會武術規范化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支持,進而引導社會武術持續健康發展,全面推動我國社會武術事業的科學可持續發展,為加快體育強國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文化驅動。
2 社會武術發展現狀概述
社會武術是以全民健身綱領為指針,滿足人民大眾健身需要、增強國民身體素質而開展的群眾性健身武術活動。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政府著力推進職能轉變,從簡政放權入手,推動放管結合和優化服務,形成了“放管服”三管齊下、互為支撐的改革局面。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加快推進體育強國建設”。習總書記的講話切實把滿足人民健康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體育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體育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為中國武術事業的發展提供重要支撐,為我國新時代社會武術事業發展提出了新的奮斗目標,為蓬勃發展的社會武術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鮮血液,拉開了社會武術發展的新篇章,把社會武術推上了新的歷史高度。
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體育工作重要論述的指引下,依據國家體育總局的整體部署和武術事業發展所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國家體育總局武術運動管理中心印發了《中國武術發展五年規劃(2016-2020年)》。繼而,國家體育總局等十四部委聯合印發了《武術產業發展規劃(2019-2025年)》,圍繞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需求,充分發揮了武術在實施全民健身國家戰略、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為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社會和諧穩定提供了堅強保障。
隨著一系列支持政策的出臺,社會武術賽事組織越來越規范,參與人群越來越眾多,結合地域文化與經濟優勢、整合不同行業資源發展的武術+旅游、嘉年華等跨界發展新模式越來越廣泛,有效促進了社會武術活動的創新發展。國家體育總局武術運動管理中心推出的太極拳健康工程活動、武術段位制、“全民健身”武術走基層以及全國武術之鄉工作,在全國形成了一系列品牌賽事與典型培訓,更加突出了社會武術賽事品牌的張力,擴大了社會武術賽事與培訓的知名度,提高了大眾的認可度,有效推動了我國全民健身事業的發展。
3 社會武術發展的現實困境
在社會武術如火如荼的發展態勢下,面對巨大的經濟利益的引誘,社會武術活動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出現一些良莠不齊的現象。為了規范全國各類武術賽事活動的組織管理,提升武術賽事活動辦賽服務水平,促進武術運動健康發展,國家體育總局于2017年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武術賽事活動監督管理的意見》(體政字〔2017〕107號),中國武術協會于2019年3月頒布了《武術賽事活動辦賽指南》(武術字〔2019〕136號),并于2019年3月至5月開展了全國武術賽事活動監管專項行動,要求“各省市武術管理中心和武術協會按照屬地管理原則承擔本省市區域內武術賽事活動的監管責任,依法依規綜合運用約談、告誡、聯合查處等多種手段,強化各類武術賽事活動主辦和承辦單位的主體責任意識,督促指導各類武術賽事活動主體規范履行職責,”以營造風清氣正的社會武術環境,引導、規范社會武術賽事活動以及個人武術行為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但是,仍然有一些社會武術團體、境外武術組織以及部分民間武術愛好者,借著國家政策支持的東風,紛紛粉墨登場。他們明知有禁令,但仍然心存僥幸,置道德品行于不顧,在國家法律法規的邊緣地帶,做出了一系列違反公序良俗、違反武術行業規范的失范行為。
(1)個人行為失范。在社會武術“百花齊放”的繁茂發展中,社會基層習武個體為了獲得社會認同感或實現自我價值,往往喪失人格底線和社會責任,采取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行為或與社會主流價值觀相抵觸的方式,在武術環境中表現出種種與行業規范、社會公德相違背的行為,造成了文化審美與價值取向的混亂。例如,前幾年曾經表演“雀不飛”和內勁拍西瓜、號稱能夠單手破裸絞的太極拳“大師”雷雷,擅長“隔空打人”功夫的太極“大師”閆芳等等,為了追名逐利,不惜背離武術常識,采用惡意炒作、虛假宣傳等手段招搖撞騙。再如,所謂的“渾元形意太極門”掌門人馬保國,自詡戰無不勝,結果在一場名為“演武堂之江湖十六”的民間擂臺比賽中,被業余搏擊愛好者王慶民在30秒內擊倒3次并休克。此事件迅速在網絡及各大社交平臺上引發了廣泛關注,關于中國武術到底能不能打的議論和質疑此起彼伏,甚至部分別有用心的境外媒體也借機諷刺中國武術,讓中國武術多年來獲得的良好形象遭到許多質疑,為中國武術事業的整體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損害。2020年9月21日,江西省武術協會發布《關于對我省余昌華違規參與“沂蒙傳奇武術擂臺爭霸賽”的嚴正聲明》,聲明中表示,余昌華在接受省武術協會約談后,雖然口頭表示不會以“約架”等方式參與商業炒作,但最終又私自參賽,“該行為惡意欺騙省武術協會,嚴重違背了國家武術運動管理中心、中國武術協會頒布的參賽指引等文件,屬于違規參賽,”江西省武術協會依據相關管理文件對其進行處罰并做出聲明。諸如此類的失范行為,嚴重損害了中國武術在社會中的形象,侵害了武術發展環境、破壞了社會和諧,成為社會武術規范化發展道路上的絆腳石。
(2)賽事組織失范。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陸續印發多個重要文件,取消了商業性和群眾性體育賽事活動審批,這一舉措激發了武術市場活力。為了加強對體育賽事活動的監管和服務,確保相關政策措施和責任落實到位,體育總局發布了《體育總局關于進一步加強體育賽事活動監管和服務工作的通知》,要求“進一步加強體育賽事活動監管和服務,保護體育賽事活動參與者的合法權益。”但是,在商業利益驅使下,一些民間武術社團、“草臺班子”,為了贏得收視率和廣告收入,滿足一己私利,藐視行業規范和社會影響,脫離武術主管部門的監督管理,私自組織“網絡約架”、“跨界格斗”等武術擂臺鬧劇。如上文中余昌華違規參加的“沂蒙傳奇武術擂臺爭霸賽”,系由北京德匯海川傳統武術俱樂部有限公司在山東臨沂違規組織并通過網絡進行直播的違規賽事,該賽事“借冒用‘沂蒙’‘武術’之名,行惡意炒作、非法牟利之實,特別是在有關部門命令禁止的情況下采用欺騙、隱瞞等非法手段頂風而上、肆無忌憚,違規辦賽,”在武術界造成了惡劣影響。賽事組織方與參與者所在地北京市武術運動協會、山東省武術運動協會已根據相關管理文件,分別對主要組織者和參與者進行了處罰并于同一時間作出相關聲明。
4 社會武術發展現實困境的成因探析
(1)社會武術發展現實困境的社會根源。在社會武術發展的具象化進程中,出現諸如“馬保國”“余昌華”等特定的社會現象,究其原因,既有社會個體對武術本質功能認知缺乏的原因所在,更是特定社會個體在名利驅使下的肆意妄為的結果。馬保國自詡為“渾元形意太極門”掌門人并橫行網絡江湖數年不倒,既表征出在當今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引導力的相對弱化,同時也說明社會大眾對武術常識認知的客觀缺失,兩個層面的因素共同推動了社會大眾對網絡炒作的文化認同。僅就“渾元形意太極門”這個名稱論,相對于武術中“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風格獨特、自成體系”的形意拳、太極拳流派而言,本身就是馬保國為搏出名創編的一個不折不扣的大雜燴名稱。再看馬保國的教學視頻,胡蹦亂跳、滑稽可笑,所謂的“閃電五連鞭”招數屢屢成為網絡熱梗。在名利的驅動下,他竟然充滿自信地參加搏擊比賽,最終被業余搏擊愛好者王慶民打的一敗涂地,還大言不慚,雷語頻出,以致于淪為大家的笑柄,在輿論場中扮演了被群嘲的角色。馬保國“口口聲聲弘揚傳統武術,實際上做的都是傷害傳統武術的事。斥責年輕人不講武德,他本身卻毫無正大光明、謹言慎行、尊崇敬畏傳統的武德”,他的行為背離了武術精神,而一些熱衷流量、推波助瀾的互聯網平臺,在網絡流量與關注度的利益面前丟棄了作為媒體的基本職業道德與操守,拋棄了媒體本應擁有的基本社會責任感,為他這種“丑行”“鬧劇”提供了傳播渠道,“放任‘丑行’成為流行,讓招搖撞騙大行其道,這本身就是對社會風氣的傷害, 特別對于尚缺乏判斷力的未成年人,這是對價值體系的毒化。”
(2)社會武術發展現實困境的文化根源。一些網絡媒體平臺,為了吸引眼球、博得流量進而達到獲取經濟收益的目的,經常制造娛樂噱頭進行毫無底線的炒作。馬保國這種脫離于武術界主流所存在的“另類”被認可,在媒體的包裝下橫空出世,成為太極“網紅”,甚至于形成了一種強勢的影響武術發展的雜音,使得原本屬于邊緣的“另類”文化借助媒體炒作“越位”凸顯,不僅獲得了展示的合法性,還躋身公共空間并且僭越主流文化的位置,受到不明真相大眾的追捧,在當今全媒體時代形成強勢影響和轟動性效應。這種文化亂象的蔓延和對大眾的裹挾,反映出大眾對中國武術的誤讀。進一步而言,是大眾對中國傳統文化認同感的缺失,對民族文化自信的缺失和對民族信仰的迷失。在媒體的炒作下,馬保國在網絡上頻頻口出狂言,失敗后反而感覺榮耀,成為低俗文化亂象的代表。低俗文化的盛行顛覆了人們的道德底線,扭曲了社會的主流價值,使大眾模糊了應有的基本價值尺度。大眾被時潮所裹挾,盲從低俗,逐漸淡化了對主流文化的敬畏感、羞恥心和審美精神。媒體大肆炒作馬保國,實際上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丑化,是對社會良好風氣的污染、是對文化信仰的褻瀆。長此以往,會使大眾缺失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進而產生信仰危機,缺失文化自信,長此以往,再優秀的民族也會降格,再輝煌的文化也會斷送。由此,我們從文化層面對這一特定現象的解構就成為認識武術文化的重要路徑。
5 新時代社會武術規范化發展模式建構
(1)推行政府行政的整體性治理體系。針對頻頻出現的賽事組織失范行為與個人失范行為,如果一味禁止,既不現實也不可能。今天禁止了馬保國,明天也許會出現李保國、張保國,今天禁止了“演武堂之江湖十六”,明天也許會有“演武堂之風云十七”。因此,既要進行糾偏和遏制,也要疏堵結合,在打擊違法賽事的同時,給出大眾一個發揮的空間,打造出合法的賽事,準確評定習武水平的高低,正確引導傳統文化在社會、民間中的傳播。首先,由武術主管部門充分發揮業務監管作用,進一步加大監管力度,完善監督機制,依據2021年1月印發的《清理整治武術亂象規范賽事活動管理辦法》,與民政、工信部門共建共管,把游離于政府管理之外的社會武術組織吸納進來,要求他們既在民政部門注冊管理,又成為中國武術協會的會員,按《關于進一步加強武術賽事活動監督管理的意見》、《武術賽事活動辦賽指南》、《中國武術協會會員管理辦法》等相關文件約束他們的行為規范,不斷強調業務指導與行業監管,優化行業環境,促進賽事組織合法化、規范化建設。其次,對于行為失范個人,也同樣吸納入中國武術協會,要求他們樹立正確的武術觀,自覺、主動接受武術主管部門的監督,遵紀守法,遵守公序良俗,科學、安全、文明習武,弘揚武術傳統文化,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全面建構社會武術法治治理體系。在全面推進社會武術規范化發展的進程中,建構社會武術法治治理體系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國家體育總局武術運動管理中心、中國武術協會于2021年1月印發的《清理整治武術亂象規范賽事活動管理辦法》中,涉及須重點清理整治的武術亂象有十條,其中既包括常見的自封“大師”“掌門”、自創門派等社會陋習,又有以“拜師收徒”“賀壽慶典”“評比表彰”等為名收費斂財的違背公序良俗行為,還有借武術之名從事賭博、詐騙的違法違規行為。因此,亟待建構規范穩定的社會武術法治治理體系,由武術主管部門與公安、司法、文化、工信等部門緊密合作,形成共治機制,依托武術行業管理網絡,注重發揮法規制度的引導、規范作用,強化體育執法,自覺運用法治方式嚴厲打擊不遵守行業規范、不把持行業操守和破壞社會道德準則的行為,共同清理整治亂象、維護武術安全。
(3)落實社會武術主體的自治能力。“馬保國”“余昌華”等一系列鬧劇行為的背后,折射出的是習武個人由于在武術界的自我身份感缺失而引發認同危機,由此表現為在身份認同驅動下產生的個人失范行為。因此,需要采取靶向施策、精準對接的治理措施,教育引導習武個人樹立正確的社會價值觀,推動社會武術行動主體自治,增強自我發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律規范的能力,將武德教育融入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武德建設,大力弘揚“崇德尚法”的正能量,充分實現武德在社會武術主體自治中的規范和約束功能。不斷強化社會規范的約束力,完善武術發展協調機制,形成社會武術主體自覺厲行法治的良好格局,實現社會武術的有序發展。
(4)提升社會武術主體意識形態領域治理能力。借助門戶網站、微信公眾號、APP和微博矩陣等多種形式,及時發布相關武術政策的解讀,回應社會關切的焦點問題,加強科學引導和典型報道。不斷強化輿論宣傳,加大對于武術常識的普及教育力度,增強社會大眾對中國武術的普遍認知,營造出良好的社會氛圍。通過全網絡、多渠道、多層次宣傳武術知識,以中國武術作為媒介傳遞正能量,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營造出純潔健康的武術文化環境,推動傳統文化成為主流文化并在社會層面形成共識,提升大眾對中國武術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感,讓馬保國之類的非主流武術騙子在大眾面前無處遁形。只有讓主流文化以自身的強力和鮮明的導向占據公共空間,在公共平臺實現全覆蓋,不斷占領意識形態領域的主陣地,才能真正抵御低俗之風、引領社會風氣,才能引導大眾重拾民族精神、重塑文化自信,打造出新時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武術發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