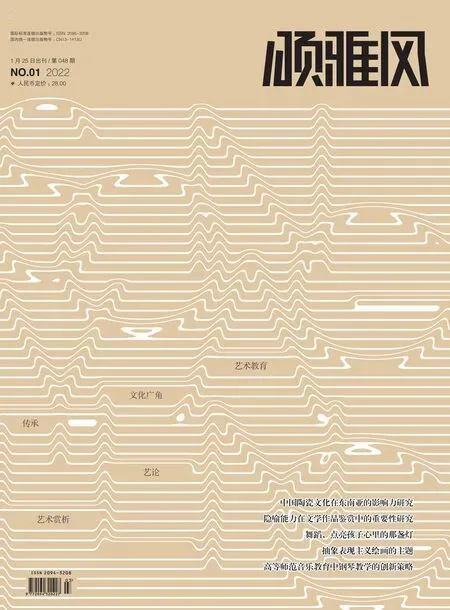技術畫像的宇宙
◎馬銘涵
弗盧塞爾在《攝影哲學的思考》一書中敘述的影像宇宙,是一種用照片圍成的“魔法圈”。我想象這個“魔法圈”像是一團不斷運動、不斷變化顏色的由馬賽克組成的云狀物質,在這樣的影像宇宙當中,照片被當作一件沒有價值的東西而接受下來,人人都能生產,人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去對待它們。但事實上我們被照片操縱了,被它程序化了,在儀式化的舉動中,充當了裝置的反饋機制。在弗盧塞爾的敘述中,渾然不覺生活在“多余的影像”洪流當中的我們,是麻木的,是放棄思考的,甚至可以說是被一種裝置潛移默化地精神控制的。
這種敘述確實給人一種很窒息、很恐怖的感覺,但同時也對弗盧塞爾的擔憂感到一些懷疑。一方面,他所形容的這個影像宇宙是真實的,人們早就對照片習以為常,對身邊持續不斷的變化習以為常,對如今影像宇宙五彩繽紛的色彩習以為常,似乎已經處于被程序化的狀態當中;另一方面,弗盧塞爾對裝置程序化的擔憂是否有些過激呢?誠然,保持警惕性是對的,但是這種對被程序化的擔憂有點像在擔心人類是否會被人工智能取代,或者說,麻木于影像宇宙的我們,真的會變成沒有手腳的缸中之腦嗎?
在一種簡單的設想當中,整個物質世界是無限的,在這個無限的世界中,隨機發生著各種事件,每一個事件都可以被無數影像記錄和說明。這些影像本身是無限的,也就是說,盡管沒有被裝置制作成照片,但是影像的無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每一個影像的可能性都包含一段信息,信息之間可能重合,但每兩個可能性所包含的信息都不完全相同。影像的宇宙就是那些被裝置捕捉到的影像的集合,是可以視覺識別的部分,看起來就像黑暗電視屏幕中閃現的雪花。針對某一事件,如果影像的可能性被足夠全面地捕捉,那么影像的宇宙對這個事件的描述就會足夠清晰,就能夠無限趨近于還原這個事件。就像一個多邊形平面的邊數無限增加,它就無限趨近于圓,這可能是某種對影像宇宙的樂觀態度。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首先,影像的可能性很難做到被足夠全面地捕捉,我們對一個事件的描述永遠都處于盲人摸象的狀態,而這頭象在我們的解讀下則會變成橡皮管子、簸箕、一堵墻和一條蛇的神秘組合;其次,即使窮盡影像的可能性,事件真的會被還原嗎?即使窮盡影像的可能性,也不過是對應著物質世界,在影像的宇宙中復制了一個同樣的事件本身,而這種影像拼成的事件的復制品本身并不具有意義,但由于它窮盡了所有可能性,即使被完全復制,也無從解讀。就像弗盧塞爾對程序的定義,那是一種完全自動的、基于偶然性的組合游戲,就像擲骰子。但是顯然,即使所有可能的從1到6的組合方式都被實現,這種全面的窮舉行為也不能構成意義,并傳達出信息。
顯然,在前面提到的樂觀設想當中,影像中包含的不同信息之間的區別類似于拍一組靜物的不同角度,如果真是如此,撈起信息洪流中所有碎片也不過是撈起一些“多余的照片”,而我們希望做到的顯然不是這樣簡單。不是按照已經規定的方式來生產具有象征性的平面,不是在攝影裝置的程序規定當中做一個兢兢業業的機器零件,而是從這一套程序當中脫離開來,再次控制裝置,找回人類對裝置的控制權。是的,在影像宇宙當中人人能夠手握相機,在攝影行為之下產生的影像大部分是沒有意義的,這里的沒有意義是指在推動影像發展角度方面沒有意義。而真正的攝影者則要努力制作有意義的影像。在此,弗盧塞爾提出了我們要前進的方向——用富含信息的影像來對抗多余的影像的洪流。
影像的宇宙是顆粒狀的,它具有量子化的特征,而裝置的世界里,那些看起來自由滑動的功能,實際上也是以這種顆粒狀的結構為基礎,所有“波浪狀的”(功能)都是由顆粒組成的。而波浪狀的功能是由顆粒縱向組織而成,那么如果將顆粒橫向拉長呢?也就是說,照片是一個固定時刻的投射,其中沒有線性時間而是自己內部的循環,如果將照片的時間點在時間軸上橫向延伸,將原本不具有時間長度的顆粒像沙包一樣向前扔出去,為照片再次擁有時間性,將重新拉長的時間的一瞬截取下來,那么我們獲得的會是更為細碎的顆粒嗎?這樣的攝影行為具有意義嗎?存在于裝置所規定的程序當中嗎?
在看照片的時候,被認為(錯覺)是在觀察現實世界,但實際上是進行一種解碼行為。如果沉浸在這種解碼行為中,不就是自愿進入程序化當中,也就是依照程序試圖理解信息嗎?那么被程序化也就是必然事件,因為我們必須要依照某一種邏輯進行,而在這之后,即使拍攝行為盡量避免程序化,但隨著解碼的進行,拍攝行為還是被并入程序化的范圍當中,然后裝置的程序變得更加復雜,所謂的黑盒子(我們害怕的、無法控制的部分)也變得更加龐大,更加難以愚弄。
應該說,攝影哲學中所期望的人類掙脫影像宇宙、奔向自由的突破口仍然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充滿實驗精神的攝影者還努力在一般意義上的裝置的語境下回答自由的問題,但最終會踏出那一步的。如果影像宇宙可以依照僵化的程序窮舉所有影像的可能性,那么依照人類大腦的程序,通過不斷地思考、批判,以及持續的實踐,也一定可以找到往前走的那一步,那呈現出來的新的領域也許是我們還沒辦法想象的光景。我很期待它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