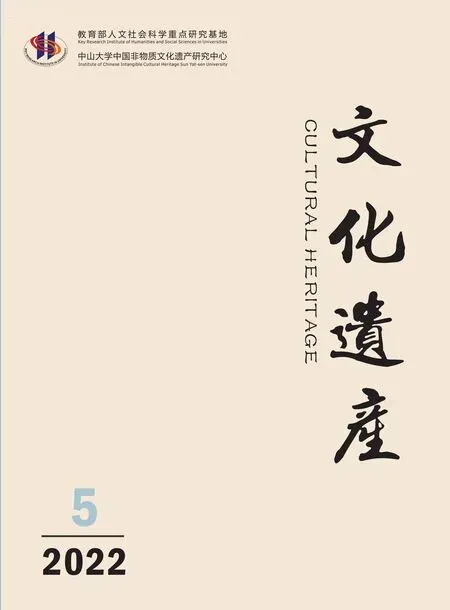從神話視角尋根中華文明記憶
吳玉萍
引 言
神話與中國文化緊密相連,從“中國神話”到“神話中國”,可見一斑。但發出原問:神話是什么?《不列顛簡明百科全書》的解釋是:“神話是一個集合名詞,用以表示一種象征性的傳達,尤指宗教象征主義的一種基本形式,以別于象征性行為(崇拜、儀式)和象征性的地點或物體(廟宇、偶像等)。”這是學理層面給出的定義。然而通俗層面來講,在人大多數人的思維里,神話同遙不可及相等,跟虛幻莫測無異,常將“神話”視為是古老的神奇事件的“象征講述”;或者,“神話”是有關人與自然古老關系的“幻想故事”。之于“象征講述”和“幻想故事”兩種說法,前者可能偏向于真實,后者則偏于虛幻。因為“象征”(symbolize)是指用具象的事物暗示特定的指向,以表達真摯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是一種以物征事的藝術表現手法,屬合理化、系統化、制度化的隱喻,并非“胡謅”。而“幻想”(fantasy)是指違背客觀規律的、不可能實現的、荒謬的想法或希望。不過“幻想”作為一種指向未來的特殊想象,可能它想象得比光速還快,大大超越了同時代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但終不失為把人們引向未來、開拓未來的“仙杖”。
綜上,不管是哪一種解說,神話都有一個共通點,即它是人類宇宙觀與生命觀的內在表現,伴隨著人類的緣起,其所涉及的都是人與自然、宇宙與人生等的一些根本性命題。神話與人類之間的關系也直接決定著神話記錄人類文明的特殊功能,因為神話的存在,中華文明成為唯一沒有斷過流,傳承下來的文明。然而,在社會不斷發展、文明不斷進步的過程中,神話一度被歷史取代,出現了神話的歷史化,中華文明的歷史長度被“截短”。
一、神話歷史化
回顧神話歷史化的進程與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解構歷史,二是建構神話。恰如列維斯特勞斯所言:“神話,從一個部落到另一個部落,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分成了兩條道路,‘一是精心虛構故事,二是從合乎歷史著眼,重啟神話。’”所謂解構歷史即將神話本來所具備的歷史成分進行解構,認為神話完全是虛妄之說。這就是精心虛構故事。
神話在中國的發展深遠,但曲解依舊存在。從文學本位看,神話原來僅被看作是文學想象之源頭,甚至被歸類為“幻想”“虛構”“子虛烏有”的同義語;在文學學科內部,則被歸入與作家經典文學相對的、下里巴人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文學”。從歷史本位看,神話相當于科學的歷史觀之對立面“偽史”。從哲學本位看,神話是非理性的孿生兄弟;因而成為哲學思考和理性的對立面。這些屬于思維方式層面對于神話的誤讀。神話在傳播層面同樣有著被遮蔽的危險。神話發端于原始人的浪漫感想,產生于無文字的大傳統時代,隨著文字書寫小傳統的獨占鰲頭,神話發生了演變,被視為虛構和不真實的“故事”。
第二個階段是建構神話,即將神話重新改造,使之完全符合歷史,甚或可以說符合歷史學家的口味。這就是重啟神話。確實,神話傳播是一個長時段的行為,每個時代都會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修改,旨在符合他們借用神話的目的。虛構和重啟中不乏有意識形態層面的,如為了滿足政治宣傳的需要,為自己純正的血統找到歸依,這時很多非英雄神話也會被改編成英雄神話。也有很多神話的重構是為了迎合民眾口味,如愛情神話,在封建時代里,愛情題材神話總是被人們寄托掙開世俗的愿景。恰如茅盾所說:“‘文雅’的后代人不能滿意于祖先的原始思維而又熱愛此等流傳于民間的故事,因而依著他們當時的流行信仰,剝落了原始的獷野的面目,給披上了綺麗的衣裳。”在這般綺麗的外衣下,神話的原初意義必然被遮蔽。
中華文明的記憶經常以歷史為參照,神話屬于不真實的想象,因為神話與歷史的對應關系以及神話的真實性一直是爭論的焦點。尤其是在中國,神話基本被淹沒,成了人們的追憶。對于這一現象,袁珂先生解釋說:“神話為什么會轉化做歷史?深一點的發掘,就可以知道這原來是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如果不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事情就絕不會這么順利地進行下去,能夠順利進行下去而且是有意識地在進行,就說明是符合的。統治階級既然把先前勞動人民在神話傳說里創造的勞動英雄據為自己的祖宗,抬高到天上去,就希望寫進歷史里的祖宗的行跡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而勞動人民群眾口頭傳說的這些英雄的行跡呢,卻頗有一些‘搢紳先生難言之’的不很‘雅馴’的東西,所以四張臉的黃帝和一只腳的夔一定要勞煩孔老夫子來為他們的形體作辨正,這辨正當然是統治階級很歡迎的。”在這樣的背景下,神話只能喪失原貌,在歷史學家們的手中置換再生,或隱蔽或刪節或誤解。
二、重新發現神話
在神話歷史化之后,神話的文化意義和文化地位被遮蔽。然而,一批為神話奔走的學者始終未曾停止給神話復位的道路。20世紀初期至四十年代,中國神話學的早期奠基者們,已經開拓出綜合運用傳統國學研究方法與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新方法來研究中國神話的學科范式創新之路,國學研究“二重證據法”與比較神話學、古典進化論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格外受到青睞。但由于中國學科體制的劃分問題,神話學研究一直被置于民間文學或民俗學的研究領域,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新方法論”熱潮的帶動下,神話學研究要求突破有限的學科范式及方法變得愈加強烈。最具代表的是文學人類學學派,從八十年代旗幟鮮明地倡導經典的“破譯”并作出了諸多行之有效的嘗試后,一直致力于構建本土理論話語,堅持打通學科壁壘,形成交叉學科研究視野,尤其重視搭建神話與考古之間的橋梁。發展至今,該學派提出的“神話觀念決定論”“大小傳統”“中國神話到神話中國”“玉成中國”“編碼理論”等理論與研究范式都給文明探源提供了重要研究視角與參照。中國神話學研究也逐步突破原來的瓶頸引發了“超越文字限制的跨學科范式”,這種跨學科范式帶來了新觀念、新思路、新方法。最突出的一點便是在突破文字書寫小傳統的圈囿,聚焦到時間更為久遠的口傳大傳統,重新發現神話、重估神話價值,從神話視角尋根文明記憶、探尋神話與文明起源。
無文字的口傳對于神話和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為神話在被文字記載并傳播的過程中,難免會被歷史學界削足適履。“原始的歷史家(例如希臘的希洛道忒司)把神話里的神們都算作古代的帝皇,把那些神話當作歷史抄了下來。所以他們也保存神話。他們抄錄的時候,說不定也要隨手改動幾處,然而想來大概不至于很失原樣。可是原始的歷史家以后來了半開明的歷史家,他們卻捧著這些由神話轉變來的史料皺眉頭了。他們便放手刪削修改,結果成了他們看來是尚可示人的歷史,但實際上既非真歷史,也并且失去了真神話。所以他們只是修改神話,只是消滅神話。中國神話之大部恐是這樣的被‘秉筆’的‘太史公’消滅了去了。”所以說,從文本小傳統到口傳大傳統的轉向使得神話的原貌及其在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性上凸顯了出來。神話學重新“以神圣敘事所帶來的社會與文化的認同與建構為核心,來確立自己獨立的文化地位。”在田野調查和文化自覺的支撐下,神話重新煥發聲色。
關于神話與歷史,如果置于文化大視域中來分析,兩者的關系便會明朗化。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認為歷史始終都滲透著,而且必須滲透著神話因素。因為“神話傳說實質是上古人民的想象,神話時代的實質同樣是一種建構于想象的文化重構與述說。神話時代的存在是在傳播中形成的,是歷史的影子,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歷史直接、簡單的對應物。神話傳說故事失去流傳(口頭語文字等形式)的介質,就很可能失去其文化生命力。”這句話道出了神話與歷史的關系,即神話與歷史相依相承。翻開中國歷史,從虞夏商周建立朝代,到諸子百家著書立言,再到《史記》《清史稿》等史家文本,無文字的口述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的太多事件與觀念有關,而這里的觀念即為“神話觀念”。因此,從神話中尋根中華文明,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代傳承的又一重要“實踐”。
三、神話與中華文明記憶
從上述發展脈絡的簡單梳理以及神話在當下的發展來看,神話與虛構漸行漸遠,從質疑與祛除到復興與火爆;從神話歷史化到神話歷史的提出;從對神話故事的追憶與講述到關注其作為文化根脈的結構性作用,人們對神話的認知發生了改變。尤其是在人類學叩響學界大門之際,探討人類起源、追尋原住民儀式背后的神話支撐、書寫民族的文化記憶成了學者們所珍視的學術真果。為此,神話學研究者們逐步嘗試理清神話在哲學、歷史等學科中所發揮的根本性作用。這一切都源于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帶來的學科反思。
民族文化如何被記憶?神話如何探源中華文明?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對文化有一個了解。關于文化的定義有很多,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對文化進行定義時說:“文化是一個復合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其他人們作為社會成員所獲得的一切其他能力和習慣。”馬林諾夫斯基在《文化論》中說“文化是指那一群傳統的器物、貨品、技術、思想、習慣及價值而言。”可見,文化是一個被表征、被承載的對象,想要在民族記憶中呈示,必然要通過一定的形式。記憶在身體中積淀和積累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體化實踐,一種是刻寫實踐。關于這兩者的關系,保羅·康納頓解釋道:“從口頭文化到書面文化的過渡,是從體化實踐(incorporating practices)到刻寫實踐(inscribing practices)的過渡。文字的影響取決于這樣一個事實:用刻寫傳遞的任何記述,被不可改變地固定下來,其撰寫過程就此截止。標準的版本和正規的創作,是這種狀況的象征。這種固定性給創新帶來動力。當文化記憶的傳播開始以復制其刻寫為主,而非以‘現場’口述之時,即席創作變得越來越困難,創新變得制度化。”很顯然文字承載的社會記憶從開始的創新到后來的刻板、僵化是因為被一以貫之地復制,只有當口頭文化以一種高昂的姿態挺近,民族的文化才能被還原,悠遠的記憶才能被喚醒,文字以外的大傳統才是直達文明之根的密鑰。
然而,在文明被書寫記載的過程中,我們依賴的主要還是文字,文字以外的大傳統沒有被重視,很多時候我們在意且記住的又都是刻寫下來的歷史,因為“回憶被當成文化活動而非個人活動的時候,它容易被看成是對一個文化傳統的回憶;反過來,這種傳統也容易被想成是某種刻寫的東西”,這就是我們在對民族過去進行回顧時依賴文字的主要原因。相反活躍在文字以外、承載獨特文化內涵、詮釋歷史多姿多面的圖像、服飾、器物、建筑、儀式等具象符號卻經常被忽略,而這些被忽略的具象符號則受神話觀念支配。有文字記載的各種生活習慣、生存禁忌、宗教信仰、民俗風情就像一個進行了編碼的“程序”,需要破譯與還原。
慶幸的是,我們已經意識到伴隨人類而生、以原始信仰為主的神話,是民族最古老的記憶,及至今天,依然具有重要價值。因此,要真正了解一個民族的歷史必須深入到神話層面,因為中國有代表的文化,如祖先崇拜、清明文化、端午文化等都能從神話學角度找到發生學的意義。知曉了神話之于文化所承載的意義、知曉了從歷史書寫到神話敘事帶來的文化崛起、知曉了神話能有效地幫助我們重覽民族的生發與前進的奪目、輝煌,能讓我們看到一個民族歷史的深遠與厚重,一個國家文化的璀璨與不朽。
結 語
習近平總書記就中華文明探源與研究問題上多次指出要加強多學科合作,如“要加強統籌規劃和科學布局,堅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學和歷史學、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聯合攻關,拓寬研究時空范圍和覆蓋領域,進一步回答好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要加強多學科聯合攻關,推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神話的跨學科研究范式與之契合,具備從文化領域深入中國文明的探源。因為神話研究不僅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相關,同樣還與中華民族的優秀精神相關。神話承載著宇宙發生、人類起源等原始意象,這些意象包含的精神內核有開天辟地的創造、舍生取義的奉獻、百折不撓的堅韌等。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些精神又與后來的先進理念一脈相承,如從“盤古”到“紅船”開天辟地精神的傳承;從“女媧”到“匹夫”擔當精神的傳承等。
中華文明發展至今,在強調復興優秀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同時,要關注到先于文字的大傳統,關注到神話與歷史的關系,關注到神話的重要意義。神話沖出文字書寫的牢籠,不僅帶來了研究范式的革命,而且也將其與中華文明牢牢地拴在了一起,成了尋根民族記憶的重要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