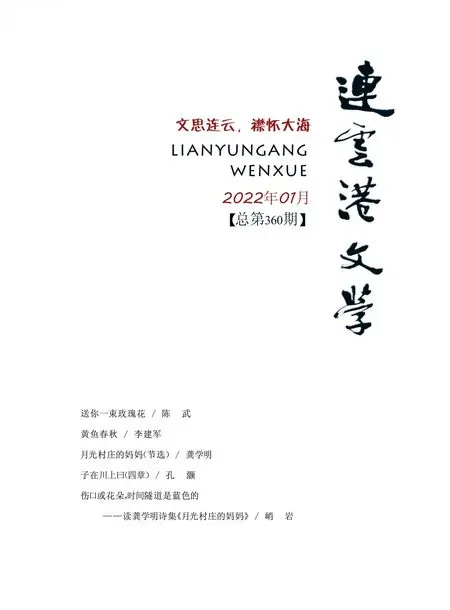送你一束玫瑰花
陳 武
1
朝九晚五,是公司正常的上班形態(tài)。她每次都是踩著點走進辦公室的,釘釘打卡后,正好九點。許多同事都為她擔心,為她捏把汗,都知道她在玩火。玩火者必自焚。
同樣,下午五點一到,她也踩著點下班,一分鐘都不多待,且行色匆匆。有N 次,她身體的某個部位都碰到了同事的椅子,驚嚇了人家,把自己都碰疼了;或者呢,碰翻了垃圾筐;要不就是自己桌子上的垃圾忘了隨手帶走。有一次,外面正下著傾盆大雨,她連傘都忘了拿。誰都會猜到,她馬上就會回來取她掛在椅背上的傘——總不會淋著一身雨走吧?家里能有什么樣的大事急事不得了的事?可她一直沒有回,寧愿淋雨,也不愿意耽誤時間。第二天,又帶來一把舊傘——雨還在下。
她叫龐雁,同事們都叫她雁子,是一家文化公司的圖書文字編輯,業(yè)務能力強,性格還算溫順,只是表現(xiàn)上有點孤傲。孤傲也是別人對她的印象——誰都不在她眼里。難道不是嗎?同事們之間,偶爾會搞個小聚餐什么的,也會在周末來個深圳周邊游,她一次都沒有參加,就算請她,她也拒絕。又沒有男朋友(大家憑感覺),更不需要接送孩子(不像是個離異者或未婚生子的女人)。那她匆匆回家干嗎呢?沒有人猜得出來。同事們嘀咕幾次之后,也就習以為常了。
話說這天下午五點一到,龐雁照例迅速關了電腦,第一個沖出辦公室,在寫字樓出口旁的便利店里,買了兩個素菜包子,邊吃邊走進地鐵六號線紅花山站,走到站臺時,正好吃完。她從包里拿出一個玻璃水杯,喝幾口溫水,地鐵就進站了。這時候還不是下班高峰期,或者說離下班高峰期還有一個小時,但車廂里已經擠滿了人。從人們疲倦的神色上看,都是下班的青年人,像她一樣,剛從寫字樓里沖出來,又趕赴另一個場所了。
從紅花山到鳳凰城,也就半個小時的時間,龐雁一時想不起來她住鳳凰城小區(qū)幾號樓,北區(qū)還是南區(qū)。鳳凰城小區(qū)太大了,有五六萬人居住,有不少是出租房。龐雁不敢說每戶人家都跑過,但敢說每幢樓的每一層都跑過,那也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了。現(xiàn)在,龐雁急著趕回鳳凰城,就是要跑樓的。這么說,大家大致都能猜到了,龐雁是一位兼職外賣員,趕回來送外賣的。
白天,龐雁是位于紅花山附近一幢高檔寫字樓里某文化公司的優(yōu)秀圖書編輯,晚上,確切地說,是五點半至十點半,包括雙休日,就是小會水餃店的外賣送貨員了。小會水餃店就在鳳凰城小區(qū)里,后門是小區(qū)一塊碧綠的草坪,草坪中間的一條小路連接著小區(qū)各條交叉的道路,和各幢建筑連成一個完整的交通網絡。
下午五點三十五分,龐雁準時出現(xiàn)在小會水餃店里,她快速地存好雙肩小包,套上一件小會水餃店的專用紅馬夾,只需朝店長一望。叫王慧的店長就大聲而干脆地說:“北區(qū)十八號樓和十六號樓的,三份,離得近,剛叫,正好,送吧。”
龐雁沒有說話,拎著打包好的三份水餃就往外沖。她知道她的自行車就放在后門草坪一側的大樹下,騎上自行車,不消幾分鐘,就可到達目的地。兩幢樓,三份水餃,算是比較劃算的一趟了,強比三份水餃三幢樓輕松多了,何況兩幢樓相距又那么近呢。送一份水餃能掙四塊錢,三份就是十二塊錢了,開門紅啊。龐雁覺得這是個好兆頭,心里高興,腳步也就輕松而快樂起來,甚至帶著小跑的節(jié)奏了。但是,在出門的一剎那,毫無預兆的,她撞到了一堵墻上,這堵移動的墻來勢兇猛,勢大力沉,一下子把她撞飛起來,她趔趄著想控制住懸浮的雙腳,無奈重大的慣性讓她重重地摔倒在大堂的桌子上,后腦勺磕到了桌角,頓時頭腦就懵了,接著是嗡嗡作響和一陣劇烈的疼痛,疼得她以為馬上就要死了。
龐雁側臥在地上不知道過了多久(其實很短),時間像停止一樣,又像消失一樣,四周的聲音也只剩下她腦子里嗡嗡的回聲了。等到她感覺有人在說話時,才聽王慧大聲地斥責什么。
2
顧大前萬萬沒有想到,吃一份水餃攤上了大禍。平白無故地,把一個女孩撞傷了。他也冤啊,他不過是走路猛了點,那也不是故意的,不過是心里著急——剛接一個大單子,要在地鐵六號線鳳凰城站C 口處接一個客人去惠州市區(qū)。跑滴滴,能接到一個大單子,多不容易啊,多大的運氣啊。看時間,還有幾分鐘,他便想著吃了晚飯正好趕上點兒,又正巧小會水餃店的水餃是他的最愛,便進來準備吃一份。到哪里也要吃飯嘛,何況又是難得的長途,吃水餃正合適——水餃又叫彎彎順,吃了水餃,預示著一切順利。哪知道就禍從天降呢?
這女孩傷勢不輕,還出血了——耳朵后邊,被桌角磕破了一塊皮。那兒皮薄,出了不少血,看起來怪嚇人的。隔著鳳凰城南區(qū)和北區(qū)的步行街上,正好有一家二十四小時藥店,附帶著一個診所,顧大前就趕快帶傷者來包扎了。水餃店店長王慧自然是向著龐雁了,她一邊指責顧大前,一邊安撫龐雁。還不放心,怕顧大前中途跑了,也跟了來。
還是在去診所的路上,龐雁已經很清醒了。除了腦袋有些懵,耳朵后邊火辣辣的疼,別的也沒有什么感覺。躺在地上時,還以為要死了。現(xiàn)在又覺得送外賣的兼職也許不耽誤。她看到撞她的人了(或者她撞的人),不認識,挺高大的,也有點威猛,羅圈腿,相貌不正,像受了擠壓的葫蘆,就是歪瓜裂棗的那種。診所的醫(yī)生查看了她的傷口,也說問題不大。不過為了方便包扎,要把耳朵后的頭發(fā)剪去一縷。剪就剪吧。醫(yī)生給傷口涂了酒精,用紗布簡單包扎一下,告訴她三天不要沾水,好好休息。
“三天,聽沒聽到,損失多大?你要賠償!”王慧是個壯實的女人,微胖,話音里自然帶著威嚴,聽不出是哪里的口音,非常仗義。她看這個叫顧大前的家伙一臉惡相,就雙手叉腰,提了提臀,挺了挺肥碩的腰,試圖在氣勢上壓他一頭,“還顧大前,我看你是顧頭不顧腚,有你那么走路的嗎?瞧把我們小美女撞的,有個三長兩短,你負責得了?來,加個微信,男子漢敢做敢當,別做縮頭烏龜!”
“誰縮頭啦?誰是烏龜?文明講話好不好?”顧大前掃了王慧伸過來的手機,“又不是故意的,多大事啊。”
“有你這態(tài)度就好,轉兩千塊錢給我——姐不是訛你,三天誤工費多少錢,還有這治療費、藥費。三天后咱們結算,多退少補——放心,我有店在這里,不會騙你這點小錢。”王慧真是個麻利的店長,什么事都想到了,“姐店里還有事——正是送餐高峰……對了,店里的損失我就不跟你算了,我的誤工費也免了,三份水餃你得賠吧?”
“三份水餃……誰說不賠啦?”顧大前的手機突然響了。他趕快接通道,“喂……我以為你到了……大約多久到?堵在路上?你不是乘地鐵?公交?你坐公交為什么非要指定在C 口?好吧好吧,這也不怨你……沒什么,我自己的事……你下了公交打我電話,我在六號線鳳凰城站C 口對面的小會水餃店,吃碗水餃就好……好好好,是我態(tài)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那三份水餃都是你的了,等會去吃吧,不會全摔爛的。”王慧的口氣緩和了點,她從他的電話里聽懂了什么,理解了他的冒失。
“兩千轉過去了。”顧大前在手機上擺弄了一會兒,帶有點威脅地說,“我也住鳳凰城,就南區(qū)十五號樓。我跑滴滴。我不怕你——也不過兩千塊錢。”
原來一個小區(qū)的。龐雁想不起來給沒給過他送過餐。應該沒有。
“雁子,不礙事吧?我要回店里了,錢在我這呢,放心。”王慧不等龐雁說話,就旋風一樣離開了。她店里的事確實太多了,接單子,派外賣,收款,還要接待堂食。馬上地鐵口就會涌出一波波人流了,小會水餃店的生意因此一直紅火,她不想錯過這個賺錢的高峰期。
醫(yī)生也包扎好了。治療費也是仁義價,一百,還配了消炎藥。龐雁付了錢,心里七上八下的,她偷偷看看顧大前,有點同情他,這個高大的漢子有點蔫了。從剛才的手機通話中能聽出來,他接了單去惠州的長途,想趁空吃個餃子,沒想到就和她發(fā)生碰撞了。其實吧,她也有責任,甚至責任是一半一半的。現(xiàn)在,在慧姐的處理下,變成他的全責了。跑滴滴也不容易,不是什么好職業(yè),也是靠辛苦和熬時間吃飯。看他這樣子,三十五六歲吧,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時候,家累肯定也不輕。她看他偷偷地嘆了口長氣,臉都灰了,臉上的胡碴青梗梗的,情緒也低落,肯定后悔自己的莽撞了。龐雁趕快看向了別處。都不容易,龐雁想。
“算我倆倒霉。”他丟下這句話,也急急地出門了。
顧大前的背影消失之后,龐雁的眼淚才汪在了眼里——不知道為什么。
“小傷,養(yǎng)兩三天吧,正好明后天雙休日。”醫(yī)生安慰道。
龐雁感謝了醫(yī)生,拿了藥,走出診所,來到小區(qū)的步行街上。說是步行街,實際上是個長條形的廣場,分隔著南區(qū)和北區(qū),中間一段隆起的區(qū)域,每天晚上都會有幾撥跳廣場舞的人。現(xiàn)在還不是跳廣場舞的時段,步行街上的人也多了起來,都是下班的人,他們大都背著雙肩包,手里或提著盒飯,或提著水果,個別人還拿著花,大部分是空著手。龐雁知道,空著手的人,回到家里,簡單洗漱一下,就會點外賣了。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人,會點小會水餃店的水餃。如果不是突然發(fā)生的意外,她第一次送單應該早就完成了,現(xiàn)在有可能在送第二單第三單了。今天是周五,單子應該不會少,因為一開始就有不錯的苗頭。可惜這苗頭剛一萌芽,就被掐斷了。龐雁心里有點焦慮,有點懊惱,雖然對方押了兩千塊錢在慧姐的微信賬戶里,那和她憑本事賺錢畢竟不是一回事啊。
晚霞已經有了晚霞的樣子了,正從西邊高樓的縫隙間照射到步行街上,潔凈的方磚上跳躍著暗紅色的光芒,霞影在匆匆行人的快速走動中,像紫霧一樣縹緲、縈繞,有一種夢幻般的美。龐雁懷疑自己的眼睛摔壞了,怎么會有這么奇妙的景象?她晃晃頭,奇妙的景象依舊。她知道了,那是女孩們裸露的長腿和華麗的衣裙與霞光作用后形成的幻覺。同時,龐雁也感覺到身體并沒有什么不適,耳朵后邊的傷,如果不去想它,似乎也不怎么疼痛。
那為何不去送外賣呢?輕傷不下火線,這可是傳統(tǒng)英雄主義的典范啊。
她不是要做英雄,她確實需要錢。想到了錢,龐雁的腦海里迅速出現(xiàn)了幾百公里外的湖南老家,那個四面被青山環(huán)抱的小鎮(zhèn),便是她從小生活、讀書、成長的地方,那里有她的雙親,有童年、少年美好的記憶。她母親是個輕度智障者,父親更是一個腿有殘疾的瘸子,靠打鐵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所謂打鐵,實際上就是白鐵匠,不用生火,材料是鐵皮,有白鐵皮和灰鐵皮兩種,靠敲敲打打生產日常用品。父親手巧,敲打出來的產品有鐵皮桶、鐵皮大盆、簸箕、舀子、勺子、水漏、三通,還有澆花的噴壺。這些看是日常的商品,早就被花花綠綠的塑料制品取代了。但是也會有一些老派的居民來買,一來是父親的產品確實精美,像藝術品,二來也比塑料制品耐用,價格也不是太貴,關鍵是,輕微損壞或出點小毛病,還免費修理。按理說,父親靠著這間處于街口拐角處的白鐵匠鋪,也能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可是,天有不測風云,在龐雁讀研的第三年,母親查出了病——腸癌。接連三次的大手術和化療,不僅花光了不多的積蓄,還借債十幾萬元。還好,龐雁及時畢業(yè)了,也順利地找到了工作。不但不用花父親的錢,還能有所補貼。本來她可能還有更好的選擇,但為了早點拿工資,她到了這家文化公司,工資雖然不高,卻穩(wěn)定,也是她喜歡的工作。去年疫情期間,她在小會水餃店吃水餃(她經常在小會水餃店吃水餃,一來二去和王慧就熟了),王慧吐槽說連送外賣的人都找不著了,有時候不得不自己送。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龐雁知道小會水餃店的生意大多來自鳳凰城小區(qū),跑起來也不費力,便向王慧說明自己想做兼職外賣的意愿。王慧一聽,好事啊。所以,龐雁就成了小會水餃店的兼職外賣員了。
既然傷勢不重,又恰逢周五,還是好好去送外賣吧,這又不影響顧大前的賠償。
龐雁穿過燈色閃耀的步行街,向小會水餃店方向走去了。
3
龐雁再次來到小會餃子店時,已經有幾個人在吃餃子了,迎面還遇到兩個外賣小哥拿著外賣小跑著出去。這會兒她聰明了,主動閃到了一邊。
“怎么還來?”龐雁剛一出現(xiàn),王慧就驚訝了,“跟你說呀,剛才那個家伙真的來把三份餃子吃了……不不不,吃了兩份半,還剩下幾個,帶走了。他可真能吃啊,我都擔心他能吃傷,我又嚇唬他一頓,被我嚇得一愣一愣。放心吧雁子,這三天的誤工賠償不會饒了他,這個賬,我會算。”
“慧姐,算了吧,他也住在鳳凰城。”
“嗨,你這孩子,讓我直接就變成壞人了。我是在幫你好不好?這個人來過店里吃過餃子,我也面熟,可他哪能跟咱們的關系比啊。放心雁子,這事我來辦,咱這是合理、合法、合情。回去休息吧,那一下摔得可不輕,都要嚇死姐了。”
“慧姐……鳳凰城有外賣要送嗎?”
王慧又驚訝了,瞪大眼睛說:“你是要錢還要命啊?差錢姐我借給你!”
“沒那么嚴重。”龐雁笑笑道,“不就破了點皮嘛,我小時候,前山后山砍柴,碰破皮肉是常有的事,沒那么嬌氣。”
“我不管你呀,你要送就送,你看……”王慧盯著電腦,“真來單了,還真是鳳凰城的。”
龐雁把一份外賣放在車筐里,小心地在便道上騎行著。她可不想再撞誰了,也不想被別人撞了。但便道上的人特別多,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如果是迎面走來的人,她總擔心這個人會撞到她車子上;要是超過前邊的人,她又怕撞在人家的屁股上,這一定是心理作用。既然心情受到了影響,那就步行吧,北區(qū)十號樓也不遠,正欲棄車時,手機響了,一看是父親的來電,趕快接通了。
“爸……有事啊?”自從母親生病以來,她最怕爸爸來電話了。平時都是她打電話回家,問問家里的情況,問問母親的情況,或給父親轉錢。她知道父親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打她電話的。
“沒有事……吃飯啦?”
“吃了。”龐雁撒了個謊,“你也吃飯啦?媽呢?”
“在這兒……也吃了。”
“……是啊,早上住進來的……還是那毛病,明天檢查。”父親的聲音越說越低,仿佛母親是多么不應該患病,他是多么不應該打這個電話似的。
“要我回去嗎?”
“回來干嗎?好好工作……”
龐雁聽到父親的聲音哽住了,心里也便悲傷起來:“爸……還差多少錢?”
“我手里有幾千了,要是能拿……一萬吧。”
“好的爸,我周一發(fā)工資了,到時轉給你。”
龐雁最終沒有和母親通話。她想回家,可她不能回家。回家要花差旅費,公司還要扣工資,影響當月獎金,還有可能影響全年獎金。她現(xiàn)在最需要的就是錢。有錢了,母親就能活下來,至少能多活幾年。她和母親通話也沒有什么話說,每次聽母親說話都會大哭一場。母親只會抱怨,不是抱怨別人,是抱怨自己生病,又害怕自己會死,母親也會毫無理由地責罵父親不管她。父親哪里是不管她啊,她就是發(fā)泄罷了。父親已經夠辛苦了,每天除了照顧母親,還要干活。有一次,父親接了一個大單子,鎮(zhèn)上的學校食堂訂了五個大菜盆,三個湯桶,父親恨不得覺都不睡地趕了出來。高興的父親還專門拍了照片發(fā)給她看。其實,五個大白鐵皮盆加兩個湯桶,最多賺八九十塊錢,還要敲敲打打四五天,沒有她一個晚上送外賣賺得多。所以拿賺錢和其他任何事情相比,錢都最重要。想到這里,耳朵后邊的那點小傷就不算什么了。
因為OA = OB = 1,所以△OAB為等腰三角形.取AB中點M,連結OM,則OM為∠AOB的平分線,因此OM是鏡面的垂線.又OI是水平面的垂線,所以,OI與OM所成的角∠IOM即為鏡面與水平面所成的角.取BH中點N,連結MN,可知∠OMN = ∠IOM.
4
在接下來的雙休日里,外賣生意出奇地好。通常早上十點前沒有生意,可周日這天,還沒到十點就接到單子了。本來龐雁周日這天也不準備早來的,她要痛痛快快睡一覺。因為昨天一天她一直送餐到凌晨一點,居然送了七十多份,是她兼職以來最多的一次,也是她最累的一天。但是,周日一早九點半時,王慧的短信突然吵醒了她,一看,是給她轉錢來了。就是誤傷他的顧大前給的誤工費,正好是兩千塊。龐雁感到納悶,怎么會是整整兩千塊呢?用不了這么多吧?怎么算的?便打電話給王慧,問個究竟。
王慧在電話里說:“有姐在,還能讓你吃虧?我當然讓他兩千塊錢有來無回了——我記得你告訴過我工資是六千五一個月的,刨去雙休八天,一個月按二十二天算,四舍五入,你每天工資三百塊,三天就是九百塊,加上一百塊錢治療費,正好一千。營養(yǎng)費我算你需要十天額外的營養(yǎng),一天一百塊錢不過分吧?十天又正好一千,這不就是兩千啦?哈哈,那小子也太實誠了,居然就同意了。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我能怎么辦?你就笑瞇瞇收下吧——我說了你也別介意,我看出來,你需要錢。”
“謝謝慧姐費心……我,我覺得,應該退一千給他。”
“退什么呀,搶都搶不到手,錢錢錢,命相連……你起來啦?早點到店里唄,今天是周日,生意不會比昨天差的。”
龐雁就這樣來到店里了。臨出門時,還照照鏡子,看看耳朵后邊的傷,已經愈合得很好了。實際上就是磕破了一層皮,損失還不如被剪掉的那縷頭發(fā)讓她心疼。龐雁越發(fā)覺得自己有點敲詐的嫌疑了。這家伙要是報警,會不會把她抓進去?
龐雁一到小會水餃店,王慧就丟下手里的活——她正在和員工們整理剛進來的一箱箱定制的速凍水餃,笑嘻嘻地說:“你來了正好,剛剛接個單子,南區(qū)十五號樓2210,鍋里正煮著呢——本來我想跟你閑聊幾句的,正好就來生意了。”
“慧姐,我是這樣想的,三天誤工補貼,不是有兩天雙休嗎?再說了,這三天我也沒耽誤送餐啊,營養(yǎng)費更是離譜,我怕……”
“打住打住,這事是姐幫你辦的,你怕啥?我都不怕你怕啥?你要是嫌多了,怕錢燒壞了手,退給我!”王慧哈哈道,“放心妹子,顧大前同意了,聊天記錄我保留著呢,一筆一筆清清楚楚算給他看了。他要是不同意,我能敢當家?沒有人訛他,也沒有人脅迫他,這錢你拿得正當。”
龐雁在送餐時,心里還忐忑著,總覺得這兩千塊錢拿得不光彩,雖然她缺錢,但也不能讓自己良心過不去啊。事已至此,找王慧看來是不行了,只好碰機會吧,萬一再能碰上他就把錢還了,他要是不要,那另當別論。
事情真是湊巧,南區(qū)十五號樓的這份餐的主人正是顧大前。顧大前看送餐的是龐雁,倒是沒覺得奇怪,似乎在他的預料之中。龐雁第一反應是,是不是王慧和顧大前合搞的陰謀?世上哪有這么巧的事?龐雁一眼就看出顧大前是一個人單租,單租說明什么?單身一族?一般情況下,深圳的普通打工族,很少單租的,合租非常普遍,除了月薪過萬的真正白領。他一個跑滴滴的,能賺多少錢?房租要去掉四五千(開間),還能剩多少?聯(lián)想到事情的前后經過,還有王慧的過度熱心,覺得這里肯定有貓膩。上上周,王慧不是還問過她有沒有男朋友嗎?又說知道你沒有男朋友,有男朋友還兼職送外賣?不想法談一個?
這樣也好,正好把兩千塊錢退給他,省得以后啰唆。
“這么巧?”龐雁把餐盒放在門里邊的鞋柜上,說,“慧姐跟我說了誤工補貼的事,兩千塊錢也收到了……這錢我不要,我也沒那么嚴重,你看我怎么退給你?”
顧大前的額頭上出了一頭汗,汗珠一顆一顆細密均勻,十分晶亮。聽了龐雁的話,他也吃了一驚,趕忙問:“什么意思?”
“把兩千塊錢退給你。”龐雁冷冷地說。
“退給我,什么意思?”顧大前的一只手卡在胃部,眉頭緊皺著,一臉痛苦狀地看著龐雁,像是要看透她話里的陰謀。
“就是……兩千塊錢我不要了。加個微信……要不我退給慧姐,由慧姐轉給你。”
龐雁話沒有說完,顧大前的手機就伸過來了,像是無奈地說:“隨你們……”
龐雁掃了二維碼,添加了好友后,把兩千塊錢轉給了他。龐雁把手機舉一下,說:“轉了,你收下。”
顧大前點點頭,跟龐雁也舉一下手。那是再見的意思,抑或是謝謝,但臉部表情更加痛苦了,像是在強忍著什么。他在側身拿水餃時,腿一軟,趕緊雙手扶住了墻,又轉頭,對龐雁說:“不好意思,前天去惠州……回來時出了點小事故……車子在修……本想在家好好歇歇,沒想到……”
龐雁看到,裝水餃的塑料袋子大幅度地搖晃著,搖搖欲墜,隨時要掉下來的樣子。龐雁聽明白了他的話,不知道他這是玩的哪一招,就是碰瓷也有可能。正欲離開時,聽到顧大前哎呀一聲,手中的快餐袋子掉落到了地上,整個人不是扶著墻,而是趴在墻上了。龐雁這才覺得不對勁,顧大前的痛苦不像是裝出來的,就算是演戲,也沒必要這樣演,不就是兩千塊錢嘛。但她依然沒敢上前。上前一步,就是他家了。少這一步,就是在走廊里。龐雁緊張地問:“怎么啦?”
“肚子疼……胃疼……不知道哪里疼……疼死了……都是那天餃子吃撐了……”顧大前跟他擺擺手,好像在說,與你無關,但他還是對龐雁說:“幫我要個滴滴……去醫(yī)院……你是好人、大救星……”
龐雁看他像個軟體動物,不,干脆就是一堆液體,順著墻壁癱到了地上。龐雁怕他真的成為液體,恐怖而慌張中,要了一輛滴滴快車。
5
本來龐雁可以離開的,覺得錢也退了,還幫了他的忙,算是做到仁至義盡了。可滴滴是她要的,她怕顧大前撐不到小區(qū)的西門口,或者和滴滴司機走岔了,再發(fā)生什么意外,惹她一身麻煩就犯不著了,于是她就跟著顧大前,顧大前扶著墻,忍著劇痛,一邊走還一邊向龐雁解釋:“覺得胃里不舒服,以為是餓了,要份水餃吃……沒想到突然就疼死我了。”
從步行街往南門口走時,沒有讓顧大前可扶的物體了,龐雁就主動把肩膀借給他。龐雁雖然一千個不愿意一萬個不愿意,但看他那寸步難行的樣子,也不佝僂著腰,怪異著向南門口急行。還好,滴滴快車也及時到了。龐雁拉開車門,把他塞了進去。奇怪的是,滴滴司機卻不走。龐雁已經大聲告訴司機了,去光明醫(yī)院,可滴滴司機還是傻傻地望著他。滴滴司機是個女的,她一定是看到他一路痛苦的樣子了,便大聲說:“你不去?車是你叫的吧?他這樣子……家屬不去我不帶啊。”
龐雁只好上車,坐到前排,充當家屬了。一路上,龐雁還在想,顧大前的病會不會和她有關?上周五那天,他一口氣把三份水餃吃得只剩幾個了,是在氣急、上火、心疼錢的情況下吃的,回程時又……是出了車禍嗎?如果真要是因為這個而導致他出車禍,再導致他生病,陪他去趟醫(yī)院,也算是求得心理上的安慰了。
光明醫(yī)院的急診科很及時地診斷出了顧大前的病,急性胰腺炎,需要立即住院治療。可醫(yī)院沒有病床了,只好臨時躺在急診室的病床上掛水。待空余出病房,再辦住院手續(xù)。從入院,到取藥、交錢,各種排隊,各種手續(xù)都是龐雁跑的。期間,王慧打三次電話來,問她在哪里,有餐要送。龐雁都說有事在忙,一會兒再過去。看著顧大前的吊水掛上了,還有幾瓶在排隊,病情也穩(wěn)定了,大約疼痛感也減弱了,才說:“我要回去送餐了,你可以吧?”
“可以可以,謝謝啦……花多少錢我轉你啊。”
“不急,你先治病。走啦。”
“哎……”顧大前又叫住了她。
“啥事?”
顧大前欲言又止地對她揮揮手。
龐雁回到鳳凰城,回到小會水餃店,正是午間最忙的時候。王慧假裝氣急地說:“送個餐怎么磨嘰到現(xiàn)在?遇到帥哥啦?被人家留下來一起吃啦?還是做了人家一個小時的新娘子?臉紅什么?哈哈,開個玩笑的。雁子,從沒看過你臉紅……雁子臉紅時怪好看的,平時看不出來啊,也是個小美人。快,這是四份水餃,分布在不同的四幢樓,你跑吧,算是對你磨嘰的懲罰。”
王慧的話讓龐雁心里一愣一愣的。但是,王慧貌似夸她的話,她聽了不舒服,什么叫“也是個小美人”?還“平時看不出來”。這話傷害不大,侮辱不小,至少在王慧的眼里,在今天之前,在她沒紅臉之前,她根本就不是個小美人。龐雁知道自己,雖然不算漂亮,也不至于像王慧說的那么不堪吧?
龐雁本想把顧大前的事告訴王慧的,隨即就上手的送餐,讓她無暇顧及了,拿了餐袋就出了門。在送餐過程中,龐雁不斷收到顧大前的微信,先是問花了多少錢。又說他找院方查到了,把錢轉給了龐雁。最后一條短信是拒收龐雁轉給他的兩千塊錢,顧大前說:“一碼歸一碼,兩千塊錢是賠償你的,不能收。而你幫我墊付的醫(yī)藥費,是一定要付你的。”
到了這時候,龐雁覺得,這個叫顧大前的人還是有其可愛的一面的,雖然樣子蠢了點,但是正直率真,沒有歪心眼兒。龐雁收了她在醫(yī)院花的錢。她轉給顧大前的兩千塊錢還掛著,沒有點收。龐雁心想,兩千塊錢也不少了,我是誠心要還你的,要是不點收,就是你的事了,退回來我不會再發(fā)的——母親又住院了,正好要用錢呢。龐雁想到這里,覺得自己并不高尚,甚至還有點小小的貪心。龐雁第一次小瞧了自己。
6
周一上班時,龐雁第一次遲到了。常在河邊走,沒有不濕腳的。她無數次挑戰(zhàn)極限,極限還是找到了她。可她只遲到了一分半鐘。一分半鐘也是遲到,這是規(guī)矩,遲到十分鐘以內要扣一百塊錢。龐雁心疼這一百塊錢啊。龐雁在心里梳理一路上的行程,和往常一樣,她正點出門,從鳳凰城站B 口上車也是掐準了時間。可能是在紅花山出站時,因為樓梯上過于擁擠,阻擋了她小跑的路線,耽誤了十幾秒吧。還有寫字樓的電梯,排隊的人好像比往日多了不少,從電梯廳一直排到大門外,等了三撥才上來(平時只等一撥)。這兩個關鍵節(jié)點,就是她遲到的原因了,一百塊錢就不在她的錢包里了。
龐雁掃一眼辦公室的同事們,他們都安坐在自己的隔斷里,已經進入工作狀態(tài)了。沒有人關心她遲到,也可能所有人都注意到她遲到了,因為電腦上有現(xiàn)成的時間,瞥一眼就心中有數。龐雁也打開電腦,她想盡快進入工作的狀態(tài)。只有進入工作狀態(tài)了,才能忘記遲到的煩惱。可是,遲到還像影子一樣,一直跟隨著她,遲遲退隱不了。這一百塊錢有那么重要嗎?她隨即就算出來了,要送二十五次外賣才能掙到這么多啊。一般情況下,一個晚上也就掙這么多,如果不景氣,還達不到這個數額。
財務室有人叫她過去——今天發(fā)工資。以往發(fā)工資,一般都是上午到賬,沒必要把員工喊過去。莫非因為今天遲到?莫非有人要提醒她?財務室也負責考勤的。
原來不是因為遲到。遲到的事,釘釘上自動生成,到時統(tǒng)計就行了——是因為上個月她工作中的差錯,被連罰帶扣了三千元。因為不是小錢,財務人員跟她細細地復述了一遍。
龐雁一邊聽,一邊難過,遲到扣一百塊錢已經讓她無法承受了,這三千塊對她來說可是巨資啊,簡直就是核打擊。她努力讓自己平靜。可她還是無法平靜,她感覺到心在顫抖,感覺到手在戰(zhàn)栗。為了掩飾自己,她把雙手疊放在兩腿中間,可她又感到雙腿也跟著戰(zhàn)栗起來。上個月的那個差錯她知道的,以為不過是丟了幾個字,算一處普通的差錯,也就是扣十塊錢而已,怎么就上升到重大錯誤了呢。重大差錯的最高處罰就是三千塊。龐雁迅速回憶著那次差錯,是把一本書的序言的署名丟了。不,不是丟了,是她主動刪了的。說起來真是詭異,那本書是一本散文集,作者不太知名。可能正是因為不知名吧,他請了一個著名評論家寫了篇評論作為代序。原來這本稿子的前期工作做得很好,在CIP數據下來之后,付印之前,龐雁最后一次核查藍紙時,發(fā)現(xiàn)序言末尾的署名和封面署名不一致,想當然地就以為應該統(tǒng)一,把序言的末尾名字改了。一想,還不對,既然是自序,就不用署名了,大筆一揮,劃掉了。樣書到了作者手里,作者自然不買賬了。好在作者是公司的老作者,和老板也是朋友,好說話,沒有繼續(xù)追究,這個事就算過去了。龐雁也就一直沒有在意,沒想到公司還是啟動了處罰機制。龐雁想想,這事也不怨,算作重大差錯也沒錯。但是,畢竟是三千塊錢啊,血淋淋地直接割肉啊。龐雁忍著心里的悲傷,忍著即將涌出的淚水,回到了辦公桌前,但終究還是沒忍住,耳邊仿佛又響起父親謹小慎微的聲音,淚水便奪眶而出了。她拿出紙巾,悄悄擦拭著,沒想到這淚也越擦越多,越擦越委屈,她干脆躲進了洗手間。
龐雁很快就想明白了,傷心有什么用?還得好好工作,吃一塹長一智,以后更加細心就是了。
說好要給父親轉一萬塊錢的。能不能湊夠呢?龐雁心里粗略地一算,夠了。處罰后,到賬三千五,加上卡里的余額,還有原來轉給顧大前的兩千塊被退了回來,綽綽有余。龐雁知道家里急需用錢,她給父親多轉了兩千。一共轉了一萬兩千元。現(xiàn)在,她余額只有幾十塊錢的零錢了。好在王慧那兒也快要結賬了,總之能夠續(xù)到下個月了。
下午一下班,她在趕往地鐵的途中,給父親打了電話:“爸,錢收到了吧?”
“收到了,剛交一萬給醫(yī)院。”
“好好照顧媽……我也回不去……買點好吃的……你也要好好吃飯。”龐雁似乎有一萬句話要跟父親說,可每次也只是這么干巴巴的幾句。父親也說多匯那兩千,正好還了一筆急需要還的賬。這同時又讓龐雁悲從中來,連帶著,也想到了顧大前,不是顧大前拒收,她還真湊不齊一萬兩千塊了。湊不齊這一萬兩千塊,父親那邊又會更艱難了。
7
龐雁是在夜里十點鐘時,來到光明醫(yī)院的。她還帶來一份水餃。雖然上周五她和顧大前的相撞,導致了顧大前吃水餃吃傷了胃,又導致后邊的一系列事件,可她實在不知道還有什么比水餃更好吃的。帶來一份水餃,也算是她對他的一點感謝吧,畢竟人家拒收了兩千塊錢。而他也不像是富有的人。好在把他送進了醫(yī)院,也算是還了他一個人情。但,和兩千塊錢相比,似乎還遠遠不夠,似乎再來看他一次,才會了卻心里的不安。
光明醫(yī)院離鳳凰城不遠,她騎自行車很快就到了醫(yī)院門口,給他發(fā)了微信,問他住在幾層哪間病房。顧大前的微信很快就回復了:“還在急診室。沒有病房。他們勸我轉院。我轉哪?我哪也不轉。我就住急診室。”
“這樣也行?”
“有什么不行?反正他們不能趕我走。”
“我在醫(yī)院門口……去看看你。”她本想說順道去看看的,臨時把“順道”刪除了。
龐雁停好車,拎了水餃,來到急診室。夜晚的急診室,不太忙,只有一個年輕的媽媽抱著孩子在聽醫(yī)生說著什么。整個急診室讓人感覺很空曠,只有兩個角落里,分別放著兩張病床,一張是空的,另一張,就是顧大前的了。顧大前還在掛水。顧大前也看到龐雁了,臉上露出憨憨的微笑。龐雁也微笑一下,走到他病床前。龐雁到處找凳子,她看到一只小圓凳,正要去拿過來,一個穿白大褂的年輕男醫(yī)生就急走過來,說:“你是他什么人?”
龐雁一時語塞。
“是這樣的”,年輕醫(yī)生說,“這是急診室,不能長住。醫(yī)院目前沒有病房,他的病也控制住了,我們建議他到別處治療。你是家屬,協(xié)助一下。”
“轉到哪里?我們不轉。”由于已經知道顧大前的態(tài)度,龐雁說話也很直接,“我看這兒挺好,就住這兒。該花錢花錢。”
年輕醫(yī)生無奈地走開了。
龐雁朝顧大前狡黠地一笑,意思是,這樣說行吧?龐雁拖過那張小圓凳,把水餃放到了凳子上,說:“你早上沒吃的餃子,我給你帶過來了。”
顧大前夸張地嘆息一聲,說:“我也饞啊,也餓啊,要是能吃就好了——醫(yī)生說了,五天不能吃東西,任何東西都不能吃,活命只靠打營養(yǎng)液。”
“怎么會這樣?”
“胰腺發(fā)炎,堵了,為了疏通它,必須讓它先休息,不讓它工作,待它痊愈后,再少量吃點流食,慢慢調理。嘿,我也不懂,醫(yī)生這樣說的。”顧大前看著那份水餃,咽了口唾液,“你吃吧。”
龐雁還真沒吃飯。不過因為下班途中吃了兩個蔬菜包子,打了底,到現(xiàn)在也沒覺得餓。叫顧大前一說,這才感覺饑腸轆轆的了。那也不能在急診病房吃啊,再說了,當著顧大前的面吃美食,不是故意饞他嘛,那也太不人道了。就在她準備打聲招呼離開的時候,看到顧大前扭過頭去抹眼淚。龐雁心里也停頓一下,莫名地傷感起來,感覺他也沒有人陪的。明天還要上班,她也不能久留,決定等他消停一下再離開。就在這時候,她看到顧大前摳摳索索地從牛仔褲的口袋里掏出幾張紙。那是餐巾紙,不同顏色不同規(guī)格的餐巾紙,已經皺皺巴巴不成樣子了,大約來自五六家飯館。其中那個疊成手帕形,帶一碗水餃壓紋圖案的,正是小會水餃店免費供應的餐巾紙;那張淺褐色的,是紅花山包子鋪的;那張疊成三角形的,如果沒有猜錯的話,是米特快餐店的專用餐巾紙。他從中選了一張,把其他幾張又塞回了口袋。顧大前看龐雁正在看他,一笑道:“上火了……我是火眼……真就奇怪了,你怎么會送快餐?”
龐雁知道他理解錯了。她的吃驚,是吃驚他使用的不同餐館的餐巾紙,這要多能節(jié)省的人才能從每家餐館順幾張微不足道的餐巾紙啊。當然,他的悄悄流淚,她雖然不能完全地理解,也能體味那么一點點。
“你說我還能干什么?”龐雁還是接上了他的話。她真不想陪他聊天,但如果聊幾句,他也許會好受點,“我有工作的……送快餐是兼職。”
“有工作還兼……賺不到錢嗎?看你像個大學生,做啥工作?”
“文化公司編輯。”龐雁看他不太懂,“就是……你愛看書嗎?看樣子你不愛看書。你要是愛看書就知道了——我是做圖書出版的,公司在紅花山那邊。”
“賣書的呀?賣書能掙個鬼錢!一本書全是利,才幾十塊錢,真不如送快餐了。”
龐雁雖然知道文化公司經營很困難,知道圖書不賺錢,微利,夕陽產業(yè),但也聽不得別人用鄙視的口氣說她的職業(yè)。正好這時候急診室送來了一個醉酒女人,緊接著又送來一個車禍受傷者。急診室一下子亂糟糟起來。便對顧大前說:“等你出院的,有空你到紅花山通廣大廈,我送你幾本書看看。”
“出院才看啊?正好這幾天無聊,早點拿來嘛。”
龐雁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就說:“明天吧。”
走出醫(yī)院大門,才想起來那份水餃忘了拿出來。但她也不準備回去拿了。看到街邊有一個小賣部,就走過去,買了一盒抽紙,還有一條毛巾、一套牙具,交了錢,請店主送給急診室正在掛水的那位顧先生。
8
過了一周,又過了一周,轉眼,一個月過去了,對于龐雁來說,生活依然忙碌而平淡,依然波瀾不驚,深圳的天氣也越來越熱了,陽光有了灼人的感覺。好消息是,龐雁的父親有幾天沒打電話了,因為母親住院檢查的各項指標都在正常范圍內。而她新發(fā)了工資后,又給家里打了八千元錢,債務壓力得到了短暫的緩解。龐雁的心情難得地平靜了幾天。這天一早,她和往日一樣,踩著上班的點走進了辦公室。照例,她還是最后一個到的。這一次,辦公室的氣氛和往日略有不同,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朝她看,臉上都有一種似是而非的、模棱兩可的笑。她先是沒注意,一想,不對呀,這都什么眼神?是她衣服穿得不對?臉上化妝不勻?眉毛一粗一細?她壓根兒就沒有化妝啊。再一看,看到那束鮮花了。那是一把大紅色的玫瑰花,包扎很考究,正放在那張閑置的桌子上。
“看到了吧?是不是你的?”一個平時愛說笑的女同事提醒龐雁了。
“誰送我花啊?不可能吧?”龐雁聽同事的話里隱藏著非同尋常的意味,確定不是她的花之后,便走過去看了看。花上沒有卡片,也沒有祝福語,是一束來路不明的花,便說,“誰的呀?這么漂亮。”
“不是你的嗎?數一數,十一朵紅玫瑰,一心一意哦。”那個女同事把這句話說給了幾個人了,她不過是像復讀機一樣又重復了一遍。辦公室里立即響起一陣善意的笑聲。
龐雁知道了,這是一束不但來路不明、還無人接受的花,便說:“誰的花誰心里有數吧。”說罷,看一眼辦公室里的其他人,十來個女生,三四個男生,大家都露出一樣快樂的、狐疑的笑。龐雁便也不再多說,投入到正常的工作中去了。
龐雁猛然想起一個人來,這個人在一個多月前,和他有過一段交集,姓什么叫什么來著?龐雁一時記憶全無。他住院了,住在急診室里。自從龐雁那晚去看他以后,他給龐雁發(fā)過四條微信,龐雁都沒有回。第一條是感謝龐雁給他送去了抽紙和毛巾、牙具。第二條是他轉了一個紅包給龐雁,紅包留言是“抽紙毛巾牙具款”。第三條是,感謝她托小賣店的老板帶了兩本書給他,他一定好好讀讀。第四條是在一周后,告訴龐雁,他出院了。四條微信,龐雁都覺得沒有回的必要,轉的紅包她也沒收。此后,他也就沒有再發(fā)來微信。這一個多月下來,緊張的工作讓龐雁忘記了很多的人和事,包括和她相撞的這個人。他還會這一手?匿名送花?如果不說是送給誰的,至少應該說是誰送的吧。這樣光禿禿的一束花,實在是匪夷所思,也有點像他的性格。因為工作和兼職以及家里的各種煩心事,龐雁一直封閉自己的個人情感,不愿打開一點點縫隙。如果真是那個人的花……龐雁的心有些凌亂了,她一再地提醒自己,注意力集中,好好干活,別出錯了。龐雁發(fā)現(xiàn),不僅僅是她,許多人都不淡定了,泡茶的、沖咖啡的、洗杯子的、整理桌面的、去洗手間的,辦公室里比往日多了些不易察覺的騷亂。
中午吃飯時,大家還是圍繞著誰的花而議論紛紛。那個多話的女生吃著自帶的豆粒燒雞塊,帶著一股醋味地說:“出來招了吧你們。”
“誰那么倒霉!”有人接話道。
“誰倒霉誰心里有數。”
有人懟道:“就你倒霉!”
大家立即哄笑起來。她在大家笑聲中,撇清道:“你才倒霉了!”
龐雁沒有笑。龐雁在翻手機。
下午下班,大家還在對那束花評論不休時,龐雁已經走出了辦公室。不消說,半個小時后,準確的時間是三十五分鐘之后,她來到小會水餃店。王慧還像往常一樣,甫一照面就告訴她單號,口氣還是和以前一樣,帶著興奮和激動:“趕巧了,南區(qū)15 號樓2210,一份水餃——點名要你送呢。”
龐雁一聽,心里突然狂跳起來,南區(qū)十五號樓2210 室,正是那個家伙的家啊。可她為什么緊張呢?要不要謝謝他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