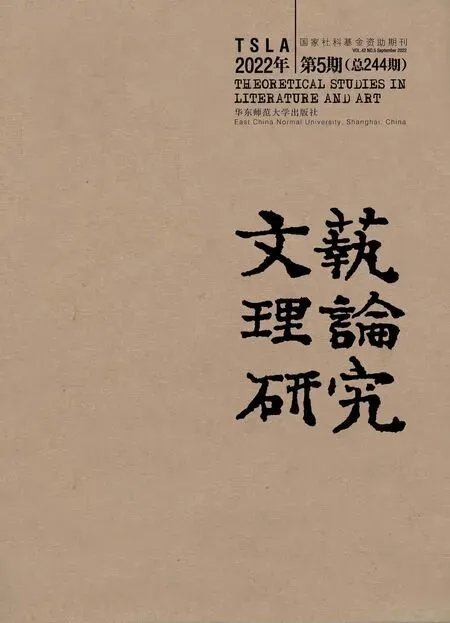“民國曲”與民族新詩之構建
——以盧前散曲為考察中心
康石佳
20世紀40年代前后“關于詩歌的民族形式”問題之討論,是抗戰期間“民族形式”文藝論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翼文學“大眾化”意識和毛澤東結合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毛澤東 37)思想的深刻影響。只不過在這場聲勢浩大又充滿豐富政治內涵的文藝論戰中,“詩歌民族形式”論爭更像是一場相對單純的文學形式的討論。之所以討論詩歌的民族形式,是出于時人對詩壇“矯揉造作、結構潦草”的新體白話詩的不滿,也認為在攸關民族存亡的戰爭年代,一味模擬西洋之“新詩”無法承擔起鼓舞民心、激發民眾抗戰熱情的時代重任。其中,擁有新、舊體文學創作經驗的學者盧前,則通過散曲研究與創作實踐得出結論,推崇并提倡以本為“詩歌之曲”的散曲作為中華民族的有聲“新詩”,進而發起“散曲運動”,呼吁眾多學人一同進行“民國曲”書寫,以具有民族形式的“新詩”來記錄社會生活,反映時代精神,鼓舞國人斗志,為中華民族的偉大抗爭鼓吹吶喊、貢獻力量。
一、 詩歌“民族形式”的探討和選擇
自清末至20世紀30年代,有關詩體寫作技巧、內容及觀念的革新,已歷經了“以新名詞入詩”“以白話入詩”“以西洋詩體為詩”三個階段,并由此形成了給舊有韻文體注入新生命、建立新“歌謠體”韻文、徹底改變詩歌語言與形式等探索路徑。其中尤以五四以來使用“白話”,又移植各類西方詩體所寫成的新體白話詩,給后世文壇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但到了30年代末,新體白話詩的創作基本歸于沉寂,對這類“新詩”的反思也成為學界關注的主要話題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新文化運動所催生的各種洋化詩歌,不僅缺乏“樂曲的基礎”(朱自清 264),更無法“吻合時代的節拍”(趙笑天 7),雖在語體變革中“白話戰勝文言”已成不可動搖的趨勢,可是新詩體“從古詩的各種形式和體裁‘解放’”出來之后,尚未嘗試出或確定下任何一種適應時代社會要求、貼近文學發展實際、切合國人審美需求的詩歌文體,反倒像“中了‘洋八股’的毒,寫出來的東西不合中國人的口味,不受一般讀者的歡迎”(蕭三 47),“新詩”創作之路越走越窄。特別是隨著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這個社會正迫切需要“民族化”的文藝來喚醒大眾、振奮精神、爭取生存和民族解放。“詩歌的民族形式”之討論便在此背景下展開,成為“目前詩壇上一個重要的問題”(“詩底民族形式集體論”版頭 第7版)。
不過,無論是蕭三、楊鐵夫、林秀燊、雷濺波、胡明樹、嬰子、謝獄、歐陽天嵐、王亞平、涂世恩等人的專文,還是“中國詩壇”第二次座談會的討論,仍將“詩歌的民族形式”的敘述重點放在了宣傳、教化層面,反復強調我們要創造“詩歌的民族形式”之重要意義,既未關注與闡說“新”“舊”文體形式的利用問題,也沒能提出如何創作“民族形式”詩歌的建言。他們主要提出的觀點是,新體白話詩缺乏讓中國老百姓聽得懂、聽得悅耳的音節韻律,“詩歌的效用便完全收不到”(蕭三 48),且內容“首首不離‘愛’,句句不離‘情’”(楊鐵夫 67),無法適應民族社會的發展、反映民族現實生活、抒發真實而強烈的民族情感。因此,當前創造的中國之“新詩”應正視歐美文藝所帶來的各種影響,在借鑒民族遺產和流行民歌的基礎上,使用跟“西洋風味”有別的、能被大眾接受的富有“中國作風”之民族形式。“民族形式是寄托于民族內容,也可以說是通過民族內容而表達出來的”,這種“為了適應抗戰的需要所創造出來的民族形式的國際意義,也就跟抗戰本身的國際意義一樣重大。”(林秀燊 7)
至于詩歌的“民族形式”到底該為何種樣式、應有怎樣具體的表現方法,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蕭三在《論詩歌的民族形式》中說,“我們今天的文化文藝應該是‘抗日的內容,民族的形式’”,要通過“古代和民間的形式”,用“新的內容,新的語言,新的意識,思想,新的社會,新的人,新的活動”來“創造新的形式”(48—49)。楊鐵夫《談談詩歌的民族形式》認為,“大眾所明白,上口和記得住”、能感動人和“喚起讀者或聽者的共鳴,成為中國民族中大多數的民眾所愛好的藝術”,即為具有民族形式的“我們底詩歌”(67—68)。1940年“中國詩壇”第二次座談會會議大綱提出:“我們要絕對地把握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徹底的采用大眾的語言,同時并消化我們的民族遺產,接受外國詩歌的影響,去創造我們詩歌的民族形式。”(林秀燊 7)雷濺波《詩歌的民族形式,口語化,形象化》強調民族形式“必須是通過民族現實生活內容的新創造”(9)。胡明樹《關于詩的“民族形式”》則主張我們所需要的最新的詩的民族形式,在于“現代的思想語言,在于我們的口頭,或在于由口頭唱出的民歌”(胡明樹 第7版)。嬰子《中國作風》推崇的“民族形式,其實就是‘中國化,通俗化,大眾化’”以及民族性的表現(嬰子 第7版)。謝獄《題材與形式》認為詩歌的民族形式要“跟著民族本身的成長”,“受著天才的民眾的修改”(謝獄 第7版)。歐陽天嵐《詩的民族形式我見》提出民族形式的詩要“樹立獨特的作風”,“還必須不息地吸養其他民族的優越點”(歐陽天嵐 第7版)。王亞平《創造詩歌的民族形式:新詩辨草之十七》談到“所謂詩歌的民族形式,是根據‘民主的內容,民族的形式’這一號召而產生的”,“詩歌的民族形式就是通過富有中國特色的詩的語言,恰當地表現了主題的素材,而被中國大眾聽得懂,愛讀而又樂于接受的一種形式”(105)。涂世恩《建立民族精神詩歌芻議》要求具有民族形式的新詩,應具有“發揚民族主義”“培養國家正氣”“統一青年思想”“鼓勵御侮精神”的社會作用及“平衡寫作技巧”之類藝術方面的要求(25—28),等等。
此時,作為新生代學人、舊體文學研究者和新詩寫作嘗試者的盧前,也參與了這場“民族詩歌形式”的討論。盧前十四歲時曾創作過新體白話詩,后來則轉向詩、詞、曲等舊體文學的寫作。他在研究過民初以來選體詩派、新學詩派、同光體、南社詩派、學衡派、新體白話詩等詩歌創作實踐后,認同使用現代白話、方言口語等通俗文字作詩,反對保守派迷戀過去,只知模仿古人、古意的寫作方式;也不贊同改進派一味崇拜西洋詩體,只會拿電報、火車、照相等新生事物堆砌詩料或直接模仿外國詩句的結構形式。盧前提出,中國的新詩在內容上必須具備時代精神和民族意識,因而不能不深入民間,與人民大眾發生關系,也不能不對社會政治與生活有所反映和影響,否則“只見新的爛調套語,鋪滿紙上”,“較舊體更為貧弱”(盧前,《廿七年來我中華民族詩歌——民國廿七年十月十日及十九日廿一日在中央廣播電臺講》 9)。我國詩歌在表現形式上,基于傳統樂府的“樂本位”來源,存在始終無法分割的音樂屬性。盧前認為,五四時期“一面采用現代的口語,一面吸收外來的形式”創作的新體白話詩,不過改換了作詩的語言工具——即把文言變成白話,而適應時代需要的新詩體“決不是中國字寫的外國詩”(《近代中國文學講話》 42),屬于民族的新詩形式也不應僅擁有中國特色的“獨立語”文字,更需要“文字本身含有音樂的因素”(《抗戰以來之中國詩歌》 61)。當時的學人既不能確立民族詩歌應有的文體形式,又看不上生硬創造出的白話詩“新體”,更囿于“新舊”文體二元對立的時代觀念的束縛而完全忽視了古典韻文中“樂府”的存在。盧前明確提出:“新的文體產出,不是我們隨時所可強辯的[……]一種新文體產生,舊的文體并不必消滅[……]現在文人意欲以一種文體統一其他文體,我以為不大合式的。”(《我對于文學的信念》 6)
盧前還從音樂現狀出發,指出:“目前的音樂有三個缺點:(一)究研西洋音樂的,完全不顧中國舊有的;(二)采擇民間歌曲的,但求娛人耳目,不論歌曲本身是如何的淫濫;(三)可歌的詩體,沒有人去注意,因此中國的音樂才衰弱到這步田地。”(盧前,《樂理講座:民族音樂(七月三十一日在本臺播講)》 13)可是實際上,“曲的音樂到現在還沒有喪失,可以說唯一可以用中國歌唱方法唱的詩”(《抗戰以來之中國詩歌》 65)。所以,要想傳承與發展我國音樂,就需要“發揚散曲——使我們中國音樂文學史上多留一點痕跡”,要在“整理歌謠”、繼承與弘揚傳統的同時,學習與借鑒外國音樂以彌補、完善我國音樂的不足,但不能因此“完全以他人的代替我們自家的”,而是要在創作上做到“根據我們的樂教,在發揚我們民族精神的條件之下,創造‘新聲’”。不過,“新聲的產生,是要經過相當時間的醞釀,不能強求”,保存民族音樂亦須“精于技巧的樂師,和深明樂律的音樂家,要互相協助,向前推進,不要忘記我們本是‘有音樂的民族’,也不要忘記我們所最迫切需要的是‘我們民族的音樂’”(《樂理講座:民族音樂(七月三十一日在本臺播講)》 14)。
由此可知,盧前立足于順應時代浪潮又尊重古典傳統,主張既要學習借鑒西方音樂與文學的長處,又要警惕這些舶來品對舊有韻文學的文體形式上的沖擊,還要防止民間小曲小調等俚歌俗曲對古典“樂府”的侵襲而導致傳統高雅趣味的低俗化。盧前曾對理想中的“民國詩”作過如此的描述:
以活潑、生動之形式與格調,揚示我民族特有的雍容博大之精神,為民主政治時代之產物,發四萬萬五千萬民眾之呼聲。縱從歷史觀,上不同漢魏唐宋明清之詩;橫從地域觀,并亦異諸英、法、德、印度、波斯之詩。于是,而有不蹈襲古人、不規撫域外,堂堂正正卓異獨立之“民國詩”。(《民族詩歌論集》 295)
盧前在散曲研究與創作過程中發現,“民國詩”的文體特質在最晚出的樂府體“散曲”中體現得最為充分與完備,“‘散曲’雖然是一種舊體,但不像詩與詞那樣被前人寫盡了,各方面都達到頂點”,“要寫我們這時代的事物,在舊體中只有‘散曲’相宜”(盧前,《散曲作法(上)》 9—10)。更難能可貴的是,散曲適用白話寫作,便于廣大民眾的閱讀與理解,也適宜將“個人”的詩推展成“大眾”的詩:
一,曲所用的詞語與現代語接近。二,曲能自由表現我們現代生活。三,曲的歌法未失傳寫成了還可唱。四,曲的性德宜于今日,一種開明的,活潑的新鮮的氣息適宜于民主的前進的今日。無論形式,方法和內容,還值得保留。而且古近體詩與詞的途徑被前人開辟無余,曲還是我們未盡其利的園地,正好犁植耕種并藉以為建立新詩體的基礎。(《論北曲中的豪語(下)》 第8版)
盧前認為散曲最接近于“新詩的形式”,也有充分的學理依據。他在高度肯定詩、詞、曲于音樂、歷史和紀實方面具有同樣的價值和意義的同時,進一步證明了散曲與詩歌在體裁上同源而異制,確立“散曲承詩詞而后,為韻文之正宗”(《散曲史》 3)的觀念。在梳理、分析前人“曲觀”后,盧前評價說:“曲體產生在元代,是‘詞’以后的一種‘新詩體’”(《抗戰以來之中國詩歌》 65),又因“小令乃街坊小調,成文章者,乃指定曲而言。由此可知,樂府與葉兒雅俗剛剛相反”,故“樂府與俚歌是相對待的,散曲的成功,是完全由俚歌進步到樂府的事實”;“原來曲有詩歌之曲和戲曲之曲兩種,散曲就是拿做詩填詞的方法去作曲的。換言之,以作詩填詞的法則施之于曲,只有散曲可以做到”(《曲海浮生》 112—113)。總而言之,“有詩歌之曲焉,有戲劇之曲焉。散曲者上承詩詞,為樂府之宗傳,元人之新詩體也,與戲曲迥異”(《盧前文史論稿》 99)。盧前按照古典“樂府”觀念,將散曲定義為“詩歌之曲”,以區別于俚歌和戲曲;又用“詩”之標準來要求散曲創作,無疑是頗具識見的價值判斷。在詩、詞、曲的文體嬗變與演進過程中,由散曲來承繼詩歌也顯得更為理所當然:“以我國可以入樂之韻語,惟散曲。而啟辟之境未窮,包羅廣闊者,莫散曲若”(《民族詩歌論集》 317),“曲體是適宜于寫爽快的、奔放的感情和情緒。曲所用的文字是最接近口語的,不像古體詩近體詩或詞那種選擇雅馴的文字”(《抗戰以來之中國詩歌》 65),“在中國文學中,這是全民族的文學,這里面有充分的新血液”(《論北曲中的豪語(下)》 第8版)。
綜上所言,盧前認為民族詩歌應有的體裁和形式大致有以下特征:如已普遍流傳的“散曲”一樣,具有相對固定的格律體制、語言規則和風格追求,其文本結構、敘述方式及所蘊含的意識形態、審美趣味等更為通俗化、大眾化,具備因應時代發展變化而靈活多變的文體活力,彰顯出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之間內在的精神聯系。他進而呼吁學人積極從事“散曲運動”,寫作這種合乎時代需要、表現社會意識、歌詠民族精神、保存百姓真實生存狀況的“我們中華民族的歌詩”(《廿七年來我中華民族詩歌——民國廿七年十月十日及十九日廿一日在中央廣播電臺講》 10)。
二、 “民國曲”之創構與影響
不難看出,盧前對于民族詩歌的構建不僅是出自理論層面上的探討,更多則源自其具體的散曲創作實踐。他一直努力突破傳統散曲模式化后某種程度的僵化、固化束縛,同時又不斷提醒國人對西方詩歌文化不必盲目崇拜、刻意效仿,并對民國散曲加以順應歷史潮流的“聲腔”(音樂性)和“文字”(文學性)改革。需特別注意的一點是,盧前并非“進化說”或“退化說”之全然贊同者。他秉持的文學觀念乃是“我之蛻化說”:“文學古今,一部分進,一部分退,進退互有其理。蓋文學之演進,若蟬之蛻皮,若蠶之破繭,層出無窮,謂為有優有劣、有進有退可,謂無優無劣、無進無退亦可。[……]進化退化,何必軒輊其間!無已,名之曰蛻化可耳。”(《盧前文史論稿》 58)他代表的其實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現實立場。盧前在1946年曾這樣總結自己多年來的“新詩”觀念及其實踐:
我是有志為詩壇創新體的人,對于近二十年來那些詩人新題的嘗試,我并不感著興趣。只有與現代口語最接近的散曲,我認為還可以試作;用現代的材料,現代的思想,融入曲體,融入這可以淋漓酣暢痛痛快快地說話的曲體。我寫作近二十年了,我的經驗是從學習元人,學習明人走到向時代學習,向大眾學習的路。我并不受曲體的束縛,至少我的曲已是我的曲了。我暫且放棄新詩體的企圖,我們在元曲,明曲之后來一個民國曲。(《散曲該怎樣學?——答淥音問》 第7版)
從文體形式來看,散曲可謂古典韻文學的終結體,由于通俗音樂靈活的旋律與節奏形式為文本變化提供了較為充足的空間;格律上,曲用韻三聲又可平仄通押,體式作法殆已達到了韻文體自由靈活的極致。無論小令還是套數,若減少或不加襯字,亦可實現“詩言志”的達意效果;正字之外多加襯字,注重駢散結合,又能形成“賦體物”式的鋪成敘事。分解至內容、技巧和風格,散曲則“(一)能抒情、敘事、寫景,也能發議論。(二)能寫戀情,也能歡樂。(三)能雅能俗,也能純能雜。(四)亦莊亦諧”(盧前,《散曲作法(上)》 12)。在詩歌創作常用的三種方式“興”“比”與“賦”中,“古體詩近體詩采用第一式、第二式的多,詞采用第二式的多;三種方式并用的是曲特有的技術,可以說曲是‘綜合的表現’的一種詩的形式”(《抗戰以來之中國詩歌》 66)。“因為曲體特有這種‘融合量’,與詩或詞不同”(《散曲作法(上)》 10),更富有貼合時代和生活的表現能力,也成為奠定盧氏“散曲運動”中提倡“以這種無所不包的體裁來寫這偉大時代的形形色色”(《民族詩歌論集》 278)觀念之基礎。可以認為,散曲文體的各項條件均符合盧前一直尋覓的民族“新詩”的要求,因而才能成為現代意義上“時代新聲”的實際典范。
比之臻于嚴整、典雅的詩、詞等文體形式,散曲本就富含白話口語、俚詞方言,所描寫與表現的內容、境界都更為現實化、世俗化,表現方法也更直率而靈活,具有詩、詞所少有的戲謔、悖逆的“反傳統”品質。盧前既肯定“曲的取材、作風,和表現的方法:與其他體制絕不相同”,“惟其本色,才能各自表現;惟其流暢,才能自由歌唱;惟其響亮,才能唱得普遍而悅耳”之獨特性(《論北曲中的豪語(上)》 第8版),又推崇“散曲的性德,比較任何體裁,活潑,有生命,又利用口語”,“便隨手引用新的詞語,在曲中也不覺得刺眼”(《散曲作法(上)》 9—10),跟廣大民眾和現代生活的距離很近。何況曲的性質是“直”,適于“把人們內心里曲曲折折的情感和事體,用一種爽爽快快的文字直達出來,使人一讀就能了解”(《曲海浮生》 110)。曲的這種易于普通讀者理解、表現手法靈活多樣的屬性,完全符合盧氏反映時代精神,同時發揮宣傳作用的文學要求。
于是,盧前一方面強調把傳統詩學中有關社會功用、題材選擇、寫作手法等觀念與方法妥善地融入現代散曲創作實踐中——“喬夢符論作曲子,說一支曲要豹頭,豬肚,鳳尾。我看一切文體都應如此”,又說,“情深語摯,這便是一首好詩。至于謀篇緊湊,鑄句雋永,煉字的當是我們最要訓練的”,“概括地說一句,用美妙的字,在最適當地方,組成音節自然,情意真摯,簡練明白的詩句。而且成為有次序有結構的篇章。這便是我們寫詩的標準”(《怎樣寫成我們的詩》 59)。除卻作品應保持的情緒、美感與品質之外,還應存有達到“普世”程度的思想和境界,正如他在《抗戰期中征求詩歌之揭曉》中評價第一名獲獎者詩歌時所說的那樣:“按此詩并不如其他詩稿,專述關于上海之中日戰爭。其所以能獲得第一名者,因所采格律及其詩之中心思想,皆為凡厭惡戰爭及屠殺之人所共感者也。”(《抗戰期中征求詩歌之揭曉》 61)這些觀念不僅擺脫了散曲寫作中的模式化傾向,也打破了詩、詞、曲之間作法的傳統界限,如盧氏早期以蘇辛豪放詞手法所作【雙調·折桂令】《朱仙鎮謁越王祠(并序)》,便被其師吳梅評為“曲中之稼軒”(江絜生 298)。盧前用一生的時間從事連續的、日記體式的散曲創作,靈活運用當代口語、各地方言、文言韻語乃至西化詞語入舊格律,融匯新生事物、新興觀念和現代學術理論成新內容與新格局,以富有現代色彩的意象及意境以描繪新世界。盧前散曲內出現的地名、植物、美食、事件均確鑿存在,其作品真實記錄平頭百姓的日常生活、民俗風貌,也記載國際、國家間發生的種種政治、社會類事件,完全具備了“化民成俗”“以曲補史”之價值功用,并以富有個性化的創作傳達群體性的思想與情感,使散曲承擔起詩歌一樣的社會、歷史、政治、文化方面的諸多作用。
另一方面,盧前既在理論上強調打譜、演唱的重要性,也從時代音樂需求的實際出發,注重現實中曲樂發展和改造的可能。盧氏所作散曲皆可自唱,也很喜歡將我國少數民族或其他國家的流行歌曲翻作為散曲。如他曾把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和烏拉特后旗的四首民歌括入北曲,成【雙調·落梅風】《擬內蒙古伊島兩盟旗牧歌》二首,可以用水磨腔歌唱;或將無名氏所作、傳唱在軍中的捷克斯洛伐克歌曲譯為兩首小令【越調·憑闌人】《捷克斯洛伐克軍中歌》。他還根據傳唱于三隴(青海、甘肅、寧夏)之間的“花兒詞”小曲,創作成小令【中呂·快活三】《花兒九章》;將新疆好友阿不都拉梯敏用維吾爾文字寫就的《上海篇》轉述為北套【般涉調·耍孩兒】,等等。盧前還熱衷于請朋友用不同類型的音樂為自己的作品譜曲,方便更多人了解和演唱,其【正宮·叨叨令】《秋夜偶書,蔭瀏為訂譜付歌者》便由楊蔭瀏據工尺譜六字調,改寫成現代歌曲簡譜,散曲內容即為歌詞,名曰《凱歌聲里》。他發表在《河南大學周刊》上的散曲【北仙呂·寄生草】《韓信點將臺上作》,后有編者注云:“此曲冀野先生南歸途中所作,聞由本大學國樂指導吳南青先生制譜,行將傳唱旗亭矣。”(河南大學群育委員會編輯組 7)
可以說,盧前鼓吹的“以新材料入舊格律,用舊技巧寫出新意境,拿詩來發揚我民族精神”(《民族詩歌論集》 277)之新時代散曲創作,使得本已走上“案頭化”“詩詞化”道路的民國散曲因此朝著“實用性”“大眾化”的方向嬗變。由于盧氏“詩歌之散曲”理論完美契合了“詩歌的民族形式”的所有要求,其創作的散曲也流傳甚廣,在當時的文壇上影響很大。因而在他不遺余力向學術界推廣散曲、興辦《民族詩壇》《中華樂府》等相關舊體文學刊物為散曲實踐提供平臺諸舉措下,于右任、夏仁虎、張鏡明、許崇灝、沈尹默、任中敏、孫為霆、宗志黃、范雪筠等諸多社會名達、文人學者紛紛呼應,主動使用散曲跟他應和交流,或選擇通過散曲記錄發生在自己身邊的大事小情,不斷創作出反映時代需求、便于大眾欣賞的“民國曲”。百余位積極參與社會事務、關注政治問題的散曲作者的加入,廣泛地把近代口語、家鄉方言帶入散曲創作之中,使得更多時事風云、市井生活實景融進新的作品,不但符合散曲文體固有的鮮活氣質,也順應了當時俗文學理念下的文藝“大眾化”需求。而在這場深入戲劇、小說、詩歌等各個文體領域的“民族形式”論爭中,盧前恰似一個“傳統”與“現代”、“理論”和“創作”間的平衡者。他強調文學的思想性、功能性,又不肯放棄對其音樂性、藝術性的追求;選擇散曲而不是時調、民歌等其他通俗形式構建民族“新詩體”,既抱有知識分子“拒絕庸俗化”的審美追求,又有不懈探尋最符合時代和現實需要的詩歌形式之企望。民國散曲也在理論、創作兩個方面,擔當起探索文學“民族化”實踐的重要使命。
三、 散曲實踐及其民族性表現
在民國(1912—1949年)期間,有近二百位學人、文士從事小令和套數的寫作。這些題材廣泛、風格雜糅的紀實性作品,充分保存了一個時代的聲韻詞匯、歷史事件及民俗風情,極為真實地反映出動蕩時代下的政治風云、軍事斗爭、人民命運和國家前途,凸顯出一種實事求是、平等客觀的現實精神和理性境界。民國散曲也通過數目龐大、眾體兼備的創作實踐,跟人民群眾的生活日常、救亡圖存的時代命題、憂國憂民的政治懷抱緊密結合,呈現了國際事件、海外知識的本土化、民眾化、普遍化,為舊體韻文學注入了新的時代因素、革命意識、民族情緒與美學要素,從內容、語言、思想、社會功用各個方面表現出民族化特征及現代性品格。
民國散曲的“民族性”首先表現在內容方面。不少作品直接取材于民眾的日常生活、風土民情和社會新聞,表現出特定時期民間社會的市井萬象。如寄恨【黃鶯兒】《醒嫖曲》揭露了各種煙花柳巷騙人的路數,【駐云飛】《擬繆蓮仙嫖賭吃著四戒》提倡戒掉吃穿嫖賭惡習,有警醒世人的意味。談善吾的【黃鶯兒】《詠判罰縱妓拉客案》《上海花會之風近稱盛行,潮州人頗遭訾議,乃潮州會館會議取締。誠盛舉也,作此美之》《詠蘇州民警沖突事》諸小令,就身邊新鮮時事進行敘述、議論,頗多俗趣,反映了民初社會狀況和民眾生活的諸多細節。吳承烜的套數【南呂】《嘆張勛》,則對這位辮子將軍逆歷史潮流而動,最終失敗的丑態進行了不遺余力的無情嘲諷;對于在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專制后建立起來的共和國,吳承烜也表現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對未來國際形勢的擔憂:“坐高高舵樓,坐高高舵樓。誰為牛后,誰為爭食雞兒口。這共和兩字,這共和兩字。天地杞人憂,風雨江神走。怕分瓜剖豆,怕分瓜剖豆。歐洲亞洲,能有幾邦交我厚。”(12)盧前散曲保存了南京、上海、成都、開封、重慶、新疆、桂林等地的風物人情、方言俗語、美食佳肴和諸多民間技藝,記錄下“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德安大捷、長沙會戰、昆侖關激戰、“六六”血戰、花園口、三劉呰、來同呰諸多戰役實況,以及由官場黑暗與戰火頻仍所導致的市場壟斷、物價飛漲、文化凋敝、民生潦倒等等社會現象。同為吳梅弟子的孫為霆親歷1940年日機連襲重慶,記錄下當時慘絕人寰的情狀,“燒炸之烈,驚心慘目”,“呼嗚嗚屋瓦飛,嘩剌剌墻磚倒。亂紛紛要逃怎逃[……]萬眾愮愮,萬口嘈嘈。覓妻兒奔走倉皇,檢骸骨匍匐號啕[……]血模糊的斷臂,斜掛在綠楊梢”(孫為霆 67—69),以及其“東歸”后所見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的艱辛世情:“為微利又逐蠅頭,柴米艱難使人愁。盼著誰能濟急,逼得我不知羞。”(55)這種緊扣時代、真實記載社會現實的創作方式,使得民國散曲重新煥發出旺盛的生命力,發揮出無可替代的文學、社會及歷史價值。
其次,在語言方面,民國散曲不但使用現代口語、方言俗語,還有西方外來語,真實保存了當時的用語習慣、聲韻詞匯,記錄下當時散曲語言變革的情狀。像盧前【越調天凈沙】《鄉味三憶》中的瓢兒菜(南方方言中的一種青菜)、萊菔(南京地產的楊花蘿卜)、板鴨;【仙呂·寄生草】《己巳除夕》里的“桃線兒(南京方言,指南京春節家家戶戶所貼的一種用紅紙制作、比春聯更加普遍的民間剪貼)”;【南呂·閱金經】《酒家寫真》的四川特產“棒棒雞”和四川方言“圈圈帽”“肚兒皮”;【越調·天凈沙】《龢廬聽賈瞽者唱道情》所述成都任第巷賈樹三演唱蘇李河梁之詞的“漁陽簡鼓”表演;從日寇占領南京后流亡途中搭船“過壩”(內地交通術語),并根據拉繩工人們相和的歌聲譜成小令【雙調·枳郎兒】《鳳皇頸絞船》,都極有特色。他在諷刺發國難財的貪官巨賈之奢靡生活所作【南仙呂入雙調】《孔猶圓先生之一日》中寫道:
【醉扶歸】也不過出家門摩托開流線,也不過到銀行支票寫美元。坐的是彈簧紗發襯絲綿,穿的是勃絨便服垂金鏈。也不過席蒙思的床榻供安眠,也不過可羅迷的器具鋪綢墊。【皂羅袍】說飲食都非上選,不過是海參,魚翅雞脯蝦丸。偶然幾盒炮臺煙,偶然幾盞蒲桃泛。偶然有咖啡,水果布丁一盤。晨餐是一湯兩蛋,生炒熟煎。在筳前擺列無多碗。【好姐姐】悶來時,游方城幾圈,倦來時看影場新片。約二三舞伴,狐步走翩翩。疾如電,嘆世間享樂尋難遍,已夢夢昏昏過一天。(盧前 175)
將民國時代權貴階層奢靡而空虛的生活暴露無遺。其哀悼“圣雄甘地”的套數【正宮·端正好】所用到的語言、典故、意象更體現出明顯的新舊交織特征,如曲中用到諸如“泰戈爾”“恒河”等人名地理名詞與“印度教”“回教”等域外宗教術語,既有“瘦巖巖”一類元代散曲的常用詞組,也出現了“拍拉西(plash)”這種由英譯詞“濺、潑”引申出“沾染、遇見”的新意。盧前在【北仙呂·一半兒】中將英文的“yes”譯作“焉斯”、將“no”譯作“努”等,都體現出散曲文體對外來詞匯的包容程度。而作為一種用來歌唱的曲辭,“自然”“俊語”“機趣”等,本為散曲語言風格的題中應有之義。這些新興詞匯在民國曲中的應用,非但沒有產生違和感,反倒突出了其“俗”“白”“活”“新”的風格特色和大眾趣味,一再用事實證明散曲確實擁有與時俱進的文體優勢。
再次,在思想方面,民國散曲不僅體現出中華民族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的精神風貌,更閃爍著自由平等意識與人性人道的光輝。民國時期不僅出現了更多創作散曲的女性作家,散曲中也塑造了眾多獨立于時代風云中的女性形象,展示了不同以往的女性意志。金長瑛在戀愛中被男方猜忌,即能灑脫地主動分手,“謝卻駑鴦債,摧殘錦繡花”(28);范雪筠為前線將士制作寒衣,也有個人的情感波動,“秋深秀閣夜熏遲,念否沙場苦戰時,霜雪全憑血肉支。贈寒衣,一半兒為公一半兒己”(86)。范雪筠在躲避空襲時還不忘帶一本《民族詩壇》閱讀,歸途“幸平安,人人歸去,爭折桂枝丹”(65),與沈尹默“防空有洞莫相驚,困餓卻無情。若能坐睡兼攜餅,可以歷昏明。行,無事過平平”(第9版)有異曲同工之妙。許多男性散曲作者對時代新女性也表達出了尊重和敬意,他們筆下的女子已經被視為鮮活的、平等交往的對象,不再是傳統視角下用來觀賞和褻玩的泛化符號。陳栩、盧前散曲中都記錄了大量有才華的女性曲家,于右任更贊揚從前線歸來的雯卿女士為“自由小姐,新詩走遍中華”(于右任,《題雯卿女士〈前線歸來手冊〉》 23)。另外,許多民國散曲作者懷揣對世道人生的深刻體悟和憂國憂民的淑世情懷,以貼近人民群眾生活和審美趣味的方式寫作。“詠史”主題在嘲古的同時,也不忘借古諷今。如宗志黃諷刺貪官,“看他費盡心思。朝為官資,暮為家私。干鬧了多時,才有個完時。咳,兩腳伸。棺材里帶不去一毫半絲,訃聞上多寫句廢話虛辭。你就是不稱心兒,也沒得法兒,將就些兒”;評價諸葛亮出《祁山》“鼎足三分勢早成。知情,那祁山六出總虛爭。呀,那祁山六出總虛爭。咳,多害了許多百姓”等(5)。他們不僅重視民生問題,還切實關注到廣大民眾辛苦勞作的不易,記錄船娘“玉臂青篙小折磨,撐到雷塘路又多”(任中敏 139)之工作艱辛;記錄“漁翁四時心自忖,那一刻容安頓。花開風信頻,雨漲濤聲狠,總不似釣寒江一竿兒拿得穩”(汪東 23)、輿夫“上坡下坡忙甚的,整日無休息。直恁鐵肩頭,擔得千斤力。看籃輿一停抬又起”(盧前,《飲虹樂府箋注·小令》 182)的艱辛不易。農民們每日勞作揮汗如雨,還要靠天吃飯:“人間一飯更艱難,旱旱旱”(346),但他們卻照舊堅強而樂觀:“青山茅屋度昏朝,喜平時耕勤飯飽”。(范雪筠 65)這些站在平等立場上描繪和贊美勞動人民樸實、堅韌、勤勞、善良的作品,早已突破了傳統“山林歸隱”“漁樵閑話”類題材的藩籬,展現出了新時代的人文精神與意境格局。
最后,在社會功用方面,民國散曲表達了全民抗戰、保家衛國的時代主題,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時代覺醒”,具備激發、鼓舞國民精神的宣傳功效,也發揮出經世致用的社會價值。如邵力子【雙調·撥不斷】曲寫道,“戰經年,志彌堅。長期苦斗爭全面,黃埔精神不瓦全,后方努力同前線,河山重建”(82);李翹慷慨陳詞,“眼中錦繡江山,都用血膏洗染,今年大事從頭干,還是堂堂抗戰”(87);吳心恒抒發作為空軍的壯懷激烈,“看鷹揚,長空萬里任翱翔。凌云浩氣山河壯。巧制機航,好男兒手段強。全憑仗,功在班輸上。愿中華金湯永固,永固金湯”(65)。于右任【南商調·黃鶯兒】《書示冀野庚由》曲,則以長者的身份鼓舞、激勵晚輩:“鐵板喚誰來,祝詞壇起霸才。獻身報國不負這全時代。酸齋苦齋,甜齋丑齋,那賢豪個個真靈在!有吾儕,中華民族,文運定新開!”(《書示冀野庚由》 79)那些承擔起新聞功能的“報章體”散曲,則更具有現實針對性,更能準確反映出社會實況,更具有感發人心、激勵斗志的政治功效,更能發揮出振奮愛國熱情、重塑國民精神的實際作用。像于右任【雙調·殿前歡】《題全面抗戰畫史》:“噪昏鴉,中原滿地逞胡笳,沿江各口窺胡馬。切莫嗟呀!看神州放異花,一戰收功也!把血史爭圖畫。更高呼:中華萬歲,萬歲中華!”(《題全面抗戰畫史》 45—46)將全面抗戰的血淚歷史比作一幅飽含民族精神的絢爛圖畫,全篇氣勢磅礴、大義凜然、轟轟烈烈,有高歌不畏強暴的“國魂”之意。他的另一首【中呂·山坡羊】《神圣戰爭》亦云:“憂愁風雨,迷離云樹。流亡不盡艱難路。寇何如?寇何如?中原春色還如故。神圣戰爭當共負!興,天定助。亡,人自取。”(《神圣戰爭》 79)從百姓流亡的苦難入手,以宣揚全民族抗戰責任為核心,認定中國人民的這場反侵略戰爭必將勝利。“神圣戰爭當共負”也是于氏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詮釋。而像【雙調·撥不斷】《祝民國二十八年》“告同胞,都知道。今年戰事應全好,入寇胡兒馬不驕,中興祖國天方曉。反攻時到”“信今年,異往年。今年國運應全轉,運轉人人唱凱旋,凱旋世世無邊患。但無忘國家多難”兩首(《祝民國二十八年》 63),便帶有于右任憑借自己的眼光與經驗對1939年時局的分析判斷,他懷著急迫的心情,想將這個“我軍即將進入反攻戰”的好消息傳達給廣大民眾。還有于右任1945年發表的《聞日本乞降作付中華樂府》,用十首小令描繪出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全國人民的歡騰場面與激動心情,為民族解放戰爭吟唱,歌頌真理與自由,給民國散曲注入了時代新思想、新生命。
綜上所述,民國散曲從散曲觀念與創作實踐兩個方面,鮮明地體現出盧前對于“民族新詩”的構想。抗戰散曲強烈的現實性、激昂的革命斗志、飽滿的民族精神及對深重苦難的擔當,也對20世紀上半葉關于“詩歌民族形式”之討論作出了圓滿的回應。散曲本是繼詩、詞之后中國古代的又一詩歌體式,并憑借白話語的運用、“豪放”的精神內核、自然通俗的本色當行及大眾化的審美追求,自民國白話運動、新詩運動、國語運動、歌謠運動等對詩歌文字內容、精神傳統進行的全面改造中脫穎而出,成為適合表現新時代文藝需求的韻體形式。民國散曲“協于韻律”的音樂性,對民族氣質、風貌的發揮,亦持續為民族詩歌注入新鮮的內在生命活力;關注現實的政治、道德意識,主“情”又充滿客觀理智、積極真誠的新時期人生態度,則完整構建起新一代的民族新詩精神。
余 論
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研究界關于“新詩”的概念界定,一直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指使用新語言、表達新思想的舊體韻文學,一是指廢除幾千年來傳統韻體形式的新體白話詩。前者傾向于改造與利用舊體,而后者志在創造新體。在今天看來,“新舊”其實跟“雅俗”一樣,是伴隨時移世易而在內涵與外延上不斷發生變化的相對性概念,其建構標準也莫衷一是。長久以來,學界存在舊體文學在新文化運動之后逐漸“衰亡”等說法,但不是指某種舊文體的停止更新或完全消失,而更多地意味著它們不再被主流學術所關注,導致自身話語權的旁落。如同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民國時期舊體“新詩”發展歷程,便可發現諸多傳統的文體形式始終與新文學多元并存,共同構建了民國文學的整體風貌。舊體文學的創作成就實在不該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敘述中被遮蔽、被曲解、被全盤否定。至于民國散曲,大量實踐已證明其文體上的“舊”特征跟新時代精神的表達并非捍格不入。在構建民族化、大眾化的詩體演進過程中,它的價值與意義也足以使之有資格在近現代中國文學史中獲得一席之地。
① 指以譚嗣同、黃遵憲、丘逢甲為代表,運用新名詞寫作舊體詩的派別,思想在守舊與革命兩派之間,屬于維新而沒能從內容和意境上有所改變的詩派,跟陳散原、鄭孝胥代表的“同光體”駢立,見盧前《民國以來我民族詩歌》中的分類。
② 最初是由胡適、康白情、俞平伯等人改換語言寫作的白話詩,后來徐玉諾、冰心、徐志摩、聞一多、梁宗岱、朱湘等人為了變更詩歌形式開始模仿散文、日本俳句、西洋詩體創作,又稱為新體詩,被盧前用“新體白話詩”統一概括,認為“學衡派”與其主張相反對。
范雪筠:【北雙調·新水令】《農村》,《民族詩壇》2.6(1939):65—66。
[Fan, Xuejun. “Countryside (to the Tune of Beishuangdiao Xinshuiling).”2.6(1939):65-66.]
——:【南商調·黃鶯兒】《桂林龍隱巖避空襲讀〈民族詩壇〉》,《民族詩壇》2.5(1939):65。
[- - -. “ReadingWhen Hiding from Air Raid in Longyinyan, Guilin (to the Tune of Nanshangdiao Huangying’er).”2.5(1939):65.]
——:【仙呂·一半兒】《寒衣》,《民族詩壇》2.4(1939):86。
[- - -. “Warm Clothes (to the Tune of Xianlü Yiban’er).”2.4(1939):86.]
胡明樹:《關于詩的“民族形式”》,《前線日報》1941年2月26日第7版。
[Hu, Mingshu. “On the ‘National Form’ of Poetry.”26 February 1941:7.]
江絜生:《吟邊札記》,《盧前詩詞曲選》,張進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97—298。
[Jiang, Jiesheng. “Notes on Poetry.”, Ci-Qu-. Ed. Zhang J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297-298.]
金長瑛:【南仙呂·桂枝香】,《庠聲》7(1932):28。
[Jin, Changying. “Osmanthus Fragrance to the Tune of South Xianlü.”7(1932):28.]
雷濺波:《詩歌的民族形式,口語化,形象化》,《戰歌》2.2(1941):9—11。
[Lei, Jianbo. “The National Form, Visualization and Colloquialism of Poetry.”2.2(1941):9-11.]
李翹:【中呂·醉高歌】《新誓》,《民族詩壇》2.4(1939):87。
[Li, Qiao. “New Oath (to the Tune of Zhonglü Zuigaoge).”2.4(1939):87.]
林秀燊《關于詩歌的民族形式》,《中國詩壇(廣州)》4(1940):6—7。
[Lin, Xiushen. “On the National Form of Poetry.”() 4(1940):6-7.]
盧前:《廿七年來我中華民族詩歌——民國廿七年十月十日及十九日廿一日在中央廣播電臺講》,《民族詩壇》2.1(1938):1—10。
[Lu, Qian. “Chinese National Poetry since 1938: Talks at China Central Radio on October 10,19 and 21,1938.”2.1(1938):1-10.]
——:《韓信點將臺上作(曲)》,《河南大學周刊》5(1932):7。
[- - -. “Composing on Han Xin’s Platform (-poetry).”5(1932):7.]
——:《近代中國文學講話》。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30年。
[- - -.. Shanghai: Huiwentang Xinji Book Company, 1930.]
——:《抗戰以來之中國詩歌》,《中蘇文化》9.1(1941):61—67。
[- - -. “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9.1(1941):61-67.]
——:《我對于文學的信念》,《中國學生》3.12(1936):4、6。
[- - -. “My Faith in Literature.”3.12(1936):4,6.]
——:《樂理講座:民族音樂(七月三十一日在本臺播講)》,《廣播周報》99(1936):12—14。
[- - -. “Lectures on Music Theory: National Music (Broadcast on This Station on July 31).”99(1936):12-14.]
——:《民族詩歌論集》,《盧前文史論稿》,孫文穎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71—319。
[- - -..’Ed. Sun Weny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271-319.]
——:《散曲作法(上)》,《民族詩壇》4.2(1940):9—13。
[- - -. “Methods of Writing Non-dramatic-poetry (Part 1).”4.2(1940):9-13.]
——:《論北曲中的豪語(下)》,《和平日報》1946年6月9日第8版。
[- - -. “On the Heroic Languages in Northern-poetry (Part 2).”9 June 1946:8.]
——:《散曲史》,《盧前曲學論著三種》,苗懷明整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3—138。
[- - -. “History of Non-dramatic-poetry.”’Qu-. Ed. Miao Huaim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3-138.]
——:《曲海浮生》,《中學生》61(1936):107—116。
[- - -. “Life in the Sea of-poetry.”61(1936):107-116.]
——:《散曲該怎樣學?——答淥音問》,《中央日報》1946年6月2日第7版。
[- - -. “How to Learn Non-dramatic-poetry: Answering Lu Yin’s Questions.”2 June 1946:7.]
——:《論北曲中豪語(上)》,《和平日報》1946年6月8日第8版。
[- - -. “On the Heroic Languages in Northern-poetry (Part 2).”8 June 1946:8.]
——:《怎樣寫成我們的詩》,《中學生》 4(1930):53—60。
[- - -. “How to Write Our Poetry.”4(1930):53-60.]
——:《抗戰期中征求詩歌之揭曉》,《民族詩壇》1(1938):61—64。
[- - -. “Calling for Poetry Works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1(1940):61-64.]
——:《飲虹樂府箋注·套曲》,盧偓箋注。揚州:廣陵書社,2011年。
[- - -.Poetry of Lu Qian:Qu-. Ed. Lu Wo. Yangzhou: Guangling Publishing House, 2011.]
——:《飲虹樂府箋注·小令》,盧偓箋注。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
[- - -.Poetry of Lu Qian:-poetry. Ed. Lu Wo. Yangzhou: Guangling Publishing House, 2009.]
毛澤東:《論新階段》,《解放》57(1938):4—37。
[Mao, Zedong. “On the New Stage.”57(1938):4-37.]
歐陽天嵐:《詩的民族形式我見》,《前線日報》1941年2月26日第7版。
[Ouyang, Tianlan. “My Opinion on the National Form of Poetry.”26 February 1941:7.]
“詩底民族形式集體論”欄目版頭,《前線日報》1941年2月26日第7版。
[“Preface to ‘Collective Discussions on the National Form of Poetry’.”26 February 1941:7.]
任中敏:【揚州·一半兒】《船娘》,徐建中、楊棟輯考“感紅室曲存”,《揚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1994):136—142。
[Ren, Zhongmin. “Boat Girl (to the Tune of Yangzhou Yiban’er).” “Collected-poetry from the Ganhong Studio.” Ed. Xu Jianzhong and Yang Dong.() 3(1994):136-142.]
邵力子:【雙調·撥不斷】《祝黃埔季刊廿八年一月創刊》,《民族詩壇》2.4(1939):83。
[Shao, Lizi. “Celebrating the Founding ofin January 1939 (to the Tune of Shuangdiao Shuangdiao).”2.4(1939):83.]
沈尹默:【仙呂·遊四門】《海秋攜餅入防空洞,公武因以餅字屬作游四門小令,為戲成之》,《中央日報·泱泱》1946年10月2日第9版。
[Shen, Yinmo. “Haiqiu Carries Cakes into the Air Raid Shelter (to the Tune of Xianlü Yousimen).”2 October 1946:9.]
孫為霆:【雙調】《巴山哀》,《民族詩壇》4.1(1940):67—69。
[Sun, Weiting. “Grief in Mount Bashan (to the Tune of Shuangdiao).”4.1(1940):67-69.]
——:《壺春樂府》,西安:陜西師范大學,1964年。
[- - -..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1964.]
涂世恩:《建立民族精神詩歌芻議》,《三民主義文藝季刊》1(1942):24—28。
[Tu, Shie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Poetry with National Spirit.”’1(1942):24-28.]
汪東:【雙調·清江引】《寒江獨釣》,《中華樂府》1.4(1945):23。
[Wang, Dong. “Fishing Alone by the Cold River (to the Tune of Shuangdiao Qingjiangyin).”1.4(1945):23.]
王亞平:《創造詩歌的民族形式:新詩辨草之十七》,《學習生活》3.2(1942):105—106。
[Wang, Yaping. “Creating the National Form of Poetry: Discriminating New Poetry (17).”3.2(1942):105-106.]
吳承烜:【南呂·香柳娘】《守邗》之六,《藝府_曲選》欄目,《小說新報》3.8(1917):11—12。
[Wu, Chengxuan. “Defending the Frontier (6) (to the Tune of Nanlü Xiangliuniang).”3.8(1917):11-12.]
吳心恒:【雙調·殿前歡】《空軍機械學校校歌》,《民族詩壇》2.5(1939):65。
[Wu, Xinheng. “School Song of Air Force Machinery School (to the Tune of Shuangdiao Dianqianhuan).”2.5(1939):65.]
蕭三:《論詩歌的民族形式》,《文藝突擊》1.2(1939):46—49。
[Xiao, San. “On the National Form of Poetry.”1.2(1939):46-49.]
謝獄:《題材與形式》,《前線日報》1941年2月26日第7版。
[Xie, Yu. “Subject and Form.”26 February 1941:7.]
楊鐵夫:《談談詩歌的民族形式》,《黃河月刊》2(1940):67—68。
[Yang, Tiefu. “On the National Form of Poetry.”2(1940):67-68.]
嬰子:《中國作風》,《前線日報》1941年2月26日第7版。
[Ying, Zi. “Chinese Style.”26 February 1941:7.]
于右任:【雙調·撥不斷】《祝民國二十八年》二首,《民族詩壇》2.3(1939):63。
[Yu, Youren. “Celebrating the 28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Tune of Shuangdiao Bobuduan).”2.3(1938):63.]
——:【雙調·殿前歡】《題全面抗戰畫史》,《民族詩壇》6(1938):45—46。
[- - -. “Writing on-(to the Tune of Shuangdiao Dianqianhuan).”6(1938):45-46.]
——:【南商調·黃鶯兒】《書示冀野庚由》,《民族詩壇》4(1938):79。
[- - -. “Writing for Jiye and Gengyou (to the Tune of Nanshangdiao Huangying’er).”4(1938):79.]
——:【越調·天凈沙】《題雯卿女士〈前線歸來手冊〉》,《中華樂府》1.2(1945):23。
[- - -. “Writing for Ms. Wenqing’s(to the Tune of Yuediao Tianjingsha).”1.2(1945):23.]
——:【中呂·山坡羊】《神圣戰爭》,《民族詩壇》4(1938):79。
[- - -. “Holy War (to the Tune of Zhonglü Shanpoyang).”4(1938):79.]
趙笑天:《祝新詩》,《學生生活》2.8(1937):7。
[Zhao, Xiaotian. “Blessing New Poetry.”2.8(1937):7.]
朱自清:《唱新詩等等》,《語絲》154(1927):263—267。
[Zhu, Ziqing. “Singing New Poetry and the Like.”154(1927):263-267.]
宗志黃:【北雙調·折桂令】《感世》《祁山》,《文苑》欄目,《安徽大學月刊》2.6(1935):5。
[Zong, Zhihuang. “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Mount Qishan (to the Tune of Beishuangdiao Zheguiling).”2.6(1935):5.]